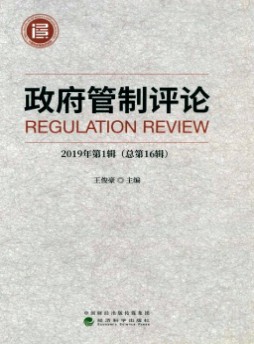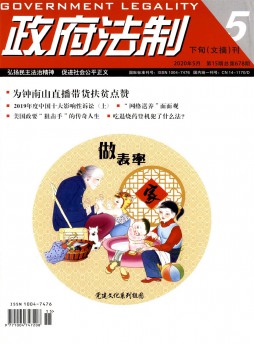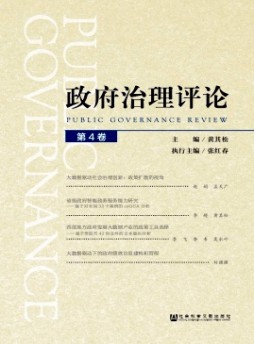政府公共危機管理問責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政府公共危機管理問責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總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加強安全生產和行政問責提出明確的要求:“要堅決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發生,實現全國安全生產狀況穩定好轉。要認真貫徹‘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完善安全生產體制,切實落實責任制”;“全面履行政府職能,著力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建立健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管理體制機制”;“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增強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是對各級政府、政府職能部門及其公務員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行為與成績進行評價。以績效為基礎,建立全面的危機管理是成功構建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的有效途徑(陶學榮、朱旺力,2005)。現階段,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的績效評價工作才剛剛起步,“官員問責”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在政府公共危機管理體系(或系統)中,績效評價和問責是較為薄弱的一環。筆者通過對我國近幾年發生的六起煤礦特別重大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結果的分析,厘清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借鑒國外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行政問責工作的先進做法,提出完善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行政問責制的建議。
一、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責任追究的基本情況
關于國外煤礦安全管理和責任追究的情況,據崔滬(2005)的研究:2004年美國生產煤炭近10億噸,但煤礦安全事故總共只死亡27人。實際上連續三年來美國煤礦安全死亡人數在0.03以下。負責礦業安全的政府部門——美國勞工部下屬礦業安全與衛生局還計劃到2008年將煤礦死亡人數再減少15%。2000-2001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煤礦生產百萬噸的死亡率僅為0.014。該州的法律法規對礦山設計師、雇主和雇員的安全都有明確規定,使得每個人對安全都負有法律責任。在各種制度中,與安全生產聯系最為密切的就是礦山安全監督員的有關條例了。在新南威爾士,有關法規對煤礦安全監察機制的機構、人員構成權限和責任都有明確規定。
我國大規模的行政問責始于2003年“非典”期間。從那時開始,不斷追究了在重大安全事故(包括礦難)、環境污染等方面失職或有重要責任的行政官員的責任。在中央和國務院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開展了行政問責。現階段,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國家逐步制定和完善有關安全生產及其績效評價的法令、法規、規章等。如200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200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2006年的《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強化生產經營單位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嚴格安全生產業績考核指導意見》以及2007年的《安全生產領域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等。(2)一批高官因特別重大安全生產事故而受到處理。如:2003年因SARS危機蔓延,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被免職;2003年因重慶開縣井噴事故,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引咎辭職;2004年因陳家山礦難,陜西省副省長鞏德順被行政記過;2005年因孫家灣礦難,遼寧省副省長劉國強被行政記大過;2005年因大平礦難,河南省副省長史濟春被行政警告;2005年因大興礦難,廣東省副省長游寧豐被行政記大過等。(3)一些地區和部門在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責任追究方面先后開展了一些探索。如:2001年鐵道部制定的《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責任追究的辦法》;2001年北京市制定的《關于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2006年河南省將安全生產納入政府績效評估體系、黨政領導干部績效考核體系、國有企業發展和經營負責人業績考核體系;2006年黑龍江省加大安全生產在黨政領導目標考核中的比重;2006年環保總局表示將依法追究江河水域污染責任人行政責任。(4)在國家層面上,已經將安全生產重要指標納入政府總體考核體系。目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已納入億元GDP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礦商貿企業從業人員10萬人死亡率、道路交通萬車死亡率、煤礦百萬噸死亡率。
盡管如此,現階段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責任追究仍存在較大的問題。陶學榮(2005)認為,我國現有的危機管理體系中,尚存在激勵機制和懲罰機制錯位的問題。常常出現“默默無聞避免危機得不到獎勵,轟轟烈烈解決危機的倒成為英雄”的現象,直接引起危機者得到懲罰,而在體制上令危機發生者卻安然無恙。在我國現有的績效評價體系下,各級政府的理性選擇卻是盡量“捂蓋子”,各行其是,無法明晰責任。這一點在山東煙臺“11·24”海難、“廣西南丹的礦井事故”中已充分暴露。
二、六起礦難中的行政責任追究情況分析
(一)六起礦難的基本情況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監察部2005年12月23日聯合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會,公布了2004年11月以來發生的六起特別重大礦難的處理結果(見表-1)。
注:本表中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受黨紀政紀處分和行政黨務撤職人數三組數字(94、81+47)與后來媒體公布的(96、126)有差距,原因是受黨紀政紀處分和行政黨務撤職中的2個人后來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二)礦難處理情況分析
1.礦難原因分析。六起礦難是綜合原因造成的,都屬于重大責任事故。主要有煤礦方面的責任、政府安監部門和行業主管部門的責任以及地方政府方面的責任。這些事故充分暴露出當前煤礦安全領域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具體反映在以下四個方面。(1)抗拒執法,非法生產。發生事故的煤礦負責人、礦主安全意識淡漠,思想麻痹。有的無視法律,無視監管,無視礦工生命,甚至抗拒執法,違法生產。(2)超能力、超強度、超定員組織生產。受利益驅使,發生事故煤礦不顧礦井生產能力、通風能力和設備負荷,超強度開采;不按礦井實際核定入井人數,超定員生產。(3)管理混亂,規章制度形同虛設。發生六起事故的煤礦中,國有大礦管理滑坡,“三違”現象嚴重,違章指揮、違章作業、違反勞動紀律;小煤礦管理混亂,安全隱患大量存在。這些礦勞動組織混亂,井下作業以包代管,濫用人力,培訓缺失,甚至不培訓,無證上崗。(4)事故背后的腐敗充當了保護傘。特別是2008年7月2日山西省寧武縣賈家堡煤礦發生的特別重大瓦斯煤塵爆炸事故,死亡36人。寧武縣煤炭工業局局長與礦山救護隊負責人共同策劃,并得到寧武縣委副書記和副縣長的縱容,謊報事故死亡19人,瞞報17人,并將這17具尸體轉移到內蒙古。廣東興寧市大興煤礦2008年8月7日透水事故,該公司董事長、副董事長身份竟是國家現職的公職人員,一些執法部門、管理部門為其非法行為大開綠燈,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腐敗問題十分嚴重。
2.礦難造成的損失分析。六起事故共造成528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億元。從表-2可以看出,陳家山礦難在死亡人數、受傷人數方面“獨占鰲頭”,而大興礦難在直接經濟損失方面則“名列前茅”。根據安全生產相關標準,從死亡人數和直接經濟損失來看,上述六起事故都屬于特大安全生產事故。
3.對礦難責任人處理結果的分析。從表-3和表-4,可以看出,在礦難中受到行政責任追究的主要分為以下四種情況。(1)對事故發生負有直接責任或主要責任,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玩忽職守罪等,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96人。他們主要是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和其他有關規定,指揮工人違章作業,或者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隱患,釀成了事故。(2)對事故發生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企業管理人員21人。他們主要是不能認真貫徹落實“安全第
一、預防為主”的方針,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普遍存在違法違規生產和超能力組織生產現象,安全生產管理存在嚴重問題。(3)對事故發生負有重要領導責任,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政府監管部門工作人員77人。這些工作人員對煤礦安全生產負有監督管理責任,卻未正確履行職責,有的甚至失職瀆職。一些管理部門違規發放許可證書和資格證書,致使一些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企業得以開工生產;有些執法部門監督檢查不到位,對發現的事故隱患督促整改不力。(4)對事故發生負有領導責任,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地方政府負責人28人。這六起特別重大事故,給國家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有關地方政府的負責人未能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沒有處理好安全與生產的關系,對安全生產工作重視不夠,未能認真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對事故的發生負有領導責任。共有28名省、地(市)、縣(區、市)和鄉鎮黨政負責人因此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地(市)8人,縣(區、市)和鄉(鎮)18人。經國務院研究決定,給予陜西省原副省長鞏德順行政記過處分,給予廣東省副省長游寧豐行政記大過處分,并責成陜西省人民政府、廣東省人民政府向國務院作出書面檢查。此外,還嚴肅查處了3起事故涉及的政府工作人員入股煤礦、權錢交易、瞞報事故等問題。
從礦難處理的主體來看,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對每起特別重大事故,都及時作出批示,要求迅速搶救遇難人員,并責成安監總局牽頭,會同監察部、全國總工會等部門和地方政府組成國務院事故調查組,嚴肅查處。在上述六起礦難處理中,國家安全生產監管總局與監察部充當了主角。
對礦難責任追究的原則,依據《行政監察法》和《安全生產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和“四不放過”原則,進行了處理,構成犯罪的,已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對具有礦長資質的,吊銷資質,五年內不得再擔任任何煤礦的董事長和礦長。并對事故煤礦依法進行經濟處罰,并建議由地方政府予以關閉。
三、礦難問責的不足
針對上述我國礦難問責的具體情況,筆者認為,當前我國的礦難問責還遠未達到完善的境地,尚難以發揮提高政府效能的目的,有許多需要進一步改進之處(見表-5)。
表-5當前我國礦難問責之不足及未來發展之方向
1.問責的目標的局限。從上述六起特大煤礦事故處理結果來看,現有的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目標和價值定為仍以“獎優罰劣”為準。在上述案例中,問責的目標為落實安全生產主體責任;依法嚴懲責任人,實施責任追究;遏制重特大事故的發生;促進煤礦安全生產狀況穩定好轉。尚未把政府公共危機管理效能的提升、建立效能政府和責任政府當成問責的目標,未把問責當成構建效能政府和責任政府的重要途徑。
2.問責主體的局限。從上述六起特大煤礦事故處理結果來看,我國現有的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主體為中共中央監察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全國總工會、地方政府。它們是煤礦、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上級主管部門,由它們來評價其下級的工作績效,難以給人以較強的說服力,也難以使被問責者口服心服。更加重要的是,沒有體現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為民服務”,讓民眾滿意的宗旨。
3.問責對象的局限。從上述六起特大煤礦事故處理結果來看,現有的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對象主要為三類:煤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相關部門(安全監督監察部門、行業管理部門)。應該說,礦難的發生與更廣泛的政府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有關,如技術保障部門、危機評價部門、危機應急管理部門等,應將他們也作為問責的對象。對他們在危機發生的責任追究的忽視,應該說是一大遺憾。
4.問責內容的局限。當前礦難問責的重點是:煤礦抗拒執法、非法生產;超能力、超強度、超定員組織生產;管理混亂,規章制度形同虛設;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不力;事故背后的腐敗充當了保護傘。而事實上,礦難的發生,可能涉及更為廣泛的層面,如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和不完善,沒有執行或執行不力等。
5.問責程序的局限。從上述六起特大煤礦事故的處理結果來看,我國現有的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程序一般為:查明事故原因;認定事故責任;對責任人提出處理意見;報國務院審批。這一程序表現為上級主管部門的單向評價,而對被評價人的權利和反饋考慮不周。問責中的溝通和反饋、相對人的權利保護等問題尚未得到很好的解決。
6.問責方法的粗糙。對礦難中行政責任的追究,當前主要是遵循國務院制定的“四不放過”的原則,即事故原因未查明不放過、責任人未處理不放過、整改措施未落實不放過、有關人員未受到教育不放過。這樣的問責方法應該說是粗線條的,缺乏定量和更加科學的評價方法。而國外政府績效評價中的一些較為先進的方法如KPI、BSC、DEA、360度和模糊綜合評價法等都未得以應用。這將會使問責的效力大打折扣。
7.問責評估結果應用的局限。從上述六起特大煤礦事故處理結果來看,對相關責任者的處理主要有三種方式: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給予黨紀政紀處分、行政撤職。而對問責之后的工作如何運作則不明晰。從實際運作情況來看,對公共危機事件中負有領導責任的人員的起復就引起了學界和公眾的疑問(如對張文康、馬富才等人的起復等)。
四、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行政問責的完善
不斷提升我國各級政府的公共危機管理意識和能力,積極應對各類公共突發事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應按照如下方向不斷完善和優化。
1.以提高行政效能為目標。“獎優罰劣”僅僅是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初級目標,而“政府效能的改善”則是終極目標。朱火弟(2003)提出在完善“問責制”、進行獎優罰劣的基礎上,應積極研究政府績效評價評估對政府效能提高的作用。卓越教授(2004)提出,“政府效能的改善”應成為政府績效評價的目標。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目標定位應是創建高績效機關,全面提升行政機關的執行力。
2.引進“多元化評價”主體。杜鋼建(2003)提出政府問責制必須強化異體問責,加強民意機關的問責,加強派的監督,加強輿論監督。政府績效評價應逐步體現“顧客導向”和“結果為本”。彭國甫(2004)明確提出政府績效評價可以分為兩類:內部評價包括自我評價、上級評價、同級評價;外部評價包括民間第三方專門機構評價、媒體評價、公民評價、派評價、人大政協評價、國家權力機關評價。目前的問題是確定多元主體的構成及主體之間的比例分配。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的績效評價和問責應逐步實現從上級問責向制度問責、從同體問責走向異體問責的過渡。努力實現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為民服務”,讓民眾滿意的宗旨。
3.擴大問責的面和對象。“政府”、“政府職能部門”與“公務員”是當前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三類對象。對這三類對象應有不同的評價目標、標準和方法。同時,企業中由政府派駐的公務員、社會上對企業進行認證評價等工作的機構和人員、技術保障部門、危機評價部門、危機應急管理部門等,也應納入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對象范圍。
4.進一步完善績效評價和問責指標體系。毛壽龍(2002,2005)提出,干部問責制有四個方面的含義,“一是道義上的責任,干部要向受害者和公眾負責;二是承擔政治責任,干部要向執政黨和政府負責;三是承擔民主責任,干部要向選民負責;四是承擔法律責任,干部要向相關法律法規負責”。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應實現從安全生產領域向其他領域過渡;從道義責任、政治責任追究走向法律責任追究。目前學術界對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指標、指標的權重、指標體系和模型的構建與設計雖有零星成果,還很不系統,針對性和操作性也不強。張成福(1998)認為,政府危機管理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應符合聯合國提出的“績效導向的政府危機管理”的五項要求(SMART)——可長期持續(Sustainable)、有明確的績效標準和專業標桿可測量(Measurable)、月內或年內可實現(Achievable)、能夠滿足不同情景的相關聯性(Relevant)、在明確時間表內完成項目的及時性(Timely)。張小明(2006)初步構建了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包括6個二級指標(信息管理、公關管理、溝通管理、決策分析、應急管理、恢復管理),27個三級指標。與之對照,國外政府機構如美國聯邦緊急事務局、交通部等多從安全生產量化指標的角度來確定公共危機管理的績效,其可操作性和科學性似乎更為前沿,值得學習。
5.設計和采用更加科學和更有中國特色的問責的程序與方法。蔡立輝(2002)提出了政府績效評估的基本程序:收集信息資料、確定績效目標、劃分評估項目、績效測定、評估結果運用。在現有的官員考評、問責制等制度的基礎上,應逐步形成更加科學和更具中國特色的評估程序和方法,要實現從運動式問責走向制度型問責。應積極解決現有問責工作中的單向評價和問責弊端,積極考慮被評價人的權利和意見反饋。認真解決問責中的相對人的權利保護等問題。應逐步探索應用KPI、BSC、DEA、360度和模糊綜合評價等方法,不斷提高行政問責的效力。
6.科學運用評價和問責的結果。應科學設計和探討問責后的工作運作問題,特別是被問責官員的起復等問題,應有更加明確的說法和法律依據。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要發揮“獎優、治庸、罰劣”的作用,要充分發揮績效評價和問責的導向作用和激勵作用。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評價和問責的結果應該積極應用于對政府、政府職能部門和工作人員的獎懲,在此基礎上,應努力改善政府機關公共危機管理的效能。
擴展閱讀
- 1政府與政府尋租
- 2政府信用與政府自覺
- 3政府責任與政府問責
- 4政府創新與政府自覺
- 5政府報告
- 6政府職責
- 7政府利益與政府信用建設
- 8市政府強化政府決策意見
- 9政府績效審計模式
- 10政府采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