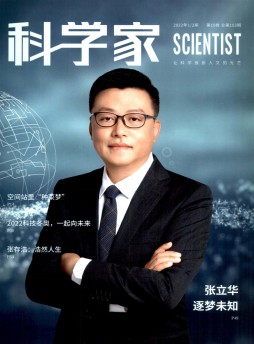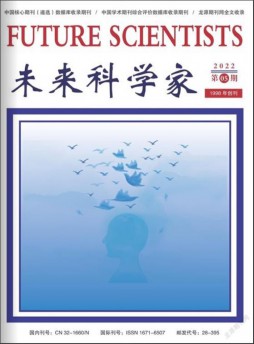科學家宗教情感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科學家宗教情感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科學和宗教在本質上是對立的。西方大部分的自然科學家都是宗教信仰者,在這些科學家身上,宗教和科學彰顯著和諧。這些科學家所信仰的上帝并非我們常人所理解的干涉自然事件、決定人類命運的最高神,而是宇宙間的自然規律、世界秩序,這種信仰是一種無神論的信仰,是一種強烈的宇宙宗教情感,這種情感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最高動力,激勵著他們去發現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奧秘。因為在他們看來,上帝佇立在科學無限探索的盡頭,研究科學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
關鍵詞:科學;宗教;上帝;宇宙宗教情感
宗教與科學在本質上是對立的。宗教的本質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為核心的信仰主義體系,它相信超自然的上帝或神靈主宰世界,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說明世界,把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歸結為神的意志和表現;而科學本質上則是反映客觀世界的性質和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它把一切研究對象都視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或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觀實在,它們的產生是基于事物本質所決定的自然原因,它們的變化服從于客觀規律,科學不承認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對世界的作用,也反對用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去說明世界的任何現象及其發展進程。在對事物的說明和理解中,如果引進超自然的力量和范疇,那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學。宗教和科學的信仰方式和理解方式有著根本的區別。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基石和指導思想,科學家是科學的堅定擁護者和忠實實踐者,從科學與宗教的本質對立而言,似乎科學家應該無緣于宗教信仰。然而縱觀科學史,我們卻不難發現:許多偉大的科學家同時又是堅定的宗教信仰者。那么,這些偉大科學家的宗教信仰是怎樣的一種信仰?這些信仰又是如何“引領”他們在科學上取得建樹?
1上帝——顛撲不破的宇宙規律、世界秩序
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在它的著作里留下了許多關于上帝、宗教、圣經等方面的論述,他在76年的生涯中,曾多次坦率地談到過他的宗教信仰。1929年4月24日,紐約猶太教堂牧師H?哥爾德從紐約發了一份電報到柏林,問愛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嗎?”并要他用電報回答。愛因斯坦當日就發了回電,內容為“我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信仰那個同人類的命運和行為有牽累的上帝。”
那么,所謂斯賓諾莎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歐洲哲學史上,斯賓諾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論。泛神論的核心觀念是: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個宇宙是一個統一體,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唯一的無限實體,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黑格爾曾指出,斯賓諾莎把自然當作現實的神,把神當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見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來;叔本華認為“泛神論是一種客客氣氣的無神論”,費爾巴哈對此也有過類似的見解:“泛神論是站在神學立場上對神學的否定”,“無神論是顛倒過來的泛神論”。在西方近代科學文化思想史上,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深深影響了西方整個文化——從哲學到文學、繪畫和音樂,再到自然科學,西方一大批偉大的思想家、優秀的藝術家和杰出的科學家無不受惠于斯賓諾莎把上帝還原為大自然這一光輝思想。泛神論成了他們共同的宗教信仰。泛神論者在宇宙中看到了上帝和在上帝那里看到了宇宙,在對宇宙秩序的贊美、欣賞中,他們的觀念和情緒相混合,創作了許多不朽的作品、發現了宇宙間的許多本質現象、規律……他們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個躲在天宮中、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顛撲不破的宇宙規律、世界秩序。
普朗克的宗教信仰也很突出。1947年,這位行將辭世的偉大理論物理學家在一封書信中解釋了他的宗教信仰,說他本人“一向是一個具有深層宗教氣質的人,但我不相信一個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談不上相信一個基督教的上帝。”作為一個具有深沉宗教氣質的人,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即世界秩序,他將自然科學的世界秩序等同于宗教的上帝,在他看來,外在世界是一個獨立于人而存在的絕對的東西,適用于這個絕對東西的規律代表著、體現著一種神性,宇宙結構中顯露出的秩序和美麗,就是上帝的化身。
牛頓對上帝也有類似的看法“上帝根本沒有身體,也沒有一個體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聽到或者摸到他,也不應以任何有形物體作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們只是通過上帝對萬物最聰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終的原因,才對上帝有所認識……”顯然,牛頓的上帝是宇宙和諧、絕妙的安排,上帝的本性不是別的而是熔鑄在他的物理學本身之中,熔鑄在他關于絕對空間、時間和重力等的概念之中。
此外,現代的許多科學巨匠,如萊布尼茨、康托爾、法拉第、玻恩等等,都是具有深沉的宗教信仰。萊布尼茨認為,上帝按照數學法則建造了整個宇宙,上帝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數學中集合概念的創立者康托爾心中的上帝是熔鑄和體現在數學的宏偉體系中的;法拉第心中的上帝是世界的終極和諧;德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M?玻恩心目中的上帝是在各種飛馳的現象中,那根巍然聳立不變的規律之桿;……
上述有關科學家心目中上帝的表述盡管不盡相同,但其隱含的本質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信仰的上帝沒有任何擬人化的特征,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諸如直指藍天白云的教學尖頂,還有半明半暗的燭光以及其他儀式,與教會信奉的那個干涉自然事件的“上帝”有著天壤之別,更與塵世善男信女頂禮膜拜、祈求賜予幸福的那個“神”沒有任何關聯;他們的上帝本質上是井然有序的宇宙結構、世界秩序、不容顛撲的自然規律,他們的信仰實質上是對實在——外部實在世界——理性本質的信賴,有著強烈的唯物主義色彩。
2“朝上帝走去”——上帝佇立在科學探索的盡頭
什么樣的志向和信仰,就產生什么樣的成就。我國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說:“學本立于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立志而圣,則圣矣;立志而賢,則賢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
愛因斯坦信仰宇宙是完美的,簡潔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能夠使追求知識的理性的努力有所感受,他的志向始終是思考一些大問題,用其自身的努力去猜測上帝的方針,揭示大自然的普遍原理,從而更好地理解上帝、接近上帝。在他看來“在我們之外有一個巨大的世界,它離開我們人類而獨立存在,它在我們面前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恒的謎……。對這個世界的凝視深思,就像能得到解放一樣吸引著我們,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許多我所尊敬和欽佩的人,在專心從事這項事業中,找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寧。……從思想上掌握這個在個人以外的世界,總是作為一個最高目標而有意無意的浮現在我的心目中。”愛因斯坦這一最高目標,正是他的志氣和信仰所在!在漫長而多艱的科學旅程中,他的這種具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宗教信仰始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是激發其志氣,使其勇于求索宇宙之秘、析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的不可窮竭的源泉。
普朗克,在大自然的規律性、對稱性面前表現出了無比的敬畏之心和激賞的情懷,認為這種規律性、對稱性恰是宇宙結構中顯露出來的秩序和美麗,而這就是上帝,是絕對的東西。在《科學自傳》中他曾寫道:“外在世界乃是一個獨立于我們的絕對東西,尋找那些適用于這個絕對東西的規律,這在我看來就是科學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在《宗教與自然科學》一文的末尾,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口號:“朝上帝走去!”他對絕對東西(如物理學中的普適常數)的追求和依賴,走近上帝的渴望,不僅構成了他從事科學研究最深厚的動力,而且使他飽經憂患的一生充滿著溫暖、慰藉和光明。最終他提出了量子假說,發現單個光子的能量E與其頻率之間有恒定的倍數關系:E=hv,h=6.62606896×10-34J?S(為紀念普朗克后人稱之為普朗克常數),從而極大地推進了量子力學及相關科學的發展。
牛頓在物理學上的成就同他對宇宙合理性的深摯信念,以及熱切地想了解它的愿望,也是分不開的。在重力這個司空見慣的自然現象前,他竟懷著一種深深敬畏和贊嘆的感情:“重力必然是由一個按一定規律行事的主宰造成”。這個規律牛頓最后找到了,那就是萬有引力定律,但宇宙最初的推動力又從何而來呢?這個問題他苦苦追索之后歸功于“上帝是第一推動力”,是上帝推動了宇宙各星體的運動,從而產生了萬有引力。
萊布尼茨也是一個渴望能看到宇宙中“預定和諧”的人,數學在他眼里,全然不是別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淵博的知識、認識和研究工作同上帝聯系起來,對上帝的認識是他的工作的最高目標,研究數學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康托爾深信無窮數列是森嚴、和諧、永恒宇宙秩序的象征,它們都具有神性,集合論中的(連續統)勢是一種神圣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通向無限的皇冠、通向上帝的皇冠的階梯;對法拉第而言,同樣是與上帝近距離接觸的渴望引導他走上了物理學研究的道路,并且做了許多偉大的實驗,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些基本奧秘;玻恩在科學研究上的沖動也是源于他對上帝、美和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渴望在飛馳的現象中、急旋的萬物中找到這些固定的、安靜的東西。
在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學家看來,科學研究是通向“上帝”之路。上帝在無限遠方的召喚,使他們的精神世界有了一個固定不變的支撐點,于是他們的心靈在這個支撐點上找到了平衡,達到了神有所歸、慮有所定、心有所寄和靈有所托的安穩境界,這種境界完全可以使他們在科學探索的征途上打破物質界的種種誘惑,心中無任何偏見、私意地投身科學,不考慮個人榮名,甚至為捍衛科學真理可以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為利奪,不為害怵。眾所周知的布魯諾就是這方面的典范,為捍衛“日心說”他被教皇處以火刑,至死都臨危不懼……反之,如果他們世界只有科學而沒有上帝,那么他們的精神支撐點將會崩潰。上帝是他們獻身科學的精神因子和人格力量。他們對上帝的信仰指引著、激勵著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探求科學真理。理解上帝、接近上帝的渴望,乃是他們追求科學真理的強大動力。新晨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些自然科學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強烈的唯物主義色彩,他們的宗教觀是泛神論,他們信仰上帝,實質上是信仰宇宙的和諧、完美和可以被理解的特征,是對實在——外部實在世界——理性本質的信賴,是對宇宙合理結構和井然有序的一種獻身、崇敬和贊嘆的感情和心理狀態。但他們對宇宙和諧、完美的虔誠和狂熱,對宇宙合理結構和井然有序的崇敬、贊嘆甚至愿意為之獻身的感情和心理狀態卻同宗教的精神如出一轍。這種虔誠、狂熱、崇敬、贊嘆的感情和心理狀態無時不在激勵著他們去發現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奧秘,對他們而言,上帝佇立在科學無限探索的盡頭,運用科學的理性去發現宇宙的法則和秩序則是通向上帝的唯一正途。愛因斯坦生前常常說“大自然是一位難以接近的女神”,科學的探索困難重重,接近上帝乃是他們克服困難、追求科學真理的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這是一種崇高、莊嚴的宇宙宗教情感,這種情感不僅是科學研究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而且也是使科學研究最富有生氣的靈感源泉!于是我們不難理解,一個科學家可能信仰宗教,一個宗教信徒也不妨礙從事科學研究,科學知識和宗教信仰在一個人身上完全可以和平共處、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科學是理性和邏輯的象征,而宗教則是情感和直觀的代表,人不僅是理性的動物,還是情感的動物,人不會充當一部只按邏輯運算的計算機。科學取消了作為第一因和目的因的上帝,卻無法取消人類對于天地萬物的終極思考,盡管這種終極思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這種非理性的思考卻給理性的科學指明了航向。難怪愛因斯坦在《科學和宗教》一文中指出:“科學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來創造。然而,這種情感的源泉卻來自宗教領域。同樣屬于這個源泉的是這樣一種信仰:相信那些對于現存世界有效的規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說可以由理性來理解的。我不能設想一位真正的科學家會沒有這種深摯的信仰。”“科學沒有宗教是盲目的,宗教沒有科學是跛足的。”“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學知識提高了境界,而且意義更加深遠了。”
擴展閱讀
- 1小學科學
- 2領導科學
- 3小學科學教學中的科學素養
- 4科學特性
- 5科學追求
- 6小學科學建構科學概念的策略
- 7怎樣培養小學科學教師科學素養
- 8中醫男科學
- 9醫院科學拓展規劃
- 10創新哲學特征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