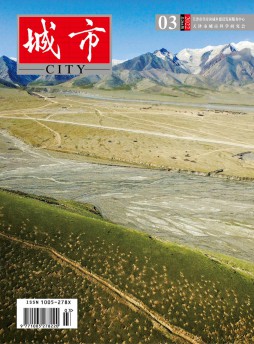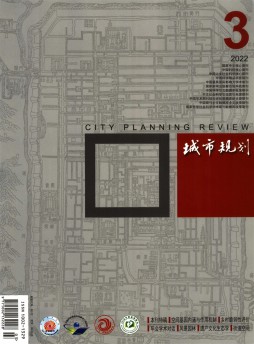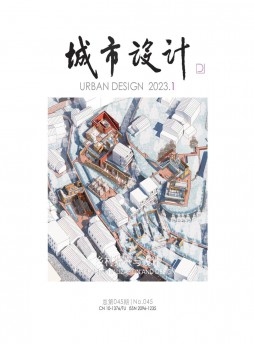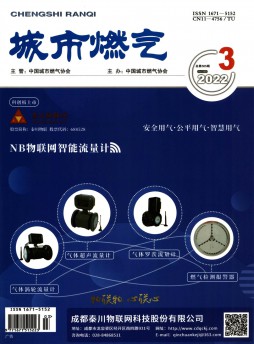城市經濟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城市經濟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根據空間相互作用、城市流強度、斷裂點等相關數理模型,分別以GDP,第二、三產業中17個行業從業人員以及兩市間距離為指標變量,對淮海經濟區20個城市經濟聯系的空間作用強度、方向與范圍進行定量測度與分析評價。
1.1作用強度
1.1.1經濟聯系強度。據公式(1)計得淮海經濟區主要城市兩兩間的經濟作用強度(圖1)。兩城市間經濟作用強度大于30個經濟度的有4對:徐州和棗莊(66.41個經濟度,下同)、徐州和淮北(47.38)、徐州和宿州(37.20)、淮北和宿州(30.66);在20~30個經濟度間的有3對:徐州和宿遷(22.10)、徐州和淮安(20.64)、萊蕪和泰安(29.84);在10~20個經濟度范圍內的城市有8對:徐州和臨沂(16.76)、徐州和淮安(14.75)、連云港和臨沂(10.62)、鹽城和淮安(13.79)、亳州和商丘(10.24)、棗莊和臨沂(17.75)、棗莊和濟寧(11.29)、日照和臨沂(13.19);其它城市間作用強度較低,均在10個經濟度以下。總的來說,開封、周口、菏澤、阜陽、蚌埠5個城市與該區其它城市間的經濟作用強度均在10個經濟度以下,徐州則與除周口外的所有城市間的作用強度都在1.5個經濟度以上,而兩城市間作用強度最小的為周口和連云港,僅為0.10個經濟度。據公式(2)計得該區主要城市空間作用的總體強度(圖1),并據此將20個城市分為四類:高經濟作用總強度的城市(作用強度在150個經濟度以上,下同)、中高經濟作用總強度的城市(100~150之間)、中經濟作用總強度的城市(50~100范圍內)和低經濟作用總強度的城市(50以下)。徐州空間作用總體強度最大,達267.71個經濟度,屬于高經濟聯系強度的城市,是位居第二位的棗莊(作用強度為144.08個經濟度,下同)的1.86倍,為總體強度最低的周口(9.25)的28.95倍,這表明徐州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勁頭較強。棗莊、淮北、臨沂、宿州處于高經濟聯系強度城市之列,與各個城市間經濟聯系較為緊密,可持續發展的潛力比較強。中經濟聯系總體強度的城市有5個,依次為淮安、宿遷、泰安、濟寧和萊蕪,在今后的發展中,其可持續發展的勢頭有待提高。處于低經濟聯系強度的城市有10個,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弱,今后發展中必須注重經濟轉型,加強與其他城市間的經濟聯系,縮小與先進城市之間差距,促進淮海經濟區的總體發展。
1.1.2城市流強度。計算城市流強度相關值(表1),據此將城市分為四類:高城市流強度城市(城市流強度值在300億元以上)、中高城市流強度城市(200~300億元)、中城市流強度城市(100~200億元)以及弱城市流強度城市(100億元以下)。由表1可知,徐州是高城市流強度城市,是淮海經濟區的中心城市。作為蘇北第一大城市、中國第二大鐵路樞紐,徐州以其獨特的交通運輸優勢和較快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較大的城市外向功能量和較高的城市功能效率,城市流強度值高達384.19億元,對淮海經濟區起著輻射和帶動作用,成為淮海經濟區的發展核心。臨沂和淮安屬于中高城市流強度城市,其城市流強度要遠遠高于中城市流強度城市,是淮海經濟區發展的重要城市,且臨沂以高于淮安10%的城市流強度成為該區發展的副級中心。中城市流強度城市有6個,依次為日照、萊蕪、棗莊、宿州、宿遷和鹽城,成為淮海經濟區發展的地方性集聚地和輻射中心。其余11個城市是弱城市流強度城市,是該區發展中較為必不可少的城市。可見,淮海經濟區“一超多強”局面較為顯著,未來發展的潛力巨大。在空間分布上,這些城市基本遵從“中心—”式分布[26]:淮海經濟區的發展核心徐州,位于其中心位置,而弱城市流強度的城市主要分散于該區邊緣地帶。這與城市經濟作用強度所得結論基本一致。
1.2作用方向據公式(3)計得淮海經濟區主要城市的隸屬度大小,由此分析淮海經濟區主要城市的經濟作用方向。由圖2可知,徐州的首位聯系城市是棗莊,其隸屬度高達24.81%;其次為淮北,隸屬度為17.70;隸屬度最低的為周口(0.42)。從空間距離上看,徐州經濟作用方向首先是距離較近但不相鄰城市,其次是相鄰城市,而對距離較遠城市也有聯系,可見其聯系方向表現為“中心—”向外擴散的模式。由圖3可知,其它主要城市對徐州的隸屬度均在各自隸屬度的前五位之列,說明徐州是淮海經濟區的發展核心。對徐州的隸屬度,排在首位的有6個城市,其中棗莊對其隸屬度最大,高達46.09%,說明徐州是其主要聯系方向;排在第二位的6個城市,隸屬度在10.35%~16.25之間不等,且各個城市的首位聯系城市表現為鄰近城市;排在第三位的有菏澤、周口、開封、萊蕪,除萊蕪的首位隸屬度達52.06%,聯系方向表現為泰安方向外,其他城市的前三位隸屬度相差不大,聯系方向均指向相鄰地域和中心城市徐州。日照、連云港對徐州隸屬度排在各自隸屬度第四位,這兩個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限制,聯系方向表現為相鄰地域指向;泰安對徐州的隸屬度排在第五位,隸屬度僅7.70%,其主要聯系城市為萊蕪、濟寧。綜上,城市空間作用的主要方向表現為與核心城市的緊密聯系和與其周邊城市緊密聯系的共同作用,即顯示出地域相鄰指向性原則和中心城市指向性原則[16]。
1.3作用范圍據公式(9)~(10)計得淮海經濟區主要城市間的斷裂點及場強(表2、表3)。由表2可見,徐州與各個城市間斷裂點明顯壓縮到終點城市,說明徐州輻射能力較強。與淮北間的場強最大,達1.19億元/km2,因此,可以此為強輻射半徑的選定場強,來確定各城市經濟輻射能量絕大部分擴散在多大范圍內。從表3可知,各相鄰城市間起點城市到斷裂點距離占兩城市距離的比重在0.4~0.6間波動,城市間輻射能力差距不大,且兩城市距離較近時,其場強也較高,說明具有向對方空間產生經濟影響的能力[27]。因此,以各相鄰城市間場強均值為弱輻射半徑的選定場強來計算城市弱輻射范圍,以反映各城市對周邊地區的主要影響范圍[28](圖4)。由圖4可以看出,淮海經濟區中部以徐州為中心,距徐州44.92km和110.92km以內分別為其強輻射和弱輻射范圍,這是由于其最強的城市綜合實力積聚了較強的經濟輻射能量;棗莊、淮北、宿州的強輻射半徑均在徐州弱輻射范圍內,說明它們受其輻射最強。東部以臨沂、淮安、日照為中心。這些城市規模相當,輻射范圍相互交叉地作用于對周邊區域,其中,宿遷幾乎被徐州和淮安的輻射平均瓜分,受這兩個城市的屏蔽效應[29]較大,不利于其自身的發展。北部以泰安、濟寧為中心,其中,泰安和萊蕪的相互作用甚密,其輻射能力向對方空間逐步滲透。而西部城市的經濟輻射能力較弱,彼此輻射半徑不相互重合,發展較為分散,綜合實力有待提高。總體來看,徐州無疑是淮海經濟區的輻射中心,呈現圈層輻射其他城市的空間結構:核心層表現為徐州的弱輻射范圍圈,包括徐州、淮北、宿州、棗莊;中心層表現為與徐州弱輻射范圍有交叉的城市,包括臨沂、宿遷、濟寧、商丘、亳州、蚌埠、淮安;層表現為與徐州的弱輻射圈無交叉的城市,包括連云港、日照、泰安、萊蕪、菏澤、開封、周口、阜陽、鹽城。
2主要結論
第2篇
依據城市物流發展水平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一致程度,將其分類為超前、匹配和滯后三狀態。只有城市物流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匹配,效用才會最大。他們的匹配是強調城市物流供給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需求相匹配。所謂匹配考察的包括單純的量上的匹配,更強調質上的匹配[3]。超前區:城市物流需求不足,小于城市物流服務供給。超前區里可能是城市經濟并沒有預期繁榮,物流需求量不足,導致物流供給量過剩,市場反映出來的現象是物流設施設備大量閑置。另一種情況是物流企業不顧城市整體經濟較落后的現實情況,引進各種先進物流技術,大量增加物流成本使物流需求方無法接受。
匹配區:城市物流需求與供給基本均衡,其表現為市場上基本無閑置物流資源,也不存在需求得不到及時滿足的現象。匹配區內城市物流技術可能不是最先進的,物流設施不是最新的,物流發展水平也不是最高的,但其職能效用得到最大化,對城市經濟的輔助協調作用體現得最明顯。滯后區:城市物流需求明顯大于物流服務供給,市場反映出來的表現為物流設施落后,誤時延時頻率高,物流管理水平低,進而導致物流成本高。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是物流發展水平遠比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落后。
二、城市物流對城市經濟的影響
城市物流支撐著城市日常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行。在第一第二利潤源相繼枯竭的二十一世紀,作為第三利潤源的物流對城市經濟的影響作用不言而喻。值得提出的是,城市物流對經濟發展有正負兩面影響。
1.負面影響無論城市物流發展水平是位于超前區或滯后區,對城市經濟和環境的消極作用遠大于積極作用。當城市物流水平滯后于城市經濟發展時,其典型表現是庫存倉儲量大、服務水平低、物流成本高、物不能通暢其流。低效率的物流運作水平,妨礙了商品流通與區域城市間職能分工與合作,嚴重損害區域城市經濟的“吸收”與“輻射”面積,更不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另一種偽命題是認為城市物流發展水平越快越好。須知若城市經濟發展速度跟不上,導致物流有效需求不足,同樣會造成物流資源大量閑置,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最后物流產業只能成為當地產業的累贅。
第3篇
1.1經濟實力的算法盡管目前并沒有形成對經濟實力嚴格的定義,不難看出,學者們至少在這方面達成了一致:城市經濟實力是城市競爭力的基礎,不僅反映了城市經濟發展的水平、規模特征,也反映了城市在吸引控制市場和資源方面的能力[19].結合當前的研究結果,根據城市經濟實力的內涵,遵循科學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并力求較完善、全面、真實地反映各城市的綜合經濟實力.本文認為城市經濟實力應是發展水平和經濟規模的函數.表征城市經濟實力難以以單一指標進行全面評估,而綜合指標也受困于評估指標和評估權重的選取,分析前人指標體系的構建發現,盡管指標選取數目、內容各異,均量指標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總量指標反映經濟發展規模,對這些指標進一步分析發現,總量指標與GDP總量有很強的相關性,而均量指標與人均GDP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本文選取人均GDP和GDP總量兩個指標來對城市經濟實力進行評價,其公式如下。式中:S表示經濟實力;gt表示某一區域GDP總量(億元);ga表示人均GDP(萬元).其中,GDP通過平減指數換算成2003年的不變價格,為檢驗該評價方法的合理性,將計算結果與《中國城市競爭力評價》[31]進行對比.
1.2數據來源及說明從2004—2013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選取全國地級市及其以上城市GDP總量和人均GDP指標,對部分數據缺失的城市通過查找該城市所在省區當年統計年鑒補齊,還有部分缺失數據通過統計年鑒中其他數據計算間接得來.截至2012年末,除港澳臺城市外,我國有289個地級以上城市,2011年巢湖市由于行政區調整成為縣級市,中衛、隴南、銅仁、畢節、三沙市成立較晚,拉薩市多年的經濟統計數據缺失,因此,本文選取283個地級以上城市作為研究單元.為了便于研究區域經濟實力差異,參考黃永斌[32]等人的做法,并做了適當的修改,把全國分為東北地區(遼吉黑三省及內蒙古的赤峰、通遼、呼倫貝爾)37個城市,北部沿海地區(京津冀魯)30個城市,華東沿海(蘇浙滬)25個城市,西北地區(陜甘寧青新)28個城市,西南地區(云貴川渝桂)45個城市,南部沿海地區(閩粵瓊)32個城市,中部地區的城市由于數量較多,分成中部偏南地區(湘鄂贛皖)52個城市、中部偏北(晉豫及內蒙古的呼包鄂、鄂爾多斯、巴彥淖爾)共34個城市.
1.3經濟實力評價結果根據上述公式計算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經濟實力指數,部分結果見表1.從評價結果來看(表1),該城市經濟實力評價結果基本反映中國城市經濟實力狀況,將其與《中國城市競爭力評價》[31]結果進行對比發現,該評價的城市經濟實力排名和指數與城市競爭力排名和指數具有較好的一致性,說明該城市經濟實力評價方法比較合理,能夠反映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狀況.
2地級以上城市經濟實力時空演化特征
從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經濟實力CRn指數變化情況(圖1)可知,2003—2012年,全國城市經濟實力的CRn指數呈下降趨勢,2008年以前,CRn指數緩慢下降,其后變化加速.說明全國城市經濟實力差異在不斷縮小,經濟實力較強的城市實力比重不斷下降,2008年以后這種趨勢不斷加快,但全國城市整體差異還較大.為了研究全國城市經濟實力時空演化特征,選取2003,2008,2012年3個時間斷面進行分析。
2.1城市經濟實力快速增長,城市之間相對差異逐漸減小從城市經濟實力描述性統計結果(表2)來看,3個時間斷面上,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蘇州經濟實力排名雖稍有變化,但一直穩居經濟實力前5名之列.固原、定西、臨滄、麗江一直在經濟實力排名后5位徘徊.2008—2012年,全國城市實力指數均值從974.07增長到2170.53,標準差分別從2650.93增長到4390.59,經濟實力前5名的城市和后5名經濟實力之比從1082.1下降到449.8.經濟實力排名前40的城市在全國城市經濟實力中的比重從75.02%下降到74.72%,而排名后40的城市經濟實力比重從0.29%增長到0.47%.這說明全國城市經濟實力增長較快,并且經濟實力較弱的城市實力增長快于實力較強的城市.城市之間的經濟相對差異逐漸減小,絕對差異卻進一步擴大.城市經濟發展中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態勢并未從根本上改變.
2.2城市經濟實力等級特征明顯,兩極分化現象嚴重為研究中國城市經濟實力特征,按平均經濟實力指數的0.5倍,1倍,1.5倍將全國283個地級以上城市分成4個等級,S<0.5為弱經濟實力城市,0.5<S<1為經濟實力較弱的城市,1<S<1.5為實力較強的城市,S>1.5為強經濟實力城市.各類城市數量及實力比重見表3.從地級以上城市經濟實力等級分布結果(表3)可以看到,2003年,弱經濟實力城市有202個,占城市總數的71.38%,強經濟實力城市占14.49%,較弱城市占10.6%;經濟實力較強的城市有10個,僅占3.53%.地級以上城市經濟實力數量特征上表現為以弱實力城市為主,其次為強實力城市.城市經濟實力等級存在著嚴重的斷層,實力較弱和較強的城市較少,并沒有形成有序的金字塔格局,而是數量上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結構特征.在時間序列上,各類城市數量等級特征上漸趨扁平狀,但各類城市數量等級變化并不明顯.從實力指數上看,強實力城市占全國城市經濟實力比重的絕大多數.2003年強實力城市占全國城市經濟比重在四分之三以上,而數量眾多的弱實力城市實力比重僅為12.12%,2012年強實力城市比重下降到69.79%,弱實力城市比重上升到13.44%.實力較強和較弱的城市比重分別從2003年的4.55%,7.76%增長到2012年的6.29%,10.48%.以城市經濟實力指數均值為分界點,強實力和較強實力的城市僅占城市數量的20%左右,卻占全國80%左右的經濟實力.這說明我國城市經濟實力差距依然較大,城市經濟實力兩極分化現象比較嚴重.
2.3全國城市經濟實力呈東高西低,實力比重東降西升格局從東中西三大地帶來看,整體上中西部經濟實力增速高于全國的增長速度,中部地區經濟實力增速領跑全國.三大地帶城市經濟實力變化情況在時間序列上并不一致.2003—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實力比重增長36.00%,而西部地區經濟實力比重卻下降將近5%,東部地區經濟實力比重從84.15%下降到79.16%,中部地區經濟實力變化速度要快于東部和西部地區.與此同時,中西部經濟實力指數比值從1.29擴大到2.16,而中東部之間的差距從9.24減少到5.56.從2008年到2012年,中部地區經濟實力增長勢頭依然強勁,經濟實力比重增長26.57%,但低于西部地區的42.66%.東部地區經濟實力比重繼續下降,到2012年,占全國經濟實力比重的71.96%.中東部之間的實力指數比值縮小為3.86,中西部之間的經濟實力指數比值也進一步縮小至1.99.盡管地級以上城市經濟實力東中西梯度差異依然明顯,中西部地區城市經濟實力增長迅速,三大地帶之間經濟實力整體差距縮小比較明顯,中部和西部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但這一趨勢正在減弱.
2.4城市經濟實力變化空間異質性顯著通過區域經濟實力平均排名變化來研究城市經濟實力空間變化的異質性,從城市經濟實力排名變化表(表4)可以看出,東部沿海地區一直是全國經濟實力最強的區域,西南和西北地區是城市經濟實力最弱的地區.時間序列上,各區域平均排名變化趨勢不盡一致.整體來看,東部沿海、西北地區排名穩中有升,2003—2008年城市平均排名處于緩慢下降階段,之后又慢慢回升,到2012年其經濟實力平均排名已超過2003年的水平.中部偏南地區及西南地區經濟實力排名穩中有降,其經濟實力排名同樣的下降和提升之后,經濟實力排名卻未能恢復至2003年的水平.北部沿海地區、南部沿海地區及西南和中部偏北地區平均經濟實力排名變動較大.南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排名一直處于下降階段,其經濟實力平均排名從2003年的94.19下降到2012年的120.31,而西北地區經濟實力平均排名則一直處于快速上升時期,其平均排名從212.11上升到190.64.北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排名經歷了緩慢的上升階段,但之后經濟實力排名下降幅度較大,總體經濟實力排名呈下降趨勢.中部偏北地區城市經濟實力排名經歷了迅速上升之后,又快速下降,但整體排名較2003年已有較大提高.為進一步研究城市經濟實力相對變化空間分異情況,把經濟實力排名分為3個等級,排名上升10個名次以上的城市為經濟實力上升型城市,下降10個名次以上的城市為經濟實力下降型城市,排名變化在10個名次以內的城市為經濟實力穩定型城市.從經濟實力排名變化圖(圖2)來看,2003—2008年,經濟實力穩定型城市有134,占全國城市近一半左右,實力上升型城市有72個,下降型的城市有77個.實力上升型和下降型的城市南北分異比較明顯,實力上升型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秦嶺—淮河以北地區,并呈團塊集中分布,冀北遼西蒙東形成了環繞京津都市圈的經濟實力上升區,及內蒙古中部向南延伸至河南,西至陜西寧夏,東至山西的經濟實力上升區.這些區域的城市大多以能源、礦業為主,經濟實力上升顯著,如榆林、延安、呂梁等城市經濟實力排名上升100個名次以上.除黑龍江的部分城市外,經濟實力下降型的主要分布在秦嶺—淮河以南地區,且集中分布在廣東、湖北兩個省區,湖南境內的京廣鐵路沿線的城市經濟實力排名下降也比較突出.2008—2012年實力穩定型的城市增加到160個,占全國城市總數的56.54%.經濟實力排名下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兩省及珠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關中城市群、蘇北及成渝經濟圈的大部分城市出于經濟實力排名上升期.總體來看,全國城市經濟實力排名變動比較劇烈,但這種程度正逐漸減緩.經濟實力較強的城市排名比較穩定,中小型城市實力排名起伏較大,尤其一些能源、礦業城市排名經歷了大起大落的歷程.排名變化較大的城市呈現整體分散、局部團塊集中的空間格局,尤其集中在中西部一些城市群或其周圍地區.
3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