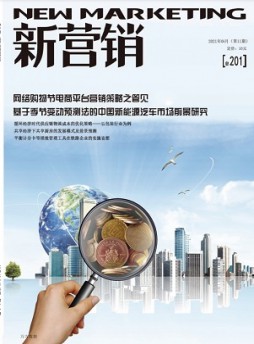營銷碩士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營銷碩士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小說的敘事視角,一般來說有兩個:一是外視角,作者作為故事的敘述者,對作品中所有人物以及事件的每個方面都了如指掌,了解每個人物豐富的內心情感,可以縱觀全局,條理分明地把小說的每個部分連貫起來,這樣的敘事視角被稱為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外視角或“廣角鏡頭”;二是內視角,作者不介入,只是讓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或者幾個人物充當敘述者,從人物的視角來觀察故事情節,體察情感。如第一人稱限知視角,只能敘述“我”所知道的人或事,“我”是作品中故事的參與者和敘述者,第一人稱敘事可以增強作品的真實感和親切感;如果由作品中的幾個人物充當敘述者,在他們之間進行視角轉換,也屬于內視角,可以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現時空。楊紅櫻兒童小說的閱讀對象是小學生,依據他們的心理特點、思維特點,“從以具體形象思維為主要形式逐步過渡到以抽象邏輯思維為主要形式。但這種抽象邏輯思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直接與感性經驗相聯系的,仍然具有很大成分的具體形象性”[3](P398)。楊紅櫻的作品以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外視角和第一人稱限知視角的敘述方式為主。
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外視角
在楊紅櫻的兒童小說中,大量運用了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外視角,敘述者就像掌控了人物的大腦,對其所思所想一清二楚,小讀者也更容易看懂,很容易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和他們同喜同悲,有一種親切感。在“淘氣包馬小跳系列”中,如《跳跳電視臺》“虐貓事件的背后”,講的就是二年級的三個女生,她們在學校表現很好,學習成績也不錯,卻用極其殘酷的方法虐待小貓,以此獲得。這件事被“跳跳電視臺”知道并采訪,在這則故事的最后,作者這樣分析與評價:“其實,這三個小女生都像那只小貓一樣可憐,她們都是在缺少愛的環境中長大,所以她們心中也缺少愛。當遇到那只跟她們的命運相同的小貓時,便用折磨它來發泄心中的恨……”[4](P135)作者站在高處,將一個涉及到兒童心理扭曲的復雜問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述給小讀者,符合他們的理解能力與思維發展,這樣也就拉近了敘述者同人物以及讀者的距離。在“淘氣包馬小跳系列”《開甲殼蟲車的女校長》中,馬小跳等人在返校日遲到了,班主任秦老師把他們叫到辦公室,當馬小跳等人陳述遲到的真實原因時,秦老師露出一副不相信人的神情:“人家大學生勤工儉學,還要你們幾個小學生教?”這個時候作者忍不住站出來評論:“為什么小學生就不能教大學生呢?如果秦老師不是帶著成見,耐心地聽他們講完,就會發現,他們講得合情合理,完全沒有編造的痕跡。”[5](P25)很顯然,作者站在馬小跳等人的立場,理解孩子的心情,說出了他們的心聲。
第一人稱限知視角
第2篇
按照我們大家傳統的觀念來看,演員最出色的地方就應該是演技才對,而不是顏值。但是現在似乎完全顛倒過來了,拍的一部電視劇,就好像拍動畫片。
似乎為了烘托女主角的絕美顏值,就好像把電視劇特效濾鏡弄得跟影樓一樣。
但實際上,我覺得這些大可不必,雖然很多時候那些盲目追星的人固然存在,但是也有一些存在理智的人在用理智的眼光和態度去看待這些問題。
聽如果這些真的發展到一個無可逆轉的地步了,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會放棄這樣一條路,繼續走下去,無論是追星,還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們都應該知道輕重才好。
就好像那些一直被抄襲的小說,還是義無反顧的被改編成了電視劇,只是因為他們有很大的商業價值。也許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值得抨擊的,但是卻沒有人了解,也沒有人知道。
第3篇
關鍵詞:小說;起源;先秦諸子;流變
引言:提到我國小說的起源和演變,從魯迅以來,學者們從諸子文章、史傳文字、神話傳說及詩賦文字等各種文章樣式上尋根溯源,結論也是眾說紛紜。筆者認為任何一種文體,其形式本身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永遠處在活躍的律動狀態之中,小說也不例外。從小說發生學的角度來看,與小說的產生關系最為密切的是諸子群書。前賢及時下有關中國小說史的論著談到中國小說的起源也往往將子書作為形成小說的源頭之一。然而前人在研究的時候只注重從小說的外在聯系或小說和其他文體的對比上去考察二者的關系,卻往往忽略了從小說的內在發展規律上把握小說與諸子之間的關系。
一、諸子群書正統地位的式微促進小說產生
從小說的最初問世來看,小說可以說是子書的副產品或末流的產物。班固說:“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務出,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舍諸侯。”①姚明娜《漢志注解》對此解釋說:“古者官師合一,私家無學。及王道既微,官失其守,始有私家之學。故天下有道,則學在上;無道,則在下。至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乃懸格以待學者,而諸子專家,于是乎起矣。②章學誠說:“至于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于典章政教也。”③由此可以看出子書和經書的區別就在于經書為官學的經典著述而子書則是官學衰微后的私學,而諸子群書作為私學的顯著特點就是能充分闡發自己的主觀見解,不用顧及學說是否公允。就如同章學誠所說:“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師言行為世法,則亦命其書為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膺之”。④這種“近取譬論”的方法其實并非小說家所發明,而正是諸子早已普遍采用的一種方法。誠然,諸子對“近取譬論”這種方法的運用也是經歷了一個由少到多的過渡過程,但恰恰是這個過程為小說的產生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劉勰曾對諸子產生流變的過程有過論述,他在《文心雕龍·諸子》中說:“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馀文遺事,錄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茲……暨于暴秦烈火,勢炎昆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留思,子政讎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鱗萃,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馀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璅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⑤從劉勰論述中可以看出子書的起源是鬻熊以“余文遺事”的方式向周文王講解“道”的原理,也就是說子書的產生是依附于經書的。其實子書包括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它的說理性;一為它的表述形式多以“瑣語”、“余文遺事”為主。而在劉勰看來,講道理是子書的本分和要義,而“瑣語”及“余文遺事”不過是一種歧途:“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子,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湯如茲,況諸子乎!”⑥他把子書這兩個要素概括為“純粹者”和“踳駁者”兩種。前者如《荀子》、《呂氏春秋》,他認為是子書的正統;而后者如《列子》、《淮南子》,他認為是子書的末流或歧途。
二、諸子群書說理形式對小說的影響
小說作為子書的流裔,它必然要牢牢地打上從母體帶來的胎記——子書的說理意味。從《莊子》到《隋書·經籍志》,盡管人們對小說性質及功能的認識相距甚遠,但有一點卻幾乎始終沒有變化,這就是對小說說理功能的認識。從《莊子》開始,子書中的說理意味就開始逐漸明顯:《莊子》里就記載“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⑦雖然一開始是對小行小言這種行為進行了否定,但無可否認的是子書中這種以“小說”來說理的目的卻在無形中達到了。像以后不論是桓譚還是班固,無論是從什么角度來認識小說,都始終沒有離開小說的說理的說理功能。如桓譚所云“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⑧ 桓譚從內容到形式等各個方面來分析小說的各種特征,最后還是落腳在“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上。以后,是否“有可觀之辭”一直成為衡量小說價值的一個重要標準。作為儒家文學思想中實施“教化”功能的普及和推行手段,這種注重小說中說理功能的傳統是“文以載道”思想的具體表現。
因此,小說雖是以“讕言”、“瑣語”而脫離子書的,但卻又常被人津津樂道為“有可觀之辭”。從子書的整個流變過程來看,“變”的一方是從子書中發展出來的以“近取譬論”為主要敘事手段的小說敘事手法,即小說由“純粹”到“踳駁”的過渡。基于正統的角度來看,這種流變或許有失體統,但從小說這種新文體的發展角度來看,這無疑是個難逢的機遇。其實小說中的那些“叢殘小語”、“街談巷語”最初并不屬于小說本身,而只屬于諸子散文流變中的一支特例;然而“不變”的一方卻是子書中的說理內核。從諸子到小說,雖然文章的形態上已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作為子書的重要特征,說理的內在核心卻始終沒有本質上的變化。而小說在這種變與不變、革新與繼承的過程中也有其自身的發展方向。從《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的作品來看,最初被劉向認定為小說的那些作品,似乎并不是要寫出一部小說,而主要是以說理為主的子書。可能只是由于其中包含有“讕言”、“瑣語”的成分而被劉向打入另冊,放在小說家之流中。所以這些作品其實更接近于子書,與日后的小說的特征差距本來較大。胡應麟對此曾指出:“漢《藝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后世博物、志怪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⑨因此可以說子書的這種“踳駁”因素的出現,于子書本身功過尚且并無定論,但對小說的產生確實功不可沒。(作者單位:營口市衛生學校)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藝文志》[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
[2]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成玄英、曹礎基《莊子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1
[4]顧實、姚明煇.《漢書藝文志講疏 漢書藝文志注解》[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5]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M].北京:中華書局.1958
[6]桓譚.《新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7]劉勰.《文心雕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0
[8]蕭統.《文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章學誠.《文史通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莊周.《莊子》[M].北京:中華書局.2007
注解
① 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類跋語。
② 引自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③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
④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
⑤ 劉勰《文心雕龍·諸子》。
⑥ 劉勰《文心雕龍·諸子》。
⑦ 《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成玄英疏:“干,求也;縣,高也。夫修飾小行,矜持言說,以求高名令問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
擴展閱讀
- 1旅游營銷模式形象營銷
- 2網絡營銷旅游營銷
- 3汽車營銷關系導向營銷模式
- 4保險營銷員關系營銷
- 5營銷思想與營銷實踐互動
- 6營銷創意營銷執行
- 7營銷創意營銷執行
- 8金融營銷
- 9CRM營銷
- 10戰略營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