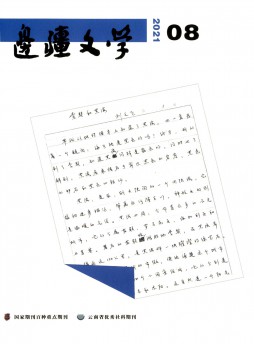文學研究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文學研究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最常見的是其與的聯系,這代表了追溯這種傳統的一種思路,即從西方舶來的理論資源中尋找提供了支撐的部分。然而應該指出,這是對于龐大的西方理論的簡單化處理。這種傳統的西方理論支柱,應該是更寬泛而又更準確的一種文學觀念,即歷史主義觀念。盛行于19世紀的西方的歷史主義觀念,雖然是個寬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將文學與外部原因,如時代、種族、社會等緊密關聯起來并對比關照。而由于其傳入的時代(20世紀初)對于思想發展的需要、以及其與進化論的糅合傳播,歷史主義觀念對中國此后的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也包括了的文論。在此同時,歷史主義觀念的傳入、沿襲與作用,并不是單一的原因。仍然從西方理論引入的角度看,在對整個西方文學的研究中,對其歷史悠久的“摹仿”論傳統的接受,必然也對此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無疑是與歷史主義觀念糾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贅言。而從中國自身的文學傳統來說,必須要提及的是“文以載道”的傳統觀點的深遠影響。文以載道,體現的就是強調社會性、功能性的文學觀。而又因為“道”的模糊性與可寫性,在歷史沿革中,這種觀點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斷地被沿襲。到了作為新文學開端的五四時期,“文以載道”作為一種舊思想受到排斥,然而與此同時興起的將文學與種種社會思潮、救國思想聯系起來的趨勢,卻恰恰變式地沿襲了“載道”的傳統。至此,“載道”便于傳入的西方文論一起,對中國以后的文學研究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興盛、熱切追求文學的“真實”,即是其中一個顯著的結果。
2.在吉林大學老一輩學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處于那樣的時期與環境下,這種特色自然是并不難見得的。如劉柏青老先生的《魯迅與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對新思潮派作總括與介紹的時候,劉老先生并未太多地從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學發展、以及新時期文學吸納革新來著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會條件為著眼點,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為主的研究方法,強調“這樣的事實,決定了明治文學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種強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積極的浪漫主義的風采”。而在論述“同魯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龍之介時,也多從其小說的敘事內容出發,與其生平、所處年代、環境相聯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會道德意味的結論:“作為一個人生的戰士,他是失敗了,而他的文學也就成了‘失敗的文學’。”在此同時,我們應該指出,劉老先生的論文里也有著豐富的文學內部研究的成果,是不應該被刻意無視的,比如在論證芥川與魯迅的歷史小說時,更多地是從文學趣味、小說文體的演變著眼的。然而此處關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為中心,并且左右著文學評價的最終定論。而且,劉老先生的此文絕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學者們的研究,作為全國主流研究的一個局部,顯現出對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對文學“真實”的追求。再如劉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藝所受日本無產階級文藝思潮的影響》、金訓敏教授的《論魯迅的“拿來主義”》、劉中樹教授的《漫談老舍的創作的民族化和大眾化》等皆對此有所體現。而在思想解放文壇革新的歷程中,這種傳統雖然依舊有其強力的影響,卻無法不受到強烈的沖擊。正如馮友蘭《新理學》中提出的“照著說”、“接著說”,乃至于“對著說”,在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之時,如何面對偏重外部研究、“真實”追求的傳統,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與超越,又一次成為了學者研究中無可避免的問題。那么,傳統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從一種絕對主流變為相對主流,并且帶上了“舊”的文化標簽以后,學術界是如何繼續研究、發展的呢?作為作者對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觀表現,題目中的要素開始豐富了起來,并且明顯地形成了一種更“復雜”的標題構造———即形成了一種更專屬于“文學”的標題形式,其中文學作為主體與許多新的美學、文藝學、社會學理論結合起來。如張福貴、馬麗玲《人類思想主題的生命解讀———張資平小說主題論之二》,張叢皞的《“大團圓”與中國現代小說創作的主體意識變遷》等等。從文本來看,在新時期的學者研究中,超越舊傳統的努力是不難尋見的。一方面,從接繼的角度來說,舊的通過外部研究拓寬文學研究的方法,通過對更大的主題的探究被延續下來,文學獲得獨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種大視野之中進行分析。如張叢皞、韓文淑的《詩意難尋的生命寓言———重讀<憩園>》,在對經典作品的重新解讀中,延續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傳統。然而這里應該注意,外部研究已經不再處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學作品內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這是與以往“從外而內”的外部研究絕不相同的,文學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關注。但仍有一種延續的趨向,即對文學“外部意義”的追求。簡而言之,是對文學意義的延伸。如張福貴、馬麗玲的《人類思想主題的生命解讀———張資平小說主題論之二》,即是從文本分析著手,進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個廣闊的生命主題。這種研究方式與舊傳統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繼承了舊傳統,體現了舊傳統的在“真實”以外的追求,即文學的廣義性,以及對“意義”的追求。而如今,這當中的“意義”在社會性與功能性上已經變得不再單一,體現出了一種非文學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學在延伸的意義中成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為“真實”與“公用”而使文學成為工具。
3.這里依然顯示出傳統的強大影響
第2篇
在文學家中有一小批人,他們不滿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層次,他們的目光總是看到人類視界的極限處,然后從那里開始無限止的深入。寫作對于他們來說就是不斷地擊敗常套"現實"向著虛無的突進,對于那謎一般的永恒,他們永遠抱著一種戀人似的痛苦與虔誠。表層的記憶是他們要排除的,社會功利(短期效應的)更不是他們的出發點,就連對于文學的基本要素--讀者,他們也抱著一種矛盾態度。自始至終,他們尋找著那種不變的、基本的東西,(像天空,像糧食,也像海洋一樣的東西)為著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這樣的文學家寫出的作品,我們稱之為純文學。我愿自己永遠行進在這個人數不多的隊列中。
"純"的文學用義無反顧地向內轉的筆觸將精神的層次一層又一層地描繪,牽引著人的感覺進入那玲瓏剔透的結構,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內核突進。凡認識過了的,均呈現出精致與對稱,但這只是為了再一次地向混沌發起沖擊。精神不死,這個過程也沒有終結。于寫作,于閱讀均如此,所需的,是解放了的生命力。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學必然短期效應的讀者不會很多,如果又碰上文學氛圍不好的話,作者很可能連生存都困難。
中國文化傳統勢力是太強大了,它那日益變得瘠薄的土壤中如今孕育的,是普遍的萎靡與蒼白,它早已失去了獨自擔負起深入探索人性的工作的力量,但它仍能匯集起世紀的陰云,擋住有可能到來的理性之光。我認為我們的文學急需的,不是那種庸俗的關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討論,(這種討論令人顯得猥瑣)而是一種博大的胸懷和氣魄,一種對于生命的執著,和對于文學自身的信心。只有建立起這樣的自信,才不會局限在日益狹小的觀念中,才有可能突破傳統的束縛,逐步達到為藝術而藝術的境界,從而刷新傳統。
一些別有所圖的大人物由于自己所處的高位,也由于知識結構的陳舊過時,在文壇上不斷發表言論,企圖將純文學的概念限制在狹小的范圍內,讓其自行消亡。他們口口聲聲強調作家要關懷他人,理解他人,對大眾的疾苦不能熟視無睹等等。試想一個人,如果他連自己的內心都不關懷,也不去認識,任其渾渾噩噩,那么他那種對"他人"的關懷,對于被關懷的對象,又有多大的作用呢?即使當下"贏得"很多讀者,他的作品又能否給讀者帶來精神上的福音?恐怕更多的是暫時的麻醉吧。還有的人將"自我"限定為表面層次的世俗觀念,缺乏起碼的文學常識,以自己的半桶子水來蒙混讀者,以掩蓋自己創造力的消失……這些觀念之所以能流行一時,說明讀者對于究竟什么是純文學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是非常模糊的。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純文學在中國這個古老守舊的國度中還是屬于新生事物,它的生長,有賴于作家們和批評家的共同努力。
當純文學的探索開始之際,寫作者立刻會發現自己站在了已經存在的自我的對立面,這個自我是由文化、社會、教育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構成的表層的自我。這些因素堅不可摧,聚成銅墻鐵壁。如果人要進行純度很高的創造,他就必須調動深層的潛力,戰勝舊的自我,到達空無所有的極境。因為只有在那種地方,精神的好戲才會開始。那一次又一次對于已有的傳統、文化等等的突破。其實也就是精神對于肉體桎梏的掙脫。每一位寫作者,他的肉身都是由過去的傳統滋養著的,而如今他所進行的發明創造,卻使得他必須決絕地向肉體挑戰,將這種自戕的戰爭在體內展開,僅憑著一腔熱血和自發的律動進行那種野蠻而高超的運動,并且絕對不能停下來,因為停止即死亡。這便是純文學作家的危險的困境,也是自古以來純文學作家的命運。
作為一名生長在中國的寫作者,血液里頭天生沒有宗教的成分,那么,當他要與強大的傳統世俗對抗之際,是什么在支撐他,使他立于不敗之地呢?這是我長久以來在體驗的問題。現在答案是一天天清楚了。藝術本身便是生命的藝術,一個人如能執著于純粹的藝術沖動,那便是執著于生命,執著于那博大精深的人性。在十幾年不懈的追求中,我在體驗到純藝術的終極意境的同時,也深深地感到,這種純美之境是同宗教意境并列的,也許還更為博大,并且二者之間是如此的相通。不知從哪一天起,作為寫作者的我便不知不覺地皈依了這種生命的哲學,只要我還在寫,我便信。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只能在行動中實現的信仰。誰又能說得清生命到底是什么?人只能做,讓一個又一個的創造物閃耀著奇跡般的光輝,這一過程,大約就是將物質變精神的過程吧。即使有一天,我因年老體衰無法再寫作了,恐怕也只能生活在那種奇境的回光之中,因為那是我作為"人"的一切。
第3篇
在歷史文學基本規律與規范的探索方面,吳秀明的研究顯示出一種理論體系建構的特色,具體成果主要表現在《文學中的歷史世界》《歷史的詩學》和《真實的構造》三部專著之中。《文學中的歷史世界》屬于文學本位立場的理論體系建構。作者將歷史文學界定為“以一定歷史事實為基礎加工創造的”“與一定史實具有異質同構聯系的文學”,以題材的自然屬性與審美超越這種雙重性為出發點,展開了對歷史文學本體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從真實性的內外在層次及其結合方式、歷史感與現實感的關系及作家的自主調節功能、作家對歷史題材進行藝術轉化的特征與條件、創作方法的差異性和藝術表現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論述了存在于歷史文學創作中的基本理論問題,并對其讀者接受和語言媒介層面的獨特性進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討了歷史文學當代實踐中所表現出的各種重大理論問題,對于社會主義新型歷史文學的獨特內涵、歷史文學的“翻案”與“影射”問題、歷史文學的“現代化”問題等,都進行了史論結合的理論闡釋與實踐引導。最后,作者扼要地論述了“深入歷史”這一歷史文學作家獨特的創作功力,并從歷史文學產生與發展的高度,揭示了歷史文學作為文學大家族一員的認識論基礎和實踐依據。通觀全書,作者所展示的實際上就是一部邏輯周密、規范初具的“歷史文學原理”或“歷史文學概論”。《歷史的詩學》實為《文學中的歷史世界》的邏輯呼應和內容補充之作。該書分為“理論篇”“發展篇”和“實踐篇”三個部分。其中“理論篇”從哲學的高度,闡述了“歷史”轉化為“歷史文學”的詩學基礎與詩化路徑,“本體論”“創造論”“形式論”則是其中具體展開的三個側面。這一部分實際上是以“歷史”為本位,與《文學中的歷史世界》第一至六章從文學本位角度論述歷史文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形成了一種思維邏輯上的映襯與呼應。《歷史的詩學》的“發展篇”與“實踐篇”則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表現出一種將自我理論建構貫徹到闡釋中外歷史文學實踐之中、并從得到驗證與豐富的學術意圖。這些內容又與《文學中的歷史世界》中有關創作現實中的理論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一種內容上的相互聯系與補充。這樣縱橫交通的相互呼應,使得吳秀明的歷史文學理論體系顯示出視角多維、層次豐富、邏輯貫通的學術特征。在《文學中的歷史世界》和《歷史的詩學》搭建起歷史文學理論體系基本框架的基礎上,吳秀明又以《真實的構造》一書著力探討了“真實性”這一歷史文學的核心問題與“斯克芬司之謎”。在上編“對歷史文學真實論的系統考察”中,作者運用在1980年代后期處于中國知識界學術前沿的系統論原理,從歷史事實轉化為藝術內容、作家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古為今用的需要和讀者的認同接受這樣四個方面,將“真實性”的系統構成分化為“映象性真實”“主體性真實”“當代性真實”和“認同性真實”四個要素。對每一個真實性要素,則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學術界慣有的理論術語和思維邏輯進行闡述,緊接著再用一章的內容以學界前沿的理論知識和作者本人獨特的思辨邏輯進行論辯。全書共分成八章,交叉運用經典理論思維和前沿知識思維,將歷史文學的“真實性”作為一個立體多維的系統進行了逐層剖析。下編“對歷史文學真實論的專題研究”,則分別探討了藝術類型、虛構手段、審美關系、現代意識和形式規范對歷史真實的藝術轉化所可能起到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實際上是以“歷史真實”為意義基點和邏輯樞紐,重構了歷史文學的理論體系。上、下編之間,共同形成一種“整體系統分析和靜態專題分析相結合”的邏輯結構。可以說,《文學中的歷史世界》和《歷史的詩學》是從不同側面建構起了歷史文學理論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歷史文學作為一個領域或學科的“學術地圖”;《真實的構造》則是聳立于這塊學術地盤核心位置的“地標性建筑”,屬于對歷史文學最基本、最核心問題的系統化闡述。這三部著作合起來,就以點面結合的研究成果,層次豐富而體系相對完整地體現了吳秀明“將歷史文學當作一種獨特的學科形態”來對待的宏大學術構想。
二、當代歷史文學審美格局的學理化考辨
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環境中闡釋歷史文學創作,存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從當代文學的全局出發,應該如何判斷和闡述歷史文學在整個文學格局中的獨特價值,二是在當代歷史文學內部,應該如何理解不同審美和觀念形態的作品。對前一方面的問題,吳秀明的專著《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建構起了一條有理有據的闡釋思路,對后一方面的問題,吳秀明則在他主編的《當代歷史文學生產體制與歷史觀問題研究》和《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造與重構》兩部著作中,顯示了一個能形成學術新空間、生發研究新論題的視野與框架。《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主要以采用傳統現實主義方法創作的、古代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為研究對象,其學術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將歷史文學的意蘊探究與文化溯源融為一體。作者走出純粹的“審美場”,借鑒文化批評的理念,將歷史小說置于一定的“文化場”中來解讀,通過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及其所隱藏的文化權力關系,視點高遠地展現出了當代歷史文學的生態特征與意義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歷史文學在文化轉型語境中的演變軌跡與創作群體,并從文化立場、現代意識、題材熱點、主體精神、文體形態和另類寫作現象六個方面,系統地分析了歷史文學的審美生態;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劉斯奮、二月河、楊書案等歷史文學名家的創作為代表,分別對思想立場層面的歷史主義典型化、女性現實主義、歷史守成主義傾向和審美境界層面的文化意味、大眾化、散文化傾向等方面,探討了歷史文學審美境界建構的文化路徑及其價值底蘊。貫穿于全書的基本線索,則是對當代歷史文學現代性內涵的豐富發掘與充分肯定。這種從思想文化高度、以現代性為線索審視歷史文學創作的邏輯思路,既隱含著對當代歷史文學內涵特征的深刻認知,也是對歷史文學在整個當代文學格局中的意義和分量予以學術強化的具體表現,其中鮮明地體現出一種以當代文學為本位來探討和判斷歷史文學價值的學術邏輯。《當代歷史文學生產體制與歷史觀研究》和《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造與重構》最為重要的主編思路,則是從當代文化整體格局的高度著眼,來體察各類歷史題材創作的合理性、建構學術考察的視野與框架。“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客觀上存在古代歷史題材和現代革命歷史題材兩類社會背景、價值基礎都截然不同的創作。而且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歷史題材,在史實‘演義’的基礎上,都帶有思潮性質地出現了純虛構形態的‘新歷史文學’。而影像和網絡的出現,更給文學創作提供了包含著審美與文化新質的新型內容載體。”于是,這兩部學術著作也就將其全部納入學術考察的范圍,并以“歷史題材創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視野范圍內對當代文學尤其是近30年來客觀存在的多元復雜的歷史題材創作作出回應”。在《當代歷史文學生產體制與歷史觀研究》一書中,研究者致力于“對當代歷史文學的生產體制、在該體制下派生的創作實踐及表現形態,存在于創作實踐中的歷史觀問題進行全面考察”。《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造與重構》一書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分首先從文藝論爭中探討當代“歷史題材寫作規范的確立”,然后勾勒了傳統形態歷史小說、新歷史小說和革命歷史小說發展概況,剖析了其中的認知境界特征與世俗化、史詩化等審美文化傾向;后半部分則通過對歷史文學經典作品的文本解讀,具體闡述了當代歷史文學的審美建構與文學成就。相對于僅僅著眼于傳統形態創作的歷史文學研究,這兩部著作的學術視野既有對歷史文學研究框架與學術外延的拓展,又體現出一種排除歷史與文學觀念高下之分、以“歷史”為本位的思想邏輯與文化氣概,對于在相互比較中理解各類歷史題材的復雜情形與審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吳秀明對當代歷史文學從兩個基本方面所展開的學術考辨,實際上是從學理化的層面,既為將歷史文學納入當代文學意義格局“開辟了一條道”,又為全方位地審視當代文化格局中歷史文學的復雜情形“打開了一扇門”,其中所體現的,確實是一片“將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有機融合起來”的“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三、學術思維與學理境界的探求
總體看來,吳秀明歷史文學研究的學術思維與學理境界,體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視野和學術重心的選擇方面,吳秀明的研究表現出一種全局性視野與問題意識相結合的特征。吳秀明將“歷史文學”界定為與歷史具有“異質同構”關系的一種文學藝術形態,并以此作為全部研究的邏輯起點,這本身就是建立在對歷史世界與文學世界全面而透徹地理解的基礎之上。他建構歷史文學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探討歷史文學理論范疇的核心問題,研究課題的選擇也是基于對歷史文學創作與研究狀況的全局性把握。在選擇和分析各種具體論題的過程中,吳秀明同樣表現出一種以諳熟現實狀況為基礎的問題意識。論述社會主義新型歷史文學時,吳秀明著重分析了人民群眾描寫與歷史記載中民眾生活內容匱乏之間的矛盾;分析歷史文學的語言時,他又對“非常態歷史文學”的語言媒介特征進行了專門考察,這些都是發現和剖析歷史文學“真問題”所獲得的獨特學術內容。吳秀明還特別注意到“找到了‘根據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實現理性的超越”,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在深入探討具體論題的過程中如何繼續保持全局性視野的問題。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視野的問題意識,為吳秀明研究的學術分量與學科意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次,在學術資源和理論依據的尋找方面,吳秀明的研究表現出一種知識體系前沿性與人文意識真切性相結合的特征。吳秀明的歷史文學研究,存在著1980年代后期的理論新思潮與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兩個重要的時代背景。吳秀明進行歷史文學理論研究正值20世紀1980年代中后期那“觀念論”“方法論”風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傳統的社會學、美學、哲學、史學批評方法的同時,也廣泛地借鑒了心理學、文化學、符號學、結構主義、發生認識論、闡釋學、接受美學、系統論等文藝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來作為論證的邏輯和體系的基礎,從而充分表現出跨學科的知識視野和多角度的思維邏輯。但饒有意味的是,吳秀明也高度重視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生命形態的人文性、創造性特征。當代歷史文學研究本就以審美創造為研究對象,關注文本的人文內涵和作家的創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歷史文學理論研究的過程中,吳秀明也時時表現出對于文學作為人類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歷史的詩學》一書中,吳秀明對歷史文學審美創造的邏輯歸結點,就是“藝術創造與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對歷史文學審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將“文體形式與生命形式的構造”聯系起來進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學術問題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為闡釋規律和指導實踐的本源性依據,使得吳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學層面本體論的思想維度。再次,在學術內涵與意義指向的探求方面,吳秀明的研究表現出規律論與方法論、理論體系建構與實踐指導訴求的統一。建構歷史文學理論體系、探究歷史文學規律與規范的學術意圖,在吳秀明的相關論著中顯而易見。他同時又認為:“學術研究當然不能太功利,對‘有用’作片面狹隘的理解,但它確實也有個價值論和當代性的問題”,因而注重“所提出的問題,來自實踐而又反作用于實踐”“對中國文學文化建設是有現實意義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堅持用前沿學術理論來推演歷史文學個性、探究歷史文學規律,又注重將研究思路切入歷史文學的內在肌理與操作規程之中,甚至注重為創作與批評提供切實可行的運作套路。《真實的構造》一書的前四章,分別存在以“超歷史性的深層規約”“文藝創作對歷史事實的正確取向”“主體自我顯現的方式與途徑”“前在經驗對創造心理的影響”為標題的小節,實踐指導意義在其中就顯得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