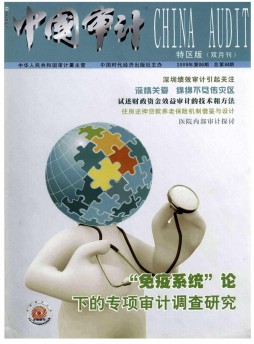中國教育史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中國教育史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引言
語言的學習始終脫離不了文化的學習,在外語教學中逐步滲透文化教育早已在外語教學界達成共識。然而,很長時間以來,外語教學工作者們都將大量的精力放在對目的語文化的輸入上,而對本國文化的輸出重視程度不夠,文化教學偏離了有效運行的軌道,從而導致了大部分學生語言功底與文化素養不成正比,不能很好地用外語表達我們本民族的文化。中國文化教育缺失現象在我國高校法語教學中也普遍存在。中國文化知識的嚴重匱乏直接導致了我們的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低下,進而大大降低了法語教學效率,因此,在推進法語教學的同時加強中國文化教育勢在必行、刻不容緩。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面針對我國高校法語教學中存在的中國文化教育缺失現象進行全方位的探討與剖析:我國高校法語教學中中國文化教育現狀及成因,在法語教學中加強中國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徑。
一、我國高校法語教學中中國文化教育現狀
“文化教育”這一概念在外語教學者眼中并不陌生,外語教學不僅是語言教學同時還是文化教學,在語言教學過程中不斷滲透文化教學早已在外語教學界達成共識。早在1997年,賈玉新便在他的作品《跨文化交際學》中提出“語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文化教育”〔1〕,隨后,胡文仲也在其1999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際概論》中指出“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文化的載體,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密不可分”〔2〕。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起,隨著交際外語教學法的不斷推廣,我國外語教學也開始逐步重視“目的語文化”導入在外語教學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外語教學開始大量引入國外原版教材,課堂上大量介紹國外的文化習俗,這種將語言教學與目的語文化教學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教學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學生在學習外語的同時還能夠了解對方的文化,這不僅拓寬了他們的視野,也大大激發了他們的學習熱情。然而,這種教學模式培養出的學生大多都存在一個通病:由于母語文化教育的長期缺失,直接導致了他們對母語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從而大大削弱了用外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清華大學的張為民等學者曾經針對這一現象做過相關調查,他們召集了一批英語專業本科生及非英語專業本科生,分別對他們進行了用英語轉述中國文化特色話題的測試,內容囊括了中國獨有的事物、名勝古跡、民俗等,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試者都不能很好地用外語表達我國固有的傳統文化。這一現象在法語學生身上同樣普遍存在,很多學生甚至都不能用法語很好地翻譯諸如“端午節”、“中秋節”等中國傳統節日,更別說翻譯中國原汁原味的詩詞歌賦了。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我國高校法語教學確實存在中國文化教育缺失的現象,并且已經開始嚴重影響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的提升。
談到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是寥寥幾句便可解釋清楚的,可以說它是多方因素長期綜合作用的結果,總結起來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教師自身中國文化素養亟待提高;其次,教師教學觀念與跨文化交際理念脫軌,長期忽視中國文化教育;最后,學校并未開設中國文化相關課程以及教材中中國元素的缺乏。但究其根本原因,還要歸咎于我國高校法語教學界對文化教育中“文化”的概念理解片面,過度重視目的語文化輸入而忽略本國文化輸出,模糊了外語教學的根本目的----培養跨文化交際人才。 “文化教學”不僅包括法國文化教學還包括本國文化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應該時刻秉承兩者并重的原則,才能夠培養出各方面都合格的高水平法語人才。 “對外國文化的理解必須把該文化放在與本民族文化的對比中進行,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切入包含著對目標語及母語的再認識。”〔3〕美國語言學家Claire Kramsch如是說到。
二、加強我國高校法語教學中中國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經過第一部分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化教育對法語教學成效的作用不容小覷,因此,將法語教學與中國文化教育有效地結合起來勢在必行,本文將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闡述加強我國高校法語教學中中國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強中國文化教育是跨文化交際的需要。人類學家、社會語言學家Hymnes將人類在恰當的場合得體地使用語言的能力定義為“交際能力”,而隨著全球化的趨勢愈演愈烈,跨文化交際也成了人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題。然而,“跨文化交際是雙方的交流,而不是單方面向一方面學習。”〔4〕任何一門外語的學習的最終目的都在于文化的吸收與傳播,學習者在目的語文化與母語文化間建立一個橋梁,能讓兩國人民順暢地進行文化交流,這才是法語教學的根本目的所在,即通過教師的不斷引導逐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與跨文化交際意識,從而培養出能夠促進中法友誼高效持久發展的跨文化交際人才。然而,在教學過程中長期忽視中國文化教育勢必將會大大阻礙這一目的的達成,因此,彌補我國高校法語教學中中國文化教育的缺失刻不容緩。
第二,中國文化在法語學習中具有正遷移作用。“在外語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會無意識地將母語的語音、詞匯、語法結構、思維方式、文化內涵等移植到外語的學習中去,這個過程就叫做語言遷移。”〔5〕總體來說,語言遷移分為兩種:正遷移與負遷移。很長時間以來,外語教學界都將過多的目光轉向了中國文化對外語學習的負遷移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正遷移作用。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文化在外語學習中所起的正遷移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如果能夠將中國文化與法語教學有效結合起來,將大大提升法語教學效率,正如劉潤清所指出的:“學習外語時,完全脫離母語是不可能的。語言之間有些普遍現象,不參考母語,不與母語對比,會造成莫大損失。”〔6〕從邏輯角度上來講,兩門語言相似度越高,正遷移作用也會越大。雖然漢語與法語分屬于不同語系,從表面上看有很多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世界上任何語言在結構上都是相通的,就比如法語中的???Aide-toi, le ciel t`aidera.??與中文里“自助者天助”便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只要將中文及中國文化與法語及法國文化的共性之處好好加以利用,便能夠促進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加快他們學習法語的速度,從而大大提升教學效率。
三、彌補我國高校法語教學中中國文化教育缺失的途徑
在國際交流中,我們要實現的是雙邊交流,我們雖然使用的是法語,但代表的是中國文化,而非法國文化,因此在法語教學中加強中國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是跨文化交際的需要,是培養學生辯證的文化意識的需要,使學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時,更加深刻地領悟絢麗多彩的、優秀的中國文化。〔7〕”而要扭轉這一局勢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也不是只靠一方面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而是要在多方的長期努力下才能夠逐漸消除的。在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三方參與者便是教師、學生、教材。筆者認為要彌補我國高校法語教學中中國文化教育缺失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教??的正確引導。作為教學的主力軍,教師能夠提供正確的引導自然是促成局勢扭轉的關鍵。當然,這里所說的“正確的引導”必須建立在以下兩個前提基礎上:首先,教師必須提高自身的中國文化素養;同時,教師必須轉變傳統的教學觀念,使其與跨文化交際需要緊密接軌。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從各個方面努力對學生進行文化滲透:既要使他們了解法國文化,又不能忽略到我們本民族的文化,使他們能夠順暢地用法語將我們的文化輸出出去,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交流。要做到這一點,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方法上多下點功夫,筆者認為主要可以用到以下兩種方法:
1.比較法
在教學中,教師應該積極引導學生通過比較去發現兩種文化的異同,逐步引導他們養成從一種文化引申到另一種文化的學習習慣。比如,從詞匯角度上來講,詞匯是構成一門語言最基本的單位,但也是一國文化最基本的載體,同一個詞匯在兩種文化里所代表的內涵可能會大相徑庭,這里就需要教師引導學生去發現,去探索,從一個詞引申到它在兩種語言中所代表的相似的或不同的文化內涵。以顏色為例,中國人偏愛紅色,自古以來,紅色在中國文化里象征著吉祥、喜慶,同時由于歷史原因的影響,紅色還能夠使我們聯想到革命,“紅心”可以指“對黨的忠誠”,而在法語中 le coeur rouge 也有這一層含義。再舉個例子,在講到動物的詞匯時,比較法便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了,因為在中法兩種文化中某些動物所代表的文化內涵是截然不同的,如 chien(狗) ,在漢語里“狗”經常會跟很多貶義的成語聯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而在法國狗與人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法語中很少能找到諸如此類的表達。再比如,俗語諺語是最能夠體現兩種文化的異同的,漢語里有“滄海一粟”,法語里也有 C`est une goutte d`eau dans la mer. ,但是在中國我們經常會說“茶余飯后”,而法國人則會說 entre le poire et le fromage (在梨與奶酪之間),因為法國人沒有喝茶的習慣,他們一般在下午茶時間都會吃點水果點心之類的食物,這就跟中國很不一樣了。
2.聯想法
在教學中,我們經常能碰到一些課文,里面的內容或背景會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一些東西,這個時候教師就要積極發揮自身的作用引導學生從一種文化聯想到另一種文化。比如北外馬曉宏編寫的《法語1(修訂本)》第15課談到法國人的飲食習慣,教師在講解這篇課文時,就可以引導學生聯想到中國的飲食,如“四大菜系”以及中國人的飲食習慣,甚至可以在下節課讓學生分組做演講用法語介紹我們中國人的飲食。再比如《法語3》第二課里面講到了上帝第六天創造了人,這里就可以聯想到我們中國的女媧造人、盤古變人的故事,同樣的也可以組織學生用法語去講述這些故事。通過這種方法,就能使學生在學習法國文化的同時還能夠加深對我們母語文化的了解,同時還能夠很好地提高他們用法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
(二)調整教材內容,注重融入中國文化,使目的語文化輸入與母語文化輸出達到平衡。大部分的教學活動都是圍繞著教材展開的,因此教材在教學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綜觀我國高校法語專業學生現階段所使用的教材,都過度傾斜法國文化的輸入,涉及到中國文化的內容少之又少,這不僅給學生傳達了錯誤的訊息,誤導他們認為學習外語就不需要學習中國文化,而且也讓學生學不到如何用法語表達中國文化,導致他們這方面能力低下。這就提醒我們,要彌補教學中中國文化教育的缺失,就必須進行教材改革,在教材中注重融入中國文化,增加介紹中國文化的法語文章,使學生在課文中就能學到表示中國特色事物、風俗等的法語詞匯、表達等,從而提高他們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當然,在現階段教材體系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教師可以自行選用一些替代教材,比如可以開設中國文化的相關課程,選用一些介紹中國文化的中文書籍作為教材,在課堂上積極組織學生展開如何用法語將我們自己的文化表達出來的討論,這樣也是可以的。
第三,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文化價值觀,增強跨文化交際意識。王宗炎曾經說過:“對自己的文化、語言和人家的文化、語言該怎么看待,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強國或強大民族傾向于自高自大,認為人家什么東西都不如自己,這是民族中心主義;弱國或弱小民族自卑,認為人家什么東西都比自己好,這是懼外心理。”〔8〕當前的中國已經不需要一味地去迎合他國文化,而更多需要的是盡可能輸出本土文化,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友人渴望學習了解我們中國的文化,我們的法語教學應該牢牢抓住這個契機,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文化價值觀,建立文化自信,鼓勵他們將禮義廉恥、仁愛禮讓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出去,在跨文化交際中始終保持自尊、自強。
第2篇
論文摘要: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當為蔣黼于1905年撰寫的《中國教育史資料》,而非通常認為的是“黃紹箕草創、柳詒徵輯補”完成于1910年的《中國教育史》,故此,中國教育史學科誕生的年限將由1910年提前到1905年。論文對《中國教育史資料》的作者蔣黼的生平圍繞其教育事業作了簡介,并析明《中國教育史資料》非翻譯而是原創著作,繼而對《中國教育史資料》的版本、內容作了介紹,并認為蔣黼與好友羅振玉共事于晚清時期的教育事業十數年,其《中國教育史資料》的內容受羅振玉有關中國教育史論文的影響至深。
教育史學界一般認為,由“黃紹箕草創、柳治微輯補”完成于1910年的《中國教育史》為我國學者自己撰寫的第一部本國教育史專著。如杜成憲等編寫的《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中即認為:“中國教育史學科的誕生有兩個標志:一是學校中開設中國教育史課程。1904年,清政府頒布并實施了‘癸卯學制’,規定經學科大學堂和師范學堂的教育類課程中,均設有中國教育史課程。二是有了對中國教育歷史的專門研究,主要是有了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中國教育史著作。中國第一本教育史著作是由‘黃紹箕草創、柳治微輯補’,起撰于20世紀初、完成于1910年的《中國教育史》。類似的研究,忽略了蔣黼于1905年連載于《教育世界》雜志上的10卷本《中國教育史資料》。該書后收人《教育叢書·五集》,并有教育世界社單行本行世。筆者認為,蔣氏《中國教育史資料》乃是由我國學者自主撰寫的第一部本國教育史,早于黃、柳合著的《中國教育史》5年。由于是首部,影響中國教育史學創立的起點年限的界定,且該本各大圖書館較少收藏,甚為稀見,本文對之進行簡單的介紹。
一
《中國教育史資料》的作者蔣黼(1866-1911),字伯斧,吳縣人,金石學家蔣清朔(字敬臣,著有《緯學源流興廢考》三卷、《洪遵泉志集證》十五卷、《選泉叢說》四卷,曾注《王子安集》)之子,與晚清著名教育家羅振玉相交好,羅氏之孫羅繼祖教授在《庭聞憶略》記載其事甚詳:“祖父和蔣先生訂交也較早,蔣先生初字覷康,后改伯斧,在上述諸人中,祖父和蔣先生的蹤跡最密。并提及羅振玉曾為蔣黼撰《墓志銘》,記述相交經過及評價曰:“予交君垂二十年,出處與共,方在淮安寓居,過從無虛日,在上海居比舍,日數見,當時賢達以人才詢予者,必首舉君以應。故予客粵中、客吳下皆與君偕,出則連較,居則接席。及君來京師,住于吾家者半歲。羅振玉給蔣黼寫《墓志銘》時在之后,其時羅氏已甚不愿再提及自己以及同僚好友諸如蔣黼于教育界的貢獻。事實上,蔣黼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且其行跡多與教育有關。1896年,蔣黼協助羅振玉創辦了農學會,作為該會的骨干,于1897年參與創辦了《農學報》,出刊至1904年末,1898年至1900年,以農學會名義參與創辦了南洋公學東文學社,培養出了諸如王國維、樊炳清(字少泉、抗甫,古文家、商務印書館編輯)、沈絨(字伯聽,翻譯家、巴黎大學法學博士)、薩端(字均坡,翻譯家、革命者)、朱錫梁(字梁任,南社詩人、東南大學教授)等一批人才。1901年,羅振玉創辦教育世界社,編譯出版教科書及我國最早的教育類雜志《教育世界》(刊至1907年末),蔣黼參與其事,且分期刊登《中國教育史資料》于其上。1904年與羅振玉等任職于兩廣學務處,參與興辦學堂等事宜。1905年至1906年,與羅振玉、王國維、樊炳清等任職于江蘇師范學堂。1906年后,任職于晚清學部,與羅振玉同為四品咨議官,后擔任京師大學堂教習,至1911年病卒。這樣一位深度參與教育活動的學者,蔣黼起意撰寫《中國教育史資料》便在情理之中。至于其著述,羅繼祖說“著作都未能成書”,現只知在敦煌學方面與羅振玉合輯的《敦煌石室遺書》,內收蔣黼輯《沙洲文錄》、《老子化胡經(殘卷)》等,此外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等論文以及一些跋文。羅繼祖教授因資料所限,所敘蔣氏著述頗有遺漏,據筆者調查,蔣黼名下論著尚有數種:據羅振玉在《國粹報》所言,他還有《中國貨幣史》(乃中國第一部貨幣專史,見金品元《歷代錢譜目錄》著錄)等著作。他有關教育學的著述,除《中國教育史資料》之外,有考察日本教育的筆記《東游日記》,另據筆者在國家圖書館查《蟬隱廬新板書目》尚有《蒙學修身書》署蔣黼編撰,《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總第69號)上載有《修身教科書編篡略》,與《蒙學讀本編篡略》一起只署“兩廣學務處稿”,應為其所撰寫,《蒙學讀本》未署名,疑亦為其所撰。另蔣黼在學部任職時,曾在學部圖書局出版《中國教育史》,時間當在1908年左右,亦早于黃、柳合著的《中國教育史》,該本僅見著錄,依理而推,或為《中國教育史資料》同書異名之作,或為其修訂版,總之與《中國教育史資料》不無關系。
二
在已知的蔣黼署名或者未署名的教育類著作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當屬10卷本的《中國教育史資料》了,因其成書于1905年,堪稱“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但最近出版的紀念柳治微的紀念文集中有論文,否認蔣著《中國教育史資料》為“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而認為完成于1910年“黃紹箕草創、柳治微輯補”的《中國教育史》才是“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理由是:《教育世界》上的大多數篇目為譯稿,依次類推,刊登其上的《中國教育史資料》亦為翻譯之作,譯自日本,而不是原創的中國教育史著作。至此認為《中國教育史》本系原創,故為第一。那么,《中國教育史資料》是不是有日本原著在的二手的譯本呢?經筆者仔細查閱《教育世界》及《中國教育史資料》,認為:第一,《教育世界》雜志上多有譯篇,尤其在1901年至1903年所謂“前期《教育世界))’’,但并不能以偏概全以印象代替事實而認為《中國教育史資料》是譯稿。其次,《中國教育史資料》連載于1905年,屬“后期《教育世界滬,其時編譯者比較集中,僅羅振玉、蔣黼、王國維、樊炳清、羅振常等數人,且經多年編輯雜志,《教育世界》雜志上篇目署名的處理還是比較規范,至少有規律可循,即:如果是譯本或者節譯本,不在題下和目錄署原著者及譯者,就附《譯者識》或《編者識》之類注明;如果是有原著可依的改寫本,則不署名;如果僅署中國學者之名的篇目,則一概為其著作而非譯本。以上三種署名的處理情況,例子甚多,恕不舉例,讀者一覽1904年至1907年的近100期《教育世界》雜志便知。《中國教育史資料》題下署“吳縣蔣黼”,與《紅樓夢評論》題下署“海寧王國維”同,又《總目》之《中國教育史資料》署“蔣黼撰”,同目《論近年之學術界》等署“以上王國維撰”,而《叔本華之思索篇》則署“譯稿”,整傷如此,可證《中國教育史資料》乃蔣黼所撰而非譯稿。第三,從《中國教育史資料》中的一些用詞,比如“中國”、“我國”、“國朝”等來看,《教育世界》雜志上的譯本中一律保持日文原樣為“支那”等字樣,故《中國教育史資料》非譯稿。再者,蔣黼通不通日文,有無能力進行翻譯還是個問題。當然,從邏輯上講,日本早于國人捷足先登著有中國教育史之類的著作,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蔣黼,蔣黼在多大程度上依之進行改寫、資料的搜集等等都是可以存議的;雖然筆者手中并無相應日文中國教育史之類的著作可供參照,但經仔細閱讀《中國教育史資料》,從其內容、體例、行文,以及它與羅振玉相關教育史論文的關系(下詳)等方面來看,實非翻譯之作。
三
《中國教育史資料》與現在通行的章節編排不同,而是分成十卷,連載于《教育世界》雜志1905年第15至22期,總第107至114號,連載時間農歷為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上旬至十一月下旬,相應公歷時間為1905年9月至12月,其時蔣黼任職于江蘇師范學堂,該學堂開設教育史課程,蔣黼是否講授中國教育史課程,((中國教育史資料》是否為學堂講義,由于資料匾乏,我們不得而知,但與之有關則可推想而知。《中國教育史資料》發表于“教育史”欄目,此前《教育世界》雜志并無此欄目,看來是為蔣黼的這個著作特開辟的一個欄目,也說明“中國教育史資料”與“中國教育史”相比多出“資料”二字,實是被當作不打折扣的“教育史”看待的,前述蔣黼有學部圖書局版《中國教育史》亦可佐證。筆者所讀《中國教育史資料》為《教育叢書·五集》中所輯,頁眉署“教育史”字樣。事實上,《教育叢書·五集》乃《教育世界》雜志第五年即1905年全年的分類匯編,《中國教育史資料》因篇幅較大單獨成冊,頁碼內側亦保留諸如“第十五期七十一”等字樣,即叢書本與原刊雜志版一樣,內容一般無二。又據((教育世界》雜志所附《本社(教育世界社)編譯及經售書目》及《蟬隱廬新板書目》所載,《中國教育史資料》另有單行本行世。
《中國教育史資料》以典雅的文言書寫,如前所說全書10卷,146頁,豎排,每頁13列,每列不計空格33字,書中多有列表,全書計約6萬字。書中認為:“中國教育之興,距今四五千年前,為世界開化最早之國。’,但其時因文獻匾乏,“記載簡略,其詳不可得聞”,故“今言中國教育,斷自周始”。盡管認為從邏輯上講,中國教育史可分為三個階段:“自周至今,中國教育約可分為三大時期。周之時,學校偏于鄉里,人民莫不就學,是為‘學校時期’;漢重鄉舉里選,學校雖立,不過選舉中之一途,魏晉及南北朝皆因仍漢法,是為‘選舉時期’;隋唐以后,專重考試,而選舉之制廢,歷千年以至于今,雖考試之法不同,然大校無甚變易,學校之設不過科舉中之一階級耳,是為‘科舉時期’。‘學校時期’考實行,‘選舉時期’采名譽,‘科舉時期’重文詞,此中國教育沿革之概略也。’,但全書分卷沒有按邏輯順序,而是大致以歷史朝代為斷:卷一為《緒論》與《周》,卷二《秦》,依次為《漢》、《三國至隋》、《唐》、《宋》、《遼金元》、《明》、《國朝》,至卷九,卷十為附錄《歷代之藏書》,為便于了解《中國教育史資料》體例、內容,特列表說明如下:
第3篇
[關鍵詞]:文化與人格理論 中國國民性 儒家思想
所謂國民性,指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總體表現出的品性,即一個國家國民最普遍表現出的人格類型,是對一國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針對正常人格而言。這種品性,既源于種族特征的不同,也可來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各個國家中不同的國民性。國民性與典型人格類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調查實踐與復雜數據,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籠統性,故較易實行。
對國民性問題的研究在西方二戰時期曾一度興起。由于全球化的影響以及西方文化的滲入,現代中國的國民性已變得較為混雜難以表述,甚至某些已與中國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馳,西學的傳入與過度應用更使現代中國國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國本土的代表性。本文僅從中國古代儒學角度對中國人的傳統國民性進行分析探討,從信仰體制、道德準則和人格培養三方面將國民性概括為忠君愛國、仁義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體制:忠孝統一
從信仰體制上看,中國古代社會中主要以信仰中國傳統宗法性宗教作為全民性的國家宗教。其宗法觀念與天人合一觀念從信仰層面進入到社會生活中各個方面,對國民性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
中國人普遍重視家族觀念,祖先意識強烈。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不僅體現在中國人祭祖的隆重儀式上,更表現在中國人“以孝治天下”的觀念上,這早在先帝舜時期就有了很好的體現。
中國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現孝子,則會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注與贊揚。漢朝時期的選官制度就以“孝”作為最基本的選拔標準,由眾人推舉,稱“舉孝廉”。中國儒家傳統“十三經”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經典――《孝經》,是關于孝的理論的集大成者。
在中國人家族傳統中,是以父權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親請教過問,包括婚姻問題,大多是父母包辦,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請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進行,否則就會有被社會指為不孝而被邊緣化的危險。
中國人如此重“孝”,包括統治者也宣揚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與維護。中國人認為,以孝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會歸順于君主,孝是忠孝仁愛信義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也。”《論語》中的此言正是體現了“孝”的一系列好處,孝子極少有犯上作亂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見“孝”是忠君愛國思想的前提。這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忠孝二者相統一的觀念,也是國民性之一大特點。
二、道德準則:仁義之上
前面討論的中國人所重視的忠孝觀念,但這種忠孝觀念是以仁義的道德準則為前提的。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就曾說過,忠孝都要“以義為先”。不符君子道義的事萬萬不可做,而這道義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仁”的實現是孔子認為最理想的社會狀態。“仁”是最重要的品格,萬事都應符合“仁”復歸于“仁”。“義”則由“仁”衍生而來。所謂仁義禮智信都是以“仁”為根本的。孔子主張回歸“仁”的道路是“克己復禮”,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回到禮的道路上來。西周時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禮是與封建等級制度相應的。“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儒家主張以禮治天下,這其中就要以統治者實行“仁政”作為基礎。實行仁政,人民就會溫順并且厚道,像先帝堯舜時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應以仁為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家主張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仁義道德理念。孔子認為,“恭而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這樣即可實現仁。仁不僅應作為社會的基本原則和統治者的根本統治手段,更是作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準則的基礎。
孔子還認為,“剛毅木訥,近仁。”這可謂是對接近仁的狀態的外在表現的較為細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國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國人普遍具有老實內斂,逢人不愛張揚,遇事不愛爭搶的特征,卻給人一種溫和敦厚的親近感。古代社會中的中國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鴻銘先生認為中國人精神的最大特點就是溫良,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響的結果,這也是“仁”在國民性格中的一大體現。
三、人格培養:中庸之道
中國古代社會中對人才的培養,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視專業技能培養,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氣節與道德觀念的樹立。中國古代社會中儒家思想幾乎是持續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對“君子”的推崇也成為中國社會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標準。
所謂君子,可用“中庸”來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經過歷史發展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氣節,體現在忠君愛國的觀念中。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可見中庸的品質在中國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質的概括,并形成一種價值趨向體現在中國人的國民性中。用孟子的話概括,這是一種“浩然正氣”。
中國古代注重對人才的培養,不僅體現在后來的教育中,也體現在在童蒙教育。所謂童蒙教育,指中國古代7~12歲的教育,即灑掃應對等基本禮儀和倫理道德的學習。其作用不可忽視,是為后期儒家系統教育、為日后學習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礎,是中國古代社會人格氣質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環。
中庸之道同樣表現在禮上。儒家主張以禮治天下,禮節是人與人之間交往乃至統治者治國平天下的核心原則。它處處體現了中國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觀念基礎上,體現了中國人高尚的修養,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種外在表現。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導的中國古代社會中,在文化與人格理論的視角下所探見的中國人國民性具有忠孝統一、仁義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僅體現在傳統的等級宗法性制度中,更體現在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普遍文化群體中。中國人特有的文化與品格特征,區別于西方,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包括政治思想、社會制度以及豐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們更應弘揚這種文化特性,弘揚中庸之道,選擇傳統并適合我們國民性的東西,而不是盲目學習西方的科技、制度,這有中體西用,才能使中國人得以重新閃耀于世界之林。
參考文獻:
[1]林耀華.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辜鴻銘著.李晨曦譯.中國人的精神.上海三聯書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