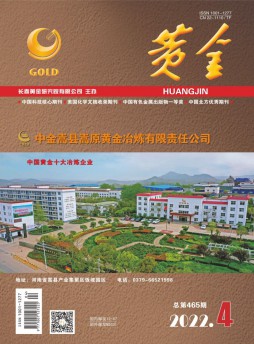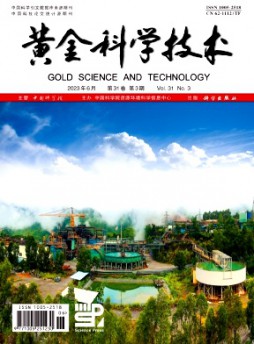黃金法則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黃金法則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9-0134-01
一、媚俗文化的內涵
媚俗是當代審美文化轉型時期所產生的一種負現象,也是一種典型的偽審美現象,或者說,是傳統美學在無法正確回應當代審美文化的挑戰時所出現的一種特定的畸形審美形態。媚俗(kitsch),臺灣學者譯為“忌屎”,對此頗有研究的昆德拉解釋云:“對(kitsch) 的需要,是這樣一種需要,即需要凝視美麗的謊言的鏡子,對某人自己的映像流下心滿意足的淚水”這種解釋雖然有一定的比喻性在其中,但仔細咀嚼著句話,我們就會發現媚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種為他人的表演性,換言之,則只要為他人活著,為他人所左右,并且為他人而表演,其生存就是媚俗的。如果用馬克思的異化觀來解釋,那媚俗文化也是一種異化,因為它表現為一種為他性的個性淪喪和個性消逝的寄主生存,生存的目的僅僅是表演,那生存的價值則為異化的存在。
關于媚俗的產生,昆德拉把它概括為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主觀態度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心里什么都十分清楚,但為了名利、地位、金錢、物質生活而主動放棄對于美得追求,趨炎附勢,以美娛人。另一種情況是外界壓力過于強大:公眾的、朋友的、親屬的、愛人的、情人的多種眼光的結合,使自己承受不了,只好與之妥協。而客觀環境,昆德拉語焉不詳,但我們可以猜想,之所以出現媚俗文化,是因為客觀環境勢不可擋的力量,特別是當代商品經濟對審美文化的沖擊,媚俗文化成為一種潛在的逆歷史規律的正常的現象。總之,媚俗文化是誤以娛樂為審美。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媚俗文化的根本內涵就是從需要回到欲望。而對于欲望,叔本華曾經做過剖析:在他匱乏的時候,使人陷入痛苦;在他滿足的時候,使人陷入無聊。面對欲望,人只能如鐘擺流動與其中,也就是人的軌跡只能是中雙向的無奈的循環,從匱乏到滿足的無聊,從滿足到匱乏的痛苦。如果具體到媚俗方面,那也只是體現了一種無奈的循環:從取悅到娛樂的低俗,從娛樂到取悅的平庸,這也正是媚俗文化的全部理論所在,即取悅,娛樂。
二、基督教“黃金法則”
對于什么是“黃金法則”,也許有許多人并不知曉,但我們可以援引《圣經?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節中耶穌的話:“無論何事,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基督教中的“黃金法則”,我們可以聯系其他的比較流行的說法來對此法則進行詮釋,即“像你期望別人對待你的方式對待別人“或”怎樣被對待就怎樣對待人”,如果聯系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黃金法則”,那應該首選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我們既然弄清了‘黃金法則’的內涵,那這條法則起源于何時呢?我們經過考察證實黃金法則以近似于耶穌基督之言的形式存在的時間遠遠早于耶穌的時代,也就是說它較早的時候以它的內容形式存在于口頭文學中,代代相傳成為人們交際的一條法則和標準。十七世紀人們把《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節和《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一節的論述稱之為“黃金法則”或“金律”。這一術語才得到廣泛使用,但其起源并不清楚。而且這條法則是非常具有伸縮性的術語,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并且在眾多文化體系中存在。例:羅伯特?恩斯特?休姆在《世界上活著的宗教》一書中引用了八個宗教和哲學系統中的黃金法則,認為它們旨在“吩咐一個人作這樣一個簡單的實驗,即他是否愿意將他對待別人的方法加諸于他自己”事實上,“黃金法則”根本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名言或是箴句,其中的“黃金”我們就可以認識到這條法則的崇高地位。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黃金法則”它被稱為一種原則,一種行為的原則,一種一般性原則,一種人類關系的普遍性原則,理性倫理的最高法則,一種重要的道德真理等等。無疑這條法則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指導性和實用性,但最關鍵的問題是:這條法則與哪些文化的結合,才會發揮其最大的作用。
三、媚俗文化對基督教“黃金法則”的消解
當大家看到我寫下這篇論文的標題時,許多人肯定會一頭霧水,你們肯定會想這是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怎么可以牽扯到一塊,更何談消解,記得有位詩人曾說過:“沒有孤立的孤島”,也就是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兩種互不聯系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在其表象或本質上進行著微妙的聯系,只不過某些聯系我們難以考察到罷了,雖然媚俗文化是當下社會中審美文化的一種負現象,是一種文化的樣態,而“黃金法則”則是一條至高無上的人際關系準則,這兩者聽起來沒有任何瓜葛,但媚俗文化對“黃金法則”的沖擊和消解會逐漸被我們注意到,以下就是我談到的兩點具體表現。
(一)畸形的取悅導致“互惠”的消亡
我們在前面論述媚俗文化的時候提到,媚俗文化就是一種完全喪失個性的畸形取悅,雖然這其中也有“利他主義”其中,但它并不是“利他主義”的本質,也沒有體現我們現在所提倡的和諧和互惠,而基督教的“黃金法則”,從本質而言是一種互惠的體現,即如《馬太福音》中提到的“你要盡心,盡性和盡意去愛你的主人,這是誡命中的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第二條也相仿,就是愛鄰如愛己”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那么上帝的圣光會降臨我們,會挽救我們于危難之中,這就是“于人于己都是利”的互惠,而在當下商品經濟時代,物欲橫流,媚俗文化不斷登大雅之堂,不斷地沖擊和消解基督教“黃金法則”,許多人甚至許多基督徒都在實踐媚俗文化,而“黃金法則”不斷地降級成為“銀法則”“鐵法則”,或許某一天這條法則可能不復存在了。就以我們當下十分流下的女性媚俗文化來探討一下這二者之間的關系。當下以女性的方式向世人獻媚的可謂“碩果累累”,你看那俗不可耐的舞廳時裝表演,斑駁燈光下頹落得只是女性的尊嚴;你看那男女主角相攜上床的“經典電影”,搖曳中滴落的只是女性的朱紅;這樣的獻媚,這樣的媚俗文化,使得所謂的珍貴性,圣潔性,隱秘性就像秋后收獲后的麥田,空空無物。不僅犧牲了女性的尊嚴,也犧牲了大眾文化中的批判,也消解了基督教中的“黃金法則”,因為在當下所謂的“互惠”已經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某些不知名文化的空殼。那“黃金法則”的表述也許就可以換為另一種,即“無論何事,你們愿意人怎樣獻媚,你們也需要怎樣獻媚”。
(二)娛樂的消遣使愛成為挽歌
第2篇
關于優劣高下的質量判斷,是音樂經驗乃至所有藝術經驗中一個不可回避、卻又令人迷惑的中心課題。不可回避,在于藝術經驗從根本上說就是裁決性的――不能做出優劣區別,實際上就等于不懂藝術,如分不清勃拉姆斯交響曲和圣一桑交響曲之間的高下,那就沒有真正窺見交響曲的堂奧;令人迷惑,在于這種分別或區別從來就沒有統一標準――所謂“趣味無可爭辯”,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所謂“蘿卜青菜,各有所愛”。而肖邦輕視貝多芬、柴科夫斯基討厭勃拉姆斯等音樂史中頗為出名的“公案”,更增添了審美判斷的神秘性和暖昧性。
于是就產生了各種各樣似是而非的說法。位于極端的是“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相對主義”認為,審美尺度變動不居,因為審美主體因人而異,其間沒有形成共識的可能,而且,藝術中的尺度產生于各種不同的環境、條件、民族、傳統、常規、風格、慣例、時代,因而就不可能存在恒定不變的價值準繩。與之相反,“絕對主義”主張,藝術中存在某些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審美規律與法則,大的如變化與統一法則,小的如“對稱律”、“黃金分割律”等等,遵循這些審美法則和藝術規律是保證藝術質量的不二法門。
顯然,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各有各的問題。很容易找到違背它們各自原則的反例。如,盡管大家趣味各不相同,但我們都愿意承認,貝多芬是比同時代的克列門蒂(Clementi)更偉大的作曲家;又如,中國人傅聰能夠地道地演奏西方的鋼琴作品,美國人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可以內行地判斷中國唐詩,這都說明極端的“相對主義”站不住腳。反過來看,有些音樂如巴托克的優秀作品,其結構布局刻意遵循“黃金分割律”的比率,但更多的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并不遵守這些清規戒律,同樣具有高度的藝術感染力和擲地有聲的藝術質量,這說明,在藝術中想尋求一勞永逸的質量準繩其實是徒勞。
所以,藝術中的質量判斷就變得非常棘手。當然,可以小心翼翼地避免判斷――但那就等于背棄藝術。或者,聽任個人隨意的決斷――那就等于放棄責任。沒有標準是不可取的,但標準又是難以捉摸的。出路何在?一句耳熟能詳的說法是,“時間是最終的審判官”。讓我們將裁決權交給未來。可惜,與其說這是認真的回答,還不如說這是滑頭的托詞。
我想到英國大詩人兼批評家艾略特(T.s.Eliot)在其著名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有一段深刻的論述:“詩人,以及任何藝術家,誰也不能單獨具有完整的意義。他的重要性,以及我們對他的鑒賞,就是鑒賞他和已往詩人以及藝術家的關系。你不能僅就他進行單獨的評價,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中進行對照、比較。我認為這不僅是歷史的批評原則,也是審美的批評原則。他之必須適應,必須符合,并不是單方面的;一旦新的藝術作品產生,以前的全部藝術作品就同時遭逢了一個新事物。現存的藝術經典本身構成一個理想的秩序,這個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引入而發生變化。這個先在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現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事物以后要繼續保持完整,整個的秩序就必須發生改變,即使改變得很小;這樣,每件藝術作品之于整體的關系、比例和價值就重新被調整;這就是新與舊的適應。”(卞之琳譯文,筆者對照原文略作改動)
第3篇
古代文學論文論唐代的規范詩學
這里使用的“規范詩學”一語,來自于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中的一個定義。鮑里斯·托馬舍夫斯基(1890—1957)在《詩學的定義》一文中指出:“有一種研究文學作品的方法,它表現在規范詩學中。對現有的程序不作客觀描述,而是評價、判斷它們,并指出某些唯一合理的程序來,這就是規范詩學的任務。規范詩學以教導人們應該如何寫文學作品為目的。”① 之所以要借用這樣一個說法,是因為它能夠較為簡捷明確地表達我對唐代詩學中一個重要特征的把握。唐代詩學的核心就是詩格,所謂“詩格”,其范圍包括以“詩格”、“詩式”、“詩法”等命名的著作,其后由詩擴展到其他文類,而出現“文格”、“賦格”、“四六格”等書。清人沈濤《匏廬詩話·自序》指出:“詩話之作起于有宋,唐以前則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范、曰評,初不以話名也。”② 唐代的詩格(包括部分文格和賦格)雖然頗有散佚,但通考存佚之作,約有六十余種之多③。“格”的意思是法式、標準,所以詩格的含義也就是指做詩的規范。唐代詩格的寫作動機不外兩方面:一是以便應舉,二是以訓初學,總括起來,都是“以教導人們應該如何寫文學作品為目的”。因此,本文使用“規范詩學”一語來概括唐代詩學的特征。
一、“規范詩學”的形成軌跡
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者,對于隋唐五代一段的歷史地位有不同看法,比如郭紹虞先生名之曰“復古期”④,張健先生名之曰“中衰期”⑤,張少康、劉三富先生則名之曰“深入擴展期”⑥。言其“復古”,則以唐人詩學殊乏創新;謂之“中衰”,則以其略無起色;“深入擴展”云云,又混唐宋金元四朝而言。究竟隋唐五代約三百八十年(581—960)間的文學批評價值何在,地位如何,實有待從總體上予以說明并作出切實的分析。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也是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大轉折。在此之前,文學批評的重心是文學作品要“寫什么”,而到了唐代,就轉移到文學作品應該“怎么寫”。當然,從“寫什么”到“怎么寫”的轉變也并非跳躍式的一蹴而就。下面簡略勾勒一下這個轉變的軌跡。
文學規范的建立,與文學的自覺程度是一個緊密聯系的話題。關于什么是文學的自覺,依我看來,文學是一個多面體,無論認識到其哪一面,都可以說是某種程度上的自覺。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孟子認為說《詩》者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⑦,能說這是對文學 (以《詩》為代表)的特性無所自覺嗎?《漢書·藝文志》中專列“詩賦略”,這表明自劉向、歆父子到班固,都認識到詩賦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字著述的特征所在。但其重視的賦,應該具備“惻隱古詩之義”;至于歌詩的意義,也主要在“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一句話,他們重視的還是“寫什么 ”。從這個意義上看,曹丕《典論·論文》中“詩賦欲麗”的提出,實在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換,因為他所自覺到的文學,是其文學性的一面。不在于其中表現的內容是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方式來表現。“詩賦欲麗”的“欲”,假如與“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中的兩“宜”一“尚”聯系起來,表達的不僅是一種內在的要求,似乎也含有一種外在規范的意味。所以我認為,唐人“規范詩學”的源頭不妨追溯到這里。
唐以前最有代表性的文學理論著作,允推劉勰《文心雕龍》。《文心雕龍·總術》專講“文術”之重要,所謂“文術”,就是指作文的法則。其開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筆的區分是對作品文學性的進一步自覺,但劉勰并不完全認同這一提法,他認為這種區分于古無征,“自近代耳”。又對這一說的代表人物顏延之的意見加以批駁,最后說出自己的意見:“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為翰。”⑧ 口頭表述者為言,筆墨描述者為翰,這反映了劉勰對于文采的重視。“翰”指翠鳥的羽毛,晉以來常常被用以形容富有文采的作品,這是時代風尚。然而在劉勰看來,用筆墨描寫的也并非都堪稱作品,強弱優劣的關鍵即在“研術”。據《文心雕龍·序志》,其書的下篇乃“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于《時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涉及文學的創作、批評、歷史等諸多方面的理論。其中創作論部分,又涉及文學的想象、構思、辭采、剪裁、用典、聲律、煉字、對偶等命題,部分建立起文學的寫作規范,雖然還不免是籠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