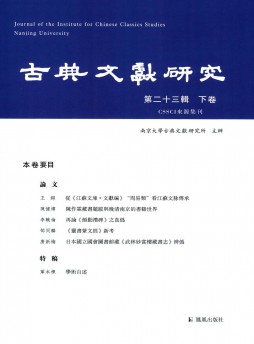古典主義文學的定義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古典主義文學的定義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司湯達;浪漫主義;古典主義;時代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10-0168-02
一、19世紀之后法國文壇上的爭議
(一)古典主義的沒落
法國的古典主義文學思潮形成于17世紀,對當時的法國文學和歐洲文學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當時看來是具有很大進步意義的。但是古典主義本質上也是一種封建貴族文學,在文學創作上很多方面都是迎合當時封建權貴的。但是經過兩個世紀之后,法國的政治、經濟、思想等諸方面已經有了很大變革,而此時的古典主義模仿者仍要求文學創作要遵守17世紀按照宮廷美學趣味制定的藝術規則,并以拉辛為武器,攻擊文學創作領域出現的創新變革。而與此同時,法國進步文學的力量也逐步成長起來,它們代表了資產階級新的美學觀點,向陳舊腐朽的古典主義美學的教條規則宣戰,莎士比亞經常被作為攻擊傳統美學的工具。19世紀20年代的法國文壇充斥了拉辛與莎士比亞、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爭論,新、舊兩種美學觀點的斗爭日益激烈化。
(二)新舊兩種文學理論之間的爭議迭起
《拉辛與莎士比亞》起因是英國劇團到巴黎上演莎士比亞受到阻撓,當時的古典主義者、保守勢力謾罵莎士比亞,引發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論戰。莎士比亞的戲劇因為觸犯了古典主義模仿者堅守的17世紀陳舊的美學信條而受到猛烈批判,司湯達的《拉辛與莎士比亞》正是為回應古典主義模仿者的進攻,推進進步文學而作。司湯達首先撰寫論文《為創作能使一八二三年的觀眾感興趣的悲劇,應該走拉辛的道路,還是莎士比亞的道路》,高度頌揚莎士比亞的戲劇,實際上司湯達以此表明了他反對把過時的古典主義教條奉為不變的準則,倡導與時代一致的進步文學的態度。當然他這部作品中提到的拉辛與莎士比亞并不是指這兩個具體的戲劇家,而是代表了新舊兩種美學觀念的對照。
我們可以通過對拉辛和莎士比亞的分析窺探到這兩種美學觀念的不同。首先,莎士比亞,基本上接觸過外國文學的人都對其耳熟能詳,英國文藝復興時的文壇巨豪,偉大的詩人、戲劇家,在文學史占據著崇高的地位。拉辛,17世紀法國古典主義杰出的作家,同樣以其古典悲劇在文學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但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直至今天仍是受人追捧的經典,而拉辛就沒有這么好的待遇。如果不讀法國文學的人很少會去讀拉辛的古典悲劇,就像我國莎士比亞的流傳度要遠高于拉辛,拉辛的流傳度并不怎么廣。提到拉辛,我們會覺得是非常久遠之前的作家,而莎士比亞卻不會給我們這種感覺,有時候甚至會有一種錯覺,覺得莎翁是近代的作家。其實拉辛(1639―1699)生活的時代要比莎士比亞(1564―1616)晚許多。之所以會有這種錯覺,是因為拉辛戲劇中典雅綺麗的風格、嚴格的三一律以及亞歷山大詩體讓我們覺得距離太遙遠;而相比之下,莎士比亞那種渾厚博大的風格中摻雜著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色彩反而會讓我們倍感親切。當然這并不代表莎士比亞一定比拉辛偉大許多,只是我們由此看出能夠切合時代的作品更容易時久不衰,古老而長青。
二、司湯達《拉辛與莎士比亞》所提出的文學理論
《拉辛與莎士比亞》這部作品中,司湯達提出的核心問題就是文藝與時代的關系,他倡導的文藝創作原則就是文藝不是一成不變的,文藝要適應時代的需要,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現實、反映時展需要在當今的文學界或許已經是被喊爛了的口號,但在當時卻是尚未取得統治地位的新的美學原則。
當時的古典主義模仿者宣傳法國的古典主義戲劇是現在、過去和將來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戲劇,固守古典主義的美學原則。而司湯達對古典主義模仿者的論調進行了深入批判,他論證了古典主義戲劇是迎合宮廷趣味的產物,已經脫離當下人們的審美趣味。首先司湯達從時代對文藝創作和欣賞的制約性闡述了他的論點。古典主義審美趣味是符合17世紀王朝興盛的時代的,但這并不是萬古不變的法則。審美觀點和文學藝術都是時代的產物,每個時代各有不同,既沒有永恒的審美趣味,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學。以此為基礎,司湯達闡明了他眼中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司湯達將一切符合時代的偉大作品都看作是“浪漫主義”的;而把一切機械模仿脫離時代的作品看作是“古典主義”的。《拉辛與莎士比亞》中關于浪漫主義藝術的定義是頗為獨特的:“浪漫主義是為人民提供文學作品的藝術。這種文學作品符合當前人民的習慣和信仰,所以它們可能給人民以最大的愉快。不同時代產生不同的意識形態。只有反映時代精神的文藝才可能產生最大的。”①因此,文藝必須適應時代需要,反映當代生活,隨時代的前進而不斷推陳出新。這一觀點貫穿全書,是司湯達文藝觀的理論基礎。
第2篇
關鍵詞:莎士比亞; 天才; 新古典主義; 康德
中圖分類號:I561.09;I109.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35
晚年伏爾泰常常攻擊莎士比亞,他指出,僅僅受本民族讀者歡迎的作者不可能是偉大的及規范的作者。與之相對應,他反復強調法蘭西的趣味――其代表是新古典主義,是歐洲趣味的核心,其他民族則只能對這種歐洲趣味作一些貢獻。法語在歐洲成為貴族的語言,這與新古典主義的影響是不無關系的。但是由于高度重視規則,重視語言的典雅,對于創作反映生活的廣泛性和自由度都帶來了很大的束縛,同時也對各國民族文學的形成造成了桎梏。在新古典主義者看來,莎士比亞是個野蠻人,但是在那些力圖要擺脫法國文學影響的人們看來,莎士比亞正是他們所需要的類型,這其中,英國人當然最先得益,其次便是德國,而圍繞莎士比亞的有關討論的最大成果,便是“天才”觀念的成熟。
一、 圍繞莎士比亞的爭論
卡西勒說:“18世紀英國文學每當討論到天才問題,每當它試圖規定天才與規則之間的關系的時候,抽象推理便立即轉到了具體事例。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碰到了兩個名字――莎士比亞和彌爾頓。可以說,他們構成固定的軸心,關于天才問題的一切理論研究便繞之旋轉。作家們都力圖通過這兩個偉人的范例去把握天才的最深刻的本質;可用以描述天才的一切可能的理論,都適用于莎士比亞和彌爾頓。”
在莎士比亞和彌爾頓這兩人中,也許莎士比亞要更接近于天才的本質。因為有關這位莎士比亞,就目前所知道的資料而言,他出生于鄉間小鎮,只受過有限的一些教育,20歲左右到倫敦謀生,在戲院看守馬匹和做些雜務,又作過演員,演了一些次要角色。由于在戲院工作,能有機會接觸戲劇表演,所以掌握了戲劇創作的一些程式,逐漸參與戲劇腳本的改編,很快就脫穎而出,名聲大噪。這樣一位成長背景的鄉間小子,卻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英國文學界最耀眼的明星,這種情況如此神奇,甚至引起諸多研究者的懷疑,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這位創作了那么多彪炳史冊的作品的莎士比亞?
按照托爾斯泰的研究,莎士比亞在他的那個時代并不受英國人待見:“在18世紀之前,莎士比亞在英國不但沒有特殊的聲望,他得到的評價還低于其他同時代的劇作家,如本瓊森、弗萊徹、鮑蒙特等人。這種聲望肇始于德國,再從那兒轉回英國。”這個看法比較偏頗,與托爾斯泰出于個人趣味或而討厭莎士比亞有關。在莎士比亞當時,的確有人出于嫉妒而攻擊過莎士比亞,稱他為“一只暴發戶烏鴉”,罵他是“地地道道的打雜工”,寫了幾句虛夸的無韻詩就自以為能同最優秀的作家媲美。但這些只證明了莎士比亞的影響之深,事實上托爾斯泰所提到的受歡迎的劇作家之中的本瓊森就對莎士比亞極為推崇,他在為第一部莎士比亞戲劇集寫題詞的時候由衷地說:“因為我必須扯上你同輩的伙伴,指出你怎樣蓋過了我們的黎里,淘氣的基德、馬洛的雄偉的筆力。”這些戲劇家與莎士比亞同時代而稍早,可以說是他的前輩,瓊森認為莎士比亞已經超過了他們。他將莎士比亞與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等希臘大家相提并論,“得意吧,我的不列顛,你拿得出一個人,他可以折服歐羅巴全部的戲文。他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所有的世紀!”這是發自莎士比亞同時代的聲音,值得特別重視,可是遺憾的是托爾斯泰由于個人趣味的不同,無視這些話語。
比莎士比亞稍晚的愛德華楊格盛贊莎士比亞、彌爾頓等人,認為莎士比亞是“現代人中最大的星辰之一”,他學問并不多,這一點本瓊森也指出,他不大懂拉丁語,更不通希臘文,但他屬于天才,天才是自然的門生,并不需要進什么專門的學校,他們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獨創性。天才是巨匠,學問只是工具,而且這種工具并不能總是起到積極的作用。當你對古人的作品過分崇拜、過分敬畏的時候,它反而會壓制你的才能。“學問咒罵自然真率之美和無傷大雅的細微疏漏,并為常常是天才無上光榮的淵源的自由,立下種種清規戒律”。[4]13而像莎士比亞這樣的天才,他不用以乏味的模仿降低自己的天才,盡管他有諸多缺點,知識不多,但他精通兩部書――“自然的書和人的書”,因為他,“不列顛舞臺上至少有和希臘舞臺上同樣多的天才”。[4]39即使是德萊頓,作為一位法國新古典主義的推崇者,也認為莎士比亞是個例外:“在所有近代或在古代詩人中他具有最廣闊、最能包涵一切的心靈。自然的一切總是在他面前,而他隨手招來,并不費力。他描寫任何東西,你不但看得見,還能摸得著。那些指責他沒有學問的人倒是恭維了他;他是天生有學問的;他不需要戴上書籍的眼鏡去窺察自然;他向內心一看,就發現自然在那里。”[39]77他尊崇莎士比亞,但認為莎士比亞是不可模仿的,他可以不需要學問與遵守規則,可是其他人則不可以,很顯然不是每個人都是“天生有學問的”。
不過托爾斯泰的看法在另外一種意義上是合乎現實的,在莎士比亞同時代以及稍后,固然有瓊森、楊格等人為他辯護,但是可以想見的是,必然有與之對立的一派,這在楊格的《試論獨創性作品》中其實就已經隱含了,那些缺乏天才,更注重學問的人咒罵莎士比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瓊森和楊格的觀點是對這些人的回應。這也可以說莎士比亞在當時的英國遠遠沒有達到聲譽的頂峰。即使是德萊頓,他在盛贊莎士比亞的天才之后說:“他往往平凡無味,有時調侃之詞流于俏皮,嚴肅之語變為浮夸。”[5]77這在17世紀之后更為明顯,其時在歐洲文學界占據統治地位的是法國的新古典主義戲劇,以及他們的創作法則,尤其是“三一律”。從他們的角度來看,莎士比亞完全是個不通任何規矩的“野蠻人”。1663年,一名叫索比爾的法國人以半外交的官方身份訪問英國,回國后寫了一本叫《航行》的小冊子,用很不禮貌的口吻報道了英國的戲劇活動:“他們的喜劇,不會受到法國人的歡迎。他們的詩人,根本不考慮地點和與時間的統一,他們的喜劇情節,從頭到尾約需25年。第一幕,王子剛剛結婚,下一幕他的兒子已開始游學與建功立業了。”[6]法國人之所以如此取笑英國戲劇,是因為他們的新古典主義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受其影響,英國新古典派批評家托馬斯萊梅攻擊莎士比亞的《奧賽羅》,說它是“淡而無味的殘酷的鬧劇”。[7]16
萊辛之后,赫爾德也非常注重莎士比亞,他的觀點直接影響了青年歌德。赫爾德是莎士比亞最熱情的歌頌者,他不吝贊美之辭。針對有人批評莎士比亞戲劇缺乏規則,赫爾德指出不能以古希臘藝術為標準來衡量莎士比亞,也絕不能要求今天的英國產生古希臘那樣的藝術。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正是那些新古典主義者,那些號稱遵循希臘藝術規則的人,違反了希臘藝術的精神。他指出:“亞理斯多德懂得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珍視索福克勒斯這種天才的藝術,并且在一切論點上都幾乎恰恰和近代人隨意曲解他的著作的說法相反……這位偉人也是本著他那個時代的偉大精神進行哲學的探討,后來人們硬要從他的著作里抽出清規戒律作為舞臺上的八股,對于這些幼稚的、限制人的瑣屑無聊的東西,亞理斯多德是絲毫沒有責任的……假如亞理斯多德復生,看到人們把他的規則錯誤地、違理地運用到完全另一種性質的戲劇上去,那他當作何感想!”[13]7273他指出在距離希臘那么遠的時代,歷史、傳統、習俗、宗教、時代精神、民族性格等各個方面都與其迥然不同,要求這種人再完全按照希臘規則來創作是荒唐的。而莎士比亞的偉大在于他就他所能發現的那個樣子采用了歷史,用創作的天才把千差萬別的材料構成一個不可思議的整體,這正是“有一個天生有神力的凡人,恰恰利用性質相反的材料、通過極不相同的寫法,產生了(與希臘戲劇)同樣的效果:恐懼和憐憫!而且兩種情感還達到了那第一種材料和寫法當初未必能夠達到的程度!這個人在他的事業上真是幸運的天之驕子啊!正是這嶄新的 、初次出現的、完全不同的東西顯示出他在本行上的原始力量。”[13]78莎士比亞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是因為他只是而且總是自然的仆人。在他的作品里,詩人掌握的時間和地點的變更以最大的聲音喊道:“這里不是詩人!是造物主!是世界歷史!”[13]82只有那些最可憐的人才會認為莎士比亞的戲劇是最笨拙最荒唐的東西。可以說正是赫爾德的這種不遺余力的倡導,直接導致了德國文學的巨大飛躍。
三 、康德對“天才”的定義
盡管在康德的三大批判尤其是《判斷力批判》中并沒有提及莎士比亞,但是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康德是非常熟悉莎士比亞戲劇的,尤其是在他的人類學講座中。在《實用人類學》第一卷“論認識能力”中他就舉了莎士比亞劇中人物福斯塔夫來說明想象力的特性。 而在《判斷力批判》中,他盡管沒有明言莎士比亞和法國新古典主義,我們從他的行文和褒貶上卻可以明確地看出,他的天才觀是完全站在對莎士比亞認同的基礎上的。
康德說:“美的藝術的產品中的合目的性雖然是有意的,但卻畢竟不顯得是有意的;也就是說,美的藝術必須被視為自然,雖然人們意識到它是藝術。但一個藝術產品顯得是自然卻是由于雖然惟有按照規則這個產品才能夠成為它應當是的東西,而在與規則的一致中看得出所有的一絲不茍;但卻沒有刻板,沒有顯露出學院派的形式,也就是說,沒有表現出這規則懸浮在藝術家眼前并給他的心靈力量加上桎梏的痕跡。”[14]320在這里我們完全可以將其解讀為是對莎士比亞和法國新古典主義的對比,如果說康德出于謹慎所以并沒有點名的話,引文中提及的“學院派”則毋庸置疑透露了此中消息。新古典主義強調“三一律”,強調各種規則,赫爾德就已經指出這些都是違背自然的,在這一點上康德顯然認同赫爾德的觀點。他并且進一步指出“天才是與模仿的精神完全對立的”,如果過于強調模仿,“藝術在某個地方就停滯不前了,因為對藝術設立了一個界限,它不能夠再超出這個界限,這個界限也許很久以來就已經被達到并且不能再被擴展”。所以藝術是有規則的,但這種規則只存在于偉大作家的作品中,別人要想了解規則只有通過作品,而決不可能從任何公式中得到這些規則,不然的話,對美的藝術就可以按照概念來規定了。因此康德對“天才”作出了如下的定義:
1. 天才是一種產生出不能為之提供任何確定規則的東西的才能,而不是對于按照某種規則可以學習的東西的技巧稟賦;所以,原創性就必須是它的第一屬性。2. 既然也可能存在原創的胡鬧,所以天才的產品必須同時是典范,亦即是示范性的;因此,它們本身不是通過模仿產生的,但卻必須對別人來說用于模仿,亦即用做評判的準繩或者規則。3. 它是如何完成自己的產品的,它自己也不能描述或者科學地指明,相反,它是作為自然來提供規則的;因此,一個產品的創作者把這產品歸功于他的天才,他自己并不知道這方面的理念是如何在他心中出現的,就連隨心所欲地或者按照計劃想出這些理念并在使別人能夠產生出同樣的產品的這樣一些規范中把這些理念傳達給別人,這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因此,天才這個詞很可能是派生自genius[守護神],即特有的、對于一個人來說與生俱來的保護和引導的精神,那些原創的理念就源自它的靈感)。4. 自然通過天才不是為科學,而是為藝術頒布規則,而且就連這也只是就藝術應當是美的藝術而言的。[14]321
從這個定義中可以看出,康德對于藝術的要求是極高的,只有那些真正的原創性的作品,也就是天才的作品才能稱之為藝術,他們為藝術創作提供典范,提供規則,后人可以對其模仿,但那些模仿之作無論在任何意義上講都是無法與他們對之模仿的作品相比的。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是高度原創性的,雖然新古典主義者們責罵他不懂規則,非常粗野,而且也不管那些古典主義者是多么精致,對于他們眼中的古代作品的模仿是多么惟妙惟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新古典主義者是無法達到莎士比亞的高度的,對于他們來說,這個高度甚至是無法想象的。他們與希臘古典作品只存在著形式上的相似,但莎士比亞雖然常常違反他們的那些規則,卻與那些古典作家在精神上高度相似。事實上就連天才自身都無法明確地說出他們創作的方式,因為這是授之于天的,更別提那些根據古代的作品來制定規則的人了,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他們的規則是多么的無聊和荒謬。
當然并不能因為康德如此的強調天才,就認為他完全否認了規則。他指出雖然天才的原創性的藝術,即真正的“美的藝術”和那些模仿的藝術,也就是“機械的藝術”之間有極大的區別,但是沒有任何美的藝術一點兒都不具有某種“符合學院規則的東西”,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這些規則是構成藝術的基本條件。即使是莎士比亞,如果他對于戲劇規范沒有一星半點的了解,他也就只能永遠是一名鄉下的威廉了,現在傳世的莎士比亞作品將統統化為零。有些東西是必須被設想為目的的,比如說創作的一些基本規范,例如詩歌的音步、韻腳等等,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所有的作品都只不過是一些偶然的產品,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藝術。但這里似乎與他強調的原創性產生了矛盾,不過這在康德的體系里并不是大問題,他在對“美”的鑒賞判斷的契機中就對其予以解釋:“合目的性可以沒有目的”,而且“惟有一個對象的表象中不帶任何目的(無論是客觀的目的還是主觀的目的)的主觀合目的性,因而惟有一個對象借以被給予我們的表象中的合目的性的純然形式,就我們意識到這種形式而言,才構成我們評判為無須概念而普遍可傳達的那種愉悅,因而構成鑒賞判斷的規定根據”。[14]228229這對于鑒賞判斷是這樣,對于美的藝術的創造同樣是這樣,目的(規則)必須被內化,以不被明確意識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也就是不露斧鑿痕跡。據此,將莎士比亞與亦步亦趨、小心謹慎的新古典主義者比起來,高下立判。
眾所周知,康德的美學思想對德國以及世界文學的影響極大。但康德藝術觀念與莎士比亞的關系似乎少有人加以注意,基于此,本文對其略加闡述,不僅可以對康德美學中的一些相關觀念有一個更清晰的了解,也算是對即將到來的莎士比亞400周年忌辰的一點微薄紀念。
[參考文獻]
[1]卡西勒.啟蒙哲學[M].顧偉銘,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315.
[2]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文集:第14卷[M].陳觶豐陳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388.
[3]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編輯委員會.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3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23.
[4]楊格.試論獨創性作品[M].袁可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5]佛朗霍爾.西方文學批評簡史[M].張月超,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
第3篇
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具有豐富的歷史內涵,它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時期,具有不盡相同的意義。即便是在音樂領域,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層面、從不同的角度所給出的定義也不一樣。為此,一些學者反對無區別的使用“新古典主義”這個術語。①一些和新古典主義相關聯的作曲家也提醒我們要小心使用這個術語,因為它在用法上不嚴格,不能恰當地描述出相應的音樂作品。②應該說,這樣的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它要求我們對“新古典主義”的起源及其在音樂領域中的發展和變化進行清晰、明確的梳理,唯有如此才能確保理論上的清晰性和嚴密性。
一、戰前的法國
根據斯科特?梅西的考據,“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這個術語大體出現在19世紀末的法國。不過,當時的理論家們并沒有明確使用“新古典主義”一詞,更多類似的表述是l'art antiquisante或者la retour à l'antiquité(返回古代),而不是“新古典主義”。③(p13,下文標注頁碼之引文均出自該著)不過,在當時這些表述上的差異并不妨礙“新古典主義”一詞想要表達的涵義:即對19世紀晚期一些作家的不屑與鄙視,這些作家機械地模仿希臘和羅馬的藝術,并且盲目地沉迷于學院派的細枝末節。(p13)
從20世紀開始,伴隨著藝術思潮的蔓延,這個詞逐漸從文學批評領域滲透到音樂批評領域,并在音樂中的使用頻率大大上升,在開始的十年里新古典主義有著明確的定義:它和19世紀一些作曲家有關,這些作曲家忠實于18世紀流行的器樂音樂形式,但是由于卑劣的模仿而丟失了音樂本質中的創造性和思想深度。(p14)很顯然這是一個貶義的概念,批判的目標直指19世紀的一些作曲家。
隨著民族矛盾的上升,一些作曲家希望復興法國音樂傳統來抵抗德國音樂,尤其是瓦格納音樂的影響,由此,“新古典主義”的使用有了特殊的語境,它的貶義色彩逐步得到了強化,批判的目標也越發集中,最終被法國的評論界用以描述19世紀的德國作曲家。“德國音樂陷入了一種不幸的痛苦之中,它沉迷于門德爾松及勃拉姆斯的新古典主義的麻醉中喋喋不休,或者被瓦格納式的浪漫的嗎啡所麻痹。”(p13)法國音樂批評家Jean Marnold尖酸刻薄的評論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瓦格納并不僅僅是唯一需要被法國古典精神所改造的德國作曲家,德國音樂還有另外一支“新古典主義的”隊伍需要被改造。
在“新古典主義”指向19世紀德國作曲家的過程中,批判的目標最終聚焦在勃拉姆斯身上,沃爾夫(Hugo Wolf)是第一位將“新古典主義”和勃拉姆斯掛起鉤來的作曲家和評論家。他并沒有明確使用“新古典主義”一詞,但是他對圣?桑和勃拉姆斯音樂的對比評價卻表露出他的用意:“圣?桑的古典主義有些類似于勃拉姆斯的,但是圣?桑的古典主義是音樂發展的自然結果,而勃拉姆斯的古典主義僅僅是為他枯竭的創造力提供了一種偽裝”。(p14)在這里值得強調的是:第一,沃爾夫區分出了兩種古典主義,盡管在他的評論中還沒有給這兩種類型定出清晰的概念,但是在他的言語中已經明確了二者之間的差異,即具有褒義色彩的圣?桑式的古典主義和具有貶義色彩的勃拉姆斯式的古典主義;第二,沃爾夫并非單純對勃拉姆斯的所謂“新古典主義”音樂予以否定,而是指出了他的“新古典主義”作品的功用。也就是說,沃爾夫不僅關注“好壞”,即“新古典主義”究竟是成功的模仿“古典”還是卑劣的模仿“古典”;而且重視“用途”,即模仿“古典”有什么功用。和沃爾夫相比,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對勃拉姆斯的“新古典主義”音樂的評論更為人所知,這與他的音樂評論家身份有很大的關系。羅曼?羅蘭依然是在貶義的概念上將“新古典主義”與勃拉姆斯聯系在一起,但是他對勃拉姆斯“新古典主義”音樂的態度卻有一個轉變的過程。在最初的音樂會評論中,他稱贊勃拉姆斯的《第三交響樂》是一個極好的新古典主義的作品,然而在1908年末,他斷定:“勃拉姆斯的‘新古典主義’音樂已經被德國藝術中令人討厭的迂腐氣息所毀壞。”(p14)在這一點上法國作曲家、評論家杜卡斯(Paul Dukas)對勃拉姆斯“新古典主義”音樂的定位與羅曼?羅蘭不乏相似之處,也經歷了一個先揚后抑的過程。幾年以后,丹第(Paul Vincent d'Indy)分析了圣?桑和勃拉姆斯音樂中的調性后,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20世紀初,德法兩國關系的緊張愈發堅定了法國作曲家的批判立場,批判的矛頭對準了,這位德國古典音樂最后一位繼承人,在法國評論家的眼中最終成為繼勃拉姆斯之后的又一位“新古典主義”代言人:“……這個作品的基本觀念是新古典主義的,相當地具有伸縮性和迷惑性……整個作品像是在過分地賣弄和炫耀收集起來的各種昂貴的古董。”(p15)
從以上的梳理中,我們得知:“新古典主義”一詞從誕生那天起就帶有極強的貶義色彩。在音樂領域中,“新古典主義”和19世紀的德國作曲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隨著民族矛盾的激化,這個術語的外延逐漸地縮小,勃拉姆斯和先后被冠以“新古典主義”的稱號,成為法國藝術家批判和指責的目標。然而“一戰”之后,“新古典主義”的語義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在德國和法國呈現出不盡相同的表現形式。
二、戰后的法國
喬治?讓?奧伯利(Georges Jean-Aubry)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法國的音樂家那樣沉迷于法國民族傳統中引以為豪”。(p75)同樣,法國音樂評論家也毫不吝嗇地將一切最美好的贊頌之詞贈予了法國音樂:優美、活潑、機智、簡潔、清晰、明了、純潔、清醒、形式優雅、色彩豐富、邏輯嚴密……,這些優美的詞匯最終以最凝練的表述方式“新的古典主義”(Nnouveau Classicism)表達了法國人民對本民族音樂的熱愛。那么什么樣的藝術形式能夠與“新的古典主義”相匹配呢?德彪西、拉威爾就這樣走進了法國人民的期待視野,從此與“新的古典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由此我們發現:“新古典主義”(Néoclassicisme)和“新的古典主義”相差甚遠。前者用于指責19世紀德國作曲家,尤其是勃拉姆斯和;后者用于贊頌19世紀后期法國作曲家,代表人物德彪西和拉威爾。
然而在1919年這一局面發生了改變,詩人和評論家毛克萊(Camille Mauclair)對德彪西的音樂評論中卻出現了“新古典主義的”這個字眼,并且是在褒義的意義上使用的。“……德彪西不顧及自己的聲望,僅僅是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愿望,他渴望成為新古典主義的作曲家,愿意成為18世紀大鍵琴的弟子,希望成為拉莫(Rameau)的子孫后代。”(p76)顯然,在毛克萊手中,“新古典主義”概念的使用已經偏離了原有的軌道。斯科特?梅西說?押“新古典主義在1920年代才獲得積極的意義,而在1914年至1920年的6年里,新古典主義依然保持著貶義的色彩。”(p76)梅西的結論表明:“新古典主義”和“新的古典主義”這兩個術語間的差異在1920年代左右變得模糊起來。
就在“一戰”后法國的評論家依然沉浸在民族主義的情緒中,對德彪西、拉威爾等人的音樂大肆宣揚時,世界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某種變化,這兩個術語的涵義也因此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一些藝術家不愿再追隨戰前的藝術潮流,主動與其劃清界限。在他們眼中,德彪西成為印象主義的代表,拉威爾和浮華的浪漫主義聯系在一起,二人不再和“新的古典主義”糾纏在一起。與此同時,1921年意大利未來派藝術家基諾?塞弗里尼(Gino Severini)在其論文中使用了“新的古典主義”一詞來描述在視覺領域中出現的一種新傾向,他的“新的古典主義”藝術風格是以幾何學的比例原則作為基礎;莫里斯(Maurice Brillant)在文章中也使用“新的古典主義”這個概念,并規定了它的內涵:“新的古典主義是一種風格,它重視結構、關注簡樸、強調脫離印象主義色彩之后的清醒”。(參閱?眼1?演,p80-81)從以上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出,在戰后的歷史語境中,“新的古典主義”依然保持著褒義的色彩,依然有一系列美好的詞匯與她相伴,只不過它不再依附于德彪西和拉威爾,而是獨立地成為一種新的藝術傾向。
然而“新古典主義”這個術語在音樂評論家的眼中不再像1920年代那么可敬可愛,它的褒義性質再一次發生了改變,并且批判的靶子也不僅僅局限于德國作曲家,而是擴大到法國作曲家。比如利?亨利(Leigh Henry)1921年在“新古典主義”這個術語前加上了一個形容詞“蒼白的” 來描述拉威爾的音樂,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至此“新古典主義”否定的意義又一次出現,只是外延擴大,這使它的面目變得撲朔迷離起來,1922年后期許多法國作曲家都拒絕和這個詞扯上任何關系。
真正將德彪西和拉威爾打入地獄的應該是科克托。據斯科特?梅西考據,在Le coq et l,arlequin一書中,德彪西成為被科克托批判的唯一的一位法國作曲家……1920年拉威爾也沒能逃過被攻擊的命運。(p77)與此同時埃里克?薩蒂(Erik Satie)的身影頻繁地出現在科克托的文章和著作中,一躍成為領導法國音樂潮流的杰出人物。盡管科克托對薩蒂贊揚的話語類似于法國“新的古典主義”的修辭,比如:清晰、簡潔、優雅……等等,但在科克托眼中,薩蒂既沒有返回18世紀古典的傾向,也與遙遠的法國民族傳統保持一定的距離,他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新的道路,他所做的一切僅僅是為了保持一種簡單、清晰、明了。因此當科克托用盡最美好的詞匯去推崇薩蒂的音樂時,他既沒有使用“新古典主義”這個和18世紀古典音樂有著某種聯系的概念,也沒有使用“新的古典主義”這個和法國民族傳統相生相伴的術語,而是反復地強調“新簡約主義”(Nouveau Simplicité)。對于這個新的理論術語,科克托有如下的解釋:“埃里克?薩蒂的‘新簡約主義’既是‘古典的’,又是‘現代的’;它是不能使人想起任何法國音樂的一種‘法國音樂’。”(p77)從科克托對“新簡約主義”的解釋和使用中可以看出,薩蒂的音樂總體上是一種新的現代音樂形式,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達到簡單明了的效果,但是這種新的音樂并不否認古典藝術的存在價值,并不拒絕用懷舊的方式和手段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
如前所述,“新古典主義”是近現代音樂史上最詭異的詞語。同一個詞語,在不同的人眼中,會有不同的理解,這一點在1922―1923年的法國表現得最為明顯。一些學者認為“新古典主義”是一個貶義的概念,例如意大利超現實主義畫家喬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將“新古典主義”看成是沒有靈感的、平庸的模仿;然而有些學者卻認為“新古典主義”具有褒義的色彩,例如佳吉列夫(Diaghilev)就是這樣認為的,他將“復興”和“發展”看成不同的事情,對他來說前者意味著恢復或模仿,而后者具備了用新的眼光和視野去解釋過去的能力”;最令人困惑的就是奧里克和六人團(Les Six),他們極力否認自己和“新古典主義”的關系,但是其他人卻將他們與“新古典主義”聯系起來。(p82―84) 法國藝術家對“新古典主義”的思考再一次顯示出了它的曖昧和含混。
三、戰后的德國
和法國相比,“新古典主義”(neoklassizismus)這個術語在德國非常少見,戰后在德國音樂領域中更為常見的術語卻是由托馬斯?曼(Thomas Mann)創造出來的“新的古典主義”(neue klassizit?]t)。和法國一樣,德國的“新的古典主義”有著大致相同的文化語境和使用動機:反對瓦格納的音樂語言和美學觀念。不同的是,德國的“新的古典主義”并不是以法國的民族傳統為基礎來對抗瓦格納音樂的影響,而是以歌德作為“新的古典主義”的基礎和典范。在這方面,托馬斯?曼可謂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他將瓦格納的音樂看成19世紀頹廢藝術的象征,而將歌德看成是崇高和純潔的化身。
如果說在托馬斯?曼那里,“新的古典主義”僅僅是對抗瓦格納的有效工具,那么在布索尼那里,“新的古典主義” 還可以為現代音樂的發展指明方向。“瓦格納的成功已經延續的太久了……現在重要的不是蔑視和貶損,而是建立永恒的價值。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古典藝術。它具備古典的特征:美麗、偉大、簡潔,使人印象深刻,這是一種穩定持久的藝術作品。”(p65―66)布索尼對“新的古典主義”的理解和運用,是在討論藝術發展演變的歷史語境中進行的。他清楚地認識到現代藝術所面臨的困境,在尋求現代藝術出路的過程中,布索尼使用這個術語以更好地表達對這種新的藝術潮流的擁護和期待。布索尼進一步用“年輕的古典主義”(junge klassizit?]t)一詞替換了“新的古典主義”,并對這兩種用法做出了區分: 后者僅僅意指對過去的模仿,而“年輕的古典主義” 意味著音樂的發展和進化體現了一個前進的、青春的、有生命力的過程,這個過程類似于自然界有機的生長過程。(p67)可見布索尼的“年輕的古典主義”概念既是對托馬斯?曼的“新的古典主義”觀念的繼承,又是對他的觀念的進一步發展。
布索尼在20世紀初藝術圈中的影響是很大的,這不僅是因為他的多重身份――鍵盤演奏家、作曲家、美學家,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基礎來源于歌德。在這點上他與托馬斯?曼不乏相似之處,但是和托馬斯?曼相比,布索尼借助于歌德的詩歌創作,在音樂的層面上規定了“年輕的古典主義”這個術語的典型特征?熏從而向世人展示出這個概念的豐富內涵,對“新古典主義”術語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p68―70)
(一)“年輕的古典主義”首要的基本特征就是單一性或一致性(Unity or Einheit)的觀點。單一性的觀點表現在:音樂就是音樂,音樂不能表現道德狀況,也不能體現民族品質,音樂不能表現抽象的觀念;一致性的觀點表現在:所有的音樂都是從單一的來源中發展而來,這也就是說,藝術家不是發明,而是在已有的藝術作品上重新塑造。
(二)音樂作品的產生是音樂要素水平發展的結果,與垂直進行無關。在布索尼眼中音樂旋律的地位至高無上,類似于古老的復調藝術,但并沒有復制它,只是遵照了它的原則,通過復調豐富的形式以及和聲藝術,音樂旋律從自身產生一種新的形式建構的能量。
(三)“年輕的古典主義”不能使用具有描繪性的音畫手法,也不能使用頹廢的和聲。布索尼認為這些手法在瓦格納音樂創作中占有顯著的地位,他不喜歡那些帶有主觀的、描繪的、夸張的、形而上學的、感官的、縱向垂直的音樂,他擁護客觀的、絕對的、清澈的、純粹的、橫向水平的音樂。
布索尼對“年輕的古典主義”的三個規定,透露出了他的美學傾向和立場:他熱衷于已有的18世紀古典音樂的精神,不贊同過分裝飾的文學化的形象描繪,拒絕歇斯底里的新表現主義,擁護理性客觀的創作而不是各音樂要素雜亂無章的聚積。在這里,布索尼發現了一個可以界定的廣泛共享的“年輕的古典主義”觀念集合,并以其對這個觀念集合的精湛理解,預見了當代“新古典主義”藝術理論并獲得了廣泛的影響。
總結通過上述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1.“一戰”后的“新古典主義”并沒有在歷史、審美、功能和音樂風格等層面上顯示出穩定連續的直線進化過程。2.在其使用過程中,一方面“新古典主義”有著眾多相關的近義詞,人們有時侯用這些術語來替代“新古典主義”,例如“新的古典主義”、“年輕的古典主義”、“新簡約主義”等等;另一方面,“新古典主義”在很多時候又缺乏明確的近義詞,太多的內涵和意義都被注入到這一個術語之中。3.不同的“新古典主義”內涵使得這個術語具有了不同的功能意義:可以是褒義性的,也可以是貶義性的。總之,此時的“新古典主義”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眾說紛紜。這種復雜的狀況最終延伸到了斯特拉文斯基身上,從而使他的新古典主義也同樣呈現出迷離朦朧的特征。
參考文獻
1William John Mahar?熏 Neo-Classic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押 a study of the ide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elected works of Stravinsky and Picasso. The University of Syracuse?熏 Ph.D?熏1972.
2鐘子林《西方現代音樂概述》,北京?押人民音樂出版社1991年版。
①Eric Salzman,Twentieth-Century Music?押 An Introduction?熏4nd ed?熏 Englewood Cliffs?押Prentice-Hall?熏2002.
②David Neumeyer?熏 The Music of Paul Hindemith.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熏1986. p1-2
擴展閱讀
- 1古典文化
- 2古典詩吟唱
- 3古典文學
- 4古典詩歌語言特征
- 5古典時代雅典婚配模式
- 6古典詞學趣范疇承傳考察
- 7古典園林建筑在古典園林中的作用
- 8古典藝術風格
- 9古典經濟學
- 10古典詩吟唱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