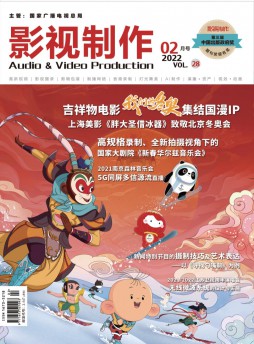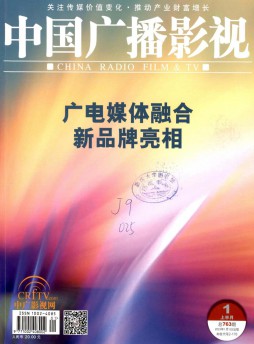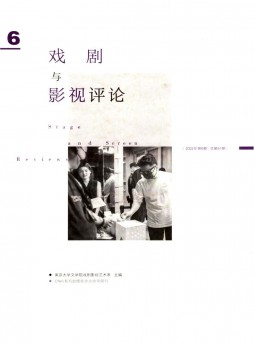影視與文學的關系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影視與文學的關系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影視作品 文學 思想 關系 結合
1、什么是文學?影視就是電影和電視劇嗎?
文學是個非常廣義的概念,是一個很深奧的詞匯,文學包括詩歌、散文、小說、劇本、預言、通話等,這些都是文化的一種重要變現形式,都是以文字語言為工具呈現出來的,以不同的體裁表現作者內心情感和社會生活。文學與哲學、宗教、法律、政治都是社會的上層學問,是社會科學的學科分類之一,文學可以代表一個民族的藝術和智慧,文學在地域上分類頁可以分成很多文學,亞洲文學、歐洲文學、美洲文學。值得一提的是莫言在去年榮膺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這不能說明中國現代、中國當代文學成就平庸,它以優秀的歷史、多樣的形式、眾多的作家、豐富的作品、獨特的風格、鮮明的個性、誘人的魅力而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瑰寶。
影視顯得更容易理解,就是電影和電視劇的合稱,拍攝、繪畫出來的帶有故事性的動畫的也算影視,電影藝術和電視藝術是通過現代科學技術和藝術相結合的產物。影視制作產業是前景無限的商機無限的,如何很好的把影視和文學相結合,如何使文學在影視藝術中發揮最大的正能量是一門學問。
2,影視作品需要還有文學性,并尊重文學。
大家應該都看過94年版的《三國演義》,電視劇尊重原著《三國演義》,以描寫戰爭為主反應了當時三個政治集團的斗爭,其中宣揚一種仁義道德、禮信忠貞的文化思想,劇中更是引用古籍中古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又能把觀眾拉回到東漢末年,一起與曹孟德駕馭良駒寶馬馳騁千里,一盞豪飲,感悟人生哲理。《千與千尋》是日本國寶動畫片,是動畫大師宮崎駿的杰作,影片大致概括了一個小女孩在一個奇特世界的冒險故事。宮崎駿帶你進入一個仿佛遠離了世俗的世界,這個世界里的每一件物品仿佛都是宮崎駿親手雕琢,富有靈性,影片一開始,小女孩的父母為了滿足食欲雙雙變成了豬,這是宮崎駿的一種黑色幽默,也寓意這不要有貪婪之心,小女孩的純真打動了觀眾,我們也要反思在現在的社會中要相信他人,影片中也映射出現代日本的環境污染問題,影片文學性非常強,宮崎駿大師在影片中埋下了很多觀眾值得思考的疑惑。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哈姆雷特》,這是一部現代版的《王子復仇記》,哈姆雷特是丹麥一家大公司已故總裁的兒子,有一天他遇到了他父親的靈魂,他父親的靈魂告訴哈姆雷特是他的叔叔謀殺了他,得到了他的公司和哈姆雷特的母親,哈姆雷特決心替父報仇,此片的背景是現代,而原著莎士比亞的小說是幾個世紀之前的事情,如何做到把古代的故事挪到21世紀來表現,導演下了很大功夫,首先是尊重原著中的人物,性格拿捏得非常準,第二,這部電影運用原著臺詞“是生存還是毀滅”等,極力的尊重原著,使觀眾在現代的氛圍中體會哈姆雷特的心情。說到莎士比亞不禁想起電影現代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影片男主角是拉昂那多,這部電影類似現代版的《哈姆雷特》,也是把幾個世紀前的故事成功拉到現代,愛情主題貫穿全篇,兩個年輕人不顧家族反對在一起廝混,由于家族問題,最后陸續殉情,詮釋了愛情的力量。
現在的影視作品經常篡改原著,甚至面目全非,徹底顛覆原著作者意圖。在商業片橫行的年代,導演追求票房無可厚非,但是一部沒有以文學思想的電影是肯定站不住腳的,前一陣看過一個新聞,大致意思是說一部抗日劇,一個抗日女俠不幸被幾個日本兵侮辱鏡頭不停的在幾個笑的日本兵臉上切來切去,幾秒后女俠爆發了,跳了起來拿幾個箭頭瞬間射死了幾十個日本兵,該情節完全邏輯混亂而且相當不科學,更像是不入流的武俠小說情節,其實導演完全可以運用文學手段把這情節合理化。我看過一部爛片叫《大灌籃》,周杰倫主演,演員陣容強大,此片抄襲周星馳電影《少林足球》,《大灌籃》主要是弘揚了功夫超群的方世杰在球場上的個人英雄主義,影片毫無內涵可循,毫無文學性,熱鬧的場景沒有任何意義只能迎合三流觀眾,觀眾如果看完此片會發現時在浪費時間。
第2篇
作為藝術門類中與科技手段、商業利益關系最為密切的現代綜合藝術,電影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糾纏在與其他藝術關系的辨析和梳理之中。對于非音樂片和紀錄片的電影來說,其核心價值是否可以通過音響效果、造型等因素體現出來?電影的最高境界是否存在對于哲學、宗教或者文學意義上的價值體現?這些問題在有聲電影取代無聲電影后漸漸的受到人們的質疑。隨著電影的劇情、臺詞等文學性因素要求的相應增強,電影對文學作品的改編和文學家對電影的介入被看作是提高電影藝術水平的必要手段。凸顯和廓清電影與戲劇、小說、文學劇本的聯系構成了中國電影理論史的一條主線。中國早期電影經歷了從無腳本到精心構思劇本的過程,所謂“影戲”、“鏡頭文學”的提法以及受蘇聯電影理論的影響而形成的文學第一性、電影第二性的觀念深入人心,忠實原著一度成為評價電影改編的最高標準。在80年代有關電影獨立性等問題的討論中,雖然分歧較大,但重視電影劇本改編質量的文學性前提則為眾人所認同。用鏡頭語言去描繪文學內涵,這似乎成了中國無數電影制作人最終努力達到的目標。
現在的影視作品經常改編文學原著,有時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徹底背離原著所表達的意圖。導演應有一定責任感,不能以追求票房,收視率而刻意迎合大眾。一些影視作品總是走著老戲套,出現個奸角就一定有個正義使者出現,然后最終邪不壓正,這樣的劇情過于矯情,看著別扭。似乎悲情有悲情的戲路,喜劇有喜劇的套子,好像人們的笑臉與眼淚都有固定取悅的方式。當今的影視藝術有明顯的娛樂化趨勢,但是有是否有人曾經想過,當一切藝術文學都為娛樂而活的時候,人們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的時候,人類文明就會有毀滅的態勢。
電影版的《活著》,里面小兒子的死法就和文學作品里面的完全不一樣。但是到底是被抽血抽死好,還是被圍墻砸死好?原則雖然沒有改變,終究是死了。但是文學里面的死法似乎更發人深思。但是用在影視里面,似乎就死了有點殘忍了,所以只能換成我們大眾思維里面能接受的死法。《肖申克的救贖》電影還是總體上忠于斯蒂芬金的原著的。一些細節的改編上,如電影中安迪長得又瘦又高,但原著中,安迪的身材屬于短小精悍,而且相貌英俊的那種。原著中說“安迪長得比較矮小,生就一張俊臉……”,同時對安迪還有這樣的敘述:“安迪在一九四八年到肖申克時是三十歲,他屬于五短身材,長得白白凈凈,一頭棕發,雙手小而靈巧。他戴了一副金邊眼鏡,指甲永遠剪得整整齊齊、干干凈凈,我最記得的也是那雙手,一個男人給人這種印象還滿滑稽的,但這似乎正好總結了安迪這個人的特色,他的樣子老讓你覺得他似乎應該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所以,安迪給人的感覺總是非常精神、非常清爽,戴著一副眼鏡,更襯托了他的聰明智慧。還有最后結局稍有不同。小說結束在Red前往墨西哥尋找Andy的路上而不確定他能否找到,以“我希望”作為結尾,而電影中Red在墨西哥的海灘找到了Andy這一幕我認為2種版本還是小說最后把希望和救贖展示得比較恰當。
我想很多人都有過花很多的時間看一部很爛的影片的經歷,就是看了開頭,就能聯想到結尾,但是不看完似乎又說不過去,看下去吧又似乎在強迫自己在嚼蠟一樣,淡然無味。一般人看影視藝術作品,是懷著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態,最后發現只不過是一部商業炒作片或者大成本投資,著名影星匯集的嘩眾取寵的豪華片的時候,會有很多的感觸,至少有上當受騙的感覺。就近而言我去電影院看了《黃金羅盤》沒想到直到劇終,還沒有敘述清楚故事的全部,一黑幕的時候全戲院的人都罵開了,原來人家還有續集。對于這樣的商業行為觀眾只能安慰自己現在賺錢不容易,人家也要養家糊口。這樣的電影反而激起去尋覓其文學作品的沖動,只為了盡快的把故事看明白。李安《斷臂山》是根據1997普羅克斯的短篇小說改編,只有數十頁的小說,文字精簡。李安用自己獨特的理解:家庭、責任、愛情與生活;“愛是可以超越文化差異的,當愛降臨時,異性之愛與同性之愛是毫無差別的,不妨把性別撇開。”引起了全世界人們的關注。電影《斷背山》在優美的西部風光和略顯滄桑的吉他音樂的襯托下兩個牛仔之間的愛情如歌如泣,達到了“從沒有過的如此純潔、神圣地刻畫兩個男人間的愛情”的地步,而影片的最后,Ennis目送自己即將與心上人結婚的女兒驅車離去,打開衣櫥,凝視著斷臂山的明信片,飽經滄桑的臉上老淚縱橫,說出那句令人心痛的“I swear”的時候是如此的凄涼,想想這忽然而已的生命中又有多少不能承受的痛苦――看著他們,想著自己,失落的天堂彌漫著每個觀者的內心,不失原著細膩優雅的文學色彩。所以說影視作品里富含文學性就能讓影視作品更具備感染性。
在西方電影發展史上也曾經歷小說與電影孰優孰劣的爭議,在早期劇情片時代,作家認為電影不能像小說那樣“充分表現思維狀況的活動”,因而藝術價值不大。但60年代以來,由于阿倫•雷乃、費里尼和安東尼奧尼等電影大師側重于描繪人物內心世界的影片獲得成功,用“有無隱喻”來衡量小說與電影的本質差異不再適宜。小說家面對電影的態度常常比較輕蔑,托馬斯•曼說:電影不是藝術,是生活。20世紀的文學大師如海明威、德萊塞、福克納、奧尼爾等人都曾受雇于好萊塢,但都聲稱電影對他們的吸引力是在經濟方面,電影未曾影響他們的創作。 中國小說家和電影的關系比較復雜。當代小說成就了中國當代電影,當代電影也提高了當代小說家的知名度,并且為其作者帶來的不只是名望還有大量的經濟收入。王朔、莫言、蘇童、劉恒、寧財神、北村等小說家的備受大眾關注這他們的作品拍攝的電影,改編的電影有關。當代社會從“話語”的文化轉向“形象”的文化與中國當前的小康社會和消費文化的總體性密切相關,反映出眼睛從抽象的理性探索轉向直接的感性的深刻變換。電影所帶來的現實利益使得許多作家不僅投身于影視的導演、編劇和策劃等工作,更熱衷于“視覺化寫作”,極力在小說創作中表現適宜影視改編的元素,不同程度地放棄了小說家面對紙筆的獨立身份,有人稱為“掛小說的羊頭,賣劇本的狗肉”。尤其是80年代后作家與影視的親密結合,實際上對小說創作不無隱患。當文學作品都寫的通俗易懂,就猶如紙上電影一樣,似乎其文學韻味就蕩然無存了。所以當代很多小說家,特別是有電影改編經歷的知名作家,都明確表達自己的作家身份和電影之間的不妥協立場。曾經感嘆“遇到張藝謀這樣的導演我很幸運”的莫言多次說到:寫小說時自己是一個皇帝,而改編劇本時是一個奴才。他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我認為寫小說就要堅持原則,決不向電影和電視劇靠攏,哪怕一百個人里面只有一兩個人讀得懂,也不要想著怎么可以更容易拍成電影。小說跟電影、電視劇的關系,我認為應該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點上契合,生出一個作品。我的態度是,絕不向電影、電視靠攏,寫小說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
影視文學比文學擁有更多的群眾性,是任何文學作品不能比擬的。因此它必須具有震撼力和表現力。文學的表現工具只是文字,有相對的限制性;影視藝術有無比的精確性和敏銳性,能較好通過影象聲音反應一切復雜的生活現象。它能對觀眾直接訴之于形象,使觀眾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視藝術具有政府空間和時間的魔力,我們可以看到同代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見一切動人心弦的歷史的重演。《亂世佳人》中瑞德說:“我不求你原諒,我永遠也不理解和原諒我自己,如果子彈打中我那倒好了。我是個,我只知道我愛你,即使這倒霉的世界和我倆都變成碎片,我也愛你,因為我們很相像,我們倆都夠壞,自私而精明,但我們能夠一眼就把事物看清。”的時候,這個南方莊園主的女兒狂野而不嬌縱,具有概括和典型化文學作品的能力。
我們看一幅畫,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可以反復玩味。對于電影來說,如果觀眾一個地方沒有看懂,或者體會不夠,他不可能要求停頓一下,甚至連思索一下的空隙都沒有,他只能在感受上留下一個缺口,缺口一多,電影給他留下的印象就會變得殘缺不全,也就很難集中精力來欣賞了。所以影視藝術要創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劇本要準確的刻畫人物性格個思想感情,不要把人物局限于某一個固定的場景里;演員的演技要出色到可以和劇本融合;其它的幕后創造英雄要在同意的創造意圖下進行工作。
第3篇
(哈爾濱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6)
【摘 要】主要以影視與文學的關系為話題,試圖探討“圖像”是否能替代“文字”,文學是否會走向“終結”這些問題,得出結論:文學和影視,文字與圖像將會永遠并存,共同豐富著人們日新月異的精神生活。
關鍵詞 改編;影視語言;文學解讀
1 影視與文學的聯姻
1.1 影視向經典文學“求教”
1.1.1 文學是影視的根基
在影視的發展歷程當中,文學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大量的影視作品都由文學作品改編成的。在影視拍攝過程中,導演最初接觸到的文學劇本是由編劇用文學語言創作的。影片中大量的人物對白和畫外音也要經過文學語言的潤色。這充分體現了電影的文學性。隨著影視的發展,大量的文學作品編成電影或者電視劇展現在銀幕上。例如古代文學作品四大名著,現代文學作品如茅盾的《林家鋪子》、老舍的《駱駝祥子》等等。
1.1.2 影視踩著文學的肩膀
年輕的影視與古老的文學之間一直存在著親密的姻緣關系,這種關系在影視發展的最初階段以及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更多表現為影視對于文學的借鑒,這種借鑒通常呈現為這樣兩個層面:一方面,文學是一整套反映生活、表達生活的方法,比如小說的敘事手法、結構樣式等,都為影視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可供借鑒的營養;另一方而,世界影視史上的許多作品都是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這些文學作品中既包括了經典作品,也包括了當代的暢銷作品,而被改編的主體則更多是敘事性的小說和戲劇。可以說,年輕的影視正是在古老文學的甘泉的滋潤下勃發出日益旺盛的生命力。文學似乎成為影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1.2 影視對文學名著的改編
1.2.1 文學作品的主導地位
在影視對于文學名著的改編過程中,作為文學作品的原作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并影響著人們對影視作品改編成敗的評判。我們知道,電影受到時長、攝制技術和觀眾的心理要求等諸多因素的限制,對于作品復雜的人物關系和社會狀況的表現往往力不從心,而無法與文學作品中那種運用文字以持續不斷地鋪陳、描寫刻畫面而帶給讀者的審美體驗同日而語。如電影《紅樓夢》盡管盡量忠實原著,但總會使千百萬觀眾不滿意。此外,影像文本能否改編成功,很大程度上還決定于編導對原著和作者的理解深度,只有和原著有著精神的共嗚和溝通,才能改編成令人信服的作品。如,電影《城南舊事》,抓住了林海音原作中那種淡淡的感傷情緒,改編獲得了成功。而電影《駱駝祥子》,編導出于對祥子的特殊喜愛,草率地變動了祥子的墮落結局,不僅破壞了祥子性格的發展邏輯,而且削弱了影片社會歷史的內涵價值。
1.2.2 影視藝術家的主導地位
有些影視所選取的文學原作并非文學名著,這些文學原作的名氣遠遠不如名著。影視藝術家以它們為素材進行再創作,使它們為一般大眾所接受,而形成了廣泛的影響。如電視劇《圍城》播出后,錢鐘書先生的原著小說在書攤上成為熱銷,而在此之前并不大為人所知。在這種改編過程中,不可否認,影視藝術家起了主導的作用。但是,他們仍然遵循著從原作到劇本到拍攝,即從“文字”到“圖像“的路徑。
2 影視與文學的疏離
不可否認影視一直在追求自己獨立的探索與發展道路,試圖把自己的觸角伸向各個領域。目前的電影制作就出現了通過高科技、大投入、大場面以追求視聽感受的發展趨勢。如風靡全球的《侏羅紀公園》、《哈里·波特>和《功夫》等影片都是靠著讓人匪夷所思的聲音和畫面效果讓觀眾如癡如醉,這些電影竭力沖擊當代技術所能提供的視覺效果的極限。但是,我們不能由電影與文學關系的這種疏離,而對這種現象在理論上進行無限引申,得出“圖像時代”的到來或是“文學的終結”。因為,在廣闊的文學天地里,仍然有很多東西是影視無從插手的。
2.1 影視對感官(影視語言)的追求
一般說來,影視是通過畫面與音響作用于大眾感官的視聽藝術,它必須把所要表現的內容一概化為視覺形象與聽覺形象,這是不同于文學語言的一種影視語言。
2.1.1 影視語言的直觀性
影視語言可借助蒙太奇鏡頭組接來充分的調動時間空間,而不會破壞它的真實性。例如,它可以從冰天雪地直接轉入百花盛開,讓觀眾感受冬去春來的時空轉換。文學主要依靠文字來傳達信息,讀者無法看到具體形象,只能借助聯想和想象來延伸。與文學語言相比,影視語言更具直觀性。在文學作品中能夠感染讀者的語句,如果放在銀幕上就可能會很難表現。
2.1.2 影視語言的造型傳意
影視語言與文學語言的不同還在于影視語言能夠通過造型傳達意境。與文學語言相比,影視語言能夠容納更多更豐富的信息,如聲音、音響和人物的活動等。比如電影《紅高糧》中的顛轎段,姜文高唱著《酒神曲》熱鬧的場面和富有沖擊力的造型充分展現了山東高密一帶的風土人情,成為影片的一大亮點。但這段場面如果用文學語言來描述則很難讓人感受到《酒神曲》的豪邁、人物的粗獷和熱烈的場面。影視可以把一些需要信息品味的藝術精華,融化為可以很容易接受的信息,隨著對影片的觀賞不知不覺中接受。
2.2 影視是嚴肅文學的通俗讀本
暢銷小說作家海巖指出,“我們現在處于視覺的時代,而不是閱讀的時代,看影視的人遠遠多于閱讀的人,看影視的人再去閱讀,其要求的閱讀方式、閱讀心理會被改造,對結構對人物對畫面感會有要求,在影像時代,從事文本創作時應該考慮到讀者的需求、欣賞、接受的習慣變化,所以作家在描寫方式上自然會改變,這是由和人物和事件結合在一起的時代生活節奏和心理節奏決定的。”但是,顯而易見,小說并不會因此而成為影視的附庸。文學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即使文學中有精英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分野,它們也是彼此共存,各有各的市場,各有各的發展;而影視不過是“嚴肅文學的通俗讀本”(蘇童語),它對于精英文學作品的改編,只不過是把它大眾化,變成大眾的精神食糧,實際上永遠無法取代它的精英本體。因此,小說的改編大戶王溯說:“寫影視劇來錢,但寫多了真把人寫傷了,再要寫小說都回不過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