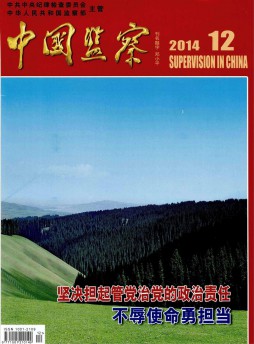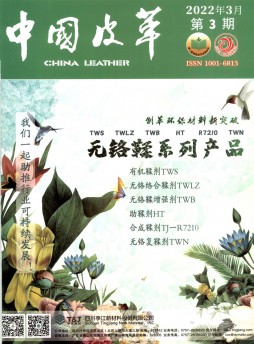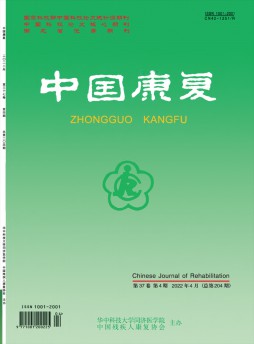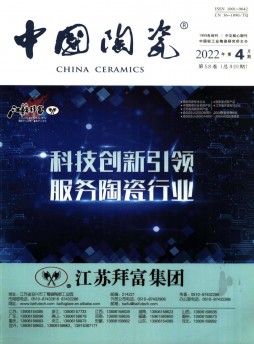中國哲學(xué)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中國哲學(xué)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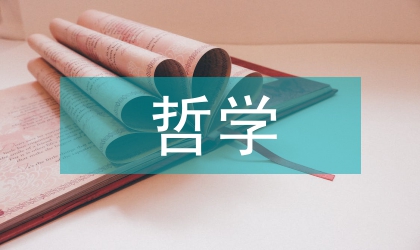
第1篇
“一句‘述而不作’,成為孔子一生治學(xué)特點的權(quán)威概括,也演化為某種扎實、不尚空言卻也帶有保守、無創(chuàng)新意向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后來卻影響了中國文化幾千年。根據(jù)孔子的記述,殷朝時代就已經(jīng)有了一位“好述古事”的老彭,孔子為什么要“述而不作”呢?我們根據(jù)歷史記載和《論語》中的相關(guān)言語,還是能有一個相當(dāng)清晰的答案的。
先秦時期乃至后世,人們一向都不太重視立言,人們所關(guān)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轉(zhuǎn)·襄公二十四年》記載穆叔與范宣子的一段對話,穆叔對范宣子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三不朽”中,“立言”只是沒有辦法的最后選擇,人們首先選擇的是要向古圣賢學(xué)習(xí),以道德垂范后世。孔子也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就是因為圣人們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讓后代的人覺得他們的言語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時候廣招門徒,史書記載孔門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藝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來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編撰教材來傳授弟子,他所編寫的《詩》、《書》、《禮》、《樂》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獨創(chuàng),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據(jù)當(dāng)時的實際情況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據(jù)魯國的史書編寫的,《詩》本來有三千多首,經(jīng)他刪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古詩者三千余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作為一個博學(xué)多識的人,為什么自己不獨創(chuàng)呢?因為在他看來,先王之道已經(jīng)很完備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論傳達出來就行了,只是當(dāng)時世道混亂,“禮壞樂崩”,本來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們忘記了,因此他才會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來教授弟子,好傳述先王之道。孔子和子貢曾經(jīng)有過一段對話,“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想多說,只是為了教授弟子才去說那么多話。在孔子生前,他并沒有自己的專著,《論語》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為其編撰的。
孔子不注重言還與他的教學(xué)思想有關(guān)。孔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學(xué)成后對社會有所貢獻,他更多地是從修身即道德方面來教弟子。“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xué)文’。”在他看來,只要道德修好了,學(xué)不學(xué)文都無關(guān)緊要,只是在時間和精力允許的情況下才去學(xué)文。從他對學(xué)《詩》的態(tài)度就可以看出這一思想。“小子何莫學(xué)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學(xué)《詩》的目的是要為政治服務(wù)的,“興、觀、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更重要。孔子還說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更可以看出他“學(xué)以致用”的態(tài)度,如果一個人學(xué)那么多的詩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能應(yīng)用,學(xué)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之后,相傳子夏傳經(jīng),曾子作《大學(xué)》,子思作《中庸》,都是來傳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樣郁郁不得志的情況下,“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幾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蘭陵著書立說,他對為什么要學(xué)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xí)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經(jīng)無所不包,只要學(xué)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說荀子的思想與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脈相承的。
第2篇
早些年陸教授曾為研究生幵設(shè)有一門叫《中國哲學(xué)的學(xué)理形態(tài)》的課,可能此書即與此課程內(nèi)容有關(guān)。其實,只要是從事中國哲學(xué)的科研與教學(xué)一段時間,大多數(shù)人都會覺得,按某些流行說法,雖說中國哲學(xué)博大精深,但其深層學(xué)理似很難以現(xiàn)代話語通俗傳達出來。如此,那些歷史上無數(shù)的賢哲大同小異的哲理思想和仿佛差不多的修養(yǎng)路數(shù)之間是否有一些共同點呢?那一本本卷帙浩繁的語錄體著述彼此之間是否也有內(nèi)在聯(lián)系和共同思想軌跡?那些研究為數(shù)眾多的哲學(xué)人物的各類論文是否有某些內(nèi)容是相通的呢?可能更為關(guān)鍵的還在于:古老智慧怎能在當(dāng)今時代學(xué)術(shù)條件下進行講解和傳承呢?這樣的憂慮或多或少很可能就是“部分人的焦慮感、危機和困境意識及其‘合法性問題’(指關(guān)于中國哲學(xué)合法性的討論)的自疑”(第1頁)。筆者雖不曾為“合法性”問題去動太多腦筋,但學(xué)習(xí)和研究中國哲學(xué)三十年來卻不免有這些“憂慮”、“焦慮感”和“危機意識”。可喜的是:“這些憂患詞語及其心藉”顯然“時常激促著哲學(xué)專業(yè)工作者致力改變這一現(xiàn)況”。的確,在包括筆者在內(nèi)的一些人那里的這些憂思依然還是憂思時,作為專業(yè)哲學(xué)工作者的陸教授業(yè)已完成如此一部大作!簡介之后,便是著名教授成中英的《序一》,和陸教授的博士導(dǎo)師張豈之教授的《序二》’。二位教授均對該書作了肯定。張先生認為,陸著堅持“中國哲學(xué)具有獨特的民族性”,“由于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長期的研究才能獲得學(xué)術(shù)卜.的成就”,該書的完成“標志著他的研究只是一個開始”。成教授則說:“我必須要說,陸建猷教授寫了當(dāng)今的一本極有創(chuàng)建性的中國哲學(xué)之書。他的闡述的方式及其豐富的內(nèi)容把中國哲學(xué)的宏觀研究推進了一大步,為中國哲學(xué)的發(fā)展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
正是鑒于其著之“創(chuàng)建性”和“非常卓越的貢獻”,以及一個“標志”的“開始”,本評論將主題擬為“篳路藍縷開生面”。探尋中國哲學(xué)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是該著主題。相應(yīng)的是糾正百年來中國哲學(xué)研究中存在的“多史少學(xué)”、“以史代學(xué)”,或“‘中國哲學(xué)史’一路而單邊的強勢傳習(xí)發(fā)展”(第7頁)和“史與學(xué)混同”(第8頁)的現(xiàn)狀。在回望百年中國哲學(xué)研究,特別是諸如謝無量、、馮友蘭、張岱年、侯外廬、牟宗三、勞思光、成中英等的研究之后,陸教授申論他對哲學(xué)與哲學(xué)史關(guān)系上的觀點。在陸教授看來,學(xué)科應(yīng)以學(xué)與史兼?zhèn)涫酒浣∪皩W(xué)”顯然是突出學(xué)理,“史”則偏重學(xué)理演進的歷史。二者的關(guān)系應(yīng)是“先學(xué)而后史,學(xué)是史的本體,史是學(xué)的進程”,尤其是“學(xué)理形態(tài)應(yīng)當(dāng)自體呈示邏輯進程,而非沒有自我實體的發(fā)展進程”。因之,“哲學(xué)的學(xué)與史是哲學(xué)科目本質(zhì)統(tǒng)一性下的兩個性質(zhì)差別的異域”。(第7頁)還說:“哲學(xué)之為學(xué)科的機體,本然地包含著哲學(xué)之‘學(xué)’與哲學(xué)之‘史’的差異性論域^哲學(xué)之‘學(xué)’是哲學(xué)之為學(xué)科的學(xué)理形態(tài)自體,它是決定哲學(xué)之‘史’的實體質(zhì)素。”(第15頁)由此自然涉及黑格爾“哲學(xué)史本身就應(yīng)當(dāng)是哲學(xué)的”那個著名的思想論斷。這個思想后來又以“哲學(xué)就是哲學(xué)史”的命題而廣泛流傳。在陸教授看來,“哲學(xué)就是哲學(xué)史”這個命題成立的條件是有限的。它不能掩蓋二者有區(qū)別的事實。我們并不能因此把哲學(xué)歸結(jié)為哲學(xué)史,也不能把哲學(xué)研究局限于哲學(xué)史研究。從這里,作者試圖開出他的《中國哲學(xué)》的立根之基來。陸教授說:“學(xué)術(shù)生命力在于與時俱進地開新其生機途道。應(yīng)世之需與綜合創(chuàng)新是《中國哲學(xué)》生成的動因條件。”(第8頁)該書比照一般哲學(xué)所關(guān)注的問題域而論中國哲學(xué)的所謂理論論域,也同時就是中國哲學(xué)之“學(xué)”所關(guān)注的問題。
除了緒言和結(jié)束語外,作者大體以此為依據(jù)將中國哲學(xué)的“學(xué)”分為本原論、格致論、名辯論、美識論、倫理觀五大板塊,各板塊有概述,且每個板塊也工整地區(qū)分為六章,全書共三十章。分述先秦諸子百家、儒、釋、道各家哲學(xué)思想,而以六經(jīng)之首《易經(jīng)》作為全書之開篇。不僅如此,陸教授還將他所思考編排的板塊、章名和節(jié)名分別稱之為“宏觀的板塊論域”、“中觀的致思問題”和“微觀的語義概念”三個層次。于此我們看到該書特殊的邏輯結(jié)構(gòu)。陸教授說:“宏觀的‘板塊論域’進向中觀的‘致思問題’,中觀的‘致思問題’在(再)進向微觀的‘語義問題’,是中國哲學(xué)現(xiàn)實學(xué)理形態(tài)的層次結(jié)構(gòu)邏輯鏈。”(第17頁)又說:“篇名意義的‘板塊論域’、章名意義的‘致思問題’、節(jié)名意義的‘語義概念’是中國哲學(xué)現(xiàn)實學(xué)理形態(tài)的主體質(zhì)素要件。論域、問題、概念的等差層階,堅實地組構(gòu)并支持著中國哲學(xué)大系及其學(xué)科理念運動的法則性。論域、問題、概念是哲學(xué)的形態(tài)質(zhì)素,也是哲學(xué)之為學(xué)科合法性的實體部件”。這是說根據(jù)“論域”劃分板塊,而以“問題”構(gòu)成不同的致思路徑,以“概念”區(qū)分語義。論域、問題、概念就不僅成為構(gòu)成橫斷面的《中國哲學(xué)》板塊與板塊、章與章、節(jié)與節(jié)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且它們又縱貫性地是論域、致思、語義間相互聯(lián)系的環(huán)節(jié)。陸教授嚴厲批判無視中國哲學(xué)現(xiàn)實學(xué)理形態(tài)存在的錯誤看法,以及那種輕鄙中國哲學(xué)研究者和教學(xué)者的不適之言。他說:“人們似乎不應(yīng)該設(shè)想某個民族國家的哲學(xué)史不合法的問題,倘若執(zhí)意擬設(shè)這一表示少數(shù)哲學(xué)工作者奇思妙想的‘問題’,那就需要等待他們拿出地球表面確實存在著‘生活著而無思想’的人類證據(jù),同時還需要回答地球表面以思想為本質(zhì)的哲學(xué)是否必要與某洲某國哲學(xué)相一致的終極難題!”.
此外,《中國哲學(xué)》還有兩大特點:一是特別突出中國哲學(xué)是關(guān)于智慧之思的學(xué)說的思想,二是強調(diào)中國哲學(xué)的美識論和倫理觀。陸教授在很多地方談到中國哲學(xué)或哲學(xué)的根本屬性問題。如其云:“哲學(xué)的本質(zhì)是思想”(第17頁);“哲學(xué)昭示著民族國家的理論智思”(第28頁);“中國哲學(xué)即是……中華民族理性思維的智慧之學(xué)”(第1頁);哲學(xué)是“精致的概念思維的學(xué)科”(第16頁),還說:“哲義涵攝主體思維認知與經(jīng)典認知與經(jīng)由認知致取的知識智慧”(第13頁),等等。最后,他仍是將中國哲學(xué)還原為一般哲學(xué):“中國哲學(xué)就是哲學(xué)國際一般意義下悠久輝煌的傳統(tǒng)的國別哲學(xué)”(第17頁)。中國哲學(xué)是否突出知i只問題,有不同認識。但陸教授突出此點是有原因的。一是他認為中國哲學(xué)也只是“哲學(xué)的國際一般",一般哲學(xué)注重知識,當(dāng)然中國哲學(xué)也理應(yīng)如此;二是陸教授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南宋的四書學(xué)”,其自然接受朱子解《大學(xué)》的方式。關(guān)于中國哲學(xué)的美識論和倫理觀兩板塊占了全書下冊,近三百頁。作者認為,“美識論是中國哲學(xué)學(xué)理形態(tài)的審美之域”(第21頁)。倫理觀的根本是如何實現(xiàn)社會公正的問題。“實現(xiàn)社會公正是領(lǐng)導(dǎo)主體對于社會進步的公共職責(zé)”(第494頁)。如果說美識論稍多地關(guān)注到道家與佛教的話,那么,倫理觀中更多闡釋和介紹的是儒家的倫理觀。
第3篇
本次會議還特別就中國哲學(xué)書寫范式的轉(zhuǎn)換與革新,從哲學(xué)、哲學(xué)史、學(xué)術(shù)史、詮釋學(xué)、經(jīng)學(xué)史、少數(shù)民族哲學(xué)、中西馬哲學(xué)的互動等角度和視野作出討論,體現(xiàn)出中國哲學(xué)界中青年學(xué)者的最新思考與推進。吳根友梳理和討論了“哲學(xué)”、“哲學(xué)史”、“明清哲學(xué)”三大方面問題。在“哲學(xué)”的問題上,他指出“哲學(xué)”的根基在于形而上學(xué),其主要方式在于通過概念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其次,在“(中國)哲學(xué)史”的問題上,他回顧和總結(jié)了各門各派的哲學(xué)史方法論,主張在回歸哲學(xué)本性的基礎(chǔ)上融會諸家,中西對比,包容開放,顯豁特色,從而展望哲學(xué)史的重寫工作。最后,在“明清哲學(xué)史”的問題上,他回顧了蕭萐父、侯外廬等人建立明清哲學(xué)史研究范式的意義與價值,同時思考了其中的某些困難,指出我們應(yīng)該從世界歷史、人類文明發(fā)展史的角度審視明清哲學(xué)。李承貴考察了20世紀中國哲學(xué)界在“以西釋中”主流導(dǎo)向之下,許多學(xué)者其實一直在進行“以中釋中”或“自我詮釋”、“自我認知”的工作。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比最近20年中國哲學(xué)界對“自我詮釋”的片面崇拜要來得富有成果。林安梧闡發(fā)了他對“《論語》及其本體詮釋學(xué)的思維”的思考;另外,他還指出學(xué)界應(yīng)努力發(fā)掘與運用傳統(tǒng)經(jīng)典中帶有生活性的話語,從而不斷地讓“道”、“言”、“人”進行良性多元的互動,最終促進中國哲學(xué)新的話語方式的生成。景海峰對“儒家與”的關(guān)系做出歷程性回望,指出當(dāng)代中國哲學(xué)學(xué)界應(yīng)作“大寫的中國哲學(xué)”思考,也即中國哲學(xué)與當(dāng)下中國的處境應(yīng)深度關(guān)聯(lián)起來,而不僅僅局限在“小寫的中國哲學(xué)”即學(xué)科分工下的中國哲學(xué)史研究中,從事大寫的中國哲學(xué)特別是儒學(xué)的思考與思辨,必定離不開中、西、馬三家哲學(xué)的良性互動。據(jù)此,他力主透過生活實踐之場的巨大能量與作用,超化中、西、馬哲學(xué)因相互隔閡而造成的對立之勢,展望未來中國哲學(xué)可能的健康發(fā)展。郭曉東的主題發(fā)言是“經(jīng)學(xué)與中國哲學(xué)史研究”,他思考一百多年來中國學(xué)界通過西方哲學(xué)范式處理中國思想資料所造成的負面效果,努力展示出經(jīng)學(xué)與經(jīng)學(xué)研究的合法性,揭示出經(jīng)學(xué)研究的缺席對中國哲學(xué)史研究所造成的某些問題與困境。蔣國保對“重寫學(xué)術(shù)史”的問題作出前瞻性建議。他分析了“學(xué)術(shù)”與“知識”的關(guān)系,指出學(xué)界將來重寫學(xué)術(shù)史宜從“元學(xué)術(shù)史”即知識的成因、產(chǎn)生、積累、擴展、變革的角度闡發(fā),這樣才能將學(xué)術(shù)史與思想史區(qū)別開來。學(xué)術(shù)史研究的是思想化為知識,而各專門史包括思想史則研究知識化的思想。蕭洪恩報告了“民族哲學(xué)研究與中國哲學(xué)未來之路”,指出未來中國哲學(xué)的書寫理應(yīng)融入中國少數(shù)民族哲學(xué),并最終形成涵蓋各民族哲學(xué)的中華民族哲學(xué)史的新傳統(tǒng)。除上述內(nèi)容外,孫邦金、鄧輝、周海春等與會學(xué)者還就另外一些相關(guān)論題作出獨到的探析。
二、中國哲學(xué)史的具體性研究
除了宏觀論述外,與會學(xué)者還通過具體的哲學(xué)史研究,直接或間接地與本次會議“中國哲學(xué)書寫范式”的主題形成某種關(guān)聯(lián)。相關(guān)論文涵蓋先秦兩漢哲學(xué)、宋明理學(xué)、明清哲學(xué)、近現(xiàn)代哲學(xué)思想等。首先是先秦兩漢的哲學(xué)思想的探索。鄭淑媛著重揭示出先秦儒家“以史養(yǎng)心”的歷史解釋模式,指出先秦儒學(xué)對于歷史的事實敘述與歷史的價值解釋是相通一致的。王林偉通過研究孟子學(xué)中“見性”的問題,指出“見性”的重要意義,認為孟子思想中,見性的整體過程包含有顯性(性由心顯)、養(yǎng)性(盡心成性)、定性(踐形生色)三個步驟。丁四新教授從文獻考證、經(jīng)學(xué)史等角度細致辨析了西漢時期《周易》經(jīng)學(xué)地位的抬升過程,并且逐一分析了西漢易學(xué)的三個主要問題,也即《周易》的立經(jīng)、《周易》經(jīng)學(xué)從“師法”到“家法”的轉(zhuǎn)變以及《周易》從卜筮到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的轉(zhuǎn)變問題;他還辨析了西漢易學(xué)與帛書《易傳》的關(guān)系,討論了兩漢易學(xué)中的仿《易》之作。其次是宋明理學(xué)研究。林宏星分析朱子對于道德動機的觀點,指出朱子將道德行動的主體歸為心,此心具有認知、情感、欲求三層面內(nèi)容。這三個層面中,認知具有首出、導(dǎo)引性意義,并通于情感、欲求,因此朱子的道德認知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內(nèi)在的實踐性,并包含有發(fā)動道德行動的動力與欲求。故朱子關(guān)于道德動機的理論乃是一種“認知內(nèi)在論”。不過,他繼續(xù)考察朱子的心的結(jié)構(gòu),指出在朱子理學(xué)中,道德認知其實并不一定會引發(fā)道德情感并落實為道德行動。劉樂恒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梳理程頤(伊川)理學(xué)中的性情關(guān)系問題,指出伊川理學(xué)中蘊涵著兩種“對比性”。但無論哪一種對比性都不能如牟宗三先生那樣證成伊川理學(xué)中性與情、理與氣等兩兩對比之物可以截然分開。姚才剛關(guān)注劉宗周的“改過”說及其倫理義涵,認為“改過”說揭示出人們應(yīng)該體知到人性本身的陰暗面,并揭示出人們應(yīng)該樹立終生改過的意識。問永寧具體梳理了明末學(xué)者、易學(xué)家黎遂球的易學(xué)思想與解易方法,對之作出定位與反思。再次是明清學(xué)術(shù)研究。李大華從莊子“自然之道”、“游”等概念出發(fā),指出船山解《莊》是要讓莊子自己說話,從而使人感受到船山的解釋毫無隔閡之感;另外他還指出,船山解莊并沒有以儒家立場來批判莊子,或借莊子之說以發(fā)揮其儒家之論,而是本著開放、求知的精神以解莊,使得其《莊子通》一書具有更大價值。鄭朝暉報告他對于清代儒者鄭吉甫關(guān)于“樸學(xué)”的言說的研究,分別從“方法優(yōu)先”、“義解為重”、“閱歷作基”、“自得成家”四方面作出梳理。最后是近現(xiàn)代哲學(xué)思想的具體研究。歐陽禎人報告了“劉咸炘對的態(tài)度”,指出民國學(xué)者劉咸炘分別超越了當(dāng)時西化派和守舊派的局限,融會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及道家的退處無為,對當(dāng)時如火如荼的作冷觀、遠觀的態(tài)度,從而試圖顯豁出劉咸炘學(xué)術(shù)思想的獨特性以及他在文化的思考觀察上的睿識。儲昭華著重疏解了嚴復(fù)由前期主張對中西文化“辨異”走向后期主張“求同”的過程,指出嚴復(fù)思想雖有前后期不同,但其對自由、富強的追求則貫徹其思想的始終;他并指出,我們不能夸大嚴復(fù)前后期思想的不同,當(dāng)今時代應(yīng)“求同”與“辨異”并存。徐水生對比了日本學(xué)者武內(nèi)義雄的《中國思想史》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xué)史》,梳理出武內(nèi)氏《中國思想史》的特色所在,然后辨析其與馮著的若干同異之處。田文軍詳細總結(jié)了張岱年對中國哲學(xué)史學(xué)科建設(shè)的歷史貢獻:首先,張先生是以問題史確立中國哲學(xué)史研究范式的;其次,張先生生前系統(tǒng)地探討了中國哲學(xué)史學(xué);最后,張先生以中國哲學(xué)史史料學(xué)研究完善中國哲學(xué)史學(xué)科體系。他還強調(diào),經(jīng)過張岱年先生的闡發(fā)和努力,中國哲學(xué)史學(xué)科乃形成一個群體或系統(tǒng),而并非單一的中國哲學(xué)史著作所可以概括者。
三、總結(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