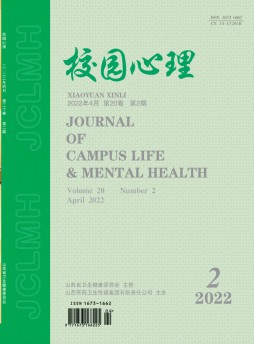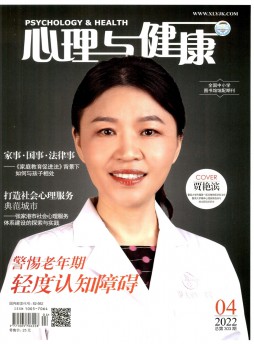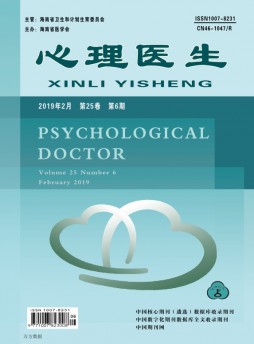心理與心理學(xué)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心理與心理學(xué)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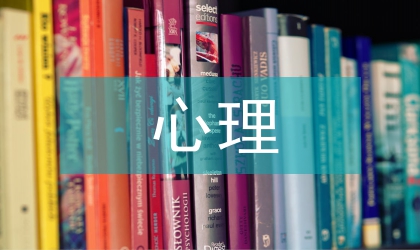
第1篇
在心理學(xué)研究中,主客體都是人,因此主客體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為“我—你”的關(guān)系,伽達(dá)默爾這種“我—你”關(guān)系劃分為三種[1],每一種類型都體現(xiàn)著主體對(duì)客體不同的態(tài)度。(1)第一種類型的關(guān)系是把人(被試)當(dāng)成物,當(dāng)成對(duì)象,用科學(xué)的態(tài)度加以把握,從同類的行為中概括出典型的規(guī)律性認(rèn)識(shí)或類型化的認(rèn)識(shí),以便對(duì)人的行為作出某種預(yù)見和一般的把握。人的行為不過是作為我們把握人性的工具,人變成了一種研究手段,在這里,人的行為與動(dòng)物的行為沒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2)第二種類型的關(guān)系是把人當(dāng)作人,這里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一種反思關(guān)系,而不是人與物的關(guān)系,要求理解者完全排除自身的歷史性與偏見,進(jìn)入到被理解對(duì)象的歷史中,設(shè)身處地的把握與理解對(duì)象。這種關(guān)系過分強(qiáng)調(diào)了被理解者的歷史性,但忽視了理解者自身同樣具有歷史性。(3)第三種類型的關(guān)系是不僅把人當(dāng)作人,而且理解者與被理解者處于一種平等的關(guān)系之中,彼此是開放的,伽達(dá)默爾稱這種關(guān)系是“效果歷史性的關(guān)系”。
根據(jù)這樣的關(guān)系,心理學(xué)研究也可以區(qū)分為“獨(dú)白”的心理學(xué)與“對(duì)話”的心理學(xué)。
一、“獨(dú)白”的心理學(xué)
主客體的關(guān)系是哲學(xué)永恒的話題,心理學(xué)的發(fā)展也是圍繞這條線索展開的。古希臘時(shí)期主客體的關(guān)系是一種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哲學(xué)是代表。從近代的笛卡爾開始,樹立了主體理性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哲學(xué)上奠定了科學(xué)的基礎(chǔ)。近代自然科學(xué)的發(fā)展為心理學(xué)提供了模仿的對(duì)象,在獨(dú)白的心理學(xué)研究中,“我—你”關(guān)系首先表現(xiàn)為“人—物”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為理性的獨(dú)白,追求絕對(duì)的理性,將世界看作是主體理性的附屬。主體是絕對(duì)的控制者和支配者,客體是受支配和被控制的,因此,理性的獨(dú)白也可以稱為主體的獨(dú)白。受19世紀(jì)生物學(xué)與物理學(xué)的影響,心理學(xué)從成為獨(dú)立的學(xué)科開始就致力于模仿自然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是主體設(shè)立起來的知識(shí)框架,目的是用理性控制與支配自然。自然世界是科學(xué)的對(duì)象,即客體,科學(xué)的目的在于使自然以主體語(yǔ)言的形式表達(dá)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就成了理性的獨(dú)白。此時(shí),科學(xué)家面對(duì)的是物,是客觀對(duì)象,由于客觀存在沒有主體性,是完完全全的客體,因此,在針對(duì)自然客觀存在的時(shí)候,這種“獨(dú)白”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心理學(xué)從一開始就陷入到自然科學(xué)的理性獨(dú)白之中。心理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最早是靈魂,從詞源上來理解,"Psychology"(心理學(xué))一詞的意思是指"Psyche—logos"(心理的理念或?qū)W問),也就是關(guān)于靈魂的研究。心理學(xué)首先面對(duì)的是人自身的心靈問題,在心理學(xué)的早期萌芽時(shí)期,心靈問題基本上包含在哲學(xué)研究之中,人們通過反省自己的心靈,通過與別人的交談和交流,共同探討心靈的問題,蘇格拉底將這種方法推向了一個(gè)高峰,這種思想方法被稱為“精神催產(chǎn)術(shù)”,真理就在平等的談話交流過程中顯現(xiàn)出來,但科學(xué)家認(rèn)為這樣的方法缺乏實(shí)證研究,不具有真理性。這種狀況到了近代得到了改觀,自然科學(xué)的發(fā)展為心理學(xué)提供了借鑒的模式。前心理學(xué)中“人—人”的關(guān)系蛻變成了“人—物”的關(guān)系,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用來了解人性的工具,成了物,成了對(duì)象。在這種“人—物”關(guān)系中,理解一個(gè)人和理解一個(gè)典型事件沒有什么本質(zhì)區(qū)別。通過對(duì)同類的行為的理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性,在這個(gè)時(shí)候,同類的行為變成了我們把握人性的工具,僅此而已。在這種研究中,人被物化,完全服從于理性的解釋。在康德看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研究應(yīng)當(dāng)具有倫理性。伽達(dá)默爾也批評(píng)了這種把人對(duì)象化的做法,“這種遵循18世紀(jì)方法論思想和休謨對(duì)此所作的綱領(lǐng)性表述的社會(huì)科學(xué)方法,其實(shí)是一種效仿自然科學(xué)論的陳詞濫調(diào)”[1],如果把人對(duì)象化,勢(shì)必產(chǎn)生對(duì)方法的崇拜。事實(shí)上,科學(xué)心理學(xué)一直致力于研究方法的精巧化,注重程序性的東西,在研究方法與研究?jī)?nèi)容之間更偏向于研究方法和手段,忽略了研究的現(xiàn)實(shí)性與內(nèi)容性。
“獨(dú)白”的心理學(xué)追求對(duì)心理的形式化解釋,用對(duì)心理行為的研究代替了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人與人關(guān)系的研究,用對(duì)理性思想的研究代替了對(duì)現(xiàn)實(shí)個(gè)體與人群的研究。注重心理的結(jié)構(gòu)與形式,忽略了作為心理行為的實(shí)際生活內(nèi)容。為了完成對(duì)心理行為的形式化的解釋,“獨(dú)白”式的心理學(xué)對(duì)科學(xué)方法有一種渴望,將科學(xué)方法運(yùn)用于心理經(jīng)驗(yàn),包括那些超出科學(xué)方法論控制范圍的對(duì)真理的經(jīng)驗(yàn),如個(gè)體的心理生活、文化經(jīng)驗(yàn)。如果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科學(xué)方法不適用于這些經(jīng)驗(yàn),就把這些經(jīng)驗(yàn)排除在研究之外,帶有強(qiáng)烈的“方法中心”的情結(jié)[2]。往往采用以偏概全的研究手法,用個(gè)案的研究來證明普遍的真理,用歸納法揭示普遍的原理,這是一種證實(shí)的過程,這樣的作法遭到了科學(xué)哲學(xué)家波譜的批評(píng)。心理學(xué)過分追求形式化的解釋與自然科學(xué)的精神有關(guān),自然科學(xué)遵循三大研究原則,即,自然一致性原則;實(shí)體原則;因果性原則。自然一致性原則認(rèn)為事物的變化是有規(guī)律的,這種規(guī)律適用于所有的對(duì)象,即不管怎樣,事物現(xiàn)象背后存在著共同遵守的規(guī)律。科學(xué)的目的就是去解釋普遍的規(guī)律,即使研究具體的對(duì)象,目的也是試圖用個(gè)別的實(shí)例去證明和補(bǔ)充普遍法則。實(shí)體原則認(rèn)為在事物之外存在著一種實(shí)體,這種實(shí)體實(shí)質(zhì)上就是事物的一種模型,是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以自然科學(xué)觀的視角看,不同學(xué)科都有不同的實(shí)體概念,例如,就社會(huì)學(xué)的研究而言,“社會(huì)”就是一個(gè)實(shí)體,就心理學(xué)的研究而言,實(shí)體就是“心理”。在這里,實(shí)體就是建立在個(gè)別基礎(chǔ)上的一般普遍性。因果性原則表達(dá)了一種現(xiàn)象之間的連續(xù)關(guān)系,一旦確定兩個(gè)或兩類事件之間存在一種因果聯(lián)系,那么就可以肯定相同的原因會(huì)產(chǎn)生相同的結(jié)果,即同因必然產(chǎn)生同果。堅(jiān)持因果性的原則導(dǎo)致將心理生活的主觀理解性與體驗(yàn)性抹煞,使心理生活成為一種客觀經(jīng)驗(yàn)的存在,成為可以共證的對(duì)象。回顧近現(xiàn)代科學(xué)心理學(xué),很大程度上是在“獨(dú)白”的狀態(tài)下發(fā)展的。無論是邏輯經(jīng)驗(yàn)主義,還是邏輯實(shí)證主義,都過分強(qiáng)調(diào)研究的客觀性,觀察的中立性,而語(yǔ)義模型理論則突出了研究者的邏輯演繹,更沒有考慮到對(duì)象的主體性。艾賓浩斯為了研究人類記憶奧秘,在實(shí)驗(yàn)室里用一些無意義音節(jié)組成的學(xué)習(xí)材料替代有意義的現(xiàn)實(shí)的學(xué)習(xí)材料,排除或忽略了被試的主觀感受,諸如情緒、體力、動(dòng)機(jī)、興趣等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得出了關(guān)于人類的遺忘規(guī)律,顯然,這樣的結(jié)論并不具有普遍的解釋效果。赫爾試圖完全用數(shù)學(xué)的推理來解釋和預(yù)測(cè)人類的行為。學(xué)習(xí)心理學(xué)家桑代克用對(duì)白鼠的研究解釋了人類學(xué)習(xí)的三大定律,托爾曼在實(shí)驗(yàn)室通過對(duì)白鼠學(xué)習(xí)情況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了人類的“潛伏學(xué)習(xí)”。斯金納也是試圖把實(shí)驗(yàn)室的強(qiáng)化理論運(yùn)用到整個(gè)人類行為的解釋上。同樣的,現(xiàn)代認(rèn)知心理學(xué)也試圖通過電腦對(duì)人腦的模擬來揭示思維的機(jī)制。這些都是一種“獨(dú)白”的行為,因?yàn)樵谶@些研究中,主體與客體是分裂的,是“人—物”的關(guān)系,二者是處于對(duì)立之中的。
“獨(dú)白”的心理學(xué)過分夸大了作為研究者的主體的地位。在自然科學(xué)研究中,科學(xué)家是絕對(duì)的主體,自然物是絕對(duì)的客體,自然物是統(tǒng)一在主體理性的范疇中,是用主體理性的語(yǔ)言來表達(dá)的。心理學(xué)家將這樣的研究模式運(yùn)用到心理學(xué)的研究中,心理學(xué)家變成了絕對(duì)的主體,被研究的人成了絕對(duì)的客體,在實(shí)驗(yàn)研究中尤為如此。心理學(xué)家強(qiáng)調(diào)自身的主體性,忽略了被研究者的主體地位,將被試視為一種模型化的存在,把被試從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關(guān)系中分裂出來,實(shí)行價(jià)值中立。在很大意義上,被試變成了一種符號(hào),一種普遍規(guī)律的個(gè)別表征。心理學(xué)家用理論模型對(duì)生活世界加以解釋和說明,他們遵循的是因果原則,通過世界事實(shí)的模型,對(duì)生活世界進(jìn)行預(yù)測(cè)和控制。在這個(gè)意義上,心理學(xué)家進(jìn)行的研究工作是一種“獨(dú)白”,沒有考慮到被研究者的感受、社會(huì)背景、需要與動(dòng)機(jī),沒有考慮到個(gè)體與群體的心理生活,一切都服從于研究者的程序,而研究者又服從于理性的規(guī)范,服從于理性的“獨(dú)白”。美國(guó)心理學(xué)是這一現(xiàn)實(shí)的代表,研究者在科學(xué)的研究程序中得出了結(jié)論,然后把這些理論無論制地推廣到其他社會(huì)和民族,用以解釋所有的個(gè)體與群體,忽視了理論解釋效能的文化差異性與有限性。研究者一廂情愿地為所有人、所有行為構(gòu)筑統(tǒng)一的心理模式,這樣顯然夸大了研究者的主體地位。理性的“獨(dú)白”由此蛻變成研究者的“獨(dú)白”。
在“獨(dú)白”的心理學(xué)中,“我—你”關(guān)系還表現(xiàn)出另一種形式,即“你”被承認(rèn)為一個(gè)人,而不是物。在這種關(guān)系中,要求“我”必須完全排除自身的歷史性和偏見,客觀地了解“你”,還“你”真實(shí)的面目。這實(shí)際上犯了19世紀(jì)施萊爾馬赫與狄爾泰的歷史主義的錯(cuò)誤,因?yàn)樗鲆暳恕拔摇北旧淼臍v史性,在這樣的關(guān)系中,主體是在完全“傾聽”客體,是另一種形式的“獨(dú)白”。這種關(guān)系在本土心理學(xué)的研究中尤為典型。如在中國(guó)本土心理學(xué)研究中,就存在著這樣的“獨(dú)白”。本土心理學(xué)是在反對(duì)心理學(xué)研究?jī)r(jià)值中立的浪潮中興起的一股新興力量,中國(guó)人意識(shí)到依靠國(guó)外的心理學(xué)理論是難以解釋本土民眾的心理生活的,于是紛紛拿起傳統(tǒng)文化的武器與國(guó)外的理論分庭抗禮,他們下意識(shí)地將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視為兩個(gè)實(shí)體,要么是外來文化,要么就是本土文化。近幾年有的學(xué)者致力于尋訪傳統(tǒng)概念,從古籍中挖掘傳統(tǒng)概念,用傳統(tǒng)概念來闡釋現(xiàn)代人的生活,還花費(fèi)大量時(shí)間與精力考證傳統(tǒng)概念的原始意義,力圖還原這些傳統(tǒng)概念的原初意義,仿佛不用本土的傳統(tǒng)概念來解釋本土生活,那就不成其為本土化。這樣做,實(shí)際上又陷入到了“獨(dú)白”的研究當(dāng)中,這種“獨(dú)白”不是主體理性的獨(dú)白,而是文本或?qū)ο蟮莫?dú)白,是主體對(duì)客體的完全“傾聽”,是狄爾泰的歷史主義的重演。狄爾泰的歷史主義要求研究者完全進(jìn)入到歷史文本之中,忘掉自我,徹底的以一種還原歷史的態(tài)度進(jìn)行研究。這其實(shí)又走到了另一個(gè)極端,即主體的喪失。在本質(zhì)上,這仍然造成了主客體的分離。在實(shí)際的理解過程中,要作到主體的“遺忘”是不可能的。本土心理學(xué)研究的目的不是尋訪傳統(tǒng)概念,而是闡釋當(dāng)代人的心理體驗(yàn)與感受。只有采取“對(duì)話”的形式,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在本土與非本土之間才能達(dá)成融合。
可以看出,“獨(dú)白”的心理學(xué)實(shí)質(zhì)上是錯(cuò)誤地理解了主客體的關(guān)系,遵循的是主客體的二分法,沒有將二者真正地融合起來,要么是主體理性的自言自語(yǔ),要么就是完全受制于客體。心理學(xué)研究要做到主客體的融合,就必須改變研究方式,從“獨(dú)白”走向“對(duì)話”
二、“對(duì)話”的心理學(xué)
在“對(duì)話”的心理學(xué)研究中,“我—你”關(guān)系既不是“人—物”的關(guān)系,也不是“人—人”的單向度關(guān)系,而應(yīng)當(dāng)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平等和相互開放的關(guān)系,即伽達(dá)默爾的“效果意識(shí)”[3]。所謂效果意識(shí),是指在主客體的交互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了新的意義,這種意義既不完全屬于主體,也不完全屬于客體,而是雙方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在這種關(guān)系中,主體與客體都沒有“獨(dú)立意識(shí)”,也沒有“依賴意識(shí)”,二者是一種對(duì)話的關(guān)系,主體不排除自身的歷史性,客體也不排除自身的歷史性,兩者的歷史性在對(duì)話中得到新的詮釋,而這種新的詮釋恰恰是我們應(yīng)該研究的對(duì)象或目的,即效果現(xiàn)實(shí)性。在對(duì)人的研究中并不存在著主客體,只有二者的相互作用,即相互理解,強(qiáng)調(diào)在“參與”或交互作用中去獲得真理或意義。伽達(dá)默爾在哲學(xué)上進(jìn)行了一次變革,既批判了西方近代哲學(xué)以來過度膨脹的主體性,也批判了歷史客觀主義,重新界定了主客體關(guān)系,這為反思心理學(xué)的研究提供了哲學(xué)上的依據(jù)。“對(duì)話”的心理學(xué)首先要排除理性的“獨(dú)白”,避免“人—物”關(guān)系的自然科學(xué)模式,不再把人當(dāng)作理解人性的工具,而是把人當(dāng)作目的。主體有自身的歷史性和前見,客體也有自身的歷史性和前見,在心理學(xué)研究中,心理學(xué)家不是絕對(duì)的主體,被試也不是絕對(duì)的客體,被試不是符號(hào),他具有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背景,有真實(shí)的動(dòng)機(jī)、興趣、情感等等。在研究中,主試與被試的關(guān)系是一種平等和彼此開放的關(guān)系,主試不是試圖去將被試的個(gè)別特征抽象為普遍的法則,而是理解被試的行為,在具體的歷史關(guān)系中理解被試,不夸大主體的地位。研究者主動(dòng)地參與所要認(rèn)識(shí)的對(duì)象,既不過分突出主體性,但也不能使主體性喪失。當(dāng)主體試圖去理解對(duì)象時(shí),一方面,主體自身帶著“有色眼鏡”,另一方面,對(duì)象也同樣生活在歷史性之中,當(dāng)進(jìn)入研究時(shí),二者便開始了一種平等對(duì)話和彼此理解的過程。事實(shí)上,在心理學(xué)理論的產(chǎn)生過程中,這種現(xiàn)象一直伴隨著心理學(xué)家。心理學(xué)的研究在本質(zhì)上就是“我—你”的交互作用過程。如美國(guó)的心理學(xué)家,他們是在美國(guó)的本土文化中成長(zhǎng)起來的,他們自身就是文化的產(chǎn)物,因此他們的理論明顯帶有美國(guó)文化的印痕。但同時(shí),他們又是美國(guó)文化的解讀者,正是這兩層關(guān)系造就了美國(guó)心理學(xué)。中國(guó)的心理學(xué)也是如此,當(dāng)外來理論進(jìn)入本土文化以后,不管意識(shí)到?jīng)]有,本土化就已經(jīng)開始了,而不是如現(xiàn)在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的那樣:本土化必須是有意識(shí)的,有目的的。在本質(zhì)上,心理學(xué)就是本土心理學(xué),因?yàn)橹黧w與對(duì)象之間永遠(yuǎn)都是一種相互理解的過程。個(gè)體的心理生活是個(gè)體對(duì)世界的主觀把握和體驗(yàn),它始終處于一種“視域融合”的狀態(tài)。所謂視域融合,是指?jìng)€(gè)體的心理生活既不完全是過去的經(jīng)驗(yàn)形成,也不完全是當(dāng)下的生活體驗(yàn)與理解,而是一種現(xiàn)在與過去的交融。換句話說,心理生活不是一種靜止的實(shí)體,而是個(gè)體生活經(jīng)驗(yàn)的融合,個(gè)體心理生活的現(xiàn)實(shí)性體現(xiàn)在經(jīng)驗(yàn)的交互融合之中。有的學(xué)者提出必須建立中國(guó)人自己的心理學(xué),實(shí)現(xiàn)徹底的本土化,其實(shí)他們沒有意識(shí)到,本土化的進(jìn)程從一開始就一直伴隨著他們的研究。我們理解中的外來理論已經(jīng)超出了它們的原初意義,我們?cè)诮邮芩鼈兊臅r(shí)候,已經(jīng)自覺地把它們納入到我們的認(rèn)識(shí)范疇之中了。就如同翻譯語(yǔ)言,當(dāng)一種語(yǔ)言被翻譯成另一種語(yǔ)言時(shí),它的意思就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了,既不是前一種語(yǔ)言的完全再現(xiàn),也不是后一種語(yǔ)言的自言自語(yǔ),而是兩種語(yǔ)言的融合。因此在這個(gè)意義上,中國(guó)心理學(xué)的本土化從西方理論進(jìn)入中國(guó)就已經(jīng)開始了,而不是明確提出中國(guó)心理學(xué)本土化的20世紀(jì)80年代。
“對(duì)話”的心理學(xué)應(yīng)當(dāng)拋棄對(duì)心理行為的形式化解釋,避免用抽象的原則來替代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對(duì)話”的任務(wù)是理解,不是解釋或說明,“獨(dú)白”則是試圖去說明對(duì)象,用主體的語(yǔ)言來規(guī)范對(duì)象。在研究個(gè)體心理生活的時(shí)候,“對(duì)話”尤為重要。人的經(jīng)驗(yàn)有兩種,一種是生活的經(jīng)驗(yàn);一種是科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生活的經(jīng)驗(yàn)是個(gè)體的主觀感受,是不可重復(fù)的,具有一次性和歷史性。科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則是可以重復(fù)的,在適當(dāng)?shù)臈l件下可以重現(xiàn)。對(duì)人來說,更根本的是生活經(jīng)驗(yàn),雖然這不是科學(xué)本身,但卻是科學(xué)的前提。人們最先接觸的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意義是一切科學(xué)認(rèn)識(shí)的基礎(chǔ)與前提。隨著科學(xué)認(rèn)識(shí)的發(fā)展,科學(xué)世界與生活世界成了兩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領(lǐng)域。科學(xué)的實(shí)踐與運(yùn)用促使科學(xué)認(rèn)識(shí)獲得不同于生活世界的意義的地位,從而使科學(xué)世界的意義支配和指導(dǎo)著生活世界的一切。心理生活是個(gè)體對(duì)世界的一種主觀把握和體驗(yàn)[4],因此,對(duì)待人的心理生活,應(yīng)該理解心理生活是怎樣形成,從而理解它的當(dāng)下狀態(tài),而不應(yīng)該試圖為個(gè)體心理生活建立原則性的規(guī)定。不同個(gè)體的心理生活是有差異的,如果一定要認(rèn)為個(gè)體心理生活有共同點(diǎn),那么這種共同性就是不同個(gè)體面對(duì)的相同情境。在這個(gè)意義上,個(gè)體心理生活是具有共通性的,但僅此而已。也就是說,心理生活的本體意義體現(xiàn)在個(gè)體與文化以及個(gè)體之間、個(gè)體與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中,它并不抽象地存在于“某地”或“某時(shí)”。在本土心理學(xué)的研究中,的確存在這樣的問題,例如,研究“古人心理”、“集體主義”、“民族性”等課題,這些課題本身并不具體。抽象化的研究目的是為這些命題尋找一種共性,而不是去理解具體的人群與個(gè)體對(duì)這些命題的注解。社會(huì)—?dú)v史的經(jīng)驗(yàn)是不能以自然科學(xué)的歸納程序而提升為科學(xué)的,而應(yīng)該在現(xiàn)象的一次性與歷史性的具體關(guān)系中去理解現(xiàn)象本身。自然科學(xué)的普遍性原則只適用于宏觀層次,而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存在,具有不可預(yù)測(cè)性,因而不具有被控制性。研究心理生活的目的不是尋求普遍原則,而是強(qiáng)調(diào)“理解”,不是急于建立理論體系,而是解決具體的現(xiàn)實(shí)問題。要面對(duì)具體情境中的具體人群,理解與闡釋他們的心理生活,不應(yīng)該為心理生活尋求普遍性。在心理生活領(lǐng)域,只能“理解”,而不能預(yù)測(cè)與控制。人是歷史性或時(shí)間性的存在,海德格爾將這種存在稱為“此在”,即人在世界上或社會(huì)中存在的這一事實(shí)本身,它具有時(shí)間流動(dòng)性。每一個(gè)體都在時(shí)間的流動(dòng)性中存在,換句話,每個(gè)人都有歷史性,而且具有不可重復(fù)性。因此,在理解個(gè)體時(shí),必須將個(gè)體置于具體的情景之中,充分考慮他們的現(xiàn)實(shí)性。本土心理學(xué)在研究心理生活時(shí),必須確定心理生活是一種連續(xù)性,不能還原為單個(gè)的片斷。
“對(duì)話”的心理學(xué)還強(qiáng)調(diào)研究的整體性。“獨(dú)白”的心理學(xué)是將人類活動(dòng)孤立地置于某處,用“標(biāo)本式”的方式加以研究,目的在于從每一個(gè)單獨(dú)的事件中尋找到他們彼此的聯(lián)系。這樣直接導(dǎo)致了心理學(xué)研究陷入到了方法與程序的泥潭,也使心理學(xué)的學(xué)科統(tǒng)一性受到了嚴(yán)重的危害。“對(duì)話”的心理學(xué)主張采用整體性原則,將個(gè)體的活動(dòng)與行為置于社會(huì)、歷史、文化之中。因?yàn)椋环矫妫瑐€(gè)體是社會(huì)、文化和歷史的塑造者,另一方面,個(gè)體也是社會(huì)、文化和歷史的產(chǎn)物。要理解個(gè)體的心理行為及心理生活,就必須了解整個(gè)文化與時(shí)代的特征,反過來,要理解文化與時(shí)代,也必須了解個(gè)體。20世紀(jì)50年代以前,心理學(xué)史主要是按編年史的體裁撰寫,主要涉及政治、外交和軍事等方面的情況,主要講述大人物和大事件,更多地考慮了宏觀面,是“自上而下的歷史”,俗稱“舊史”。20世紀(jì)50年代以后,這種狀況發(fā)生了變化,“新史”出現(xiàn)了,它是“自下而上的歷史”,試圖描述被舊史所忽視的無名群眾的個(gè)人生活[5]。這種變化體現(xiàn)了一種趨勢(shì),即整體性的研究趨勢(shì),在整體中,局部是理解整體的條件,同時(shí)整體又是更好地理解局部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人類的實(shí)踐活動(dòng)是一個(gè)整體性的活動(dòng),心理學(xué)應(yīng)該在現(xiàn)實(shí)的總體性聯(lián)系中探討心理現(xiàn)象與心理生活,突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相互影響。
20世紀(jì)后期,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沖擊著人們的傳統(tǒng)觀念,進(jìn)入90年代,在西方漸漸興起一種新的心理學(xué)思潮,即后現(xiàn)代主義的心理學(xué)。后現(xiàn)代主義心理學(xué)以反對(duì)實(shí)證主義心理學(xué)為目標(biāo),主張?jiān)谛睦韺W(xué)的研究中拋棄傳統(tǒng)的二元主義認(rèn)識(shí)論,擺脫實(shí)證主義那種“標(biāo)本式”的研究,強(qiáng)調(diào)采用辯證的方法,突出人的社會(huì)性和現(xiàn)實(shí)性。可以看出,在心理學(xué)研究中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話”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對(duì)話”是心理學(xué)發(fā)展的方向,也是心理學(xué)重新樹立在社會(huì)文化和心理生活中的權(quán)威和地位的必經(jīng)之路。
參考文獻(xiàn)
[1] 伽達(dá)默爾.真理與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2] 周寧.本土心理學(xué)與心理學(xué)的本土化問題[J].西北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1,(4).
[3] 洪漢鼎.理解的真理[M].濟(jì)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第2篇
禪學(xué),是佛教禪定之學(xué)的通稱,包括禪宗之學(xué)在內(nèi)。禪定在佛教修持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小乘“戒、定、慧”三學(xué)實(shí)際上是以禪定為中心,禪定貫徹三學(xué)中最重要的定、慧二學(xué),大乘六度中禪那、般若二度,禪宗“見性成佛”與密乘“即身成佛”之道也無不是統(tǒng)攝于禪。佛教認(rèn)為,通過“禪”的修習(xí),可以“探究身心世界之奧秘,認(rèn)識(shí)自己,開發(fā)本性潛能,激發(fā)出般若智慧,解脫以生死為中心的一切系縛,解決人本性中絕對(duì)自由之追求與客觀現(xiàn)實(shí)的矛盾,達(dá)到常樂我凈的彼岸,從而凈化人心,莊嚴(yán)國(guó)土”。
狹義的心理健康是指預(yù)防和治療各種心理障礙、心理疾病;廣義而言是指維護(hù)和增進(jìn)心理健康,培養(yǎng)健全人格,提高人類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適應(yīng)和改造能力。
探討佛教禪學(xué)和心理健康之關(guān)系,首先要區(qū)分兩個(gè)問題:第一,佛教禪學(xué)對(duì)心理發(fā)展有什么樣的作用,其發(fā)生機(jī)制又是如何;第二,能否把佛教禪學(xué)應(yīng)用到我們?nèi)粘I钪校鳛轭A(yù)防、治療各種心理疾病、維護(hù)心理健康的方法。
禪定對(duì)心理發(fā)展的影響
佛教一向重視“心”的作用,《華嚴(yán)經(jīng)》中“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被視為佛法心要的高度概括。在佛教看來,我們內(nèi)在身心乃至外在山河大地,無非都是因?yàn)樾乃斓臉I(yè)力所成。大乘經(jīng)總結(jié)為“萬法唯心”,宣稱世間三界五道、出世間的聲聞、獨(dú)覺皆是由心而生。然而,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三界,一切眾生的心都被無明所覆,產(chǎn)生貪、癡諸種煩惱,而有生老病死等無盡的苦果。在這種認(rèn)識(shí)背景下,佛教提出了“自知其心”、“自宰其心”、“自凈其心”的心理發(fā)展路線,而達(dá)到解脫的終極目標(biāo)。禪定正是佛教知心、宰心、凈心的具體實(shí)踐。如大乘《解深密經(jīng)》卷三說:“一切聲聞及如來等,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當(dāng)知皆是此奢摩他毗婆舍那(止觀)所得之果。”通過禪定的修習(xí),人可以如實(shí)了知心的體性、本質(zhì)、各種功能,進(jìn)而學(xué)會(huì)控制自己的心靈,將之凈化,最終達(dá)到常樂我凈的解脫境界。
為什么禪定能有如此大的力量來改變心靈呢?按佛教的解釋,這種力量是我們的心本來具有的,禪定只是用來激發(fā)這種力量的工具。這種力量,佛教解釋為“般若”,即出世間的智慧,分為聞、思、修三種。其中最重要的修慧,就是通過禪定的修習(xí)而證到的如實(shí)智、自然智。只有激發(fā)出出世間的般若智慧,才能真正證得“心”的本性,進(jìn)而自凈其心。小乘三學(xué)、大乘六度,乃至禪宗定慧一體之禪,無不是圍繞這點(diǎn)展開的。
禪法在心理健康中的運(yùn)用
心理學(xué)的快速發(fā)展推動(dòng)了人們對(duì)自己心理探索的渴求,此時(shí)人們突然發(fā)現(xiàn),早在人類古老的過去,東方就流傳著心靈鍛煉和探究的特殊方法。東方的瑜伽、氣功、禪等散發(fā)出神秘誘人的氣息,吸引著空虛繁忙的現(xiàn)代人。于是,一些學(xué)者試圖把佛教禪法應(yīng)用于心理保健中,從東方古老的智慧中尋求現(xiàn)代人心靈保健的良藥。
佛教的禪法有其嚴(yán)整次第的體系,在修習(xí)禪定之前還應(yīng)具備種種條件,并不是人人均可修習(xí)。《修習(xí)止觀坐禪法要》中說,修習(xí)止觀(禪定)的人,要先具備五種條件:即持戒清凈、衣食俱足、得閑居靜處、息諸緣務(wù)、近善知識(shí)。可以理解為具備身心的健康、一定的物質(zhì)基礎(chǔ)、安靜的修習(xí)環(huán)境、充足的修習(xí)時(shí)間、真正懂得禪法的老師指導(dǎo)這五個(gè)條件。在當(dāng)今時(shí)代,其中很多條件都不易滿足。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緊張繁忙,使人們難得擁有安靜的心理環(huán)境和充足的時(shí)間。現(xiàn)代人的身心健康狀態(tài)也不容樂觀,環(huán)境污染、人炸、不良的生活嗜好,造成種種身心疾病的泛濫。如果沒有親身體驗(yàn)過禪定的修習(xí),如何能指導(dǎo)別人修習(xí)呢?從這些條件中,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佛教禪定的修習(xí)以最終覺悟人生為目標(biāo),因此它的起點(diǎn)就很高、很嚴(yán)格。而我們想要達(dá)到的目的是治療心理疾病、維護(hù)心理的健康、提高現(xiàn)代人的心理適應(yīng)能力。二者的目標(biāo)雖然都是提升心理層次,都是向內(nèi)的探究,但畢竟仍是有質(zhì)的差異。從現(xiàn)代心理保健角度看,心理的健康指在身體、智能以及情感上,在與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圍內(nèi),將個(gè)人心理發(fā)展成最佳的狀態(tài)。在佛教看來,這些正是修習(xí)禪法的基本條件,而且僅僅是高樓大廈的基礎(chǔ)而已。
第3篇
學(xué)校心理學(xué)是心理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學(xué)校心理學(xué)是學(xué)者們研究的熱門領(lǐng)域,近幾年來學(xué)校心理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由原來對(duì)學(xué)生的關(guān)注逐漸增加了對(duì)老師和管理者的關(guān)注,對(duì)學(xué)校心理學(xué)研究的越透徹越有利于教育教學(xué)的展開。隨著研究的深入,學(xué)校心理學(xué)研究的范圍逐漸擴(kuò)大,總結(jié)前人的研究,本文提出學(xué)校心理理論。學(xué)校心理理論不同于學(xué)校心理學(xué),前者關(guān)注的范圍更廣,不僅研究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心理、老師的教學(xué)心理,同時(shí)研究學(xué)生人際交往過程中的心理,以及管理人員管理過程中的心理。雖然學(xué)校心理理論與學(xué)校心理學(xué)都是研究和學(xué)校有關(guān)的心理學(xué),但是二者存在顯著的區(qū)別,明確二者的區(qū)別對(duì)進(jìn)一步深入豐富理論研究,同時(shí)進(jìn)一步促進(jìn)實(shí)踐發(fā)展具有重要意思。
1概念界定
1.1學(xué)校心理理論的概念
學(xué)校心理理論是指和學(xué)校生活有關(guān)的各類人員的心理現(xiàn)象的總和。包括學(xué)生學(xué)習(xí)心理,教師教學(xué)心理,工作人員管理心理等眾多方面。學(xué)校心理理論是一個(gè)新的概念,是一個(gè)統(tǒng)稱,涉及面廣,范圍寬。學(xué)校心理理論涉及多門學(xué)科知識(shí),并把多門學(xué)科的知識(shí)進(jìn)行融合,在運(yùn)用到學(xué)校教學(xué)和管理中。
1.2學(xué)校心理學(xué)的的概念
近年來學(xué)校心理學(xué)研究的內(nèi)容由學(xué)生延伸到教師、管理者,學(xué)校心理學(xué)的概念也隨之發(fā)生相應(yīng)變化。學(xué)校心理學(xué)是心理學(xué)與學(xué)校教育實(shí)踐相結(jié)合的結(jié)果,是心理學(xué)應(yīng)用和服務(wù)于學(xué)校的具體表現(xiàn)。它是在發(fā)展心理學(xué)、教育心理學(xué)、臨床心理學(xué)、咨詢心理學(xué)等學(xué)科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是研究教育教學(xué)情境中各類成員的心理活動(dòng),并運(yùn)用心理學(xué)的理論與技術(shù)手段直接或間接地促進(jìn)學(xué)生與其它構(gòu)成成員和諧發(fā)展的一門應(yīng)用性心理學(xué)分支學(xué)科。
2研究?jī)?nèi)容
2.1學(xué)校心理理論的研究?jī)?nèi)容
學(xué)校心理理論主要研究和學(xué)校教育教學(xué)、學(xué)校管理過程中有關(guān)的心理知識(shí),以及如何運(yùn)用這些知識(shí)更好的服務(wù)師生。因?yàn)閷W(xué)校不僅包括教育教學(xué)活動(dòng)還包括管理,人際交往等活動(dòng),每個(gè)涉及的領(lǐng)域都是學(xué)校心理理論研究的內(nèi)容。學(xué)校心理理論的研究對(duì)象包括教育教學(xué)過程中學(xué)生的心理、老師的心理,還包括學(xué)校中各種崗位工作人員的心理。所有在學(xué)校中涉及到的心理現(xiàn)象都是學(xué)校心理理論研究的內(nèi)容。
2.2學(xué)校心理學(xué)的研究?jī)?nèi)容
學(xué)校心理學(xué)主要研究教育教學(xué)過程中學(xué)生的心理,以教育心理學(xué)為其主要研究對(duì)象,研究教學(xué)過程中學(xué)生出現(xiàn)的心理現(xiàn)象,以及針對(duì)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yīng)策略。學(xué)校心理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集中在6~18歲從小學(xué)至高中的學(xué)生群體,更傾向于關(guān)注有心理問題的學(xué)生,學(xué)校心理學(xué)主要研究教育教學(xué)過程中學(xué)生的心理現(xiàn)象以及在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各種心理問題,研究者向教師提供心理知識(shí),便于教師在教學(xué)過程中及時(shí)引導(dǎo)學(xué)生走向正確的方向。
3理論構(gòu)成
3.1學(xué)校心理理論的構(gòu)成
學(xué)校心理理論包括的內(nèi)容很多,主要構(gòu)成如下:知識(shí)學(xué)習(xí)的心理理論、技能學(xué)習(xí)的心理理論、能力培養(yǎng)的心理理論、德育的心理理論、人際交往的心理理論、自我認(rèn)知的心理理論、教學(xué)的心理理論、管理的心理理論、學(xué)生心理輔導(dǎo)。在每個(gè)構(gòu)成方面都涉及到很多心理學(xué)知識(shí),研究者對(duì)這些心理現(xiàn)象進(jìn)行研究,并對(duì)這些心理現(xiàn)象給予反饋。學(xué)校心理理論不僅和發(fā)展心理學(xué)、教育心理學(xué)、臨床心理學(xué)、咨詢心理學(xué)等分支學(xué)科關(guān)系密切,而且也是這些心理學(xué)分支融合的結(jié)果。
3.2學(xué)校心理學(xué)的構(gòu)成
學(xué)校心理理論是心理學(xué)的應(yīng)用分支,是心理學(xué)與學(xué)校教育實(shí)踐相結(jié)合的結(jié)果,是心理學(xué)應(yīng)用和服務(wù)于學(xué)校的具體表現(xiàn)。學(xué)校心理理論雖然也關(guān)注學(xué)校教育領(lǐng)域內(nèi)其他成員的心理健康,但其側(cè)重的主體主要還是學(xué)生。學(xué)校心理學(xué)的構(gòu)成主要包括教育心理學(xué),發(fā)展心理學(xué),心理健康教育。學(xué)校心理學(xué)目前在中小學(xué)開展工作,比較關(guān)注對(duì)學(xué)生的心理測(cè)量,心理輔導(dǎo),學(xué)校適應(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