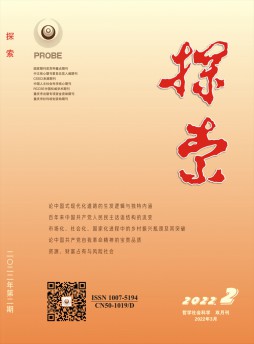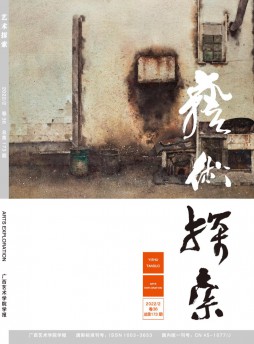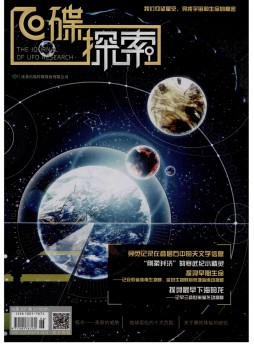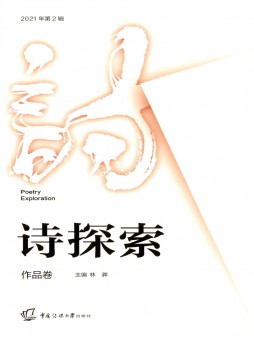探索陶行知的民族教育理念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探索陶行知的民族教育理念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925年12月,在《內(nèi)蒙革命與教育》一文中,陶氏針對(duì)內(nèi)蒙古民眾開展國(guó)民革命運(yùn)動(dòng),特別是內(nèi)蒙古人民革命黨提出“我內(nèi)蒙民眾亦應(yīng)設(shè)立民權(quán)自治政府”等十四條宣言,向中央政府提議應(yīng)在民族聚居區(qū)創(chuàng)設(shè)自治政權(quán)。他說:“蒙古與內(nèi)地各省言語不同,文字不同,宗教不同,生活狀態(tài)不同,應(yīng)當(dāng)有不同的政治組織以適應(yīng)他的特別需要”。這一組織就是:“中華民國(guó)政府應(yīng)當(dāng)依據(jù)民族自決的原則,給他一個(gè)充分自治的機(jī)會(huì)。具體些說,為謀民族合作起見,中國(guó)應(yīng)設(shè)聯(lián)邦政府,內(nèi)蒙應(yīng)做這聯(lián)邦政府中之一邦”。他還認(rèn)為:“我們不但應(yīng)當(dāng)如此對(duì)待內(nèi)蒙,凡和內(nèi)蒙具有同樣的區(qū)域都應(yīng)當(dāng)如此辦理,方能鞏固五族的基礎(chǔ)”。1927年以后,陶行知的民族觀有所發(fā)展。
首先,陶氏了解到國(guó)內(nèi)遠(yuǎn)不止五族民眾,他不再使用“五族共和”口號(hào),開始關(guān)注五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如在1934年刊行的《普及教育研究院組織大綱》一文中,陶行知提出未來設(shè)立的普及教育研究院除須研究蒙古教育和西藏教育外,還須研究苗族教育和瑤族教育。在1939年刊行的《曉莊研究所初步計(jì)劃之研究問題》一文中,陶氏指出曉莊研究所除須研究回族教育、蒙族教育、藏族教育外,還須研究夷苗教育。
其次,在抗戰(zhàn)建國(guó)的背景下,陶行知認(rèn)為國(guó)內(nèi)各族有著共同的國(guó)家利益,應(yīng)一致對(duì)外御敵。如1938年10月,陶氏針對(duì)日本挑動(dòng)我國(guó)回漢兩族關(guān)系緊張的情況,在《海外的故事》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guó)各民族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guó)主義”。同月,陶氏在提交的《推進(jìn)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戰(zhàn)力量而樹立建國(guó)基礎(chǔ)案》中,建議中央政府應(yīng)抓緊訓(xùn)練蒙、回、藏等族人才,促使各民族群眾“參加抗戰(zhàn)建國(guó)大業(yè)”。最后,他還反對(duì)任何大民族主義的作法,認(rèn)為應(yīng)尊重各民族群眾的政治地位。如1945年5月,針對(duì)國(guó)民黨高層認(rèn)為國(guó)內(nèi)各民族只是中華民族的一個(gè)分支宗族,而把邊疆少數(shù)民族群眾統(tǒng)稱為“邊民”的作法,陶行知發(fā)表《實(shí)施民主教育的提綱》一文,提出嚴(yán)厲批評(píng),認(rèn)為不承認(rèn)少數(shù)民族為民族的做法是錯(cuò)誤的。
總之,1924至1946年間,陶行知從關(guān)注內(nèi)外蒙古問題擴(kuò)展到關(guān)注國(guó)內(nèi)整個(gè)邊疆民族問題,從注意民族關(guān)系問題延伸到注意民族與國(guó)家關(guān)系問題。他的民族觀也隨之發(fā)展,并形成一以貫之的內(nèi)容,即認(rèn)為中國(guó)是一個(gè)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guó)家;國(guó)內(nèi)各族民眾應(yīng)相互團(tuán)結(jié)、平等相待;政府部門應(yīng)尊重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民族地位,應(yīng)維護(hù)其合法權(quán)益。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維護(hù)各民族權(quán)益是以捍衛(wèi)國(guó)家統(tǒng)一為前提的,這與當(dāng)時(shí)一些民族人士受到西方“民族自決”說的影響、不惜以分裂國(guó)家來保護(hù)本民族利益的做法是顯著不同的。這在陶氏闡述他的民族教育思想時(shí)就有著鮮明的體現(xiàn)。
一、陶行知的民族觀對(duì)其民族教育思想的影響
陶行知提出民族教育思想大體與他關(guān)注邊疆民族問題同步。如前所述,1924年陶行知撰文評(píng)論內(nèi)外蒙古問題時(shí),曾對(duì)如何發(fā)展蒙古教育提出過看法。爾后,他在關(guān)注西南民族問題時(shí),也在一些文章中闡述過他的民族教育思想。從這些文章看,陶氏提出的民族教育思想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平民教育思想、生活教育理論和民族觀的基礎(chǔ)之上。如1924年1月,在察哈爾特別區(qū)推廣平民教育時(shí),陶行知在致溫佩珊及其夫人的信中,結(jié)合平民教育思想,指出政府部門要建設(shè)五族共和國(guó),“只有趕快推廣平民教育一個(gè)法子”。在1934至1935年間先后發(fā)表的《普及現(xiàn)代生活教育之路》和《中國(guó)普及教育方案商討》兩文中,陶行知?jiǎng)t結(jié)合生活教育理論發(fā)表了如何發(fā)展民族教育的看法。其中,前文指出應(yīng)在國(guó)內(nèi)各族民眾中“普及現(xiàn)代生活教育”,[后文呼吁政府部門應(yīng)采取“工學(xué)團(tuán)”形式組織邊疆民族學(xué)校,以使這些學(xué)校能“依‘即知即傳人’之原則繼續(xù)推進(jìn)”。[簡(jiǎn)言之,陶行知結(jié)合平民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理論,著重思考了發(fā)展民族教育的辦法、內(nèi)容和組織形式。與上述思考不同,陶行知結(jié)合他的民族觀,則重點(diǎn)思考了發(fā)展民族教育的作用、方針及教學(xué)語言等問題,并提出了他的一些主張。
首先,陶行知從捍衛(wèi)國(guó)家統(tǒng)一、維護(hù)民族團(tuán)結(jié)、提高民族群眾的自治能力,以及抵御外來侵略出發(fā),呼吁教育界人士大力發(fā)展民族教育。如在《五族共和與教育者之責(zé)任》一文中,陶行知提出解決內(nèi)外蒙古問題的辦法就有教育的辦法。在他看來,當(dāng)時(shí)內(nèi)外蒙古問題反映出五族民眾不夠團(tuán)結(jié),多是在“各干各的”,五族民眾的國(guó)家觀念不夠濃厚。而恰當(dāng)?shù)慕逃翱梢詼贤ň裆系呢暙I(xiàn)和缺乏”,即,可以促使五族民眾“明白自己是中華民國(guó)的國(guó)民”,使得他們意識(shí)到彼此間“有共同利害,有存則共存、亡則共亡的關(guān)系”,形成兄弟般感情。于是,他號(hào)召教育界人士承擔(dān)起發(fā)展民族教育的責(zé)任。與此同時(shí),陶行知在《內(nèi)蒙革命與教育》一文中指出:政府部門把“一個(gè)專制的內(nèi)蒙變到一個(gè)自治的內(nèi)蒙”,最要緊的是“從培養(yǎng)領(lǐng)袖、訓(xùn)練公民入手”。故他建議內(nèi)蒙古革命群眾抓緊發(fā)展教育。[6]P.2871927年以后,特別是抗戰(zhàn)期間,陶行知?jiǎng)t希望通過發(fā)展民族教育為抗戰(zhàn)建國(guó)起到作用。如在1938年12月生活教育社桂林成立大會(huì)上,陶行知指出該社在戰(zhàn)時(shí)的重要任務(wù)是“幫助全民族都變成抗戰(zhàn)建國(guó)的真力量”。翌年3月,在生活教育社12年周年紀(jì)念大會(huì)上,陶氏強(qiáng)調(diào)戰(zhàn)時(shí)生活教育社應(yīng)抓緊推動(dòng)民族教育的發(fā)展,以使民族群眾參加抗戰(zhàn)建國(guó)大業(yè)。
其次,陶行知基于增進(jìn)國(guó)內(nèi)民族團(tuán)結(jié)的考慮,強(qiáng)調(diào)發(fā)展民族教育應(yīng)培養(yǎng)民族群眾的公民資格,并將此納入民族教育方針中。如在1924年7月召開的中華教育改進(jìn)社第三屆年會(huì)上,陶行知指出發(fā)展民族教育須培養(yǎng)民族學(xué)生的公共觀念和國(guó)家認(rèn)同感,須為民族群眾的福祉發(fā)展教育。于是,他與范源濂、馬鶴天、郭道甫等人提出了四條蒙古教育方針。其中,“養(yǎng)成五族共和公民資格”列為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此后,陶行知還在各種場(chǎng)合努力矯正教育界人士輕視“養(yǎng)成五族共和公民資格”的作法。如1925年,郭道甫應(yīng)陶行知的邀請(qǐng),撰寫了《蒙古教育之方針及其辦法》一文。在文中,郭氏沒把“養(yǎng)成五族共和之公民資格”一條納入到方針之列。對(duì)此,陶行知在文章的按語中作了委婉的批評(píng)。他說,盡管郭道甫肯定了“蒙古確為中國(guó)之一部”,強(qiáng)調(diào)了發(fā)展教育應(yīng)使蒙古族民眾“盡立國(guó)之義務(wù)”;但是,“養(yǎng)成五族共和之公民資格”關(guān)系著民國(guó)的前途,“在教育方針里特別提出總是有益處的”。在按語的末尾,陶行知還意味深長(zhǎng)地說道:“共和不忘自治,自治不忘共和”。這實(shí)際上提醒郭道甫在維護(hù)民族權(quán)益時(shí)須以捍衛(wèi)國(guó)家政治統(tǒng)一為前提。
最后,陶行知從尊重民族群眾的民族地位、維護(hù)他們的合法權(quán)益出發(fā),倡導(dǎo)使用民族語言文字開展教學(xué)活動(dòng)。前面講到,陶行知認(rèn)為國(guó)內(nèi)不少民族群眾在語言、文字、宗教和生活習(xí)慣上不同于漢族群眾。于是,他為了維護(hù)民族群眾的合法權(quán)益,力主中國(guó)應(yīng)實(shí)行聯(lián)邦制政體。與此相配合,在教育方面,陶行知呼吁使用民族語言文字開展教育教學(xué)活動(dòng)。如在改進(jìn)社第三屆年會(huì)上,陶行知指出:發(fā)展蒙古教育“乃為蒙古人而辦蒙古教育,非為漢人而辦蒙古教育,非為教育界開新天地,占蒙古地盤,乃幫助蒙人”。他遂與郭道甫一道把“保持蒙古民族之獨(dú)立性(語言文字等),并發(fā)展其優(yōu)點(diǎn)”列為蒙古方針之一。后來,陶氏在1934年撰述的《普及現(xiàn)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還對(duì)教育行政部門“喜歡劃一”,“一定要用漢字”普及教育,而不尊重民族文化的作法提出了批評(píng)。他說,“運(yùn)用各民族自有的大眾語及文字符號(hào)去普及現(xiàn)代生活是最快的方法。因?yàn)榻處煬F(xiàn)成的多,要省掉許多麻煩。這樣一來,也能免除民族間的成見猜疑,更能鼓舞各民族自動(dòng)普及教育的興趣,進(jìn)步自可敏捷”。[為此,他提議用民族文字編輯民族教材。概言之,陶行知把發(fā)展民族教育視作解決邊疆民族問題的重要手段,對(duì)之賦予了很高期望。他結(jié)合自身的民族觀重點(diǎn)思考了發(fā)展民族教育的作用、方針和教學(xué)語言等方面問題,并提出了一系列主張。這些主張構(gòu)成了其民族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因?yàn)椋矫窠逃枷牒蜕罱逃碚撌翘帐显跂|中部地區(qū)長(zhǎng)期從事教育實(shí)踐的結(jié)晶,陶氏結(jié)合這些理論思考民族教育只是遷移運(yùn)用;與此不同,他結(jié)合自身的民族觀提出的民族教育思想,則是他深入反思國(guó)內(nèi)民族問題、與民族知識(shí)分子多方交流、指明民族教育發(fā)展方向的創(chuàng)造性成果。
二、陶行知民族教育思想的歷史意義
陶行知結(jié)合自身民族觀提出的前述一系列民族教育思想,其旨趣在提升各族民眾的國(guó)家認(rèn)同感、給予少數(shù)民族文化一定的發(fā)展空間。在傳統(tǒng)國(guó)家向近代民族國(guó)家轉(zhuǎn)型的歷史背景下,這些思想的提出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眾所周知,陶行知主要生活于20世紀(jì)上半葉。在這段時(shí)間里,除像吳文藻、楊堃、費(fèi)孝通等一批人類學(xué)家外,社會(huì)各界人士尤其是大多數(shù)政府官員對(duì)國(guó)家、民族的概念及其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不是很清楚,他們?nèi)允艿絺鹘y(tǒng)國(guó)家觀念的影響,或從暫時(shí)穩(wěn)定政局出發(fā),或以綜合國(guó)力不逮的原因,繼續(xù)推行著傳統(tǒng)民族政策。如北京政府在創(chuàng)建之初曾一度廢除清末民族政策,提出“不能如帝政時(shí)代,再有藩屬名稱”,力圖實(shí)現(xiàn)“五族共和”、“內(nèi)政統(tǒng)一”的政治目標(biāo)。但時(shí)隔不久,羈縻政策死灰復(fù)燃。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京政府于1912年8月頒布《蒙古待遇條例》,恢復(fù)第十三世達(dá)賴?yán)锏拿?hào),在蒙藏院中設(shè)置專門司科保護(hù)蒙古、西藏王公、喇嘛們?cè)械奶貦?quán)等等。[11]PP.253-254此后,以為首的國(guó)民政府在處理民族問題上如出一轍。1934年,蔣氏在《中國(guó)之邊疆問題》的演講中指出,“今當(dāng)革命時(shí)期,實(shí)力不夠,欲解決邊疆問題,只能講究政策”,這種政策就是“柔性的”羈縻政策。依照這一精神,國(guó)民政府繼續(xù)保留王公貴族制度和封建特權(quán)統(tǒng)治,在教育方面則以招收王公貴族的子女為重點(diǎn)。從當(dāng)時(shí)的情況看,這一政策雖然暫時(shí)緩和了嚴(yán)重的邊疆矛盾,但作用只是一時(shí)的。因?yàn)椋糠稚蠈淤F族并沒有由于羈縻政策的推行而增進(jìn)國(guó)家認(rèn)同感;相反,在個(gè)人利益受到?jīng)_擊、在西方列強(qiáng)的調(diào)唆下,他們成了破壞國(guó)家統(tǒng)一的潛在勢(shì)力。
更為嚴(yán)重的是,由于羈縻政策的推行,邊疆民族地區(qū)原有的政治經(jīng)濟(jì)制度以及社會(huì)組織形態(tài)得以保留,廣大邊疆民眾接受國(guó)民教育的機(jī)會(huì)有限,他們國(guó)家觀念很淡薄的情況絲毫沒有改變。如一些邊疆民眾或由于宗教信仰,或由于部族力量強(qiáng)大等緣故,沒有產(chǎn)生過國(guó)家觀念,遑論近代民族國(guó)家觀念。[13]針對(duì)于此,一批學(xué)人從1930年代開始陸續(xù)批評(píng)政府部門“過分重視王公喇嘛,敷衍殘余的封建勢(shì)力”的作法,他們提出要從培植優(yōu)秀青年著眼,提供邊疆青年為國(guó)服務(wù)的機(jī)會(huì)。而相比政府部門的保守作法,以及近代學(xué)人較晚關(guān)注民族教育在提升邊疆民眾的國(guó)家認(rèn)同感的作用而言,陶行知提出“養(yǎng)成五族共和公民資格”、增進(jìn)民族群眾國(guó)家認(rèn)同感的觀點(diǎn),毫無疑問有著時(shí)代進(jìn)步性。另一方面,陶行知基于尊重民族群眾的民族地位、保護(hù)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考慮,要求使用民族語言文字開展教育教學(xué)的思想,其歷史意義也不容忽視。20世紀(jì)上半葉,由于受到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熏陶,邊疆民族人士特別是一批邊疆民族知識(shí)分子的民族意識(shí)逐漸產(chǎn)生。他們認(rèn)識(shí)到本民族有著不同于漢族的族源,有著璀璨輝煌的歷史,有著別具一格的文化。于是,他們要求發(fā)展本民族文化,不愿意接受越俎代庖的“漢化教育”;同時(shí),邊疆民族人士把語言文字視作民族認(rèn)同的重要符號(hào),力主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如郭道甫在《蒙古問題》一書中明確反對(duì)“專重漢文漢語以消滅蒙古固有文字言語”的作法,他認(rèn)為這種作法違背了民主自由原則。
然而,近代政府官員沒有正視邊疆民眾的合理要求,反而根本否定邊疆民眾的民族合法地位。他們?cè)诎l(fā)展教育方面表面上提升邊疆民眾的文化水平、增進(jìn)內(nèi)地民眾與邊疆民眾的交流,但實(shí)際上因襲了傳統(tǒng)“以夏變夷”的辦學(xué)取向。如不承認(rèn)中國(guó)多民族國(guó)家的基本國(guó)情,而認(rèn)為中國(guó)只有一個(gè)民族即中華民族,包括漢族在內(nèi)的各民族均是中華民族的宗族。在此基礎(chǔ)上,蔣氏極力推動(dòng)民族學(xué)生學(xué)習(xí)國(guó)語、國(guó)文。這種作法結(jié)果引起邊疆民眾的強(qiáng)烈不滿。1944年,新疆爆發(fā)了“三區(qū)革命”,革命群眾向國(guó)民政府提出廢除國(guó)語、國(guó)文教育政策,允許各族民眾使用本民族語文開展教學(xué)。與此同時(shí),作為親國(guó)民黨的新疆上層人士,伊敏、麥斯武德、艾沙等人也表達(dá)了同樣要求。[最終,在上下兩方面人士的推動(dòng)下,國(guó)民政府不得不作罷。1948年,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zhǎng)凌純聲宣布不再強(qiáng)行要求民族學(xué)生學(xué)習(xí)國(guó)語國(guó)文了。[19]事實(shí)證明,陶行知倡導(dǎo)使用民族語言文字開展教學(xué)活動(dòng)的主張更切合中國(guó)多民族國(guó)家的實(shí)際。
作者:張建中肖海燕單位:湖南師范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學(xué)院井岡山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
- 上一篇:西南民族地區(qū)教育淺析范文
- 下一篇:地方跨境民族教育路徑分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