腎毒性生物標志物的研究進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腎毒性生物標志物的研究進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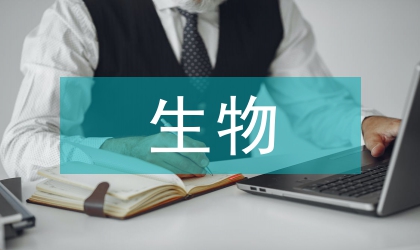
摘要:藥物腎毒性已成為醫藥界廣泛關注的問題,而生物標志物在早期診斷及干預過程中尤為重要。本文主要闡述腎小球損傷標志物(β2-MG、CysC)、腎小管損傷標志物(clusterin、KIM-1、TFF-3、albumin)和其他生物標志物(NGAL、L-FABP、IL-18、OPN、microRNA等)對腎毒性早期診斷的意義及其優劣勢,為藥物腎毒性評價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腎毒性;生物標志物;KIM-1;白蛋白;NGAL;OPN腎臟
由于其功能和解剖學特點,是藥物毒性的重要靶器官之一,藥物導致的急性腎損傷約占所有腎損傷病例的33%。目前,臨床用于腎毒性的診斷方法是以急性腎損傷(acutekidneyinjury,AKI)診斷標準為依據,即腎功能急劇下降,48h內血清肌酐(serumcreatinine,SCr)升高到損傷前的1.5倍或增加26.4μmol/L,和(或)尿量<0.5mL/(kg•h)持續6h以上[1]。但依靠SCr診斷AKI存在以下局限性:SCr是腎小球濾過率(glomerularfiltrationrate,GFR)依賴指標,不能反映腎小管的損傷情況,其在血液中蓄積只與GFR降低相關,且只有當GFR下降超過50%時SCr才開始升高,此時AKI已發生,因此依靠SCr診斷AKI明顯滯后;SCr水平變化易受年齡、性別、種族、肌肉代謝和蛋白質攝入等因素的影響。尿量則更易受循環血量、脫水劑、利尿劑應用以及尿路梗阻等因素的影響[2]。因此需要特異性更高靈敏度更強的生物標志物用于早期腎毒性診斷。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和歐洲藥物管理局(EMA)已批準了幾種用于藥物臨床前安全性評價的腎毒性生物標志物,其中β2-微球蛋白(β2-MG)、血清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C(CysC)作為藥物腎小球損傷(或腎小管重吸收障礙)生物標志物;叢生蛋白(clusterin)、腎損傷分子-1(KIM-1)、三葉因子-3(TFF-3)和白蛋白(albumin)作為藥物腎小管損傷生物標志物[3]。部分尿酶如N-乙酰-β-氨基葡萄糖苷酶(NAG)、γ-谷氨酰轉肽酶(GGT)、堿性磷酸酶(AP)、谷胱甘肽-S-轉移酶(GST)也可以及早且快速診斷腎損傷。除此之外,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相關脂質運載蛋白(NGAL)、肝臟脂肪酸結合蛋白(L-FABP)、白細胞介素18(IL-18)、周期阻滯生物標志物(TIMP-2和IGFBP-7)、骨橋蛋白(OPN)、視黃醇結合蛋白(RBP)、神經生長因子(Netrin-1)、microRNA等在預測腎損傷方面也存在潛在優勢。
1腎小球損傷生物標志物
1.1β2-微球蛋白(β2microglobulin)
β2-微球蛋白(β2-M)相對分子質量為1.18×104,是有核細胞表面表達的主要組織相容性類I類分子的輕鏈。正常情況下,β2-M在細胞內經過合成、脫落、脫離重鏈的過程進入循環,經腎小球濾過,被近曲小管重吸收代謝[4]。在嘌呤霉素和阿霉素引起的腎毒性研究中,尿β2-M診斷腎小球損傷的ROC曲線下面積為0.89,優于血清肌酐(0.55)和尿素氮(0.80)[5]。臨床上血清β2-M預測心臟手術術后AKI有較高的潛能[6]。然而β2-M作為生物標志物的缺點是在尿液不穩定,在室溫和pH值<6的尿中迅速降解。
1.2胱抑素C(cystatinC)
CysC是有核細胞以恒定速率產生的非糖基化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不與血漿蛋白結合,由腎小球自由過濾,被近端小管重吸收并降解[4]。血漿CysC水平與性別、種族、肌肉質量無關,但可能受甲狀腺功能紊亂、吸煙、炎癥、癌癥和糖皮質激素等因素的影響[7-8]。CysC達到穩態比血清肌酐快3倍[9],一些研究已經證明,急性腎損傷中CysC水平增加可能比SCr提前1~2d[10-12]。然而,Togahsi等[13]利用順鉑致大鼠腎小管損傷,發現血清CysC水平升高不明顯,尿液CysC卻可以預測由順鉑導致的大鼠早期腎小管損傷。因此,血清CysC可能主要預測腎小球毒性而非腎小管毒性。此外,CysC和白蛋白均被近端小管巨蛋白內吞而重吸收,因而當蛋白尿存在時可能競爭性抑制CysC的重吸收,增加其尿排泄[14]。因而對于持續尿蛋白增加患者,尿CysC診斷并不可靠。
2腎小管損傷標志物
2.1叢生蛋白(clusterin)
clusterin是一種糖基化蛋白,由多種器官的上皮細胞產生。腎損傷后腎小管上皮細胞產生clusterin,發揮其抗凋亡、脂質再循環、細胞聚集和黏附的作用。研究顯示,比格犬順鉑給藥8d后尿clusterin水平顯著升高,靈敏度遠高于血清肌酐和尿素氮[15]。此外,在慶大霉素誘導的大鼠腎損傷研究中,尿clusterin水平的升高持續到腎損傷恢復前期[16],因此認為clusterin可能參與腎損傷的恢復過程。
2.2腎損傷分子1(KIM-1)
KIM-1是一種1型跨膜蛋白,腎臟局部缺血或毒性損傷后,其在去分化近端小管細胞中表達上調[17-18]。KIM-1被認為在上皮損傷修復的去分化過程中起作用,也可特異性識別凋亡腎小管上皮細胞上的磷脂酰絲氨酸抗原,與其結合后可吞噬小管腔中的凋亡和壞死物質[19]。KIM-1脫落可以通過p38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號通路促進生長因子產生,參與細胞的增殖和修復。在大鼠草甘膦類除草劑腎毒性研究中,只有KIM-1在損傷8h能較好地預測組織病理學變化[20]。在順鉑誘導的腎毒性中,24h尿KIM-1水平顯著高于在3d時達到高峰的SCr[21]。此外,尿KIM-1還可用于AKI不良后果預測,其預測兒童AKI患者30d和3個月死亡率的AUC分別為0.55和0.60[22]。KIM-1在尿液中極其穩定,且尿KIM-1水平與病理損傷程度一致,這些特性表明尿KIM對腎損傷的早期診斷有較高的價值。然而,KIM-1水平上升緩慢,常滯后于腎損傷,并且可受持續性蛋白尿的影響[23],從而降低其診斷腎損傷的特異性。
2.3三葉因子-3(TFF3)
TFF3是由多種組織的上皮細胞和黏液生成細胞產生的一種肽類激素,相對分子質量為7×103。TFF3通過抑制細胞凋亡和促進細胞遷移參與上皮表面修復。一項研究對給予順鉑治療的大鼠腎組織進行免疫組化評估發現TFF3表達水平顯著降低[24]。另有研究顯示,從57例接受順鉑治療的實體瘤患者中收集的尿液中發現TFF3水平在第10天升高2倍[25]。由于在順鉑暴露條件下TFF3在大鼠腎臟和人類尿液中的表達存在差異,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揭示腎毒性過程中TFF3表達的機制。
2.4白蛋白(albumin)
白蛋白是一種高分子量蛋白質(6.65×104),腎小球和(或)腎小管損傷患者可被檢測到。順鉑輸注4h后尿白蛋白濃度升高,4~10d達到峰值,約2周開始下降[26]。Vlasakova[27]研究表明,KIM-1、clusterin和白蛋白對藥物誘導的大鼠腎小管損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最高,而白蛋白在檢測藥物性腎小球損傷中表現最好。然而,尿白蛋白作為人類心血管和腎臟風險標志物已經得到證實,在收縮期心力衰竭、炎癥、劇烈運動或發燒等情況下,尿白蛋白水平也會升高[28]。
3尿酶類生物標志物
3.1N-乙酰基-β-葡糖胺酶(NAG)
NAG是存在于近端和遠端腎小管細胞的溶酶體酶,相對分子質量大于1.30×105。因其相對分子量較高因而不被腎小球濾過,尿NAG酶的活性增加提示可能存在腎小管細胞損傷,或無細胞損傷的酶活性增加[29]。研究表明,亞臨床和臨床患者在順鉑治療后3~5d內尿NAG濃度增加,但尿NAG濃度不反映損傷程度,與接受順鉑的累積劑量也無相關性[26]。Mishra[30]研究發現,NAG預測AKI兒童患者死亡率的AUC為0.724,其對死亡率有中度的診斷能力。然而,生物標志物的聯合應用可提高其診斷能力,在心臟外科手術AKI患者中將具有較高特異性的尿NAG(AUC=0.75)與具有較高敏感性的尿L-FABP(AUC=0.72)聯合應用可使AUC值增加至0.81[31]。
3.2γ-谷氨酰轉肽酶(GGT)與堿性磷酸酶(AP)
GGT和AP都是腎小管刷狀緣酶,當微絨毛結構喪失,刷狀緣膜有顯著損傷時,釋放到尿液中[32]。GT和AP的排泄增加意味著近端小管上皮細胞的損傷。這兩種腎臟標志物的研究數據相對較少,一項對一般ICU患者的前瞻性觀測研究表明,在AKI12h后,當eGFR≥60mL/min,GGT預測AKI的AUC≥0.73[33]。而另一項橫斷面研究顯示,肝臟移植術前升高的GGT和AP都可作為術后AKI發生的風險因子[34]。GGT和AP能否作為腎損傷診斷及預后的生物標志物還需要更多的前瞻性隊列研究來進行驗證。
3.3谷胱甘肽-S-轉移酶(GST)
GST蛋白家族分為α、π和μ三個主要亞類,主要參與自由基解毒,其中腎臟主要以α和π形式存在,α-GST位于近端小管而π-GST位于遠端小管,在腎小管上皮細胞受損的情況下,細胞質酶在尿中積累并可被檢測[35]。有研究表明,尿π-GST預測體外循環術病人術后2h發生AKI的AUC為0.620,優于尿α-GST(AUC=0.56),將二者結合可提高α-GST的預測能力[36]。在已確診的AKI患者中,尿π-GST預測透析需求或死亡的能力較α-GST好(AUC:0.59vs0.56)[37]。大多數文獻表明,π-GST較α-GST而言對腎損傷有著較好的預測能力。
4其他腎毒性生物標志物
4.1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相關脂質運載蛋白(NGAL)
NGAL屬于脂蛋白家族,亦是一種鐵血黃素。NGAL與鐵載體復合物螯合,限制細菌對鐵的吸收。推測受損的腎小管釋放不穩定鐵螯合物,可以阻止羥基自由基和超氧物的形成[14]。除了抑菌作用外,NGAL還具有抗凋亡,促進腎小管上皮細胞增殖的能力,是腎臟保護的潛在途徑[38]。NAGL是一個被大量研究的生物標志物,且其診斷及預后能力在不同條件下被評估。有研究顯示腎損傷3h后尿液中NAGL濃度開始升高,損傷6hNAGL濃度達峰值,腎損傷5d后尿NAGL仍持續處于高水平[39]。尿NGAL可以識別鉑類似物治療后AKI,對順鉑、卡鉑和奧沙利鉑的化療反應,尿NGAL濃度增加分別為基線2.3倍、2.7倍和1.5倍[40]。NGAL也被用于預測腎移植后腎功能延遲及兒童和成人造影劑腎病[41]。NGAL被認為是輔助診斷腎毒性的強有力標志物,但血清NGAL和尿NGAL水平在炎癥和感染情況下也升高[42]。因此,需更多的研究揭示腎毒性引起NGAL上調的機制。
4.2肝臟脂肪酸結合蛋白(L-FABP)
肝臟脂肪酸結合蛋白(liverfattyacidbindingprotein,L-FABP)來自脂質結合蛋白家族,相對分子質量為1.4×104。L-FABP可能是氧化應激過程中重要的細胞抗氧化劑,通過促進細胞內代謝和尿排出來維持腎小管細胞質低水平的游離脂肪酸[10]。位于近端小管的L-FABP還通過減輕H2O2誘導的氧化應激發揮細胞保護作用,可將結合的毒性過氧化物酶產物排泄到管腔中[43]。在缺血條件下,腎小管L-FABP基因被誘導表達,近端腎小管重吸收L-FABP減少。Nakamura[44]研究表明,人類L-FABP轉基因(TG)小鼠在給予頭孢氯啶、順鉑后中,L-FABP的尿排泄量增加。另有研究顯示,腎前損傷ICU病人的尿L-FABP水平較無AKI病人明顯升高[45],尿L-FABP對發生AKI的心臟外科手術小兒患者也有著較高的辨識能力[46]。由于L-FABP在肝臟中表達,當共存肝病時,尿L-FABP可能對腎臟疾病失去特異性。對于尿白細胞增多、血尿及全身炎癥反應對尿L-FABP診斷腎損傷幾乎沒有影響[42]。在此種情況下,尿L-FABP比尿NGAL有著更優的預測能力。
4.3白細胞介素18(IL-18)
白細胞介素18(interleukin-18,IL-18)是由腎小管上皮細胞和巨噬細胞產生的促炎性細胞因子,相對分子質量為2.2×104。在缺血再灌注損傷導致的AKI中,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1介導Pro-IL-18向活性IL-18的轉化,活性IL-18由腎小管細胞釋放,介導腎實質中性粒細胞浸潤[10]。因此,可以看出IL-18在AKI進展期發揮促使AKI進一步惡化的作用。動物實驗表明,IL-18基因缺陷小鼠可以免受缺血-再灌注誘導的AKI[47]。血清IL-18對AKI具有中度的診斷價值,預測AKI發生的AUC為0.696[48],但血清IL-18對膿毒癥致AKI具有優良的診斷價值,ROC曲線下面積(AUC)為0.719優于SCr(AUC=0.677)[49]。此外,尿IL-18在急性腎小管壞死和腎移植后腎功能延遲患者中也明顯升高[50]。Faubel[51]研究顯示,順鉑誘導的AKI小鼠腎臟IL-18水平升高,提示IL-18也可以應用于藥物誘導的腎損傷。然而,IL-18作為腎毒性AKI潛在標志物還需要更多實驗驗證。IL-18水平在膿毒血癥、關節炎、炎性腸病、系統性紅斑狼瘡、銀屑病、肝炎和多發性硬化等情況下增加。這個屬性降低其特異性,顯著限制了其運用[52]。不難看出,IL-18作為腎毒性生物標志物的限制性主要來源于其作為炎性因子的特性。
4.4骨橋蛋白(OPN)
OPN是一種糖蛋白,除了在骨骼和上皮中高表達外,還廣泛表達于內皮細胞、血管平滑肌、巨噬細胞和活化的T細胞,參與生物礦化、組織重塑、細胞黏附、遷徙等[53]。在大鼠毒理學研究中,OPN鑒定藥物誘導的腎小管上皮變性壞死的能力均優于肌酐和尿素氮[54],可作為順鉑治療大鼠腎毒性研究的良好生物標志物[55]。然而,尿液OPN增加并不特異于腎損傷,在對乙酰氨基酚誘導的肝損傷小鼠中尿OPN也明顯增加[56]。
4.5周期阻滯生物標志物
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結合蛋白7(insulin-likegrowthfactorbindingprotein7,IGFBP7)和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劑-2(tissueinhibitorofmetalloproteinase2,TIMP-2)都是G1細胞周期阻滯生物標志物,這些細胞周期阻滯蛋白在受損的腎小管細胞中合成和分泌,通過結合內皮細胞表面的α3β1整聯蛋白,阻斷內皮細胞增殖及血管生成[57],并影響參與腫瘤抑制和細胞衰老的胰島素生長因子的生物利用度[58]。研究報道,IGFBP7也可用于預測腎功能恢復、AKI嚴重程度、腎臟替代治療,且比NGAL更加準確[59]。有研究評估了340種候選生物標志物對危重病人發生AKI風險的預測能力,結果表明,尿TIMP-2和IGFBP7比其他生物標志物(特別是NGAL、IL-18、L-FABP和KIM-1)更具優勢[60]。[TIMP-2×IGFBP7]即TIMP-2濃度與IGFBP7濃度的乘積,是極具有應用前景的指標。尿[TIMP-2×IGFBP7]對兒童心臟手術后、膿毒癥患者和高危手術患者發生AKI具有良好預測能力,并且研究表明[TIMP-2×IGFBP7]的截斷值在0.3~2時12h內有中度至高度的AKI風險,[TIMP-2×IGFBP7]截斷值大于2有著極高的AKI風險[61-62]。對于藥物誘導的腎損傷,研究發現,順鉑給藥24h后發生AKI的病人,IGFBP7濃度沒有變化,而TIMP2水平則增加了1.1倍[63]。另一項研究表明,在順鉑治療后第3天和第10天,TIMP2或IGFBP7以及[TIMP-2×IGFBP7]與基線相比無明顯變化[64]。TIMP2和IGFBP7對藥物誘導AKI的早期診斷能力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進行驗證。
4.6視黃醇結合蛋白(RBP)
RBP由肝臟合成,相對分子量為2.1×104,在維生素A從肝臟運輸到組織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RBP經腎小球自由濾過后,由近端腎小管重吸收代謝。其靈敏度比β2M低,但比NAG高,在GFR未下降或輕微下降時,增加的RBP是腎小管損傷的一個重要的特殊指標,因此尿RBP可作為近端小管損傷早期檢測的理想標志物[4]。RBP水平升高可作為順鉑、鉛、汞、鎘和環孢霉素誘導的腎毒性的早期診斷指標。與其他低分子量蛋白相比,RBP產生速率恒定且在尿液pH值下穩定[65]。然而,RBP作為維生素A轉運體,RBP檢測值在維生素A缺乏癥患者中有所降低,并且作為腎損傷生物標志物對重度腎小球蛋白尿患者的特異性不高。
4.7神經生長因子(Netrin-1)
Netrin-1是一種多功能層黏連蛋白相關的神經元導向蛋白,廣泛表達于各種組織中,在正常腎臟的腎小管上皮細胞中幾乎不表達。與健康志愿者相比,AKI患者尿Netrin-1排泄量增加,提示尿Netrin-1可能是一種很有前途的早期檢測腎損傷的生物標志物[10]。缺血、造影劑、膿毒癥和藥物誘導的急性腎損傷患者,與健康對照組相比尿Netrin-1含量均升高[66]。Netrin-1水平在膿毒血癥AKI患者ICU入院1h內顯著升高,在3~6h達到高峰,并在48h內持續升高,入院3h對AKI的預測能力達到最高(AUC=0.858)[67]。雖然Netrin-1具有較高的診斷能力但其特異性較低,能否具有實踐意義有待更深層次地研究考察。4.8microRNAmicroRNAs是21~25個核苷酸的非編碼RNA分子,它們可以誘導mRNA降解,亦可通過與靶mRNA的3’-非翻譯區(UTR)結合來抑制蛋白質的翻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大多數基因受到miRNA的調控[68-69]。有證據表明,miR-687、miR-489、miR-494、miR-24、miR-21、miR-126這幾種microRNA參與缺血再灌注誘導的AKI的發病機制[68]。一項初步研究篩選了10種microRNA即miR-101-3p、miR-127-3p、miR-210-3p、miR-126-3p、miR-26b-5p、miR-29a-3p、miR-146a-5p、miR-27a-3p、miR-93-3p和miR-10a-5p,證明它們對ICU患者發生AKI有極高的診斷價值(AUC:0.935-1.00)[70]。體外腎毒性研究表明[71],miR-21、miR-29a、miR-34a和miR-192可作為藥物(順鉑、替諾福韋、環孢素A和妥布霉素)誘導近端小管上皮細胞損傷的敏感性生物標志物。
5蛋白質組學與代謝組學技術在腎毒性生物標志物發現過程中的應用
當前最為先進的蛋白質組學與代謝組學也被用于尋找更敏感更準確更可靠的腎毒性早期生物標志物。一項關于腎損傷的蛋白質組學研究表明,CYR61、HGF、TNF-α、FGF23、PTGDS、AAP、LDH、SOD1、信號素-3A、TGF-β1、IL-6、CX3CL1、P/E選擇蛋白、TLRs、Caspase-1、CAF、CXCL5等蛋白在腎損傷進展中占據關鍵位置,可作為AKI的候選生物標志物[72]。順鉑誘導的AKI大鼠尿代謝產物3-吲哚硫酸酯水平顯著下降,提示3-吲哚硫酸酯可作為檢測藥物誘導AKI的生物標志物[73]。Li[74]等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譜-飛行時間質譜聯用技術趨勢分析篩選出5種腎毒性生物標志物:胸苷、溶血磷脂(16׃1)、溶血磷脂(18׃4)、溶血磷脂(20׃5)和溶血磷脂(22׃5)。由于腎毒性標志物的毒性機制方面的報道較少,還需探討藥物毒性相關的代謝通路及與蛋白多肽類標志物之間的相關性,以驗證這些候選生物標志物是否可靠。
6結語
在腎毒性研究中,KIM-1、clusterin和白蛋白對腎小管損傷的敏感性高,白蛋白在檢測腎小球損傷方面優于所有其他標志物。其他標志物,如OPN、NGAL,是很有前途的腎小管毒性生物標志物,但其特異性問題并未得到解決。尿酶類生物標志物由于其穩定性差的原因,臨床應用較為困難。迄今為止,以上腎毒性生物標志物依然沒有取代尿素氮和血清肌酐,而是作為傳統指標的補充。為了加快這些生物標志物的應用,需要更深入了解生物標志物在藥物造成腎毒性過程中的產生機制和動態變化。不同藥物導致腎損傷的病理機制不同使得單個分子的預測相當困難,因此可以將多種候選生物標志物聯合運用以提高腎毒性的早期診斷能力。近年來新興崛起的蛋白質組學技術及代謝組學技術成為腎毒性生物標志物尋找的新工具,蛋白質組學技術可獲得蛋白質組的全局圖像用來描述發病機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途徑和蛋白,而代謝組學技術則是活體系統對病理生理刺激或遺傳修飾的動態代謝反應的定量測量。組學技術帶來了大量的腎毒性生物標志物,然而這些生物標志物并非都具有高敏感性和特異性,能否取代傳統生物標志物還需要大量的動物實驗和臨床數據加以驗證。盡管這些被發現腎毒性生物標志物并未取代傳統生物標志物,但這些生物標志物的使用,給臨床醫生帶來識別出患者危險的機會。在新藥研究方面,新的腎毒性標志物給藥物的腎毒性預測提供更多的途徑,使藥物臨床安全性評價的數據更加安全可靠。
作者:畢海燕1,2;劉靜2;侯衍豹2;張宗鵬2;呂雄文1 單位:1.安徽醫科大學藥學院,2.天津藥物研究院新藥評價有限公司
- 上一篇:生物農藥的登記及推廣應用現狀范文
- 下一篇:農村新零售發展戰略與成本管理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