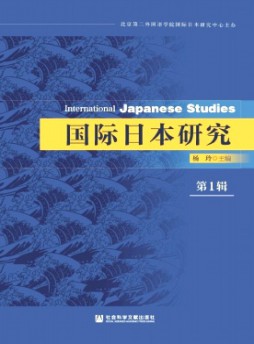日本病奇跡到?jīng)]落警示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日本病奇跡到?jīng)]落警示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日本病奇跡到?jīng)]落警示下](/upload/piclabel/64225403_1616a.jpg)
三、支離破碎的日本金融:關(guān)系型融資的沒落需要流血的改革
我們不妨以金融為主線,觀察日本政府、銀行和企業(yè)之間的“捆綁式”關(guān)系,日本金融體系以所謂“關(guān)系型融資”(RelationshipFinancing)和“主辦銀行制”(MainBankSystem)為主要特征。在這樣的賽局中,銀行因執(zhí)行政府的產(chǎn)業(yè)政策而獲得隱含貸款擔保,特定行業(yè)的企業(yè)因被納入優(yōu)先發(fā)展序列而接受大量融資,市場機制因扭曲而被冷落,只有政府在其中扮演“自由人”的角色。這樣的管制性的產(chǎn)業(yè)金融體制不能支持強調(diào)獨立創(chuàng)新的信息技術(shù)的融資需求,使日本經(jīng)濟從奇跡的巔峰滑落到困頓的孤獨。
有利益可分享的貿(mào)易黑字,無人負責的泡沫破裂。在日本模式下,日本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是由競爭力強大的傳統(tǒng)制造業(yè)如汽車、電子、化工等和軟弱的金融、不動產(chǎn)、流通、建筑等服務性行業(yè)構(gòu)成的。前一類產(chǎn)業(yè)在國際競爭的壓力下不斷提高生產(chǎn)率,愈發(fā)增強了其產(chǎn)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類產(chǎn)業(yè)卻在政府的保護下,生產(chǎn)效率低下,由此產(chǎn)生的內(nèi)外價格差距使得日本國內(nèi)市場帶有很大的封閉性,同時也造成內(nèi)需嚴重不足,最終構(gòu)成了國際貿(mào)易黑字不斷增加而國內(nèi)經(jīng)濟危機不斷加深的奇特現(xiàn)象。
構(gòu)建于傳統(tǒng)利益分配基礎(chǔ)上的“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團”三角同盟的政治體制,使得執(zhí)政者在重大決策上顯得左右搖擺、猶豫不決,常為眼前利益而放棄未來長遠發(fā)展目標。例如,1985年的日元升值,為“日本模式”敲響了警鐘。已經(jīng)是資金過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更是實力倍增,日本本應該利用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寬松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對“日本模式”進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是“政、官、企”“鐵三角”關(guān)系的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進行認真的改革,其中特別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過剩資金倍增時,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導型轉(zhuǎn)向內(nèi)需主導型上,即著名的“前川報告”。倍增的過剩資金用沖向房地產(chǎn)和股票。在當時日元升值、資金過剩、超低利率的條件下,銀行以及證券公司大量向不動產(chǎn)和股市提供資金,直接推動了泡沫經(jīng)濟的形成。
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還是需要告別的日本模式?如前所述,盡管管制性的產(chǎn)業(yè)金融體制在日本經(jīng)濟起飛階段促進和支持了日本經(jīng)濟奇跡的產(chǎn)生;但同時也帶來了更深重的災難,即政府主導釀就產(chǎn)業(yè)政策→產(chǎn)業(yè)政策需要關(guān)系融資→關(guān)系融資隱含政府擔保→政府擔保導致不良資產(chǎn)。1996年底日本大藏省認為不良債務總額為50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1995年GDP的10%。美國議會調(diào)查局推算日本的不良債務總額在70-80萬億日元之間,而有些學者認為不良貸款數(shù)字高達100萬到150萬億日元!自90年代以來,日本金融業(yè)一直陷于嚴重的危機之中,破產(chǎn)風潮此起彼伏,經(jīng)營丑聞屢屢爆光,國際地位江河日下。盡管經(jīng)過多年的掙扎,日本的金融體系依然沒有明顯好轉(zhuǎn),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惡化,戰(zhàn)后日本的金融業(yè)獲得了超常的發(fā)展,形成了近乎神話的“奇跡”。80年代中后期,世界500家銀行排序時,前10家大銀行幾乎為日本所壟斷,但現(xiàn)在日本的銀行業(yè)在國際上的排名急劇下滑。此前,美國穆迪評級公司對日本的部分銀行的金融能力給出了E+的等級(等級范圍從A到E),從評級結(jié)果看,其現(xiàn)在的狀況只比克羅地亞的銀行體系稍許好一點。面對嚴峻的形勢,實際上日本在80年代就曾經(jīng)進行過金融體制改革。1981年,對實施近50年的《日本銀行法》進行了修改,被稱為日本“金融改革真正的元年”,1985年開始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由于當時日本正處于泡沫經(jīng)濟的鼎盛時期,不僅改革不徹底,甚至在某些方面使其原有的弊病有所強化。到1993年4月日本實施了新的金融改革法,但起色并不大。1997年初又推出被稱為“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其主要目標就是減少政府干預,賦予金融機構(gòu)更大的經(jīng)營自由和權(quán)力,推動管制性的產(chǎn)業(yè)金融體系轉(zhuǎn)向市場化的商業(yè)金融體系,以適應目前金融全球化的大趨勢。
對于日本這次金融體制改革的前景,國際經(jīng)濟學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日本經(jīng)濟界普遍認為這是一場“需要流血的改革”,“日本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要徹底改革管制性的產(chǎn)業(yè)金融體系,就首先意味著要對長期形成的日本模式進行全面的改革,因為管制性的產(chǎn)業(yè)金融體系是與日本模式的其他方面密切相關(guān)的,而自從1997年日本金融改革全面鋪開之后,其金融形勢不僅沒有出現(xiàn)轉(zhuǎn)機,反而進一步加深了,特別是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gòu)明顯增多也許值得考慮的是,日本到底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還是需要有勇氣對日本模式永別,重新予以市場機制以起碼的尊重?
成也金融敗亦金融,“日本病”似乎仍廣泛根植。在日本的經(jīng)濟起飛時期,日本的管制性產(chǎn)業(yè)金融體制為日本的制造業(yè)企業(yè)提供了大量廉價資金,這使得日本公司可以負擔很低的資本回報率,向員工提供終生雇傭制度,無限制地追求市場份額,形成了過去的日本模式。隨著日本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和國際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變化,日本經(jīng)濟復蘇的關(guān)鍵依然在日本金融業(yè)順利實現(xiàn)從管制性的產(chǎn)業(yè)金融體制轉(zhuǎn)向市場化的商業(yè)金融體制。真所謂成也金融,敗也金融。為了治療日本病,國際經(jīng)濟界不少學者紛紛獻計獻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克魯格曼所開的“藥方”是,設(shè)定一個通貨膨脹目標(inflationtargeting),實行“有管理的通貨膨脹”(managedinflation),大量投放貨幣,以擺脫通貨緊縮的困境。克魯格曼并沒有深刻地認識到,1991年以來日本所陷入的經(jīng)濟危機,不是常規(guī)意義上的經(jīng)濟危機,在銀行不良資產(chǎn)這個巨大的冰山下面,還隱藏了日本經(jīng)濟體制中存在的一系列結(jié)構(gòu)性的問題。日本能否走出日本病,日本的管制性產(chǎn)業(yè)金融體制能否順利地轉(zhuǎn)向市場化的產(chǎn)業(yè)金融體制,關(guān)鍵在于能否探索出一種適應新的國際經(jīng)濟經(jīng)濟金融環(huán)境的、更為市場化的發(fā)展模式,放松金融管制,打破既得利益階層的阻撓,努力實現(xiàn)從政府管制下的產(chǎn)業(yè)金融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yè)金融體制的轉(zhuǎn)換。從發(fā)展方向看,無論是日本的發(fā)展模式、日本的金融體系,都可以說存在三種可能:一是在政府的主導和協(xié)調(diào)下,對現(xiàn)有的體制進行強制性的變革,考慮到目前缺乏清晰的變革目標,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較小。二是以民間的自發(fā)努力和企業(yè)的探索為主,,通過以市場化的企業(yè)之間的競爭,即所謂誘致性的制度變遷,逐步建立新的體制。三是過大的傳統(tǒng)體制的慣性、傳統(tǒng)體制上依附的既得利益階層的阻撓等使得日本的現(xiàn)有體制遲遲不能與國際國內(nèi)經(jīng)濟金融環(huán)境的變化相適應,強制性的變革遭受失敗,在舊體制崩潰的同時,新的體制卻無法建立,使得日本經(jīng)濟陷入更深的危機。目前來看,以企業(yè)自發(fā)探索為基礎(chǔ)的誘致性變遷是比強制性變遷更為有效的途徑,日本的模式變革、日本病的醫(yī)治應當沿著這個方向前進。任何對于日本經(jīng)濟、以及日本金融體系的過于短期的、盲目樂觀的看法,都是缺乏現(xiàn)實依據(jù)的。客觀地說,這將是一個相對較長的制度演進的過程。至今日本隱約有不將“日本病”視做病癥,反而視做精華的“氣概”。無論在歌舞升平還是今非昔比時,日本經(jīng)濟學界“日本特殊論”的主張仍死而不僵:即認為日本的經(jīng)濟體制中包含了許多不同于歐美的、特殊和異質(zhì)的模式特征,有些制度特征看起來已經(jīng)違背了市場經(jīng)濟的一般原理,但是依然可以保證日本經(jīng)濟的持續(xù)增長,這主要表現(xiàn)在政府的過渡干預、對金融體系的嚴格管制、對外部市場的隔離等。至今這種奇談怪論仍廣泛存在。市場機制總是有其內(nèi)在邏輯的,諸如參與著的平等競爭,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由市場自發(fā)決定等。任何借口本身的國情特殊而否認市場規(guī)律的一般性的企圖,無論出于什么動機,都必然在長期內(nèi)受到市場規(guī)律的懲罰。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曾經(jīng)有人一度鋪設(shè)了鐵軌,并用馬拉著火車前進,重新發(fā)明了既安全又省卻了環(huán)境污染的“火車”;也曾經(jīng)有人接受了市場經(jīng)濟的名詞,并用政府主導褻瀆了“看不見的手”基本原則,重新詮釋了和市場經(jīng)濟無關(guān)的有特色的“市場經(jīng)濟”。
四、中國應該警惕什么:昔日奇跡的楷模今日困窘的前車日本一度成為東亞群起效仿的楷模,至今也并無群起誅伐的跡象。但也許,我們應該三省吾身,將上述盛極而衰的過程看得完整些,因為在亞洲得“日本病”的并不僅僅是日本,也涵蓋了很多其它經(jīng)濟體。令人不安的是,中國經(jīng)濟成長所帶有的“日本病”色彩在被涂抹開來,連“創(chuàng)新”這樣千差萬別、箐蕪俱存、主要由私人部門進行的事情也被冠以“工程”之名。如果視其為楷模,那已是昔日曾經(jīng)的楷模;而如果視其為前車之鑒,則今日已是從理論和實踐中重新審視,避免重蹈覆轍的時刻了。
不安跡象之一是體制復歸的潛流洶涌。“日本病”已經(jīng)揭示出:產(chǎn)業(yè)政策在趕超的初期也許是奏效的,但必將趨于弱化和失效;而無人對產(chǎn)業(yè)政策失敗負責怎又將導致政府重新依賴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靠凱恩斯類似“酗酒”的方式刺激需求。而這種跡象在我國已隱然浮現(xiàn)。1、目前政府動用私人部門資源,注入效率低下的國有經(jīng)濟部門的趨勢有所強化,但舊企業(yè)的虧損乃至破產(chǎn)和新企業(yè)的崛起和壯大正是市場機制這枚硬幣的兩面,無論是國有企業(yè)還是私人企業(yè),試圖讓其長生不死始終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無論是年愈50年的幼稚產(chǎn)業(yè)還是“過度競爭”的產(chǎn)業(yè),都是市場機制被阻滯不能完成起碼的資源配置的惡果。2、過去我們也是熱衷于制訂產(chǎn)業(yè)政策。產(chǎn)業(yè)政策失靈后,又重拾日本的牙篲,祭起財政、貨幣政策的大旗,走上艱難的宏觀調(diào)控之旅。雖然,目前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還有一定的操作空間,還可以再支撐幾年,但若干年以后,我們該怎么辦?!既有日本這個前車之鑒在眼前,我們?yōu)槭裁催€要沿著錯誤的路線往前走呢?我們不應該拿經(jīng)濟的發(fā)展前途去打賭,期望在支撐若干年以后我國經(jīng)濟能自動變好。到時一旦沒有奇跡出現(xiàn),我國可能陷入目前日本所處困境。3、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歷史表明,推動經(jīng)濟不斷發(fā)展的持久動力只能是來自于不斷創(chuàng)新,英國的由盛而衰、美國的長盛不衰和日本的趕超失敗等幾個例子都能得到很好地說明這一點。最重要的創(chuàng)新始終源自私人部門,中國20年的奇跡,經(jīng)濟學家的貢獻也許僅在于為已出現(xiàn)的奇跡在事后尋找理論支撐,恰恰是安徽小崗村農(nóng)民用按血受印創(chuàng)造的土地承包制,是江浙農(nóng)民重拾資本主義尾巴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使得改革具有了最深厚的民眾基礎(chǔ)。更何況,任何創(chuàng)新,即使是政府的集體創(chuàng)新,也只有在事后經(jīng)得起市場考驗才稱其為創(chuàng)新,我們?yōu)槭裁床荒軓纳迫缌鳎詣?chuàng)新求發(fā)展呢?!跡象之二是漸進體制的宿債未償。中國金融體系受不良資產(chǎn)之累日久矣!但這并不意味著金融部門存在著大規(guī)模的腐敗,而只是中國銀行業(yè)為漸進改革支付了成本。社會信貸始終必須為產(chǎn)業(yè)政策和國有企業(yè)的改制保薦護航,而不是尊從市場信號,因此不良貸款的沉淀是金融部門極其軟弱,扮演“準財政”角色的結(jié)果。部分企業(yè)能夠不被淘汰出局,無非也是依賴銀行長期輸血。政企、銀企關(guān)系和日本如出一轍。估計目前不良資產(chǎn)已經(jīng)突破三萬億人民幣,并且是宿債未償,金融信用和國企集團的信用正被隱含的國家信用所取代。
表2、關(guān)于中國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幾種估計
估計者
估計樣本截至時期
估計值
不良貸款占銀行總貸款的百分比
李欣欣(1998)
1996年
1997年中
24.4%
29.2%
北大中國經(jīng)濟研究中心(1998)
1997年
24.0%
樊綱(1999)
1998年
28.3%
銀行重組成本占GDP的百分比
穆迪氏(1999)
1999年
18.8%
Dornbusch和Givazzi(1999)
1999年
25.0%
資料來源:約翰.伯寧黃益平:“中國國有銀行的壞賬及其處置辦法”《經(jīng)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6期。
如同支離破碎的日本金融一樣,管制型的中國金融之所以令人不安,也并不純因歷史包袱使然,而是我們在化解這樣的問題時,諸如成立政策性金融機構(gòu)、成立四大資產(chǎn)管理公司等等,仍然高度依賴集體的智慧,而不是群眾的智慧和市場的力量。至今金融機構(gòu)的商業(yè)化和股權(quán)多樣化仍未有亮色,國有企業(yè)無預算約束的資金需求仍然勒掛在銀行業(yè)的脖子上,私營銀行和股份銀行仍遙不可及,甚至表示資金價格的利率信號也仍然殘缺不全。總言之,我們似乎仍然恐懼社會的微觀金融基礎(chǔ)有順應市場機制的根本變化。我們?nèi)绾文芷谕儑械摹⒄深A的專業(yè)銀行能夠“商業(yè)化”?!中國要告別的,也仍然是一種舊的金融模式和管制思維。換言之,如果期待一片森林,需要有資格播種、澆水和收獲的大眾,而不是三兩個勤勉的老園丁在四五株飽受病害的大樹周圍修茸枝枝葉葉。跡象之三是對市場機制的恐懼仍深。盡管改革開放20年來,順從市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逆市場的改革也并不鮮見。這突出表現(xiàn)在對經(jīng)濟成長速度主要取決于市場機制缺乏信任,對政府決定增長卻寄托不切合實際的厚望。
在重新審視日本病時,我們更深切地感受到,對待市場經(jīng)濟只可能有實事求是一種態(tài)度,而不能虛與委蛇,所有的特色是在市場沖刷后仍不改的特色,而不是事前用油氈布密密裹來生怕市場沖擊的古董。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