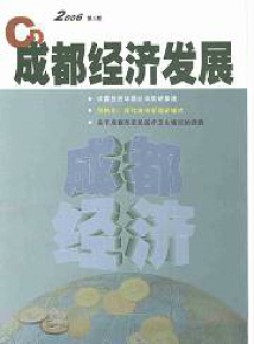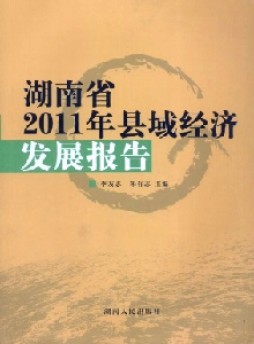經濟發展中人的可持續發展的論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經濟發展中人的可持續發展的論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從廣義的價值維度來探討“發展”,發展倫理意蘊和哲學視域不僅僅局限于增長,更不是直接等同于經濟增長。馬克思的“異化”、涂爾干的“失序”和韋伯的“工具理性的鐵籠”等理論揭示了人類在追求“增長”(經濟增長)發展過程中支付的無限代價和陷入的倫理困境。古萊認為傳統經濟“發展”“使手段絕對化,使價值物質化,并產生結構決定論”。阿馬蒂爾•森(AmartyaSen)也嚴肅指出,“主流發展觀倡導的充溢‘眼淚和鮮血’的‘殘酷’發展,將人類拖入倫理困境”。
“發展”最終必然指向“人自身”,正如古萊所指出,發展的實質在于界定美好生活、公平公正的社會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關系。發展目標必然是應然層面的人類生活改善(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和自由)與實然操作層面的優化社會安排的合理有機統一。優化社會安排在于為人們提供日益廣泛的選擇,進而尋求共同的和個人的福祉,達到改善人類生活質量,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目的。“雖然發展可以作為經濟的、政治的、技術的或社會的現象來進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終目標則是存在本身:為全人類提供充實美好的人類生活的機會。這樣來理解的話,發展就是提升一切個人和一切社會的全面人性。”路易•約瑟夫•勒布雷特(LouisJosefLebrett)在“經濟與人道主義”論證中指出“一個特定的人群及構成它的所有近鄰人群單位,以可能的最快節奏,以可能的最低代價,并考慮到存在于(或應當存在于)這些人群與近鄰人群之間的團結紐帶,從較少人道向較多人道階段的一系列過渡。因此,發展學科就是研究如何達到更加人道的經濟”。
在他看來,“發展”必定以人道為基礎,偏離對人和人性的關注,發展科學就會成為偽科學。近年來,我國學界對“發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主要觀點有:“發展”并沒有內在地包含著倫理的因素,但是與人有關的發展卻必然包含著倫理的要素。“發展根本上是人的發展,是人的解放過程。”“為了什么發展”和“什么樣的發展才是好的發展”這一價值論的問題關鍵是討論“合理的發展”所指何事,發展應“圍繞人為中心”,而不是“人圍繞發展為中心”。而這一問題正是傳統的社會發展理論和“增長”發展模式所忽視的,但對人類的生存與和諧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發展”的倫理實質在于對“人的發展”的指向上,在于如何促進人自身的進步和完善方面。
一、經濟“反發展”的倫理審視
在現代社會,在探討“發展”價值旨趣的同時必然也要深刻反思“反發展”問題。古萊對“反發展”的理解最具代表性,“如果一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新的壓迫和結構性奴役,那么這個社會就患了“反發展”。“每當有關人們規范界定的美好生活的某些基本因素———對最佳生存、尊重、自由和自我實現與集體實現的看法———減弱而不是增強時,就導致了反發展。”“反發展”是如何產生的?“其原因在于工業經濟往往失去它作為一種手段的正確地位而去掃蕩生活中所有領域的非經濟價值。”古萊認為,世界上所進行的發展可以導向經濟增長,提高部分人的生活水準,但因為好處沒有惠及世界上的貧苦大眾,所以并沒有符合使整個人類得到總體提升所要求的某些價值觀,是“發展”可能成為“反發展”的緣由。“經濟發展是伴隨著社會代價的,但是,如果這種代價是使‘發達’成為吞食千萬活人的當代莫洛哥神的,那么,這種發展就是‘反發展‘’偽發展’。”卡思陀瑞狄思(C.Castoriadis)以“社會想象的表意”來描述現代的增長發展實質。他認為,想象先于真實、理性和運作,這樣的想象不再能夠提供“定性的目標與觀點”,意識不到增長的極限,從而不再意識到社群的前進方向。真正“發達”的國家是它的人民即使并未擁有財富卻活得豐富的國家。
世界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是這些好處沒有惠及世界上的貧苦大眾,沒有符合使整個人類得到總體提升所要求的某些價值觀(例如,普遍團結),那么,這種“發展”實質上還是“反發展”,還是物主宰人的現實,而不是人得以發展,也無法增進整個人類的福祉。“今天‘發達’社會所顯示的現代化特點至多代表一種混雜的福祉,不能盲目效仿。”價值目標錯位的表征為“許多人錯誤地認為人類最重要的需要是他們的物質需要”。現代人類正在上演著荒誕的一幕:打著“發展”的旗幟卻做著“反發展”的行為。“反發展”導致人類片面狂熱追求物質財富的享受,為獲得當下利益而不擇手段,不惜侵犯后代權利,顛覆和摧毀人類正確的價值觀和精神家園,最終結果是造成人類社會的全面異化。“反發展”“以物為中心”,使“發展”成為脫離人性和人道的“偽發展”。
二、經濟發展壁壘:“反發展”導致“人的異化”倫理思考
“反發展”最直接的表象就是“人的異化”現象出現。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資本論》等著作中對資本邏輯的無限擴張導致的“異化“”物化”發展倫理問題作出了深刻揭示。20世紀70年代以前,人類認為“增長”與“發展”二者在內涵和外延上都是相同的。近代以來,雖然人們為發展實踐設定了民主、獨立、自決等價值目標,但實質上,在這些道德言辭的背后,人們真正的發展理想和目標卻是效率的提高、財富的積累和經濟的增長。人實際上成為發展的手段與工具而不是發展的目的所在。歷史事實表明“,反發展”使人類為了獲得更多物質財富而付出種種代價,出現了“人的異化”“單面化”:人陷入物質化的趨利活動中,迷失自我,喪失主體性,導致人被物質所束縛和奴役,淹沒了人的目的性存在趨勢。“人的異化”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重要障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與“發展目標是改善人類生活和社會安排,以便為人們提供日益廣泛的選擇來尋求共同的和個人的福祉”相背離,與馬克思主義提倡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終極指向和價值目的都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相背離。
“人的異化”是巨大的物質財富增長和精神家園的萎縮的結果之一。經濟發展的失誤在于只注重經濟總量的增長而淹沒了人的精神追求以及人的全面發展,認為可以通過機械運算度量人所有的經濟行動,忽視人的價值情感理性。因此,20世紀以來,伴隨著物質財富的豐富,人類普遍出現精神焦慮,人們開始反思、批判以往的人類中心主義經濟發展觀,重新檢視自身的主體性,意識到過去的主體性是片面、狹隘和不成熟的,是一種以“個體性為基礎、以統治自然為目標的人類中心的主體性”。因而是一種“黃昏的”、異化的主體性。“人的異化”是現代消費盲目和混亂的結果之一。傳統的經濟發展觀認為消費與經濟發展的貢獻成正比。因此,人們普遍追求的終極理想目標是最大限度的高消費,導致人類日益滋長急功近利、及時享樂的心態,導致人類的物質貪婪和精神空虛。這勢必把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的身心間的全面豐富、互利協調的關系簡化扭曲為單向、單一的利益索取關系,把本應全面發展的人,變成單面的、物化的“經濟人”或“工具人”。人在擺脫自然經濟條件下的“人的依賴關系”的同時,又深陷于“物的依賴關系”之中。人不僅被物化甚至被“動物化”。正如美國著名戰略學者茲•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指出,一股追求在豐饒中的縱欲無度的精神空虛之風正在開始主宰人類的行為。
“人的異化”是將人作為經濟增長的手段,偏離了經濟發展終極價值目標和倫理關懷的結果之一。烏里希•貝克指出,以財富為中心的生產同時系統地生產了社會問題、社會風險。片面的生產觀是人類進入全球風險社會的深層理念原因。現代社會成為“人為的不確定性”(manufactureduncertainties)的由人自身所引發的全面問題風險社會,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倫理關系。在經濟增長的主導意識下,人們對效率的追求優先于對倫理的關懷,物欲社會使人在慶幸自身逐漸脫離自然力的奴役和壓迫時,卻又不幸地遭受到自身創造出來的異己力量的奴役和壓迫。商品、貨幣、技術等人造物成為一種“新自然”,人被迫置于其奴役和壓迫之下,成為利益的工具、商品的附庸和金錢的奴隸,成為“經濟動物”“集體無意識”異化了的人。
這是抽象、狹隘的發展理論,而不是佩魯所倡導的“以促進該共同體每個成員的個性全面發展”的現展理論,“征服自然”“無限增長”,不僅導致階層之間、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掠奪資源、破壞環境、損害全體人類的利益,而且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初衷。
三、經濟發展利弊:以“人的可持續發展”為“發展”的終極目的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和最高價值是什么?其倫理向度如何界定?這個問題能否解決,關系著能否真正實現“發展”而不至于走向“反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和核心,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因此,我們應以“人的可持續發展”為價值指向,確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和最高價值。人的可持續發展”充分地展示人自身的全面的完整的本質,弘揚和實現人自身的全面的完整的價值,將片面的人、殘缺的人、生物的人提升為集自然活動、社會活動和精神活動于一身的最高社會有機系統的人,也就是完整的人、全面發展的人。經濟發展以人的主體價值終極關懷為切入點和基本點,才能真正實現快速、穩定、蓬勃增長。“使人們擺脫壓制性奴役(大自然、愚昧無知、受制于他人、體質、信仰)而取得自由。”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包括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的滿足、人的主體性的彰顯、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人的自由度的提高等。
在馬克思社會存在論層面的哲學視野中,發展倫理是對現代性生成、轉換過程中以人為中心的本質關系呈現。“人的可持續發展”在人性層面來說,是“人的異化”的有效倫理途徑,其目標是克服異化、實現人道,重建“發展理想”。發展倫理學家古萊對發展的業績倫理評價是:為發展支付的代價衡量、對發展的障礙評估,以及發展是否增進人類福祉的標準判斷。而他認為,區別“發展”還是“反發展”的終極價值標準就是判斷發展是否能增進人類的福祉。因此,經濟發展的真正任務是取消異化,實現技術、政治、倫理理性的有機統一,實現人的“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與自由”(古萊語)。經濟發展是發展倫理核心的問題,經濟的根本是尋求發展,而發展的根本是現實存在中“人”的發展,其實質是“人”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經濟發展不僅關注“為什么行動”(know-why)“如何行動”(know-how),更應關注“能否實現”(know-whether),其目標是如何實現人的自由。“人”的這種物種的“可持續生存”是發展的終極目的或終極價值。”
經濟進步的旨趣還是為“人”,物是為人而存在的。理性地探討和肯定人的發展問題是首要問題,樹立新的發展觀,將人的可持續發展確立為經濟發展的內在訴求和終極追求,是避免反發展及“人的異化”,達到經濟良性發展目的的根本。“人的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發展的真諦。人的可持續發展要求經濟發展的進程都應立足人的發展而不是物役人的“人的異化”。現在國際社會提倡新的國富標志,是以“國民幸福總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代替“國民生產總值”GNP(GrossNationalProduct)作為衡量人類發展的指標。這反映出現代化的重大倫理從“生產總值”轉向“幸福總值”。GNH將發展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完善方面而不是在經濟增長上,這顯現了公平、正義等價值原則。幸福指數關懷在一定意義上成為發展理論和實踐體現人的主體精神和終極價值追求的一種重要形式。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已不只是追求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字增長,其最終目的應在于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提高人的內心真正幸福指向。國家的長治久安,最終系于人民幸福(happy)不幸福(unhappy)。
“人的可持續發展”是發展的根本動力和終極目的。馬克思論述社會發展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前提和目的,強調發展的主體性。“人的可持續發展”的“以人為本”的倫理取向可以從根本上扭轉傳統發展模式“重物不重人”和“見物不見人”的傾向,將發展導向最人性化的方向,它應該成為我們發展經濟的一種共同的價值觀以及基本的思維方式和執政理念。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發展觀”,認為發展是一個與“個人自由和社會承諾”緊密聯系的過程,也是擴大人們真正享有經濟自由和各種權利的過程。他將人的生存與發展當作最高價值目標,消除“人的異化”,既重視人的社會價值,又體現著人的自我價值和終極關懷。
“人的可持續發展”是新的經濟發展理論建立的基礎。“發展”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才是發展的目的,以人為目的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本身的反省和評價提供了價值論基點,對“發展天然合理論”是一個重大進步和突破。人的物種的“可持續生存”,應當是發展的終極目的或終極價值。遵循“人的可持續發展”新理念,新的經濟發展觀必須堅持三個“倫理維度”作為其價值目標:發展的“基本需求戰略”是優先生產和發展那些滿足人民大眾健康生存的基本生活資料;必須“限制那些為了少數群體炫耀性消費而進行的生產”;將消除貧困、社會公正以及所有人健康生存作為評價標尺,真正實現經濟與人的發展兩者具體的、歷史的有機統一。
作者:唐海燕單位:廣西師范大學
- 上一篇:民間借貸對經濟發展的價值范文
- 下一篇: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研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