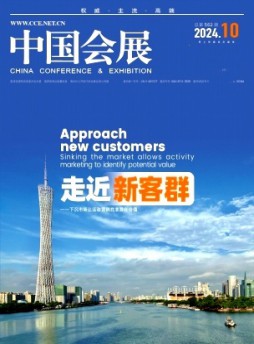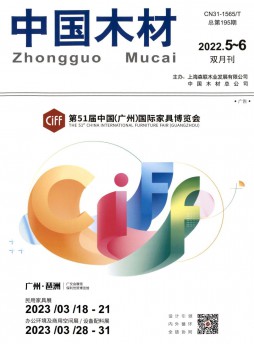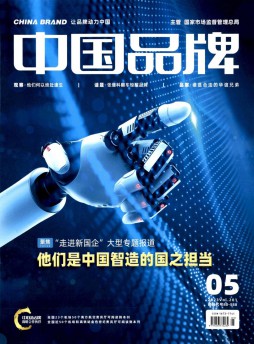中國地方經濟發展模式演化展望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地方經濟發展模式演化展望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引論:對我國經濟地方化與市場化的一般性評注
我國乃泱泱大國,地廣人多,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發展路徑各異。這決定了經濟學者必須避免對我國國情一概而論,任何整體描述或者借助均值進行描述易于流于空洞無義,因此應在經濟分析中因區域而論,即采取“地方主義”(regionalism)分析范式(herrmann-pillath,1995年,前言第30-31頁)。也正是出于同樣的原因,胡鞍鋼博士在最近的一次杭州講話中把我國的情況歸納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所謂四個世界,乃指浦東之類為第一世界,浙江之類為第二世界,農村地區為第三世界,邊遠山區為第四世界。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經濟管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這才有了地方的相對獨立行為主體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對獨立行為主體地位,才也為地方之間的橫向競爭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縱向競爭之加劇埋下了伏筆。通過權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國有企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轉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國企產權主體的"地方產權制度"(regionalpropertyrightsoflocalgovernments)(何夢筆,2000年,第1頁)。
另外一個方面,80年代鄉鎮企業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為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本文的語境中,鄉鎮企業是指廣義的鄉鎮企業概念,即“除了包括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建立的企業外,還包括農民聯戶辦和戶辦企業,以及各層次的聯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和農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業”(唐忠等,2000年,第3頁);鄉鎮集體企業是指內含集體股份、其份額大到鄉鎮村足以控股或者對其經營活動(包括利潤分配)行使各種干預的企業[2].但是,鄉鎮集體企業雖則屬于民營企業范疇,其產權制度是一種集體產權制度,實際上可以與地方政府的國企產權制度相比擬。在本文中,我們把鄉鎮集體企業的集體產權制度稱作為鄉鎮村的“地方產權制度安排”。與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國企產權主體的“地方產權制度”一樣,鄉鎮村作為鄉鎮集體企業集體產權主體的“地方產權制度”都是企業產權的“地方化”形態。
我國的“抓大放小”戰略實際上是把我國的中小國有企業通過各種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場,實行“民營化”(包括私有化)、“市場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減少),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我國鄉鎮集體企業的改制也是沿著通往市場化的同樣邏輯理路進行,實現同樣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國的諸種經濟發展模式,著重關注“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以這些模式為切入點,本文將從側面(而非正面)證實兩個判斷。判斷之一為:經濟領域的“地方化”現象要被“市場化”所取代。
判斷之二是:隨著我國引入競爭機制,地方之間的競爭加劇,各種企業之間的競爭也加劇,而治理結構較差的企業一般來說成本(包括內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農成本)較高,治理結構較好的企業的經營成本較低。企業之間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為治理結構的競爭,即制度競爭。在競爭壓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業淘汰出局或者虧損的可能性更大。我國企業大量改制的動力也源于此。
從上述判斷出發,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并初步論述五個方面的命題:(1)"浙江模式"的本質是"自組織經濟模式";(2)"浙江模式"具有可擴展性;(3)"蘇南模式"具有過渡性;(4)晚清文化傳統中的近代化因素對中國經濟發展諸模式有著整合作用(陳建軍);(5)"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擴展秩序(extendedorder)模式"或者"自發秩序(spontaneousorder)模式".
2.我國諸種經濟發展模式盤點
一般來說,所謂“溫州模式”,就是以發展個私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所謂“蘇南模式”,就是以發展鄉鎮集體企業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體發展可以總括為“浙江模式”,它是“溫州模式”的更新和擴展模式。其原因是:“溫州模式”在不斷變遷之中,逐漸得到規范,脫去了過去“坑蒙拐騙”形象;浙北地區原來學習“蘇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溫州模式”;近年來浙江鄉鎮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國的前頭。
過去許多人熱衷于討論“浙江之路”尤其是“溫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資的問題。事實上,這種討論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早在半個世紀前,弗萊堡學派代表人物歐肯就拋棄了往往引入誤入歧途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兩分法,而是對經濟現象采取創造性的形態學分析(morphologicalstudy)理路(歐肯,1995年中文版,第5頁)。他把經濟現象分為兩種理想類型,其一即為交換經濟,其二即為統制經濟或稱集中領導的經濟(比較歐肯,同上,第106-122頁)。所謂交換經濟,是指“整個社會經濟是由兩個或多個個別經濟組合起來的經濟,其中每個個別經濟(馮注——指企業和家戶)都提出和執行自己的經濟計劃”(梁小民,1996年,第123頁)。對于歐肯,理想的“交換經濟”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理想的經濟秩序則是一種競爭秩序。
還有一種“江浙模式”的提法產生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會科學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來,而對之最為具體的分析是由陳建軍完成的(陳建軍,2000年,第3頁)。陳考察了1978-1993年間江蘇和浙江的工業化路徑,之所以把江蘇和浙江的經濟發展歸納為“江浙模式”,理由是兩者都有著這樣的特點:主要依靠區域內部或國內的資金積累和轉移,對外資依賴性較小(從而區別于外資依賴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后來演化而成的“華南模式”),主要依托國內的銷售市場,由此帶動非國有企業,帶動經濟發展,全面推動地域經濟的市場化和高速增長(陳建軍,2000年,第19頁)。兩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華人文化,都有商業文化傳統。陳的觀察期較早,故而不能涵蓋后來的發展。
“浙江模式”中企業所有權構成和“蘇南模式”是不一樣的,前者以私人產權為主,后者以集體產權為主。在浙江,即使過去有許多鄉鎮集體企業,其中也有許多實屬假集體、“紅帽子”企業。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產權特征越發明顯,而始于1998年的“一次改制”后的蘇南集體產權卻以另外的形式(“不可分配給個人的集體股”)存續。近年來亞洲金融危機成為一種試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經受住了考驗,“蘇南模式”遭遇嚴峻的挑戰。從這一角度看,分頭探討“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要比籠統討論“江浙模式”妥當,除非我們不區分經濟運作中的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
3.對“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本質特征的甄別和認識
本文對“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的內涵作一重新梳理,關鍵目的在于對兩種模式的本質區別作一強調。我認為,既應從產權結構、又應從市場和政府在兩地經濟發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的本質,從而區別于一般的區分方法。
“浙江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市場解決模式、自發自生發展模式和自組織(self-organizing)模式(比較馮興元,2000年),在其中,政府的作用雖則重要,但起著促進性的、輔助性的、倡導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經濟管理作用。政府的經濟促進作用不同于經濟管理作用。后者屬于計劃經濟時代的術語[3].政府的經濟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首先,要維持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競爭秩序,這也是德國奉行的秩序政策;其次,在市場失靈或競爭失靈時可采取與市場一致(marketconform)的過程政策,它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經濟過程,這種介入不在于扭曲經濟,而在于為市場競爭打通道路,并以此為限。我們可以看到,政府也可以通過制度模仿和創新發揮熊彼特意義上的“公共企業家精神”(publicentrepreneurship)(伯恩斯,2000年,第284-289頁),輔助、促進、倡導或者主持一些經濟活動,正如在市場競爭當中,私人企業家也可以弘揚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精神,不斷地模仿和創新,實現"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destruction),推動經濟的發展(熊彼特,第147頁)。但是,這些“公共企業家”的活動有其限度,那就是它們必須遵循與市場一致的原則。我們認為,浙江的總體情況是符合以上這些理念的。
這里有必要對上述“自組織(self-organizing)”概念作一注釋。哈耶克認為,“自組織”、“自組織系統(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統(self-generatingsystems)”之類的概念來源于控制論,意謂系統內部的力量的互動創造出一種“自生自發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譯“自發秩序”,這種自發秩序源于內部或者自我生成的,有別于另一種由某人通過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導和控制其運動的方式而確立起來的人造的秩序、人為的秩序、建構的秩序或者建構(construction)(哈耶克,2000年中文版a,第55頁)。比如,最典型的自發秩序是有機體的自發秩序。哈耶克認為,自發秩序不是人類設計的產物,但屬于人類行為的產物。他認為,人為的秩序或一種受指導的秩序可以稱作一個“組織(organization)”,它來自外部,是一種“外部秩序(taxis)”,從而區別于自生自發的、源自內部整合的“內部秩序(cosmos)”(哈耶克,同上,第57-58頁)。從“組織”的定義,我們可以反觀“自組織”的定義。
有關經濟的自組織理論,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和德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何夢筆教授均有論述(krugman,1996年;herrmann-pillath,1997年)。克氏關注的是一個經濟作為復雜系統,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互動和相干作用,存在著各種混沌(chaos)和隨機(randomness)現象,互動和相干作用的結果是一種自發的秩序。克氏描述了一些空間經濟的自組織模型。何氏關注的是,“人們越來越把轉型(包括中國的轉型)感受為一個過程,該過程從長期角度看是自組織的,而非外部組織的”(herrmann-pillath,1997年,第335頁)[4].
“蘇南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政府超強干預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模式[5]、干部經濟模式、政績經濟模式(均見新望,2000年,第32頁)、干部資本主義(cadrecapitalism)模式(比較herrmann-pillath,1997年,第343頁),“(準)地方政府的地方產權制度模式”(比較何夢筆,2000年,第1頁)。我還認為,它也是一種地方(準)行政經濟模式。
如上所述,蘇南村、鄉、鎮政權對鄉鎮集體企業的實際干預和控制權可以看作為一種“(準)地方政府的地方產權制度”[6],這種對鄉鎮集體企業的地方產權制度安排雷同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安排,都有著政企不分的問題、同時產生低激勵和負激勵效應[7].國有企業在進行張維迎意義上的“民營化”(包括顯性和隱性私有化)[8](張維迎,1999年,第205-224頁),農村鄉鎮集體企業在大量改制,道理一樣。
80年代,包括蘇南在內的全國各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與“縫隙經濟”的發展有關(何夢筆,1996年,第6-7頁)。德國何夢筆教授認為,中國的鄉村工業明顯地處于“正式”經濟體系之外。農村工業的發展有著類似于“縫隙經濟”的發展。所謂“縫隙經濟”(nicheeconomy),是指“在一個具體的經濟制度里,基本上處于正式經濟結構之外的、以特定的專業化為基礎的企業運行的一種經濟形式。企業之所以可能專業化,首先是因為企業在正式制度之外活動,能夠運用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能夠取得特殊的交易成本優勢,其次是由于某些市場還沒有被其他企業系統地開發出來。”(何夢筆,同上)確實,改革初期大量經濟縫隙的存在為包括蘇南地區在內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提供了歷史機遇。何夢筆教授認為,歷史的偶然因素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國80年代中期猛烈的信用擴張和上海與江蘇這樣的地區間協作(何夢筆,同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蘇南地區政府超強干預模式取得了輝煌的成果。作者曾經在1996年考察了蘇南吳縣,那里企業盈利可觀,經濟實力雄厚,部分利潤被抽取用來建立學校、鄉村的養老院,農地被集中到種田大戶,一個村莊辦起了期貨交易所,許多青年在做綠豆期貨買賣,另一個村莊蓋起了一排排的小樓房,舉村老小都遷入新居,全村還在村領導的號召下建立了幾道數公里長的高大的水泥長廊,上面爬滿葡萄藤,穿越過茫茫綠色田野。這是一座鄉鎮集體經濟的“豐碑”。身臨其境,蔚為壯觀。這里,我們也看到了鄉鎮企業承擔了大量社會政策職能。但是,這種“公共企業家精神”已經超越了上面所述的“公共企業家”活動界限。政府干預的結果盡管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帶來積極的結果,但是政企不分的集體產權制度安排之隱患最終由于外部宏觀環境和競爭環境(如買方市場的出現)的變化而加劇了蘇南經濟滑坡,使得人們對“蘇南模式”提出疑問。
包括蘇南地區在內的鄉鎮集體企業與鄉鎮村干部的關系千絲萬縷,地方干部干預問題嚴重。這些地方干部本身往往就是“能人”,“能人經濟”的推行和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得我國經濟從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走向以鄉鎮企業為第三元的“三元經濟”(胡必亮,1998年,第288頁),為打破國有經濟壟斷、消除城鄉障礙、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和條件、實現我國經濟的全面騰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另一方面,必須看到,經濟騰飛初期與市場規范化后的政府作用是不一樣的。經濟騰飛之前和初期,市場尚不規整。許多地方傾向于集中動用一切可動用的資源,包括“權力資本”或“政府干預資源”(如開辦集體企業、國有企業、推行地方保護主義等)。但是,隨著市場規范化、一體化程度提高,一些市場扭曲因素得到糾正,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發生了作用。只有交易成本較低的企業,才能最終勝出。這里,個體企業、私營企業、股份公司、有限責任公司之類的企業產權明晰,交易成本就低,集體企業或者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交易成本就高。比如鄉鎮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職能(辦學、修路、修養老院、補貼農業等)就意味著其負擔較重。這意味著,在市場規范化之后,政府干預的功能應日漸消隱(從“越位”到“歸位”),企業的產權應交還真正的企業家,企業的管理由企業家選定的經理來管理。此外,對于政府干預和政企不分可能帶來的腐敗問題,在此可引用英國阿克頓勛爵(siracton)的一句名言來說明:“權力造成腐敗,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
隨著我國市場日益規范化而且進入買方市場,經濟縫隙的數量、形式和分布都有了變化,同一個經濟縫隙中有時擁擠著數量眾多的企業,而且必然會擠掉一些績效較差的企業。東南亞金融危機更使得我國多數鄉鎮集體企業的外部環境惡化,暴露了原先掩蓋的大量經營和制度問題。1998年,蘇南鄉鎮集體企業經歷了的第一次改制。蘇南的做法是大多是把鄉鎮集體企業改成集體控股的企業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化以后,鄉鎮村的“地方產權制度”問題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不能有所改觀,由于設置“不可分配給個人的集體股”以及地方政府通過集體股掌握的決策權等等做法,地方產權制度以另外一種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比較佐佐木信彰,1999年,第152-153頁)。
4.浙江和蘇南經濟格局的繼續演化
蘇南地區上述第一次改制并不成功,這使得許多縣市在考慮進行必要的“二次改制”(新望,2000年,第34頁)。其方向必須是政企分開,打破鄉鎮村的“地方產權制度”,確立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市場中的自主地位、私人作為獨立產權主體的地位。經濟的地方化(地方行政經濟和準行政經濟)格局必須讓位于市場化格局。這里,包括蘇南的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的紛紛轉制,正說明了經濟壓力促使企業作出適應性調整,改革集體產權制度,選擇能夠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私人產權制度。
蘇南二次改革實際上是要重新讓蘇南的市場內生發展力量發揮作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蘇南將需要“三次改制”、“四次改制”。“二次改制”的必要性說明了“蘇南模式”的過渡性。“二次改制”任重道遠,蘇南地區過去的選擇決定了它未來的選擇,這種“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y)”和路徑鎖定(lock-in)問題將會持續一段較長的時間。“二次改制”后蘇南經濟的走向似乎應與“浙江模式”趨同。蘇南“二次改制”轉移出來的鄉鎮企業社會政策職能將需要政府承擔,正如浙江省農村社會政策的缺位需要政府發揮相應作用一樣。由此出現一種趨勢,那就是蘇南的經濟發展路徑將向著浙江模式的趨同。也就是說,事態的發展可能導致根本沒有獨立的“后蘇南模式”。當然,這一判斷并不意味著蘇南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可能會有問題。江蘇實力雄厚、技術先進的企業數目似乎比浙江多,經濟結構更為合理,上市企業數目更多,重工業如鋼鐵工業也在發展之中,當前的結構調整幅度很大,也可以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后勁。浙江經濟也還在演進中,浙江的經濟結構過去以“輕(工業)、小(工業)、集(體企業)、加(工業)”著稱。有人把這種經濟結構的特點看作是“浙江模式”的特點,把“浙江模式”概括為“農村工業化+專業市場”(參見金祥榮,1998年,第122-123頁),這是片面的。這些都是一些表面現象。浙江模式的核心是上述提及的自發和內生的經濟發展,帶有強烈的自組織(self-organizing)特征,其動力來源于民間力量和浙江的傳統文化,也就是說,在浙江,市場力量起著自組織的作用,政府起著促進性和輔助性的作用。恰恰是這一實質區別于蘇南模式。蘇南模式的動力來源更多的是來源于鄉鎮村干部的干預(如“能人經濟”,其中“能人”往往是鄉鎮村干部)以及它和鄉鎮企業的政企不分。
浙江的改制在全國最為徹底和超前,許多縣市的改制已經基本完成。由此,浙江模式的表面特征“輕、小、集、加”變成了“輕、小、加”。浙江經濟尚在蓬勃發展中。在其中,企業家作為行動者(actor)甚或能動者(agent),其學習過程起著重要的作用。浙江各地較有規模的未上市民營企業也在尋求上市。浙江經濟在轉型中,不會滿足于“輕、小、加”。但是,浙江的經濟結構調整也存在路徑依賴問題,要克服該問題尚需時日。經濟結構調整總是一個長期的問題,不過,浙江的行政經濟色彩已經非常淡薄,這有利于企業通過購并重組擴大企業規模[9].
5.歷史卡片:晚清傳統文化中近代化因素的影響和整合力量
浙江省地處東南沿海前線,資源貧乏。出于備戰的需要,中央一方面把工業投資分散在全國各地,另一方面不在浙江發展重工業。改革開放前30年,國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資只有420元,屬于全國投入最少的省份(周明生,2000年,第5頁)。但依靠企業制度創新和政府職能轉換,民營經濟得到了蓬勃發展,使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3.5%(同上,第6頁)。政府政策只要有所放寬,浙江的自組織機制就會運轉。“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浙江成為一片政府無意的自組織市場試驗場。尤其是“天高皇帝遠”的溫州,早在改革開放之前就不時推出制度創新,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名聞全國的“溫州模式”。推動這些發展的是非正式制度,包括浙江的重商文化傳統尤其是溫州的重商文化傳統。溫州地區和蘇南地區都有人多地少的特點,為什么前者走上了主要發展個私經濟、后者走上了主要發展集體經濟的道路?實際上,兩個地區都有著發展工商業的傳統。
晚清以來,蘇南地區就大力發展并擁有了較發達的經濟作物種植業和家庭手工業,到了20世紀二
十、三十年代,無錫、常州、鎮江等地已成為我國民族工商業的重要基地(邱成利等,2000年,第51頁)。在計劃經濟時代,蘇南地區的社隊企業有了一定的基礎,這也便利了蘇南發展鄉鎮集體企業。溫州地區從唐宋以來一直是我國東南部手工業、小工業名城,有著提倡“功利”、“重商”的區域文化傳統,這種“甌越文化”有別于重義輕利、崇本抑末和重工輕農的傳統儒家文化(張仁壽等,1990年,第26-27頁)。早在萬歷、乾隆年間,就有這樣的史書記載:溫州人“能握微資以自營殖”(萬歷《溫州府志》卷5)、“人習機巧”、“民以力勝”(乾隆《溫州府志》卷4)。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溫州模式的文化淵源,從而不難理解問什么溫州人喜歡當小老板、搞個私企業。
我國晚清時期曾出現過一場頗具規模的地方自治運動,它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自發舉辦地方自治階段,包括兩種類型,其一由地方紳商公舉倡辦地方自治團體,以1905年成立的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為代表,其二由地方官員督導推行地方自治團體,以1906年成立的天津自治局為代表。后一階段始于1909年1月,當時清政府正式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鎮鄉地方自治選法章程》,該階段的特點是,在清政府的統籌規劃與督導下,作為籌備立憲的基礎工作,全面推行地方自治(梁景和,1999年,第157頁)。在第一階段末,有人統計地方紳商自發成立的自治研究會約有五六十個(沈懷玉,第317頁),已自發籌辦和試辦地方自治的組織機構約有六十余個(不計各省奉旨設立的自治總局)(江景和,同上,第158頁)。這些自治組織和研究會中,與我們所描述地區直接有關的至少有12個(轉引自梁景和,1999年,第157-160頁)[10].在第一階段,此外還有一些由地方官員督導推行的地方自治團體。這表明,當時的紳商階層的參政意識已經不是個別省市的特殊現象。清末后一階段,各省區大部分都已成立了各級自治機構。由于清政府的介入,使得自治團體的參政活動只能是在政府的框定下進行。《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頒布后,許多紳商更加積極地投入到地方自治運動當中。清政府把地方自治設為上下兩個級別:城鎮鄉為下級地方自治,府廳州縣為上級地方自治。到1911年,江蘇建立了40個城自治公所,210個鎮、鄉自治公所,浙江建立了54個城自治公所、30個鎮自治公所、403個鄉自治公所(同上,第172-174頁)。
晚清時候也是許多政治與非政治會社(包括經濟性會社)層出不窮的時候。著名的同盟會就是在1905年成立的。當時較為著名的會社還包括興漢會、保皇會、中國教育會、軍國民教育會,還有一些早期留日學生社團等等。
此外,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憲政后,各地以紳商為主體的社團組織活動興盛,如行會、商會、教育會、農會。許多秘密會社公開活動,類型也由單一的政治組織發展為多樣化的功能團體。當時人們對我國的國民性批判熱烈。清末先識者注重小學教育和普及教育,為國民意識的文化啟蒙做了大量的工作;許多會社還開展調查,創辦實業(桑兵,1995年)。
對于這些地方自治活動和會社活動的重要性,國外學者早已關注,許多文獻里均有涉略,但我國經濟學界則少有人關注。德國中國問題專家何夢筆教授就認為,19世紀末中國城市文化日趨活躍,本來可以為公民們建立形式多樣的、在“市民社會(civilsociety)”意義上的自發組織提供契機,但這些契機隨著推翻帝制和其后的政黨紛爭和軍閥混戰而被扼殺殆盡。何還認為,從那時起,中國實際上謀求實現基本上是一些集權主義性質的現代化方案和一種從上到下的專制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改造。何指出,中國目前出現的、被許多人稱作為“社團主義”的多種形式的城鎮自助組織,可以被理解為早已被人遺忘的晚期帝國時期社會經濟變遷趨勢的復興(何夢筆,2000年,第391頁)。這里,需要補充的是,我國沿著晚清傳統文化發展軌跡本來是能夠實現現代化的,這一現代化進路被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爆發、此后的戰亂以及戰后計劃經濟化所打斷(陳建軍語)。
我國歷史上不是沒有“市民社會”或者哈貝馬斯所言的介于個人和國家之間的“公共領域”((哈貝馬斯,1999年中文版)的實踐和文化傳統,上述晚清文化傳統就說明了這一點。浙江模式的發展進路似乎是撿起了30年代被掐斷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線索,似乎是晚清文化的重續。大多數中國學者在談到我國的城鄉能否建立市民社會時,都紛紛搖頭。他們沒有看到當前浙江的發展趨勢,沒有看到各地改制向著“浙江模式”趨同的普遍趨勢。人們易于看到政府的力量,即“看得見的手”(visiblehand):它們在禁止農村合作基金會,在禁止“亂集資”,在糧食流通環節搞“計劃化”,諸如此類。但是人們不容易看到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即“看不見的手”(invisiblehand)。
晚清文化中的地方自治和自發社團活動,是與市場經濟或者市場社會的發展進路兼容的。它還體現了國家和個人、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市場之間的自下而上的“分工”理路。歐盟和德國實行的輔助性原則(principleofsubsidiarity)實際上就對應于這種分工理路,我們在此申述如下:(1)凡是個人/市場/社會能夠獨立承擔的事務,政府任由個人/市場/社會來承擔。如果個人/市場/社會無法獨立承擔,則由國家提供輔助;(2)凡是下級政府能夠獨立承擔的事務,上級政府任由其自行來承擔,如果下級政府無法獨立承擔,則或由下級政府聯合承擔或由上級政府提供輔助;(3)國家對個人或者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輔助不得替代個人或地方政府的自助;(4)國家在承擔一項事務時需考慮其正當性,比如在市場失靈時考慮政府糾正市場失靈問題是否會造成政府失靈,而且考慮政府失靈問題是否比市場失靈問題更加嚴重(比較馮興元,1999年,第208頁)。可能有人對此原則表示擔憂,但是這一原則隱含的適用前提是認同國家的統一性和一體性,而這種認同在我國是存在的。
至于在市場上,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是一種橫向的平等交換關系,生產者之間是一種橫向的分工網絡關系。
晚清的文化傳統不僅在浙江有,在江蘇有,在上海也有。晚清文化傳統中重工重商重教因素非常類似于韋伯意義上的"新教倫理",有助于推進經濟的現代化。如果說浙江模式是我國的晚清文化傳統的重續,蘇南鄉鎮企業朝著政企分開方向發展的“二次改制”又是趨向“浙江模式”,那么蘇南經濟的發展進路也是向著晚清國民意識和文化傳統的回歸。
反過來說,我們認為浙江模式是可擴展的,它可以擴展到蘇南,也可以擴展到我國其他地區。這種擴展雖非一朝一夕之事,卻是一種長期趨勢。
這里,我們隱約看到了晚清文化傳統中的近代化因素的影響力量和對我國經濟發展諸模式的整合力量。
6.一個有待進一步論證的命題: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擴展秩序模式?
哈耶克最后一部巨著《致命的自負》是圍繞人類發展的擴展秩序(extendedorder)展開其論述的(哈耶克,b,2000年中文版)。晚清時期文化發展進路和浙江模式的內在理念就是符合哈耶克所言的擴展秩序邏輯的。擴展秩序秩序的涵義主要是:(1)這個秩序是“自發的”,非人為設計的,但也是人類行為的產物,它融入了無數個體的分散知識,哈耶克在書中接著李約瑟的研究指出過,中國古代停滯發展的原因在于政府控制最終扼殺了市場的生命。(2)這個秩序是可以不斷擴展的(比較汪丁丁,1996年,第50頁)。哈耶克在此之前一直使用的是“自生自發的秩序”即“自發秩序”的概念。后來可能強調此種秩序的擴展性,因而改用了擴展秩序概念(汪丁定語)。但是,據我個人的感覺,國外學者基本上還是主要引用和分析“自發秩序”概念、而不是“擴展秩序”概念。我們也沒有發現兩者有何其他區別。哈耶克之所以強調“擴展秩序”或者“自發秩序”,是因為他認為理性主義的建構主義是“理性的狂妄”和“知識的狂妄”,沒有任何一位計劃者能夠充分掌握和利用人類的全部知識。在此,哈耶克堅持了一種演化理性(evolutionaryrationality)的邏輯理路。
為了便于我們進一步理解“擴展秩序”和“自發秩序”,我們在此簡單介紹一下哈耶克對“自成法”制度(nomos)、“人成法”制度(thesis)以及兩者與“自發秩序”的聯系的理解。德國何夢筆教授對此作了非常明晰的歸納,具有指導意義。哈耶克認為,自成法是指歷史的、自發地生成的秩序(即自發秩序),人成法是根據人的理性構建的秩序(轉引自何夢筆,1996年,第118頁起)。國民經濟學理論特別趨向于把基本的法律框架納入人成法范疇,而把無關緊要的邊緣法權(如自發生成的經濟權利)納入自成法范疇。在憲法的契約理論中,這一觀點特別明顯。這種觀點認為,正是基本的法律規范,應該根據所有當事人一致同意的理性決定來確定(即一致原則)。何教授認為,哈耶克對自成法和人成法的區別卻完全與此相反。對于哈耶克,法律秩序的基本方面,只可能看作是自成的,即作為長期歷史進化的結果。從總體上看,法律的基本方面,不可能是由一個理性的決策所確定,也不可能自行決定的。理性構建主義的決定也許只是與自成法的逐步改變有關(馮注:等同于哈耶克同意波普爾可以通過“零星社會工程即piecemealsocialengineering”零星構建的觀點),所以總的規律秩序最終只能作為自成法。它在實施中,逐步加入了人成法的要素。但是,自成法應該始終是協調人成法的理性構建的原則。何教授認為,經濟整合的自發秩序,事實上是一種歷史現象。中國目前的發展,是“一種特殊的自發秩序”。何教授進一步認為,“應該像哈耶克所強調的那樣,正確理解自成法。不能把它簡單地理解為正式的法律中的一項條文,而是應該理解為一個大范圍的總體秩序。它不僅僅包括正式法規,而且本質上也包括非正式的行為規范。”我們從何教授對哈耶克觀點的洞見可以理會到,自發秩序和自成法是一脈相承的,是總體秩序的真正主要的來源。回頭觀察我國當前的情況,我們大致可以認為“浙江模式”似乎符合哈耶克擴展秩序、自發秩序,似乎是一種哈耶克意義上自發自生的、自組織的、可擴展的“擴展秩序”模式或“自發秩序”模式。“浙江模式”中的自發、自組織的(市場和社會)秩序的擴展是橫向的,基于效率原則、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的,而政府干預的擴展則是擾動性的、扭曲性的、反自由的、等級性的。政府干預往往與計劃化相關聯。計劃化的邏輯就是只要計劃者制定了一個方案,為了執行該項計劃方案,計劃者就必須把計劃擴展到全部個體的全部生活領域,從而使得計劃者的偏好替代所有個體的不同偏好,最終導致干預、強制、不自由和反人性。在“蘇南模式”中,與集體產權制度相關聯的人為安排和計劃構建的秩序成分較多,存在著發揮市場和社會的內生自組織力量的必要性。趙偉先生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文章,稱隱約發現成熟后的“溫州模式”與歐洲古典市場經濟早期發展有些相像,從而認為似乎可以把“溫州模式”稱為“中國式新古典工業化模式”(趙偉,1999年,第3版)。他的判斷有其較為充分的理由。在本文的語境里,我們不想牽扯如永無完結的“新古典”、“古典”、“凱恩斯主義”模型之類的無盡糾葛。“新古典”理論是有別于我們在此采用的演化理性(evolutionaryrationality)分析理路的。“新古典”理論強調信息的完備性和個體的原子化,而我們強調“競爭作為(知識和信息)的發現程序”(哈耶克,1969年德文版)、個體的能動性以及介于市場和國家之間的“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或“市民社會”的力量。我們還想在思想層面更深度爬梳作為“溫州模式”之更新和擴展模式的“浙江模式”,根據以上的比較分析,我基本上認為“浙江模式”符合哈耶克擴展秩序模式或自發秩序模式的必要條件。
基于上述分析,我在此提出這樣一個命題,供讀者進一步論證:“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擴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發秩序模式”。但是,要實現這一模式的擴展,需要回歸和重續晚清時期已經出現的文化傳統:即“市民社會”、“地方自治民主”、類似于韋伯“新教倫理”的倫理觀等等。這一命題很可能是革命性的,也可能是大錯特錯的。
7.結語
本文論證了“浙江模式”的自組織經濟模式本質和可擴展性、“蘇南模式”的過渡性、晚清文化傳統的近代化因素對我國經濟諸模式的整合意義。我們還認為隨著市場規范化,政府的職能需要轉換(從“管理經濟”到“促進經濟”,從“越位”到“歸位”)。我們還論述了市場秩序是可擴展的,是建立在效率、自由和平等原則基礎上,而計劃秩序或者干預則是擾動性的、反人性和反自由的。本文最后還提出了一個有待進一步論證的命題:“浙江模式”很可能就是“哈耶克擴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發秩序模式”。本文也從側面論證了我國經濟領域的“地方化”必須讓位于“市場化”,論證了隨著競爭的引入和加劇,企業治理結構的競爭即制度競爭將使得治理結構較差的企業更易淘汰出局或者虧損。
參考文獻:
1.伯恩斯,湯姆·r,《結構主義的視野—經濟與社會的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0年。
2.陳建軍:《中國高速增長地域的經濟發展—關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0年。
3.馮興元:“嘉興:不喜歡張揚”改制成果“——浙江經驗與弗賴堡學派理論的啟示”,載《經濟學消息報》,2000年9月15日第一版。
4.馮興元:《歐洲貨幣聯盟與歐元—歷史沿革、現狀、前景和經驗》,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
5.哈耶克,弗里德利希·奧古斯特·馮:《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一卷,鄧正來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2000年。
6.哈耶克,弗里德利希·奧古斯特·馮:《致命的自負》,馮克利、胡晉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0年。
7.何夢筆:《網絡、文化與華人社會經濟行為方式》,山西經濟出版社,太原,1996年。
何夢筆:《政府競爭:大國體制轉型理論的分析范式》,ntas項目(編號96/0076)研究報告中譯文,維藤,2000年。
8.何夢筆:“市場經濟中社區的作用—理論基礎、德國的經驗和中國改革所面臨的挑戰”,在《德國秩序政策理論與實踐文集》,何夢筆主編,龐健、馮興元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0年。
9.胡必亮:《中國經濟問題評析》,山西經濟出版社,太原,1998.
10.金祥榮:“‘浙江模式’的轉換與市場創新”,載《組織創新與區域經濟發展》,杭州大學出版社,金祥榮等著,杭州,1998年。
11.梁景和:《清末國民意識與參政意識研究》,湖南教育出版局社,長沙,1999年。
12.梁小民:〈弗萊堡學派〉,武漢出版社,武漢,1996年。
13.邱成利、馮杰:“‘蘇南模式’的發展及其路徑依賴”,載《中國工業經濟》,2000年第7期。
14.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生活·讀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5年。
15.沈懷玉:《清末地方自治之萌芽(1898-1908)》,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9期。
16.唐忠、孔祥智:《中國鄉鎮企業經濟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2000年。
17.熊彼特,約瑟夫:《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年。
18.汪丁丁:“哈耶克‘擴展秩序’思想初論(上)”,載〈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6年。
19.張仁壽、李紅:《溫州模式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
20.張維迎:〈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1999年。
21.趙偉:“溫州力量”,載〈經濟學消息報〉,1999年11月26日,第1、3版。
22.周明生:“體制創新——面對新世紀的重大抉擇”,載《中國改革》,2000年9月。
23.佐佐木信彰:《中國現階段經濟分析—來自日本的觀察和評價》,吉林人民出版社,長春,1999年。
24.hayek,f.(1968/1969):derwettbewerbalsentdeckungsverfahren,in:derselbe,freiburgerstudien-gesammelteaufsaetze,tuebingen,s.249-265.
25.krugman,paul:theself-organizingeconomy,blackwellpublishers,cambridge/oxford,1996.
26.herrmann-pillath,carsten:"wirtschaftspolitischesteuerungversusinstitutionelleselbstorganisationpolitisch-oekonomischersysteme:dietransformationpost-sozialistischervolkswirtschaften",in:selbstorganisation.jahrbuchfuerkomplexitaetindennatur-,sozial-undgeisteswissenschaften,band9,dunker&humblt,berlin1998,s.333-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