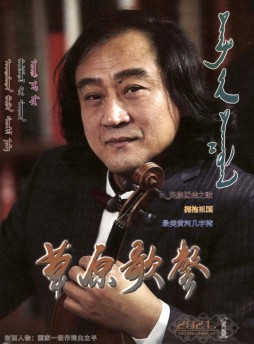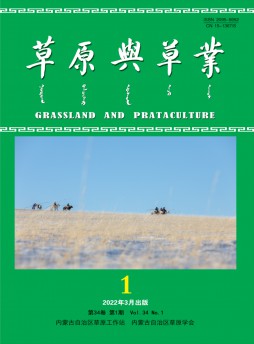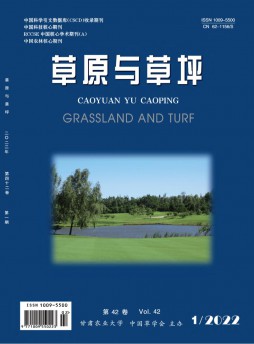草原游牧文化經濟形態的轉變及原因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草原游牧文化經濟形態的轉變及原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寧夏;游牧;經濟形態;轉變
摘要:從考古材料看,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銀川以南、寧夏中部地區就形成了以牧業為主的細石器文化,寧夏南部地區則表現為定居農耕業文化。春秋戰國時期,寧夏地區人群從事的經濟生活以畜養、游牧為主。這種經濟形態的轉變當與環境的變遷、草原畜牧的種類、馴養技術的發展、馬的馴養和御馬器的出現有關。
一、新石器中晚期寧夏地區的經濟形態
寧夏北部有陶樂縣察罕埂遺址[1]。南部有西吉縣興隆鎮遺址[2]、海原菜園遺址[3]、曹洼遺址[4]、隆德縣頁河子遺址[5]、固原海家灣墓地[6]、店河墓地[7]等遺址。1963年在陶樂縣察罕埂發現三處遺址。高仁鎮遺址采集有石核、石葉、刮削器、鏃、鉆頭、尖狀器;磨制石器有斧、錛、磨盤、磨棒、礪石等;陶器有泥質紅陶、泥質灰陶、夾砂紅褐陶、夾砂灰陶四系,器形有缽、罐、瓶、鬲等。還發現有大量動物骨骼和3件裝飾品。程家灣遺址發現的石器、陶器和高仁鎮遺址采集的基本一致。察罕埂遺址磨制石器有斧、刀、鐮、刮削器、尖狀器、鏃、磨盤、磨棒、敲砸器、礪石、石核、石葉、小石片等。陶器與高仁遺址出土物基本一致。以上三處遺址發現的遺物中“細石器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三處遺址除程家灣外,有彩陶發現,紋飾主要是條帶、弧形三角,說明這些遺址與仰韶文化有一定的聯系,其時間大致和仰韶文化同時期或稍晚”[8]。西吉縣興隆鎮遺址位于葫蘆河畔,在灰層中采集有石斧、錛、刀以及陶片等。發掘2座墓葬,M1出土細泥紅陶長頸雙耳罐和夾砂紅陶鬲;M2出土夾砂紅陶單耳罐和夾砂灰陶鬲足。墓地采集陶片以手制夾砂紅陶為主,有圈足器、尖底器、瓶等,不見生產工具。所出陶器均為齊家文化常見器物。海原縣菜園遺址1984年發掘切刀把墓地,1985~1988年發掘馬纓子梁、林子梁、石溝遺址和二嶺子灣、寨子梁、瓦罐嘴墓地。馬纓子梁遺址的年代最早,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彩陶較多,以泥質陶為主,夾砂陶次之,與馬家窯文化聯系緊密,與該地區的林子梁居址及各墓葬出土陶器有別,文化性質當不屬于菜園文化遺存[9]。林子梁遺址發掘報告定為四期五段,各期間文化內涵不盡相同。遺址內發現石器109件,以磨制石器為大宗,打制石器次之。磨制石器有刀、斧、鏟、錛、鑿、鏃、磨棒、礪石。打制石器有刀、斧、石核、尖狀器、刮削器、石球、砍砸器等。骨角器有耒、鑿、匕、鏟、針、錐、簪、鏃、環等,另外還發現羊、牛、鹿、豬、雞等動物骨骼。陶器以泥質紅陶和夾砂紅陶為多,器形主要是各種罐、甕、缽、碗、甑、尊,陶刀、陶紡輪亦多見。房址以半地穴式為主,窯洞式房屋也已經出現。菜園遺址切刀把、二嶺子灣、寨子梁、瓦罐嘴共發掘墓葬117座,隨葬的陶器與林子梁遺址的同類器近似,應屬于同一性質的文化遺存[10]。從以上遺址、墓葬出土遺物分析,菜園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有狗、豬、黃羊、北山羊、盤羊、馬、黃牛、梅花鹿、馬鹿、麝、中華鼢鼠、野兔、旱獺、雞、鷲等15個種類。這些多屬于北方草原動物類群,適宜在半荒漠山坡草地生活。牛、豬、狗可能為家畜,野生狩獵種類有鹿和黃羊。鼠類、兔、旱獺、鷲、雞的骨骼應與人類的捕食有關[11]。這些表明菜園遺址古代居民過著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及狩獵的經濟生活。
1986年發掘的曹洼遺址,陶器包括泥質陶和夾砂陶兩類,器形主要有夾砂罐、彩陶罐、盆、壺、瓶等。石器僅發現一件殘斷的石斧。從出土遺物看曹洼遺址文化的性質屬于馬家窯類型[12]。頁河子遺址地層堆積可分為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二期。仰韶文化陶器有盆、缽、罐、甕缸類及尖底瓶等。龍山時期遺存發現有房址、窖穴,主要器類有高領折肩罐、夾砂深腹罐、單、雙耳罐以及鬲、斝、盆、豆、器蓋等。頁河子仰韶遺存與秦安大地灣第九掘區仰韶晚期遺存[13]面貌基本相同,當屬仰韶晚期文化遺存。龍山時期遺存年代相當于秦魏家M89[14]和皇娘娘臺M38[15]為代表的齊家文化的年代。海家灣墓地1964年共清理墓葬3座,出土有泥質、細泥質紅陶單、雙耳罐、灰陶單耳罐,紅陶盆、瓶,夾砂紅陶單耳罐,石刀等。并在斷崖發現灰土、紅燒土、白灰面,文化層厚0.1~0.3米,是為當時居民定居生活的反映。店河墓地1965年清理墓葬6座,墓坑長方形或橢圓形,均為單人屈肢葬。出土石器有斧、錛、綠松石飾,均為磨制。陶器有瓶、單耳罐、雙耳罐、罐、紡輪。骨器有齒槽骨片和骨珠。“店河墓葬具有少量的半山類型因素,而陶器則顯示出和齊家文化的相同性,盡管部分陶器具有本地區明顯的特點,但就總體來說,仍屬于齊家文化。”[16]以上這些考古資料表明,寧夏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居民住在臨近河谷的臺地上,以農業為主,以狩獵或家畜畜養為輔。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是,在這些地區的生產工具中細石器占有較大的比重,說明當地新石器時代晚期人群比中原地區同時的人群更依賴狩獵。約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這種定居的混合經濟生活,造成當地的人口增長,而部分聚落由河邊遷于谷地的斷崖上,似乎也顯示著由人口增長帶來的資源競爭[17]。同時,我們也看到這里的居民與仰韶、馬家窯、齊家文化人群有著密切聯系。他們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受到以上三種文化農業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為了適應當地干旱的氣候,他們也更依賴獵取或畜養動物,以擴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在這樣的混合經濟中,農業與牧業(或狩獵)原就是互補的,在某一方面的挫折會使人們加重對另一方的依賴[18]。就寧夏地區北部與寧南南部比較而言,南部地區發現羊、牛、鹿骨骼,以及骨角器數量增加,體現了當地人群對動物的依賴,并逐漸產生了畜養業。
二、春秋戰國至東漢初年寧夏地區的經濟形態
春秋戰國時期寧夏地區普遍發現以車馬器具、裝飾品、兵器和工具為主要內涵的北方系青銅器文化,出土地點有銀南地區的中衛狼窩子坑[19]、中寧倪丁村[20]墓地,但分布集中區域則以固原地區為主。銀川以南地區的中衛狼窩子坑、中寧倪丁村墓地均有殉牲。倪丁村墓地有馬頭骨出土。兩墓地出土青銅兵器有短劍、戈、矛、鏃、鐓,工具類有斧、錛、刀(削)、鑿、錐、針管,車馬器類有馬銜、當盧、節約、銅泡、鈴及竿頭飾,裝飾品數量最多,包括各種帶扣、牌飾、環飾、管狀飾等。另倪丁村出土有3面銅鏡、狼窩子坑出土2件銅柄鐵劍。骨器制品有鏃、針、帶鉤及環、穿等裝飾品。陶器有單耳罐。石器有礪石、石勺及各種珠串。固原地區的楊郎馬莊[21]、彭堡于家莊[22]、河川石喇村[23]等墓地,彭陽縣張街村[24]、王大戶[25]、中莊[26]等墓地中,墓葬普遍流行凸字形洞室墓,盛行馬、牛、羊頭骨或蹄骨殉牲,隨葬青銅器以車馬器具為主,裝飾品次之,再次為兵器、工具類器物。骨器較多,制作精美。陶器單一,主要為數量較少的罐。另有少量鐵器、銅柄鐵劍等出土。從出土遺物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銀川以南地區以馬具、裝飾品和兵器為主,銜、鑣、當盧、車軎、轄等車馬器普遍發現,表明此時期已經普遍馴養馬匹,并用于戰爭。隨葬品未見有生產工具,陶器少且質地粗疏,另發現有銅、骨針、錐等器,均說明當時此地區的居民從事的經濟生活已經轉變為以畜養、游牧為主,當屬游牧人群。上述各地墓葬殉牲以羊、馬居多,牛次之。殉牲之風大行與當時社會上存有大量牲畜有關,這種盛行的葬俗,應當是畜牧加重,轉化為游牧化的結果。西漢中晚期到東漢初期,在寧夏中部地區的同心縣發現有倒墩子、李家套子墓地。1985年,倒墩子發掘墓葬27座,墓道內有牛、羊的頭骨和蹄骨殉牲。隨葬品以銅器為大宗,有牌飾、帶飾、環飾、管狀飾等裝飾品,另有刀、鐏、鈴、泡。骨器有匕、管、長方型牌飾、珠飾等類。陶器均為罐。鐵器有斧、刀、錐、鑿、環、帶扣及耳環等。石制品有長方形牌飾、礪石、珠串等。金器僅有耳環一種。另有漆器、海貝、蚌珠、料珠等若干。墓葬中出土了689枚五銖錢,為該墓地斷代提供依據。李家套子發掘墓葬5座,隨葬銅器有車軎、鐓、環、泡、牌飾、帶扣、劍具,漆器有漆奩、漆盤、漆耳杯,鐵器有鐵環、鐵釜。陶器僅泥質灰陶罐一種,另有“半兩”“五銖”“貨泉”、海貝、珠飾等。上述墓葬符合匈奴墓葬的埋葬習俗,以木棺為葬具,部分墓葬為石槨、石棺墓。普遍流行單人仰身直肢葬,以羊、牛等食草類家畜為殉牲。裝飾品最具特色,圖案有伏臥狀駱駝、龜蛇相斗、雙羚羊、騎馬驅車捉俘等。多為浮雕或透雕帶飾。部分帶飾表面鎏金,圖案為軀體翻轉的馬、羊、虎等。
三、寧夏游牧經濟形態轉變的原因
1.氣候、環境的變遷全新世中期的氣候存在著冷暖、干濕的變動[27],我國出現了“仰韶溫暖期”。然而這個“大暖期”本身也不穩定[28],距今約5000年和4000年的有兩次極端降溫事件,給中國北方文化造成了重大影響[29]。從公元前11世紀開始至西周時期,全新世中期溫暖期結束,氣溫下降,趨于干冷期。約自公元前8世紀中葉至春秋時代,氣候又轉暖了[30]。氣候帶南移,氣候趨于干冷化,不適于農業的發展,于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寧夏北部普遍出現大量細石器,而寧夏南部地區骨角器開始逐漸增多,并有不同種屬的動物骨骼被發現。由于農業的衰退,人口又相對集中,對資源的競爭日趨激烈,導致戰爭頻繁出現。同時人群開始較大幅度的移動,最終導致經濟形態發生轉變。這也就可以解釋緣何經歷仰韶、馬家窯、齊家之后的在此長期活動的農主牧副的混合經濟聚落人群消失了。直至春秋中晚期出現了新的從事游牧的人群。
2.草原畜牧的種類及馴養技術的發展從墓葬殉牲習俗我們了解到,春秋中期至西漢中晚期寧夏地區的游牧人群主要是以牧養牛、羊為主。寧夏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由于沒有經正式發掘,遺物多為采集,所以在動物的種屬方面難以斷定。陶樂高仁遺址出土有“大量的動物骨骼”[31],可見除從事農業外,兼營畜養或狩獵行為是存在的。菜園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有狗、豬、黃羊、北山羊、盤羊、馬、黃牛、梅花鹿、馬鹿、麝、中華鼢鼠、野兔、旱獺、雞、鷲等15個種類。牛、豬、狗當為家畜,野生狩獵種類有鹿和黃羊,鼠類、兔、旱獺、鷲、雞的骨骼表明與人類的捕食有關。可見寧夏南部地區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漢中晚期,主要以牛、羊為畜養放牧的對象。墓葬中未見有豬這種動物用于殉牲或豬題材的青銅器出現。這是因為豬行動能力弱,是與草原游牧經濟不能相容的動物。王明珂先生指出豬與馬、牛、羊在生理上有基本的差異,不僅僅是它的移動性(特別是在初生階段)差,更重要的是在環境資源困乏時它與人類在生態上是處于競爭地位的,飼養馬、牛、羊等食草動物才能擴張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范圍[32]。而寧夏地區未見有豬這種動物,正是這一地區草原游牧化程度較高的表現。
3.馬的馴養和御馬器的出現春秋中晚期寧夏地區青銅文化墓葬出土車馬器和殉牲馬頭骨、蹄骨,說明馬在此時已被馴養,并用于牽引和騎射。目前,在中國長城以北的北方地區發現最早的馬具,時代約在西周晚期[33]。寧夏地區在春秋中晚期就普遍出現青銅馬鑣、馬銜、節約、當盧。戰國晚期還出現了鐵馬銜、鑣等,另外骨制馬具也很發達。這都證明了春秋中晚期以來普遍存在的游牧經濟生活。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寧夏地區游牧業的起源經歷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以農主牧副、兼營狩獵的經濟生活時期;因氣候的逐漸干冷化,在春秋中期,游牧化程度較高的游牧人群在寧夏銀南和寧南地區出現,并創造了以楊郎馬莊代表的寧夏北方系青銅游牧文化。此時期,從畜種來說,羊是占絕對的數量,馬、牛、羊混合放牧。兩漢時期,寧夏中部地區的匈奴民族屬內附人群,漢化現象比較明顯,在經濟上已經不是游牧民族了,可能從事牛、羊的畜養,并與臨近的漢族交換獲取生活所需,出土的大量五銖錢能說明這一點。不見有馬殉牲,可能預示著此時期的中央政權對內附的匈奴民族在馬匹的馴養上是有嚴格限制的。
參考文獻:
[1]鐘侃.寧夏陶樂縣細石器遺址調查.考古,1964,(5).
[2]鐘侃等.寧夏西吉縣興隆鎮的齊家文化遺址.考古,1964,(5).
[3]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寧夏菜園:新石器時代遺址、墓葬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4]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等.寧夏海原曹洼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3).
[5]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等.寧夏隆德縣頁河子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4).
[6]寧夏回族自治區展覽館.寧夏固原海家灣齊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5).
[7]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店河齊家文化墓葬清理簡報.考古,1987,(8).
[8]鐘侃.寧夏陶樂縣細石器遺址調查.考古,1964,(5).
[9]陳斌.論菜園遺存與周邊文化的關系.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編.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95.
[10]陳斌.論菜園遺存與周邊文化的關系.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編.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95.
[11]陳斌.論菜園遺存與周邊文化的關系.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編.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103.
[12]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等.寧夏海原曹洼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3).
[13]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秦安大地灣第九掘區發掘簡報.文物,1983,(11).
[14]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齊家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75,(2).
[15]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皇娘娘臺遺址第四次發掘.考古學報,1978,(4).
[16]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店河齊家文化墓葬清理簡報.考古,1987,(8).
[17]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起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
[18]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起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
[19]周興華.寧夏中衛縣狼窩子坑的青銅短劍墓群.考古,1989,(11).
[20]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考古隊.寧夏中寧縣青銅短劍墓清理簡報.考古,1987,(9).
[21]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93,(1).
[22]延世忠.寧夏固原出土戰國青銅器.文物,1994,(9).
[23]羅豐.寧夏固原石喇村發現一座戰國墓.考古學集刊(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30~131,142.
[24]楊寧國等.寧夏彭陽縣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考古,1999,(12).
[25]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大戶與九龍山:北方青銅文化墓地(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26]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大戶與九龍山:北方青銅文化墓地(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27]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1).
[28]施雅鳳等.中國全新世大暖期的氣候波動與重要事件.中國科學(B輯),1992,(12).
[29]韓建業.距今5000年和4000年氣候事件對中國北方地區文化的影響.周昆叔等主編.環境考古研究(第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59~163.
[30]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1).
[31]鐘侃.寧夏陶樂縣細石器遺址調查.考古,1964,(5).
[32]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起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
[33]翟德芳.北方地區出土之馬銜和馬鑣略論.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3).
作者:馬強 單位:南京大學歷史系
- 上一篇:探討北方造林技術與管理范文
- 下一篇:草原鼠害的中草藥防治方案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