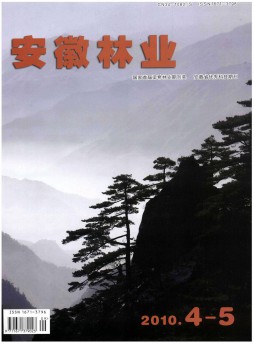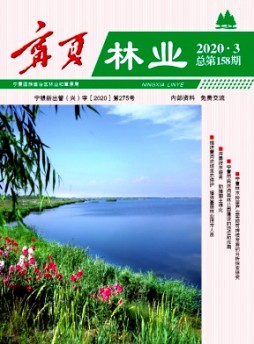梁希大林業思想探索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梁希大林業思想探索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大林業思想”是梁希最重要的林業思想。所謂“大”,在梁希看來,林業、農業、水利三者屬于一個大的生態系統,林業在其中是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用梁希的話說:“有森林才有水利,有水利才有農田。”1以后梁希年年宣傳這一觀點,從1949到1958年,發表的74篇文章里有40多篇都在強調這一觀點。梁希認為,林業是水利和農業的根本,沒有林業就沒有水利和農業;抓住了林業,就等于抓住了解決中國諸多生態問題的關鍵。中國歷史上旱災、水災、沙災頻仍,長期襲擾著農業。母親河黃河決堤之事時常發生,頻頻危及兩岸兒女;而長江已有學者如姚傳法、郝景盛發出警告:“如果長江各支流,都變成了嘉陵江,我敢預言,并且堅決的武斷,今日的長江,會變成來日的黃河。”2沙災問題更是遠比水旱災嚴重。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沙化面積就已達到國土總面積的17%,范圍涉及全國29個省區,而且沙化還在呈逐年擴大之勢,并非夸大的說,已經逼近北京城下。3要解決這三類棘手的問題,非重視森林、發展林業不可。早在1950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就發表社論對梁希的“大林業思想”予以支持,標題是“重視森林,保護森林”。文中重點論述了梁希的“沒有森林就沒有水利,沒有森林就沒有農業”的觀點,指出了“水災和荒山的密切關系”,并提出“沙之為害,更甚于水”,指出“沙的災害,只有培植森林才能解決”。借以說明中國當時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重視森林,大力發展林業。對梁希的大林業思想,陳曉原等很多學者發表文章予以支持,進一步論證森林與水利、水旱災的關系。高層決策人士也基本持肯定態度,特別是對森林所起的生態作用方面。總理一直強調“要合理砍伐,保護森林資源”,認為“保護森林是關系到國計民生、子孫后代的一個大問題”。如果梁希的“大林業思想”能夠被順利接受,那么中國朝向現代化的轉型從20世紀50年代初即已開始。多數現達國家(蘇聯、美國、德國、日本、加拿大以及芬蘭、瑞典、挪威北歐三國等)是從重視林業發展林業開始的。這時因為林業不僅僅保障農業、保障國土安全(指水利),它還向工業尤其是建筑業提供木材,向化工業提供原料,向人民群眾提供生活用品、生活副食品,提供休息場地,提供療養場所;一旦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了,它還提供旅游景點、森林公園,豐富生活內容,提高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當初孫中山以“建設生態環境”為治國方略,應該是考慮到了發達國家的成功之路。可惜歷史無法假設。先是1950年年底的抗美援朝,原先擬定的林業全面規劃不得已作出了大幅修改;接著是1953年中國在“一五”期間全面地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在東西方思想的強烈碰撞下,有著西方學習背景的梁希以及與西方并軌的“大林業思想”落在了下風,最明顯的信號就是林業部從治山治水治黃的主角悄悄退位為配角;到了50年代中期,全國城鄉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以農村為例,農民進入了合作社,一部分農民原先具有的林權受到了干擾,以后合作社、高級社升級為,林權全部交給了,農民對林產的關心程度受到巨大影響。在廣大農村,如果沒有農民的積極參與,任何良好的愿望都要大打折扣,林權的表現最為典型。梁希“大林業思想”的落實,其依靠的對象恰恰主要是農民。更重要的還在于,最高決策者與梁希等科學家之間在治國理念上有差異。主席當時考慮更多的是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問題,因而未能認識到大林業思想中包含的積極意義;而且在看來,農業才是基礎,林業只是大農業中的一部分。所以,在的語言排序中總是農、林、牧、副、漁。1959年7月4日(時梁希已經去世),在一份中央下發的文件中特意加了一段話,其中第一句就是:“所謂農者,指的農林牧副漁五業綜合平衡。”4這樣一來,林業的地位再一次降回到農業之下。思想不一致,這很正常,如果說服不了只有等待。只是這一等待,時間長達半個世紀。直到1998年驚心動魄的長江大水災之后,中國人民重新認識與重新接受了“大林業思想”,中國的林業這才開始步入良性健康發展的道路。
二、“大林業思想”中包含的治黃情結
在梁希看來,林業既然是農業的根本,是水利的根本,林業對治山治水就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甚至可以說是份內的事,沿著這樣的思路繼續朝前,根治黃河水患就被新任的林業部長視為天經地義的份內事。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夠明白梁希在1946年元旦發表在《林鐘》復刊號上的“我們的責任在山林”和希望“黃河流碧水,赤地變青山”的提法。可見梁希早就把“黃河流碧水,赤地變青山”當作是林業研究人員必須加倍努力務求實現的奮斗目標,否則便對不起自己,對不起林鐘。談到根治黃河水患,從國際上看,世界上發達國家大多沒有水利部,如與中國水利部相對應的美國是環保署,俄羅斯是自然資源部,德國、芬蘭、瑞典、挪威等國為環境部,英國為國際發展部,日本則是由建設局、農林水產省、國土廳、通產商業省、環境廳共管。原因很簡單,并非真的沒有旱災水災,而是多數國家在自然災害形成的初期就緊急著手處理,直到恢復青山綠水,所以雖有水利問題無需像中國設水利部以應對。以日本為例,日本由于曾經發動侵略戰爭,國內森林大多砍伐一空,戰后災害連年發生。1952年,梁希曾對日本的水災有過擔心:“出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議的日本代表宮腰喜助先生說:在大戰中,秋田、高知、歧阜、愛知、長野、青森、山形等縣的大好森林,都遭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無情的濫伐,木材被造船廠搶購,拿去造二百五十噸與一百五十噸的木船。小材被造船廠與人造絲工廠爭買,三十年上下的小樹恰合胃口,濫伐的結果反映甚快,大分、宮崎、岡山、兵庫等縣河川下游的地方,普遍地遭到歷史上不常見的水災。”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由于戰時和戰后的森林過伐和盲目開荒,出現了大量巖石裸露的荒山,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史料記載,“據建設廳調查,日本現存巖石裸露荒山32萬公頃,每年因暴雨還將出現新巖石裸露荒山4800公頃,每年從新舊巖石裸露荒山中總共要流出土沙7100萬立方米,又據1950年調查,在日本54個水庫中,由于水土流失,已有24個水庫淤塞了大半,有的甚至喪失了蓄水能力。森林的過伐也加劇了洪水災害,如戰時,將本州北部北上川上游森林砍完以后,1948年發生了一次大水災,曾有550人死亡。”2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加強了治山治水的工作,20世紀50年代初期成立了治山治水對策協議會,制定了治山治水五年與十年計劃,治山治水事業費增至每年1086億日元。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日本已再現青山綠水的原貌。法國也是治理水災成功的典范。梁希的原中央大學森林系的同事李寅恭曾撰文介紹法國一度出現水災且為禍甚烈,最后通過植樹造林戰而勝之。“法國南境多山,先是十九世紀初時,森林濫伐,結果山洪瀑發,流沙遍地,為害至烈。自一八四一年工程師舒赫氏發表《根本之法在營林》計劃,繼以林學家孟德斯氏確說欲救水患,非理水防沙治保安林不可,政府乃草擬強制保安造林法,嗣是水災即減輕大半。”當地農民看到森林對農業的有益作用,遂積極參與種植保安林項目,“上阿勒伯與下阿勒伯兩省,受森林賜福尤多,農家不唯不反對收買民地,而且請求政府加編其田產,入保安林。”3日本和法國通過大規模植樹造林可以根治水患,而中國通過大規模植樹造林沒有理由不能根治黃河水患,這就是梁希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所以,就在1950年,梁希提出了林業部治黃的初步規劃:林墾部最近派人到渭、涇、洛、汾、無定河五大支流作初步的宜林地調查,明年還要派更多的人員,作更進一步的測勘,準備建造黃河水源林,以防止河沙為害。我們打算穩步前進,在沿長城的沙荒地,在黃河的水源地,由重點造林逐步前進到普遍造林,由局部的封山育林逐漸擴張到全面的封山育林。我們要請地方政府協助,重視森林、保護森林,營造森林,完成這一件大事,把西北從可怕的水災中解放出來!問題很清楚,河流兩岸沒有森林作防護網,夏天洪水一來,梯田里的泥沙勢必奔向河心,河床勢必提高,河水勢必抬升,兩岸的堤壩勢必要再加高,一年又一年,下游的許多地方黃河都成了一條“懸河”,河面比有些中心城市的樓房還高。為了防止堤壩潰決,在加高培厚堤壩的工程上面,據戰前統計,平均每年要付出二千四百萬銀元,梁希視察的1950年,黃河工程費用也達一億四千萬斤小米,而且據中央水利部觀察,與安全標準相去還甚遠。對于梁希的權威性意見,森林萬能論者、林業部高級工程師郝景盛很快發表文章予以支持。2郝氏在文中語涉水利專家,從而引發了一場20世紀50年代初期治黃究竟應該是生物措施為主還是工程措施為主的大辯論。帶著治山治水治黃的歷史責任,1952年11月,梁希第三次考察黃河,主要考察黃河的支流涇河。1953年3至4月,70高齡的梁希四下黃河,考察了無定河、延水、洛河流域,寫出了《涇河、無定河流域考察報告》,給中央的治黃工作作為參考。1955年7月,鄧子恢副總理發表了《關于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報告》。這份報告充分聽取了梁希等老一輩科學家意見,提出“工程措施與生物措施并舉”,所列生物措施包括:在溝底和溝坡造林,在河岸和河灘造林,在水庫岸邊造林,在堿地造林;營造防風固沙護田林;封山育林、坡地和丘陵地造林。梁希對決心根治黃河一事表示滿意,認為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規劃。1955年10月,在林業部、農業部、水利部和中科院聯合舉行的第一次全國水土保持工作會議上,梁希作了專題發言,繼續宣傳“要保土必須保水,要治河必須治山”,建議“采取各種措施:護林、造林、封山育林。”此時黃河中上游的治黃造林運動已蓬勃開展。1956年,梁希已七十三歲,當他得知在延安正召開五省區青年治黃造林大會時,親筆以《黃河流碧水,赤地變青山》為題向大會作長篇賀文(該文后來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繼續向青年們宣講治山治水保土保水的關系。對于根治黃河的偉大宏圖,梁希不僅看到的是黃河兩岸人民的迫切愿望與沖天干勁,而且也看到了成功和希望一定在未來。梁希逝世半個世紀以后,現在的中國治山治水治黃的思路已經完全和梁希的大林業思想合拍了。實踐證明,走了一段彎路并不可怕,只要認識到了,走回到直路是必然的。
三、梁希“大林業思想”的現實價值
據資料記載,歷史上長江流域森林覆蓋率曾高達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進入20世紀,長江流域尤其是源頭地區森林資源遭到掠奪式開采,森林覆蓋率銳減,水土流失嚴重。1957年,長江流域覆蓋率下降到22%,水土流失面積達36.36萬公頃,占流域總面積的20%;到1986年,森林覆蓋率銳減到10%,原始植被喪失了85%,水土流失面積猛增到73.94萬公頃,四川省森林覆蓋率由20%降到8%,云南省由50%降到25%。
森林資源掠奪式開采的后果最終顯現。1998夏季,降雨量特別大,持續的時間特別長,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幾百萬軍民日夜奮戰在大堤上,江西九江決堤的場面,長江兩岸多個地點因不得已爆破分流疏散人群的電視畫面,一次次牽動著全國人民的神經。據當時前方報道,湖北沙市中心一幢10層高的樓頂與長江水面持平,“一旦決口,要搶是非常困難的”,“可能江漢平原的歷史要重寫,長江要改道,數百萬生靈要遭涂炭”。最有說服力的數據還在于:宜昌水面最大洪峰流量每秒超過6萬立方米的年份至少有23年,但1998年8月8日在每秒只有56400立方米的情況下,長江水位卻一再創出歷史新高,高過往年1~2米,這個問題有力地說明了各地水土流失造成了河床抬高,問題再明顯不過,1998年8月28日國家林業局宣布:長江大河源頭及上游森林植被的嚴重破壞是造成此次大水災的根本原因。1
1998年長江大水災造成的經濟損失究竟有多大,當時及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公布,直至13年之后,方由原國家林業局局長王志寶披露為2000多億元人民幣。21956年,聽林業部匯報,當聽說林業部門每年產木材1000萬立方米,每年給國家上繳利潤5至6億元,就高興地說“林業真是一個大事業,每年給國家創造這么多的財富,你們可得好好辦哪!”3包括在內,許多人無論如何想不到大自然的報復會來得這么猛烈,這么加倍。大水災的到來驚心動魄,痛定思痛的結果是,中國自上而下展開了大討論。時已87歲的生態學家王戰在這場大水災的20年前就撰文發出警告,并提出了許多積極的有戰略意義的建議。其文章《長江確實有變成黃河的危險》在發表的當時就引人注目,此次洪災證明了他的預見,國家林業局特派專人赴沈陽求教王戰,聽取他的意見。王戰認為:從今年長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特大洪澇災害來看,主要是我們對森林作用認識的不足。大江大河的源頭和沿岸毀林開墾、森林植被被破壞是導致今年特大洪水的根本原因,是我們破壞大自然得到的必然報復。森林與水自古聯系在一起。王戰感慨地說,從千山萬水、青山綠水,到山窮水盡、窮山惡水,這個教訓必須得到深刻反思。人類必須提高對森林的長壽性、多功能性和多效益性的認識,加強對森林綜合效益評價的研究。王戰反映的其實正是“大林業思想”。這并不奇怪,王戰1936年畢業于北平大學森林系,梁希曾是該系資格最老的教授。4
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我國水土保持學科奠基人之一、北京林業大學教授關君蔚言簡意賅,“林水結合,兒孫幸福萬代;林水分家,后患無窮”,直接點到了問題的核心所在,即:國家的主要資金主要精力不能主要投放在工程措施上,應主要投放在“林水結合”上,世界上發達國家在治水方面走的都是這一條路。1999年1月,國家林業局赴日考察團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考察,結果所到之處,滿目青山、層林盡染,仿佛身在綠色的畫廊中,領略山青水秀的美景,體會到日本林業工作者的自豪,也感受到中國林業工作者的責任。日本全國森林面積2515萬公頃(1955年數據),森林覆蓋率為67%。其中天然林1338萬公頃,占53.2%;人工林1040萬公頃,占5.4%。森林蓄積量34.83億立方米。年消耗木材約1億立方米,自產2000萬立方米,從美國、俄羅斯等國進口8000萬立方米。日本是一個島國,又是臺風的中心,山洪相對于中國要多,日本解決水災的辦法自始至終就是植樹造林,從考察中得知,日本從昭和三十年(1955年)起就開始劃定了保安林,到1996年,全國劃定了17種保安林,總面積900萬公頃,這些森林主要分布于深山險峻地帶、江河兩岸、重要水源區,其中有很多是天然林,棲息著珍稀野生動物,特別是已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的自然保護區,對這些森林依法實行保護,不能隨意砍伐,對于私有林被指定為公益林的,國家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結果日本真正做到了青山常在,永續利用。1
各路專家的正確意見很快成了黨中央國務院重要決策的依據,自1998年長江大水災之后,“生態”一詞持續升溫。當年8月,天然林保護工程在生態地位十分重要的四川省率先啟動,隨后重慶、云南、陜西、甘肅、青海等省市相繼宣布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東北、內蒙古國有林區有計劃地調減天然林采伐量。2000年12月,天然林保護工程全面啟動,工程規劃期為1998~2010年,總投資968億元,工程設施范圍包括云南、四川、重慶、貴州、湖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山西、河南、吉林、黑龍江、海南、新疆17個省區,明確長江上游、黃河中上游地區全面停止天然林的采伐———讓天然林休養生息,這是梁希當年夢寐以求而不能的。讓天然林休養生息這還僅僅是第一步,黨中央國務院緊接著又開始了退耕還林工程,該工程自1999年在四川、陜西、甘肅率先試點,2000年在全國17個省區的193個縣啟動了退耕還林還草試點示范工程,截止2000年底,完成退耕造林面積136.3萬公頃,2002年1月,該工程范圍擴大到25個省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規劃在2001年到2010年,完成退耕還林還草2.2億畝,造林2.6億畝。這是一項最得民心的工程,因為受到了廣大林農的擁護,成為繼土地家庭承包之后我國農村經濟制度的又一項重大變革,截止2010年,確權到戶的林地是22.36億畝,占私人林地的81.69%,6825萬農戶拿到林權證,3億多農民受惠。2還有四項工程,分別是: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等重點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野生動植物保護及自然保護區建設工程,重點地區速生豐產用材林基地建設工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然保護區,據最新消息披露,全國林業系統建立和管理的自然保護區達到2035個,占國土陸地面積的12.9%,3將這么大面積的林地或草地全封閉或半封閉地保護起來,這更是梁希當年夢寐以求而不能的。這六項工程給國家帶來的最大變化是:全國沙化面積由上世紀末的年均擴展約3436平方公里(面積相當于三個香港)變為目前的年縮減約1717平方公里,總體實現了從“沙逼人退”到“人進沙退”的歷史性轉變。
當然,這六項工程,國家投入的資金也是前所未有的(見表1)。這六項工程突出了八個字“:普遍護林,重點造林。”這八個字正是建國初期林業部包括正副部長在內27人共同擬定的林業規劃,可惜當時客觀條件不成熟,致使中國的林業建設走了長長一段彎路。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人民日報》2003年9月11日)。該決定認為:加強生態建設,維護生態安全,是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共同主題;該決定第一次提到:堅持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相統一,生態效益優先。該決定強調三點,一、沒有良好的生態,就沒有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先進生產力。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先進文化最本質的內容。森林是人類的搖籃,是人類文明的源泉,21世紀將是一個生態文明的世紀,建設秀美山川,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既是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發展先進文化的客觀要求。三、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需求,林業不僅對改善生態面貌,拓展人類生存空間,維護國土生態安全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對促進旅游、擴大城鄉就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都有著巨大的作用。這項決定讓中國的林業在與發達國家的林業并軌的路上走得更快了,梁希的大林業思想重回主導地位了。2009年,中央林業工作會議上,國務院總理說:“林業在貫徹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態建設中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開發中具有基礎地位,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至此,大林業思想的內涵更豐富了,林業不僅在生態建設中具有首要地位,即林業在與農業、水利這一大的生態系統中是龍頭老大,而且林業在貫徹發展戰略中還具有重要地位,在西部大開發中還具有基礎地位,在應對氣候變化中還具有特殊地位。先說林業在貫徹發展戰略中具有首要地位。1999年,美國能源部組織法國、荷蘭、德國、奧地利和馬來西來等國科學家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到2050年,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氣、煤)接近枯竭,全球液體燃料的80%以上將來自木本植物,尤其是木本植物中的油料植物,以及草本植物。2該結論很快在各國政要間達成共識,于是跨越式發展林業、主動性開發生物質能源就成了當務之急。再說林業在西部大開發中具有基礎地位。據專家介紹,我國山區面積占國土面積69%,有近8億畝宜林荒山荒地,相當一部分集中在西部。3如何開發宜林荒山荒地,目前最熱門的建議就是種植可以直接或間接提煉生物柴油的木本植物。華東師范大學王子嬌就提供了一份關于《甘肅省河西地區荒漠能源植物資源利用與產業化可行性研究》(刊于《資源環境與發展》2009年第1期),該研究認為,甘肅河西地處大西北,具有豐富的土地資源,在生物質能開發方面很有潛力,作者是根據我國林業工作者在該地區引種數十種固沙灌木獲得成功的先例,建議大范圍引種同為固沙灌木的文冠果樹。報告還指出,文冠果是我國很有發展前途的木本油料植物之一,該樹種性極耐寒、耐旱,對土壤要求不高,種子含油率為30%~36%。種仁含油率為55%~67%,采用化學反應法、物理處理法和生物合成法可提煉出合格的生物柴油。報告在結論與展望中寫道,河西地區具有豐富的荒漠能源植物資源,這些植物不僅對環境具有良好的適應性,而且可以保持水土、防風固沙。在水資源過度開發利用的情況下,將生產力低下的耕灌土地,改成荒漠植物生產基地,使油質高的荒漠植物產業化,為生物能源的開發開辟更廣闊的前景。
最后再來說林業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具有的特殊地位。森林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中的獨特功能和作用,曾得到1985年《蒙特利爾議定書》和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認可,200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3次締約方大會,將植樹造林、加強森林撫育、減少毀林等列為“巴厘島路線圖”的重要內容,加快林業發展、減少碳排放量已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和行動。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高度重視國際林業政治對話,積極參加國際間林業議題談判。全面闡述中國林業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立場和主張,在氣候變化的國際進程中發揮著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作用。截至2008年年底,中國的森林面積已達到1.95億公頃,森林覆蓋率20.36%。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對全球資源的評估,中國近年來開展的大規模植樹造林和天然林資源保護,對遏制亞洲地區森林資源下降趨勢作出了積極貢獻,認為亞洲森林保護有所好轉主要歸功于中國大規模植樹造林。目前,中國大力發展綠色經濟,推動生態文明,已經為國際社會樹立了良好的形象。今天的中國林業,真正是大林業了,它帶動著方方面面,而梁希的“大林業思想”在21世紀的中國林業已經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