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考古遺址與現(xiàn)代建筑的并置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碎片化”考古遺址與現(xiàn)代建筑的并置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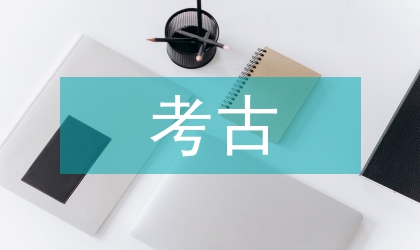
摘要:自夏商周以來,我國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均留下了大量的古代遺跡,而宋元之前的古遺跡多以考古遺址的狀態(tài)疊壓重合在現(xiàn)代城市下。在現(xiàn)代城市的擴(kuò)建及改造過程中,常伴隨著大量“碎片化”考古遺址的發(fā)現(xiàn)。隨著文物保護(hù)工作以及城市更新及轉(zhuǎn)型進(jìn)程的推進(jìn),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guān)注這類“碎片化”考古遺址的價(jià)值,并嘗試著在新建的公共建筑中保存并展示這些遺址。文章通過對兩個(gè)遺址上的公共建筑案例——希臘國家銀行管理樓(馬里奧•博塔,雅典,2002)、主教廣場辦公樓(諾曼•福斯特,倫敦,2005)的研究,從“物、場、事”三個(gè)維度對這兩個(gè)實(shí)例進(jìn)行了對比,總結(jié)出“碎片化”考古遺址與現(xiàn)代公共建筑的并置應(yīng)兼顧“遺址保護(hù)”“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事件融入”三方面內(nèi)容,并指明“事件融入”是此類新舊元素并置的策略要點(diǎn)。
關(guān)鍵字:并置;“碎片化”考古遺址;公共建筑;遺址保護(hù);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事件融入
1“碎片化”考古遺址
我國的歷史城市下常常疊壓著許多大型古代城市遺址或人類聚落遺址,經(jīng)過我國近三十年來的城鎮(zhèn)化建設(shè),這些大型遺址區(qū)多數(shù)已與現(xiàn)代城市建成區(qū)重合或部分重合。然而,能在當(dāng)前的城市建成區(qū)內(nèi)保存下來遺址的往往只是大型遺址的局部或片段,其中不乏規(guī)模較大、等級較高的遺址區(qū)域,如城墻或城壕局部(如新鄭-鄭韓故城東北角城墻遺址)、大型墓葬或車馬坑(如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大型建筑基址(如西安-大明宮遺址)、大型窯址或倉儲(chǔ)(如洛陽-回洛倉遺址)等,這些遺址多采用遺址公園或遺址博物館的形式進(jìn)行保護(hù)及展示。但在城市擴(kuò)建或更新的過程中,更多的情況是遇到一些規(guī)模較小、等級較低的遺址點(diǎn),如道路、水渠等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的局部、建筑或庭院基址局部、小型墓葬等,它們有的是在建設(shè)過程中初次被發(fā)現(xiàn),有的則是在上世紀(jì)的城市建設(shè)中回填后又重新發(fā)掘的。受建設(shè)項(xiàng)目建設(shè)情況限制,這些遺址點(diǎn)分散在城市中不同位置、遺址本體的結(jié)構(gòu)和信息也不完整,我們可以把這樣類型的遺址統(tǒng)稱為“碎片化”考古遺址。
2考古遺址與公共建筑的“并置”
在上世紀(jì)城市快速發(fā)展的過程中,這些“碎片化”考古遺址常常在發(fā)掘之后讓位于建設(shè)項(xiàng)目被請理回填。但近年來,隨著文物保護(hù)工作以及城市更新及轉(zhuǎn)型進(jìn)程的推進(jìn),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guān)注這類“碎片化”遺址的價(jià)值,并嘗試著在新建的公共建筑中保存并展示這些遺址,這種古今結(jié)合的遺址保護(hù)方法在我國還處于探索階段,建成的案例也較少,其中著名的有廣州光明廣場-南越國水閘遺址(600m2,2000-2007)[1]、南京圖書館新館——六朝建康宮城建筑遺址(300m2,2003-2007)[2]成都國際金融中心(IFS)——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1200m2,2007-2014)[3]等項(xiàng)目。這種考古遺址與新建筑“并置”(juxtaposition)的方法,是歷史城市發(fā)展過程中的必然途徑,如同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羅馬城一樣,“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事物沒有消失,所有的早期與晚期的發(fā)展階段一起并存”[4];通過“并置”,考古遺跡與新建筑建立了一個(gè)對話關(guān)系,在這種對話中,城市的歷史文脈得到了尊重與延續(xù);而對于處于城市舊城區(qū)域,面臨著開發(fā)壓力大、牽扯利益主體復(fù)雜等情況的建設(shè)項(xiàng)目來說,這樣將遺址與項(xiàng)目并置的方法無疑為城市建設(shè)與文物保護(hù)之間的平衡找到了一個(gè)結(jié)合點(diǎn)。由于這些“碎片化”的考古遺址多數(shù)位于城市的歷史中心區(qū),在當(dāng)前“存量型”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建于遺址之上的公共建筑往往肩負(fù)著保護(hù)及展示遺址、整合城市歷史文脈、促進(jìn)所在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環(huán)境提升等任務(wù),因此,這種類型的建筑設(shè)計(jì)項(xiàng)目比之其他的城市建設(shè)項(xiàng)目更為復(fù)雜。本文結(jié)合國外兩個(gè)著名的設(shè)計(jì)案例,嘗試找出這種將“碎片化”考古遺址與現(xiàn)代公共建筑并置的設(shè)計(jì)方法及要點(diǎn)。
3案例介紹
3.1案例一:希臘國家銀行管理樓,雅典(NationalBankofGreeceAdministrationBuilding,byMarioBotta,Athens,1997~2002,6500m2)(圖1~圖5)希臘國家銀行管理樓所在地塊位于雅典建于19世紀(jì)的歷史城區(qū)南部,在1833年的規(guī)劃方案中,主要空間結(jié)構(gòu)分為兩大部分,“一個(gè)理性的街道布局的地區(qū),以及一個(gè)考古公園”[5],所以北部以巴洛克式放射狀的街道布局,南部是以雅典衛(wèi)城為中心的不同時(shí)期的古代遺跡區(qū)域。新建的管理大樓所在的地塊下局部疊壓著古希臘時(shí)期的城墻遺跡——阿察尼恩門(AcharnianGate),遺址位于地下2.6米~6米處,主要包括城墻、城壕及古代道路和車轍等遺跡,該遺址曾在1974年發(fā)掘,而新大樓的設(shè)計(jì)則開始于1997年[6]。博塔將考古遺址保留并展示在地下室中,地面層結(jié)合入口廣場處采用挑空結(jié)構(gòu),展示了阿察尼恩門的擋土墻的修復(fù)部分,以及局部的古道路;在建筑的背面則采用了通高的天井空間,將自然光引入室內(nèi),從位于地下一層的遺址擴(kuò)展到地面17米的屋頂空間。結(jié)合基地周邊歷史環(huán)境,博塔采用了地上六層、地下四層的設(shè)計(jì);建筑立面則與周邊的新古典主義建筑一致,采用了對稱的原則,外部采用砂石貼面[7]。
3.2案例二:主教廣場辦公樓,倫敦(BishopSquare,byNormanFoster,London,2001~2005,101521m2)(圖6-圖10)主教廣場辦公樓位于司匹特菲爾德(Spitalfields)區(qū)域,緊鄰羅馬倫敦老城,即現(xiàn)在的倫敦金融城①的東北角。原先為一座建于1893年的水果市場,鄰近金融中心區(qū)的區(qū)域位置以及地塊內(nèi)日漸凋敝的經(jīng)營狀況,給該地區(qū)來了更新的機(jī)遇與需求,“主教廣場辦公樓”則是司匹特菲爾德區(qū)域城市更新計(jì)劃的一部分[8]。地塊的前身是一座中世紀(jì)醫(yī)院的墓園,其部分在水果市場建設(shè)時(shí)期被毀壞,1991年至2002年的發(fā)掘工作期間發(fā)現(xiàn)了的一萬多具人骨,其中還有羅馬的石棺[9]。福斯特設(shè)計(jì)的新辦公樓把所在地塊內(nèi)的遺址保存在地下室中,并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下沉的室外庭院,將一個(gè)骸骨堂的遺址展示給公眾。另外,結(jié)合地塊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設(shè)計(jì)保留了一半的老市場,并在南側(cè)沿老街道設(shè)計(jì)了低層商鋪與保留建筑呼應(yīng);同時(shí)在體量上采取退臺(tái)式的處理手法,避免了高層建筑對歷史街道景觀的破壞。
4對比與分析
對比這兩個(gè)著名歷史城市中的案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gè)案例都是近年來位于考古遺址地塊上的再開發(fā)項(xiàng)目,都位于城市的歷史區(qū)域,也都背負(fù)著遺址保護(hù)與城市更新的雙重使命。考慮到歷史城市中的各種背景因素——“時(shí)間與空間”“物質(zhì)形態(tài)與非物質(zhì)形態(tài)”以及“文化遺產(chǎn)與城市建設(shè)”,城市空間是一個(gè)由不同歷史時(shí)期“層層積淀”②而成的共生體系,這個(gè)共生體系可以從兩個(gè)維度進(jìn)行解讀,縱向可以時(shí)間為維度來分段解析,橫向維度可以看作在固定時(shí)間下(也即時(shí)間斷面中)的歷史城市要素解讀,歷史性城市景觀給出了城市背景的范疇:“主要包括遺址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其建成環(huán)境,不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當(dāng)代的;其地上地下的基礎(chǔ)設(shè)施;其空地和花園、其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間安排;感覺和視覺聯(lián)系;以及城市結(jié)構(gòu)的所有其他要素。背景還包括社會(huì)和文化方面的做法和價(jià)值觀、經(jīng)濟(jì)進(jìn)程以及與多樣性和特性有關(guān)的遺產(chǎn)的無形方面”[10]。在以遺產(chǎn)為主要研究脈絡(luò)的前提下,這些內(nèi)容可以歸納為三大部分:“物像(objects)”“環(huán)境(sites)”及其關(guān)聯(lián)的“事件(events)”[11],對于上面兩個(gè)現(xiàn)代設(shè)計(jì)案例,我們可以從這三個(gè)方面進(jìn)行對比與分析。(1)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城市建成區(qū)域內(nèi)的考古遺址,因此“物象(objects)”一項(xiàng)可替換為考古遺址“本體”,包括遺址的材料構(gòu)成、空間布局及保存狀況等內(nèi)容(表1)。(2)由于考古遺址需要原址保護(hù)③,本文中考古遺址所在地塊的“環(huán)境(sites)”主要指遺址所在地的城市環(huán)境(自然環(huán)境、歷史環(huán)境、現(xiàn)狀環(huán)境等),由于兩個(gè)案例都處于城市歷史區(qū)域,因此這里我們主要分析兩者面臨的歷史環(huán)境,主要指歷史城市的肌理,包括主要街道形態(tài)、開敞空間、標(biāo)志建筑等,兩個(gè)案例均對這些歷史環(huán)境要素進(jìn)行了梳理,并采用不同的設(shè)計(jì)方法協(xié)調(diào)應(yīng)對(表2)。(3)相關(guān)“事件(events)”這一項(xiàng)所包括的內(nèi)容有很大的外延性,可以包括相關(guān)個(gè)人或集體活動(dòng),也可包括城市的文化、經(jīng)濟(jì)及行政管理等活動(dòng)。結(jié)合本文中兩個(gè)案例情況,我們可以從考古遺址的展示、公共建筑的運(yùn)營以及城市更新的策略來進(jìn)行分析(表3)。(4)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兩個(gè)案例的設(shè)計(jì)內(nèi)容都包括以下三個(gè)方面——“遺址保護(hù)”“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以及“事件融入”。在“遺址保護(hù)”與“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兩方面,兩個(gè)實(shí)例都做得可圈可點(diǎn),但在“事件融入”方面,顯然兩者在項(xiàng)目的功能定位及城市更新的思路上有著很大的區(qū)別——希臘銀行管理樓的功能設(shè)置單一,更新思路為政府主導(dǎo)的“宏大場景”的塑造;而主教廣場辦公樓則功能復(fù)合多樣,更新思路結(jié)合當(dāng)?shù)鼐用竦纳钚枨螅⒅匚⑿ ⑵矫窕目臻g環(huán)境的營造。筆者在現(xiàn)場的參觀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兩者的完全不同的效果,希臘銀行門前的冷清與主教廣場前的熱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在并置考古遺址與公共建筑的設(shè)計(jì)時(shí),應(yīng)考慮“遺址的保護(hù)”“環(huán)境的梳理”“事件的融入”三方面的內(nèi)容,而這三者之中“遺址的保護(hù)”是前提與基礎(chǔ),“環(huán)境的梳理”是準(zhǔn)則與規(guī)律,而“事件的融入”則應(yīng)作為重點(diǎn)予以關(guān)注,而在“碎片化”考古遺址密集的城市存量地區(qū),新建公共建筑的“復(fù)合化”功能定位以及“平民化”的城市環(huán)境的營造才是地塊更新的關(guān)鍵,而考古遺址的保護(hù)與展示也將受益于更新計(jì)劃的成果。
總結(jié)
本文雖然探討的是“碎片化”考古遺址與現(xiàn)代公共建筑的并置這一問題,但這種新舊元素的并置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城市遺產(chǎn)與城市空間的新舊共存的情況中。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并置,都應(yīng)樹立“外內(nèi)結(jié)合”的城市設(shè)計(jì)視角,整體綜合的解讀梳理地塊所在環(huán)境的歷史要素、考慮多方相關(guān)利益者的需求,從而確定項(xiàng)目的定位。另外,從本文的兩個(gè)實(shí)例我們可以看到考古遺址的保存與展示方法可以多樣化、彈性化起來,具體的保護(hù)展示方法要因地制宜,只有與公共建筑的定位有效結(jié)合起來,考古遺址才能更好地融入到所在地塊或城市的事件中,讓城市空間因遺址的并置而更加豐富連續(xù)、特色鮮明,讓考古遺址因城市生活的并置而充滿活力。
參考文獻(xiàn):
[1]易西兵.城市核心區(qū)的考古遺產(chǎn)——廣州南越國遺跡的保護(hù)與展示實(shí)踐[J].城市觀察,2014(04):184.
[2]保留300平米六朝遺址南京圖書館“神來之筆”迎得喝彩,江南時(shí)報(bào),2005-10-19
[3]安博.城市遺址保護(hù)更新與人文遺址游憩型CBD的模式初探——以四川省成都市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更新為例[J].建筑工程技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15,(12):15.
[11]陸邵明.“物—場—事”:城市更新中碼頭遺產(chǎn)的保護(hù)再生框架研究[J].規(guī)劃師,2010,26(09):110.
作者:劉文佳 石明燕 曹森 單位:鄭州大學(xué)建筑學(xu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