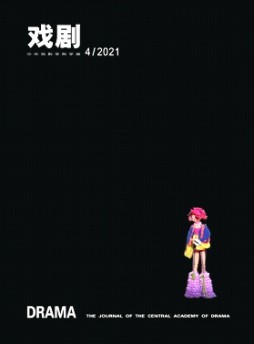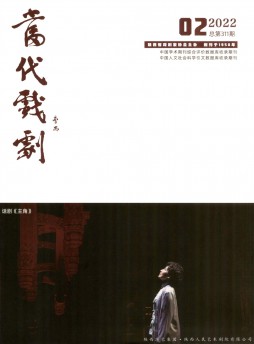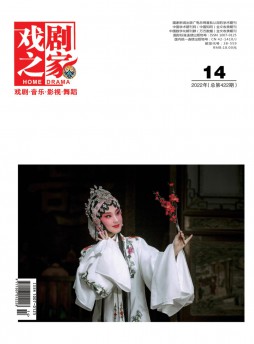曹禺戲劇創作中的宗教意識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曹禺戲劇創作中的宗教意識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曹禺的戲劇創作具有一種濃厚的基督教意識,其作品中的原罪意識、對罪惡的審判與懺悔,這些有關基督教的情節設置顯而易見。而曹禺戲劇創作中所呈現出的善惡明辨的慈悲情懷,眾生平等的意識和“輪回”現象都透露出某種佛教意識。此外,曹禺對宗教的矛盾心理,又使他的戲劇創作具有一種宗教反叛意識,并具體表現為理性思維下的宗教叛逆精神和對宗教“禁欲”教條的反叛。
關鍵詞:曹禺基督教佛教反叛
曹禺戲劇創作具有一定的宗教意識,但“曹禺接受宗教的影響決不囿于某一具體宗教形態,它是一種泛宗教影響。”[1]結合曹禺的人生經歷和戲劇作品考察不難發現:曹禺戲劇創作中的宗教意識主要表現在濃厚的基督教意識、佛教意識的關照以及宗教反叛意識三個方面。
一、濃厚的基督教意識
基督教對曹禺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在曹禺早年的生活環境中基督教堂是重要的存在,他“在課間休息時,跑到二樓的小平臺上,去聽海河那面教堂傳來的鐘聲,悠揚沉實的鐘聲也常常使他佇立凝思。”[2]17清華大學期間對西方文學作品的閱讀,讓曹禺對基督教有了更多了解。而在天津女子師范學院教《圣經》文學的經歷則令他在情感上更為親近基督教。在基督教的深刻影響下,曹禺的戲劇創作帶有一種濃厚的基督教意識,這不僅明顯地表現為《雷雨》序幕和尾聲這樣具有濃郁基督教氛圍的場景設置以及《日出》對《圣經》的熟練應用,劇作的具體情節也展露無遺。
(一)原罪意識《圣經》記載,在上帝的伊甸園中,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在蛇的誘惑下,偷吃了禁果,成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們的行為觸惱了上帝,上帝不僅懲罰了他們,還將這份罪遺傳給他們的子孫,成為人類一切罪惡、災難、痛苦和死亡的根源。因此基督教認為人生而有罪(即“原罪”)要受到懲罰。在曹禺所構筑的戲劇世界中,到處都充滿著基督教的原罪意識和人性的罪惡。《雷雨》里,蘩漪違逆人倫與周萍發生亂倫關系,為爭奪周萍失去母親的天性,將兒子拉入情場。周樸園更是罪孽深重,為人夫他無情無義,年輕時為迎娶門當戶對的大小姐拋妻棄子,年老時對妻子蘩漪專制冷酷;為人父他毫無慈愛理解,兒子們對他無比畏懼;為商他奸詐狡猾、視人命如草芥,為扣除每個小時工身上的三百塊錢,故意讓江堤出險淹死兩千二百多個小時工。而魯侍萍年輕時與周家少爺糾纏氣死母親;作為母親“明知一對兒女的血緣關系,卻允許他們遠走高飛,知罪而隱罪更是道德上的犯罪。”[3]魯貴他偷奸耍滑,嗜賭成性。身為下人不守規矩,經常順手牽羊;作為父親,把子女視為獲取利益的工具。《原野》中的焦閻王更是罪大惡極。他搶走仇虎家的地,燒了仇家的房子,誣告仇虎一家人是土匪,活埋了仇虎父親,把仇虎妹妹賣到妓院,搶走仇虎的戀人嫁給自己兒子,并將仇虎送進衙門。上一代的罪孽注定下一代生來負罪,這種原罪意識在曹禺劇作中年輕一代的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為逃避與蘩漪名義上的亂倫,周萍追求同母異父的妹妹四鳳并令她懷孕,反而陷入真正的亂倫罪惡中。魯大海與生父周樸園的階級對立與無比仇視、四鳳和周萍糾纏與亂倫、無辜的周沖的意外身亡都是原罪意識的具體顯現。焦大星和小黑子因為是焦閻王的子孫,注定他們生來“繼承”焦閻王的罪孽,最終難逃淪為焦仇兩家恩怨犧牲品的命運。可見原罪意識在曹禺劇作中并非偶然,而這諸多人物原罪性的背后,顯示的正是基督教對曹禺戲劇創作的影響。
(二)對罪惡的審判與懺悔基督教強調對罪惡的審判,《馬太福音》中有專門描述上帝審判的情節,曹禺的戲劇創作也受到了基督教這種審判意識的影響,他說:“我是個貧窮的主人,但我請了看戲的賓客升到上帝的座,來憐憫地俯視著這堆在下面蠕動的生物。”[4]78《雷雨》的第四幕其實就是一場審判:周宅客廳里劇中的人物齊聚一堂,所有真相在人物的對質中展現:四鳳和周萍私訂終身,還有了孩子;蘩漪和周萍曾是情人關系;四鳳的母親就是周家三十年前已經死去的太太,也就是周萍的生母。原來,周萍、四鳳、蘩漪都犯了亂倫之罪;周樸園曾為利益拋妻棄子;魯侍萍深藏了兄妹亂倫的秘密。在這場審判中,塵封的往事被提起,每個人的身世都真相大白,而曹禺賦予讀者(觀眾)審判一切的上帝視角,將其帶入到這場審判之中,俯瞰一切恩怨糾纏。“上帝則一方面命定人犯罪,另一方面又竭力引導人皈依。”[5]基督教通過向上帝懺悔來達到對靈魂的救贖。《雷雨》中不乏一種懺悔的意識,周萍經常去教堂,試圖通過向上帝懺悔來消解他亂倫的罪過。魯侍萍不讓女兒四鳳當下人,是對自己年輕時與周家少爺糾纏的懺悔。就連罪惡深重的周樸園也在懺悔,他一直使用三十多年前的家具,保留侍萍年輕時的習慣,是對侍萍的死懺悔;周公館成為教會醫院,也是周樸園對其一生罪孽的懺悔。這些對罪惡懺悔情節的設置,透露出的正是曹禺濃厚的基督教意識。
二、佛教意識的關照
曹禺父親在世時經常念《金剛經》,繼母也曾教曹禺背過枉生咒①。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雖然曹禺最終并未皈依佛教,無疑,在潛移默化之中曹禺也會受到佛教的影響,“父親死后,曹禺對宗教逐漸產生了興趣。……他對宗教的興趣,倒不是尋找解脫,好像宗教能給一些人生思索的啟迪。”[2]112佛教意識關照下,曹禺的戲劇創作呈現出善惡明辨的慈悲情懷、平等意識與“輪回”現象。
(一)善惡明辨的慈悲情懷佛教希望人們明辨善惡,積極修行,持有像五戒十善這樣的善惡觀。曹禺劇作中的人物有惡有善,曹禺曾表示:“無法無天的魔鬼使我憤怒,滿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淚。我有無數的人像要刻畫,不少罪狀要訴說。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無邊慘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巔,仔仔細細地望穿、判斷這些叫作‘人’的東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樣復雜的個性和靈魂。”[4]70在佛教善惡明辨的思維啟示下,曹禺的戲劇創作呈現出去惡從善的主題和一種慈悲情懷。曹禺的戲劇作品中有罪惡的資本家周樸園、奴顏婢膝的魯貴、老奸巨猾的潘月亭、道貌岸然的胡四、矯揉造作的顧八奶奶、心狠手辣的焦閻王等丑惡的形象。也不乏像朝氣蓬勃的周沖、真誠善良的翠喜,這樣閃爍著人性光輝的形象。曹禺在善與惡交織的戲劇世界構筑中,洞察人性的本質,勾勒出一幅幅社會百態圖。在善與惡的鮮明對比中,彰顯了善的可貴和惡的丑陋,立場鮮明地展現出他對善的歌頌和對丑的貶斥。“愿給一切眾生安樂叫做慈,愿拔一切眾生苦叫做悲。”[6]曹禺悲天憫人,懷有一顆慈悲之心,他曾坦言“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物的爭執。我誠懇地祈望著看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4]78曹禺試圖在戲劇創作中,將這種感情傳遞給觀眾。也正是因為曹禺那顆悲天憫人的慈悲之心,才讓人們為《雷雨》中周家兩代人的恩怨糾纏扼腕嘆息;才讓人們對《日出》里小東西的自殺感到震撼;才讓人們深刻思索《原野》中仇虎復仇的意義。
(二)平等意識與“輪回”現象平等是佛教的基本理念。所謂眾生平等,是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平等,沒有高低、親疏之分。曹禺將佛教的這種平等意識賦予了他筆下的人物。《雷雨》中最富有人性光輝的人物是周沖,在他的眼里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他拋棄門第觀念,喜歡上四鳳,一心想資助她學習幫她擺脫現狀。他從來不高看自己一等,愿意替動手打人的哥哥登門道歉,即使魯大海惡言相向,他仍愿意和他做朋友。周沖愛身邊的人,也愿意盡自己所能去幫助別人,甚至他最終也是為了救觸電的四鳳而亡。周沖作為《雷雨》中至善至純的完美形象,透過他我們能窺視到曹禺對其身上獨有的平等意識的贊美。同樣在《日出》中,曹禺也塑造了一個極富人性光輝的人物形象———翠喜。作者在刻畫這樣一個人物時,并沒有戴著有色眼鏡,反而賦予了她許多高貴的品格。翠喜雖然是社會地位低下的妓女,但她卻有一顆金子般的心,雖然自己境遇艱難卻還同情小東西的悲慘遭遇,把她當成妹妹般真心相待,給小東西幫助并鼓勵她勇敢活下去。曹禺表示“在舊社會婦女是受到壓迫的,男女之間太不平等,我總覺得婦女是善良的……我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詞來描寫最美好的婦女。”[4]29-30曹禺對翠喜美好人性的贊美,正是基于男女平等意識下對眾生平等的提倡。輪回是佛教一個常見的概念,“輪回”有流轉的意思,是指生命體生死相續,沒有止息,“輪回”現象在曹禺戲劇創作中絕非偶然。《雷雨》的故事發生在三十年來樣貌沒有怎么改變的周公館,那里上演了已經“死了”的魯侍萍和周樸園的重逢。三十年前遺留的愛恨糾纏,三十年后在“同一地點”繼續上演。而周樸園與侍萍之間的少爺戀上丫頭的故事,也從他們的身上輪回到自己子女的身上。《日出》中可憐的女孩小東西從旅館輾轉到妓院,不過是從一個高級妓院輪回到一個下等妓院,沒人能夠拯救她,她依舊要在悲慘、恐懼中度日,最終難逃死亡的命運。《原野》里仇父與焦父的仇恨,隨著父輩的死亡輪回成為仇虎與焦大星子輩間的仇恨。這種故事情節上的輪回現象,頗具佛教意味,在增加曹禺作品戲劇性的同時,也極大地加深了戲劇的深度。
三、宗教反叛意識
宗教作為人類精神的慰藉,目的是為人的心靈尋找一個安放之地。宗教實質上是一種唯心主義,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自我構建,帶有濃厚的感性色彩。然而曹禺在接觸《圣經》時,并沒有像虔誠的教徒一樣,對基督教的教條深信不疑、對上帝心悅臣服,反而卻帶著一種理性意識來“探索人究竟應該怎樣活,為什么活著應該是什么樣的人生道路?”[2]113在宗教里只有神即耶穌或是菩薩才能拯救苦難的人們,神為信徒創造了天堂和凈土等理想之地,只要虔誠信仰和修行就能到達。因此宗教成為在現世中經歷苦惱的人們暫時擺脫煩擾的精神寄托。而曹禺在受到宗教意識影響的同時又能夠超然于宗教,帶著一種理性意識來關照現實世界,思索人生存和發展的意義,尋找一條真正有意義的人生道路。這種試圖通過自身的努力,而從根本上達到自救的精神,實質上是否定了神的作用,肯定了人的作用,帶有一種宗教叛逆精神。宗教鼓勵人們約束自身,通過控制自身欲望來達到修行的目的。一般宗教都帶有禁欲的色彩,如佛教的素食主義、基督教對性格修行的要求等。曹禺雖然受到了宗教的影響,但卻對宗教的這種“禁欲”要求,充滿反叛精神。《雷雨》中的蘩漪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但她的婚姻卻非常不幸,丈夫周樸園的心里只有死去的侍萍,對她專制而缺少關愛。這個如雷雨般敢愛敢恨的女性,不甘在壓抑中消耗掉青春,她背負亂倫的罵名和周萍在一起,在他身上寄托了一個女人對幸福的所有渴望。盡管在基督教里亂倫是罪大惡極的,然而曹禺卻對蘩漪充滿同情和肯定,“在遭遇這樣不幸的女人里,蘩漪自然是值得贊美的。她有火熾的熱情、一顆強悍的心,她敢沖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獸的斗。雖然依舊落在火坑里,情熱燒瘋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憐憫與尊敬嗎?”[4]81《原野》中仇虎雖然外表丑陋性格兇殘,但當他歸來復仇時,焦花氏仍愿意拋棄一切和他重新在一起。“作家拋開了基督教義對人倫道德的規范而讓他和花金子演繹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從肉體到靈魂的戀愛……在對他們戀愛場景的設計中,絲毫看不到作家的道德評判。”[7]這種對自然人性和合理欲望肯定的背后,展現出的正是作者對宗教“禁欲”教條的反叛。
四、結語
宗教意識對曹禺的戲劇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濃厚的基督教意識使曹禺的劇作存在著原罪意識、對罪惡的審判與懺悔這樣富有基督教色彩的情節設置。與此同時,佛教潛移默化的影響使曹禺戲劇創作受到佛教意識的關照,具體表現為作家善惡明辨的慈悲情懷、平等意識與“輪回”現象。同樣不容忽視的是,盡管曹禺的戲劇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宗教意識的影響,但他對宗教的矛盾心理,也使他的創作帶有一種理性思維下的宗教叛逆精神,展現了曹禺對宗教“禁欲”教條的反叛。注釋①佛教凈土宗信徒持誦的一種咒語,亦用于超度亡靈.
參考文獻
[1]高虹.靈魂的懺悔與救贖———從周樸園的形象看曹禺作品的原罪意識[J].現代語文,2010(4):64.
[2]田本相.曹禺傳[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
[3]馬艷艷.從《雷雨》看曹禺與基督教文化[J].現代語文,2007(7):66.
[4]曹禺.曹禺自傳[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5]高浦棠.“升到上帝的座”上重新審讀曹禺的《雷雨》———《雷雨》本源真詮[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3(5):48.
[6]陳義孝.佛學常見詞匯[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8:284.
[7]王存良.從曹禺前期劇作中的人生探索看其基督思想的流變[J].黔西南民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9(4):51.
作者:冀巖 單位: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 上一篇:社會主義新時期戲劇創作的任務分析范文
- 下一篇:淺談打擊樂在戲劇中的作用分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