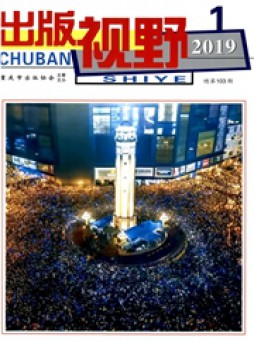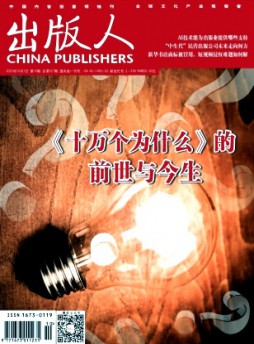出版角度下的文學翻譯質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出版角度下的文學翻譯質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20世紀90年代以來,批評文學翻譯質量的文章常見諸報端,如北大教授把孟子譯成“門修斯”、清華譯者將翻成“常凱申”的事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再如,2010年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評得火熱,唯獨優秀文學翻譯獎尷尬空缺,《北京青年報》不得不用“呈現頹勢”評價當時的文學翻譯狀況。若干現象疊加在一起,一些媒體和讀者便得出了悲觀的結論:文學翻譯質量每況愈下,譯者水平一代不如一代。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一、文學翻譯水平下滑的“非質量”原因
中肯地說,文學翻譯質量盡管有待改進的空間的確很大,但若綜合考量,并沒有證據表明當前文學翻譯水平有顯著下滑的態勢。給媒體和讀者造成負面印象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質量”和“非質量”兩類,“非質量”的原因表現如下。
1.文學譯作數量大幅上升近年來文學翻譯作品數量大幅上升,當今讀者接觸到的新譯作數量和清末、民國、新中國成立前后、改革開放前后相比已經不是一個數量級的概念。眾所周知,引進版文學類圖書一直都是圖書消費市場上的活躍因子,2013年我國共引進圖書近858萬冊,光文學藝術類就占了1/5以上。總量增加后,接觸到劣質譯作的概率也隨之增加。逮住一批不盡如人意的例子,就殃及更多其實還可以的文本,有片面夸大之嫌。把關注焦點投射在劣質譯作絕對數量之上的縱向比較,本身就不太合理,更何況這樣的比較還時常夾雜另一問題:拿新作品的新譯本和經過歷史沉淀、再版修訂多次的經典譯本做比較,是否有失公允?
2.讀者水平顯著提高高等教育普及之后,讀者文化水平顯著提高,外國文學愛好中不乏外語好手,因此,譯作被糾錯的概率直線上升——豆瓣上甚至活躍著一批專門“找茬”的民間翻譯高手。當然,互聯網也在其中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今天發現的錯誤,明天就傳遍大街小巷。有人說翻譯是“徒勞的工作”,因為不管審核多少遍,修改多少回,總有訛誤或欠缺,只是從前不易被發現,或者發現后也不具備大規模傳播的渠道,而如今隨著互聯網的火速擴散,難逃讀者的火眼金睛。不過,這對出版社而言倒不盡是壞事。完整的出版鏈條上有作者、譯者、出版社、發行渠道、讀者等幾個核心環節,而出版質量的把關長期以來都過于仰仗上游的力量——作者和譯者的職業道德操守、出版社的社會責任感、上級機關的質檢抽查;而讀者處于半缺位狀態,抒發不同意見的方式至多就是拒絕購買。圖書出版市場化運作后,讀者的位置一下子拔高了,反饋的手段既迅速又直接。譯者和出版社不再是高高在上、傳道授業的角色,而必須經常與讀者交流切磋,接受或反駁他們的批評和質疑。
3.讀者需求明顯變化與讀者水平提高所對應的是,讀者的需求已不同于以往。換作西洋文學剛傳入中國的年代,讀者甚至能接受不諳外文的林紓用“聽留學生口述后改編改寫”的方式進行翻譯。這種對文化引進曾起到驚人推動作用的翻譯方式放在今天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被讀者認可的——他們不能接受譯者對原作的刪節、篡改或二度創作,也不再滿足于聽一個自圓其說的好故事。幾十年前倘若將aspoorasachurchmouse直譯為“窮得像教堂的老鼠”而不是“一貧如洗”,肯定有人指責“翻譯腔濃”“不接地氣”“不考慮目標語國家的語言文化習慣”。而現在誰都不感違和了,因為語言和文化都在接納新的血液,變得愈發寬容和活躍。翻譯的歸化、異化之爭想必不會有定論,但譯者功力的強弱時常體現在如何兼顧這南北兩極:如果說以前的讀者更需要譯者以接地氣的方式理順故事、傳達思想,那么現在的讀者更傾向于譯文不要丟失原語的文化意象。昨天還被罵為“不倫不類”,遭到質量投訴的譯法,今天就已被普遍接受,沒準不遠的將來,誰都知道“下貓下狗”就是“瓢潑大雨”在英文中的表達,誰都適應帶著些微翻譯腔的英文長句而不需要譯者切割成更符合國人口味的短句。從這個角度而言,譯者翻譯一本書如果什么文化意象也沒有傳遞,什么佶屈聱牙、拗口艱澀的詞匯都沒有,每個可能造成理解障礙的地方都“本土化”處理,每個句子都停留在當下讀者的“舒適轄域”內,反倒沒有多大的意思了。當然把握火候是技術活,料下得過猛必然導致可讀性下降。
4.個體閱讀習慣差異大好與不好的判斷難免有主觀的成分在內。舉個簡單的例子,有讀者抱怨三個字就能說清楚的“環頸雉”不該拖沓地譯成“頸部有色環的雉雞”。但其實原文采用的就是描述性的語言,而非物種學名,所以譯文保留了表述上的特點,說來并不算訛誤,但讀者認為這屬于表達不當。有些現代和后現代文學作品故意避開或破壞傳統的敘事模式,你越習慣什么,它就越不給你看什么,讀者適應起來尚需時日,否則就很容易將語言顛三倒四和情節前后不搭全都怪罪到譯者頭上。意識流部分幾頁連成一片沒有標點,引文和對話完全不用引號隔開造成費解……哪怕是這些最小的“逆大眾傳統閱讀體驗而行”的實驗做法都有可能遭吐槽、被投訴。此外,文學翻譯中常有譯注,但有的讀者堅持認為這種做法破壞了閱讀的連貫性,是譯者“無中生有”。以上這些都屬于比較極端的案例,無非是想說明:什么樣的譯文才算好?很多時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常常會受到個人好惡、個體閱讀習慣的影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來網絡上流行將外文的大白話譯成文采斐然的古漢語,常博得叫好聲一片——為數不少的讀者把最唯美的語言界定為最優秀的翻譯,認準了“雅”才是譯者實力的體現,卻不知道或不介意譯者在追求“雅”的同時悄悄犧牲一部分的“信”和“達”。這并非一個好的趨勢,如果把翻譯行為比作射擊,所謂的“勝過原文”“比原文更有文采”“譯出了原文未有的意境”其實就是譯過頭,和譯不到位一樣,都應判作脫靶。造成翻譯出版物“質量下滑”印象的最主要原因還是無法找到理由開脫的質量硬傷,而這些硬傷往往是翻譯態度所致,甚至還沒到談論翻譯水平的地步。比如懶得考據、望文生義,將Guatemala(危地馬拉)譯成“關特瑪拉”,將巴黎塞納河畔的watersprays(供游人消暑的噴水龍頭)譯成“浪花”,將ineconomicterms(用經濟學術語來說)譯為“按經濟來衡量”;而將mayparadoxicallyprolongthelifeofsomebynarrowcastinginminoritytongues(某些小語種也可能得益于小范圍定制播放服務而延長了壽命)譯成“也會似是而非地以少數人的口口相傳延長壽命”,基本可以判定譯者自己既沒看懂也沒查證就下筆交差了。劣中之劣當屬打著“編譯”“譯述”“節譯”的幌子肆意篡改原文,或是用“中譯中”的手段抄襲剽竊。責任編輯很難察覺后者,因為文章已經改頭換面,唯獨被侵權者才會發現斟酌許久、只屬于自己的獨特表達(甚至是誤譯)竟會數度遭人撞車——2014年豆瓣上吵得沸沸揚揚的“龐某抄襲案”就是靠被侵權者自己發現的。舉證難、判定難、懲罰難,讓此類行為屢禁不止。回頭看當年烜赫一時的“卡內基/卡耐基成功學”書籍,鬧哄哄數百品種,多數都是利益驅動下靠“中譯中”手法易容后的產物。
二、文學翻譯出版現狀和問題
從出版角度談文學翻譯質量,首先,繞不開的坎兒就是優秀翻譯人才的匱乏。資深編輯、翻譯家蘇福忠曾一語道破:“如今,幾乎沒有人能以翻譯文學作品為生。人們翻譯這類作品只是出于對這一行的熱愛,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業余時間從事翻譯工作。”在有些國家,譯文的稿酬甚至高于寫作,因為寫作可以自由發揮,翻譯卻是“戴著腳鐐舞蹈”。中國大陸出版社文學翻譯的普遍稿酬是50元—80元/千字,一本20萬字左右的圖書,翻譯連同數輪修改潤色往往要耗去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稅后收入卻難達萬元。盡管低收入絕不該和低質量畫等號,但不可否認的是,出版界目前的翻譯稿酬養不起專業人才,請不動一流的譯者。文學翻譯成了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占用時間長,報酬低微,也不算作科研成果。外語功底扎實、出版經驗豐富的高手有許多條比當“譯書匠”更具性價比的出路,不愿在文學翻譯上投入精力。
其次,較之譯作的質量,譯作結構失衡的問題或許更應該引起重視。引進書中,文學類圖書占據絕對優勢,工業技術和前沿學科資源的引進則相對集中于少數幾個國家,引進數量有限,質量詬病更多。編輯在物色高端科技著作的譯者時常遇到這樣的尷尬:不少人語言過關卻不具備專業知識,不少人具備專業背景卻缺乏語言功底,為數不多的復合型人才根本不屑于從事翻譯工作。當然,出版社不太愿提及的是其自身也缺乏相應的審校力量,有些單位借口文責自負,索性放棄了對譯文質量的審核與把關,催生了一批劣質譯作;其余一些繼續打“安全牌”,出版專業要求低一些、受眾面廣一些的文學類譯作。此外,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略社會效益和出版責任也是劣質譯作的助推力。傅雷翻譯《約翰•克里斯多夫》用了5年時間,瑞典漢學家陳安娜翻譯莫言的《生死疲勞》用了6年時間,蕭乾和夫人文潔若合譯《尤利西斯》尚且用了4年時間。這些例子略顯極端,翻譯時間長的很大原因是原作難度較高,但好的譯文勢必需要充足的時間字斟句酌,就算是一般難度的文學圖書,再快也需要半年的翻譯和出版時間。可有些出版社為了迅速占領市場,甚至能在某些名人去世后一兩周內就推出其傳記的譯本。劣質譯作不少出自缺乏翻譯出版資質的單位,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與民營公司或獨立工作室“協作策劃”“協作出版”的:有的為了搶占先機,多人分譯卻不統稿,一個專有名詞多個譯法,讀者看了云里霧里,甚至無法將前后的人物關聯起來;有的根本沒有外語編輯,索性放水;有的將稿件外包給特約編輯后不再把關;有的直接采用港臺未經校訂的譯本,甚至將他人的譯本改頭換面就重新出版。上述現象究其根源,就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錯位,而這些領域法規的缺失以及監管不到位,也是造成文學翻譯質量問題老生常談卻無明顯改觀的一個因素。
無論是提高譯者待遇、積累優秀譯者資源,還是調整引進書的結構,或是實行專家呼吁已久的翻譯質量問責制度,如果沒有政策的扶持和法規的監管,一味依賴宣傳和倡導提高譯者職業道德和出版職業道德、依賴市場自身的調節,那么恐怕短期內很難突破現狀。
作者:趙舒靜 單位: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上一篇:熱帶氣旋對海上風電支撐結構的影響范文
- 下一篇:女性文學敘事特點及出版轉向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