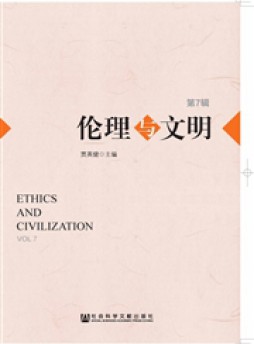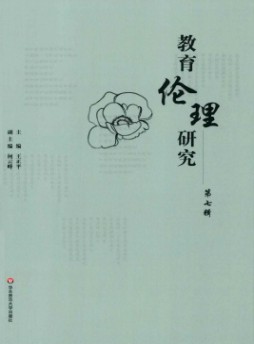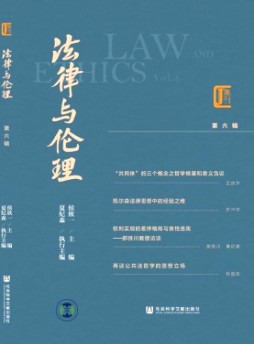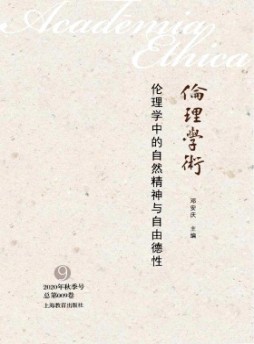倫理選擇的困惑及光芒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倫理選擇的困惑及光芒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卡勒德·胡賽尼的小說《追風箏的人》講述了一個發生在主人公阿米爾和他的仆人之間的故事。小說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小說所蘊藏的倫理內涵。文章以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理論為依據,分析主人公阿米爾在人生三個不同時期所做出的倫理選擇,闡釋阿米爾一步步棄惡向善的道德之路。文章認為,主人公阿米爾的每一次倫理選擇都為其后來的情感煎熬、道德升華做出了倫理鋪墊,也揭示了“罪惡與懲罰”“行善與救贖”的倫理意義。小說也借此實現了文學文本勸人棄惡揚善的教誨意義。
關鍵詞:《追風箏的人》;文學倫理學批評;倫理選擇;倫理環境
卡勒德·胡賽尼是美籍阿富汗作家,1965年出生于阿富汗的喀布爾。1980年,胡賽尼一家移民到了美國加州的圣荷西。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一篇塔利班禁止市民放風箏的報道,勾起了他對兒時生活的回憶,從而成為他文學創作的題材。2001年,胡賽尼將自己寫的故事補充為一部完整的小說,取名為《追風箏的人》。故事講述了兩個阿富汗男孩之間的友誼、背叛與救贖。小說中的這個家庭,是阿富汗社會的一個縮影。透過小說,讀者可以看到阿富汗的民族倫理觀、社會階級倫理觀以及家庭倫理觀。兩位同在一個屋檐下的主人公來自兩個不同的民族,他們之間的等級劃分和沖突無疑象征著阿富汗社會的兩個民族之間深深的淵源。主人公阿米爾來自阿富汗的主體民族———普什圖族,哈桑則是哈扎拉族。深深的民族階級倫理觀已然印在尚是孩童的阿米爾心中,哈桑的出身也為他后來無可奈何的悲劇命運做了鋪墊。小說從幼年時期的兩人開始描述,看似講述了兩個少年的成長過程、經歷與遭遇,實則反映的是整個阿富汗社會的風貌、民族之間的愛恨糾葛。主人公阿米爾自身的成長也折射出兩個民族在復雜的歷史社會根源下,努力掙扎前行的腳步。小說中,父親的摯友———拉辛汗召喚他踏上“再次成為好人的路”①,正是這種努力的象征。小說情節構造巧妙、人物性格飽滿,加之用英語書寫了溫情脈脈的阿富汗,所有的這些因素使得小說在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關注的同時,也在中國學術界掀起了研究的熱潮。張金艷②從敘事學的角度解讀了小說并認為,《追風箏的人》所呈現出的敘事效果符合弗蘭克提出的三個側面———語言、結構和讀者感知,完美地突出了小說“罪惡與救贖”的主題。鄭素華③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結構理論解讀了主人公阿米爾從背叛走上救贖的心理歷程。黃瑩①研究了這部小說中的眾多意向,如風箏意向、石榴樹意向、彈弓意向以及兔唇意向,她認為,這些意向具有文化隱喻性以及敘事功能。郭巧懿②從認知詩學的角度分析了小說的主題,認為這是一部觸動人性的成長小說,它生動地再現了人性的殘酷與溫暖。由此可見,小說從多方位、多角度引起讀者、學者們的共鳴。仔細閱讀《追風箏的人》,不難發現,這部作品飽含倫理蘊意,它不僅僅是作者娓娓道來的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而且具有深刻的教誨意義。因此,本文旨在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視角出發,通過解讀阿米爾在三個時期不同的倫理選擇,論證小說勸善懲惡的教誨功能。文學倫理學批評“是一種從倫理視角認識文學的倫理本質和教誨功能,并在此基礎上閱讀、分析和闡釋文學的批評方法。”③小說中,阿米爾與哈桑的感情是貫穿全書的情感主線,也是全書的倫理主線。阿米爾經歷的兩次重大事件構成了小說的兩個倫理節。這兩個倫理節將阿米爾的人生分為了三個時期:道德搖曳期、道德折磨期以及自我救贖期。作者認為,主人公阿米爾在每個時期做出的倫理選擇并非偶然,而是在具體的倫理環境下做出的符合其倫理身份的選擇。主人公所做出的每一次倫理選擇,都為其成長做出了最好的鋪墊。正是這些倫理選擇,推動著他在“惡”與“善”之間的轉變,最終完成了其道德升華。
一、道德搖曳期
文學與倫理之間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倫理因素在文學作品的產生、表達,以及對人類行為的導向等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④倫理因素不但廣泛存在于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同時也在人與人的交往之間起著最重要的作用。⑤西方倫理批評的興起、衰退、再興起的過程也都見證了文學與倫理之間的不解之緣。我國學者聶珍釗教授正是在這樣的理論沃土上創立了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體系的。該理論體系吸納了西方倫理學批評的精華,同時也傳承了我國的道德批判傳統。⑥它有自己的話語批評體系,屬于方法論范疇。它強調“回到歷史的倫理現場,站在當時的倫理立場上解讀和闡釋文學作品。”⑦在《追風箏的人》中,主人公阿米爾對哈桑一直充滿著各種情感糾結,這些復雜的情緒發于道德,卻不止于道德,這正是倫理情節。如上文所述,阿米爾的人生有兩個重大事件,即兩個倫理節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道德搖曳期:主要指阿米爾的幼年、少年時期,直至他目睹哈桑被阿塞夫強奸之前。這個時期,他與哈桑一起長大。一方面,與其情同手足;另一方面,由于他年幼喪母,一心想獨占父愛,因而對哈桑充滿了排斥之情。要解析阿米爾復雜的內心,筆者認為,應該從他所處的倫理環境入手。倫理環境是人物倫理選擇的決定因素之一。小說中,宗教因素和家庭倫理觀都構成了阿米爾成長的倫理環境。倫理環境則幫助讀者認識到文學人物的復雜性以及其內心的多面性。而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多元性和復雜性,“為復雜的文學現象的解讀提供新的方法和多重聲音。”⑧通讀小說,不難發現,阿米爾內心的糾結與煎熬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成長的倫理環境。Shamel認為,在卡勒德的小說中,民族關系和宗教信仰問題是造成當前阿富汗社會不公平現象以及社會心理失衡問題的主要根源①。普什圖族是阿富汗的主體民族,處于統治地位,屬于伊斯蘭教的遜尼派。哈扎拉族是蒙古人的后裔,人數較少,屬于伊斯蘭教的什葉派。由于歷史與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哈扎拉民族在阿富汗成為一個“異質而孱弱的民族”②,遭到普什圖人的歧視和迫害。小說中,出身于普什圖族的阿米爾雖與哈扎拉族的哈桑一起長大,但是其內心深處,也隱藏著一份普什圖族的驕傲以及對哈扎拉族的歧視。另外,阿米爾出于對他們父子之間的倫理親情的渴望與維護,他將哈桑視作與他爭奪父愛的對手。這種相依相斥的搖曳之情是在家庭倫理和民族倫理關系的雙重作用下的結果。阿富汗地處交通要塞,注定了這里一直是戰火紛飛的必爭之地。普什圖族人是在戰火中歷練的民族,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建立了近代的阿富汗國家。由于長期戰爭的原因,普什圖族人崇尚武力、以武為榮,并且仰仗部落、家族,造就了他們極為強烈的家庭觀念。
阿米爾的父親是一個典型的普什圖族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曾經“赤手空拳和一只黑熊搏斗”,是那種“讓魔鬼跪地求饒”的勇士。然而,阿米爾卻沒有繼承父親的勇武,他不喜歡舞槍弄劍,不喜歡足球比賽,甚至在別的孩子搶他的玩具時,他都無力反抗。相比于武力,他更加醉心于文字之美。父子之間的強烈反差使得其父親無比懊惱。他黯然神傷,并且對阿米爾在文字方面的天賦不以為然,有的時候甚至還表現冷淡。在一次跟拉辛汗的談話中,父親對阿米爾懦弱的性格表示了強烈的擔心和失望。這種日漸疏離的父子關系深深地刺痛著阿米爾,他開始嗅出了自己性格中的卑劣。當拉辛汗對父親說阿米爾至少性格中并不存在常人眼里的某些缺陷時,他認為,“拉辛汗錯了”。盡管父親對他很失望,但在阿米爾的生活里,父親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對父親的崇拜和依賴,不僅僅因為父子的倫理身份,也在無形中受到了傳統的普什圖族的道德規范標準的影響。父親是高高在上的英雄,又是抱他在懷里的慈父。他想獨占父親所有的愛,卻發現哈桑在默默地分走父親的關愛,成為他和父親之間似乎永遠跨不過、繞不開的障礙。在這種倫理環境中,阿米爾內心深處所重視的倫理身份并未得到認同,此時,他做出的倫理選擇是對哈桑的排斥。盡管與哈桑朝夕相處、感情篤深,但他內心深處并沒有把哈桑當作朋友。他開始費盡心思地排擠哈桑,不惜撒謊、隱瞞等手段,這表面看似是小孩子們爭寵的小把戲,實則包含了阿米爾那份渴望得到倫理認同的執念。他嫉妒父親請醫生為哈桑治療兔唇,甚至“詛咒”自己能身患某種殘疾以博得父親的憐憫。這份倫理之內的父愛正在慢慢腐蝕著他的心靈,扭曲了他的倫理道德觀,為日后兩位主人公各自的悲劇命運埋下了禍根。此外,在小說中,宗教信仰不同所導致的民族歧視也時常可見。例如,當阿米爾將有關哈扎拉人的歷史那一章節指給老師看時,老師對之嗤之以鼻,“提到什葉派這個詞的時候,他皺了皺鼻子,仿佛是某種疾病”。街道上也經常有較大一些的孩子用語言來奚落哈桑,稱他為“塌鼻子的巴巴魯”。可見,社會的主流思潮也處處滲透著主體民族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因此,在阿米爾的成長過程中,父子之間的微妙關系激發了阿米爾對自己倫理身份認同的渴望。而來自學校、社會的民族階級倫理觀則幫助他完成了心里鋪墊。“我是普什圖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遜尼派,他是什葉派,這些沒有什么能改變得了。”根深蒂固的宗教倫理觀念左右著青少年時期的阿米爾對哈桑的感情。這種在道德情感上的搖曳之情以及自己性格中的卑劣進一步將阿米爾推向了“道德墮落”的深淵。在此時期,哈桑的善良和忠誠也無法喚醒執迷的阿米爾。小說撼動人心之處在于,人物的成長和變化扎根于其所處的倫理環境,人物的命運則沿著小說的倫理主線一步一步向前推進,這樣,小說情節的展開自然、真實、細膩。
二、道德折磨期
在經歷了道德搖擺不定之后,阿米爾進入了飽受道德折磨的人生階段。這一時期是指強奸悲劇發生后直至他決定回國面對之前罪過的二十多年的這段時間。在此期間,阿米爾的內心飽受道德的折磨。青少年時期的情感基礎為阿米爾后來的背叛埋下了伏筆。阿米爾十二歲那年,發生在小巷中的那場強奸事件將阿米爾和哈桑的人生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形成了小說的第一個倫理節。哈桑為了替阿米爾追回最后掉落的那只風箏,在小巷里被惡霸少年阿塞夫強奸,隨后趕到的阿米爾目睹了這一切。此時,阿米爾的面前放著兩條道路、兩個道德選項:勇敢地為哈桑挺身而出或者懦弱地看著哈桑遭人凌辱。聶珍釗認為,倫理選擇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倫理選擇指的是通過倫理選擇達到個人的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指對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道德選項,選擇不同則結果不同。”①阿米爾在此情此景中所面臨的選擇,就猶如命運在他面前為他設定好的岔路一般。如果選擇了前者,他和哈桑的未來也許會是另一番景象,但阿米爾卻選擇了后者,將自己和哈桑都推入了命運的深淵。然而,阿米爾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非常復雜,可以說這是阿米爾身上人性因子和獸性因子博弈的過程。“我眨眨眼,看見自己依舊咬著拳頭,咬得很緊,從指節間滲出血來。我意識到還有別的東西。我在流淚”。阿米爾的掙扎躍然紙上,讀者可以看到一個天生善良但性格卻懦弱的男孩。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從小到大的玩伴遭此慘禍,卻不敢上前阻止,因而在痛苦中掙扎。在這樣的倫理選項面前,阿米爾使自己陷入了倫理兩難的困境,他無法說服自己上前阻止,但內心又充滿了深深的自責,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不恥。從那一刻開始,他心靈上的煎熬和折磨從未停止過。讀者在這里看到的阿米爾,雖然不是罪惡的“主犯”,但無疑也是哈桑悲劇命運的另一個推動者。然而,在慘劇之后,阿米爾還有彌補的機會。如果他選擇將這件事情告訴父親,并勇敢地承認自己的不作為,父親或許可以為哈桑討回公道,而他也許不會因此折磨自己的后半生。可是,阿米爾并沒有選擇在這個時期做出補救,而是一直陷在自責與膽怯中無法自拔。他疏遠哈桑,盡量不與他交流。反倒是哈桑,這個為他受了凌辱卻還忠心耿耿的仆人、朋友還是一如既往地對待他。在他意識到阿米爾疏遠自己的時候,甚至還祈求阿米爾原諒他。最后,阿米爾在痛苦的道德折磨中,再次做出了自認為能解決其內心苦惱的選擇。他設計逼走了哈桑父子,希望以此來忘掉這件事。如果用單純的道德批判的標準去衡量,阿米爾可謂道德敗壞:他見死不救,設計害人,背叛朋友等等。可是,當我們再次回到阿米爾所處的倫理環境中,不難發現,阿米爾依舊是那個年幼喪母、性格內向、極端渴望父愛的孩子。
從小在父親的光環下無憂無慮地成長,甚至連搶玩具都不敢搶的一個孩子,在面對那種慘劇的情況下,他的沉默不語也不難理解。并且,哈桑為他追回的那只風箏從某種程度上確實改善了他們父子之間的關系,“爸爸緊緊抱著我,不斷撫摸我的后背。在他懷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為。那感覺真好”。童年時期的倫理觀念“恰到好處”地跳了出來,指引著阿米爾的倫理道德觀。阿米爾依舊是那個無助的孩子,一個用盡最后一絲道德掙扎企圖奪回父愛的孩子。“這個世界沒有什么是免費的。為了贏回爸爸,也許哈桑只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我必須宰割的羔羊。這是個公平的代價嗎?我還來不及抑制,答案就從意識中冒出來:他只是個哈扎拉人,不是嗎?”如果僅從道德立場出發,這時讀者看到的阿米爾似乎喪失了理智,變得不擇手段,嫉妒像魔鬼一樣吞噬了他。但當我們回到他所處的倫理環境中,這樣的判斷未免太過簡單。樊星、雷登輝②認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的一個鮮明的特征是其源于道德批評,同時,又超越了簡單的道德批評,將文學中諸多倫理因素綜合考慮,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道德批評的主觀性和二元對立性。同時,“文學批評必須超越單憑個人好惡的最主觀的判斷。”③這樣有助于讀者掙脫非黑即白的道德框架和束縛,使得人物更加真實飽滿。讀者看到的不再是單純的“好人”與“壞人”之分,而是一個個在獨特倫理環境中不斷做出倫理選擇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因此,阿米爾在此做出的倫理選擇并不能簡單地理解是對朋友的背叛和友誼的背叛,而是在特定倫理環境下做出的一個導致后來災難發生的倫理選擇。文學倫理學的觀點認為,在人的身上共存著人性因子與獸性因子。人性因子即倫理意識,能夠促使人分辨善惡的意識;而獸性因子則是“人在進化過程中的動物本能的殘留”①。它不受理性的控制,展現出人性中最原始的獸性。此時,阿米爾對哈桑的背叛,是在人性因子和獸性因子博弈后,獸性因子占了上風的結果。一個父親在孩子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一份隱藏在內心深處不可撼動的民族、宗教的偏見都讓阿米爾的獸性因子在此占了上風。也正是這種不平等的觀念最終使他下定決心———背叛了哈桑。“一旦倫理的天平開始傾斜,精神世界便失去了支點。”②此時的阿米爾,喪失了理智、喪失了倫理判斷,再一次做出了一個讓他后半生都無法釋懷的錯誤選擇。由此可見,當我們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角度去分析,阿米爾只是一個有著一顆善良柔弱的心,在特定的倫理環境中,做出了錯誤的倫理選擇的孩子。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然而,同樣是對“惡”的再次選擇,這將阿米爾推向了“罰”的深淵。
三、自我救贖期
第三個時期是阿米爾的自我救贖期。在這個時期,他得知了哈桑的真實身份,并且決心彌補父親和自己當年的錯誤。在阿米爾設計逼走了哈桑之后不久,祖國阿富汗陷入了戰火,他和爸爸被迫離開祖國,逃往美國。阿米爾的生活環境看似由阿富汗轉變到了美國,然而,他和父親在美國的生活依舊沒有離開自己的同胞。剛到美國不久,爸爸找到了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個阿富汗人開的加油站里當助理。在阿米爾高中畢業的那天,父親帶他去一家阿富汗餐廳慶祝。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們父子倆每逢周末都要去圣何塞阿富汗人的跳蚤市場。他后來所娶的妻子也是自己的同胞。這一切為他們搭建了阿富汗文化的倫理環境。阿米爾本想帶著自己的秘密,在這個遠離故國的新國度,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在他眼里,“美國是河流,奔騰前進。往事無人提起。我可以蹚進這條大川,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帶往沒有鬼魂、沒有往事、沒有罪惡的遠方”。可見,罪惡感與他如影隨形,從未遠離,這使他一直背負著良心債。一方面,阿米爾性格中的人性因子逐漸占了上風。另一方面,他依舊身處故國同胞之中,倫理身份并未發生太大的轉變。他依舊是那個非常重視家庭倫理的阿富汗少年,只要他對父親的依賴感存在一天,他對哈桑的負罪感就永遠不會消失。阿米爾最終決定走上“再次成為好人的路”是在他接到父親摯友拉辛汗的電話之后的事情。阿米爾從美國重回阿富汗,故土情懷依舊牽動著他。回到故土,倫理環境更加真切地被重現,為他最終做出正確倫理選擇做了倫理鋪墊。風燭殘年、疾病纏身的拉辛汗其實早已知道阿米爾心中的秘密,也了解他善良的性格。最重要的是,他心里還藏著一個阿米爾家族的重大秘密,關于哈桑的身世,關于哈桑與阿米爾的兄弟血緣。哈桑是阿米爾同父異母的兄弟,是阿米爾的父親與他家仆人的老婆的孩子。但是,哈桑已遭塔利班的毒手,哈桑的兒子索拉博也已被當年強奸哈桑并且此時已加入塔利班的阿塞夫所控制。拉辛汗之所以抖出這個深藏多年的秘密,其用意是希望阿米爾去解救哈桑唯一的骨血。同時,他也希望阿米爾借此機會來彌補他與他父親當年所犯下的罪惡。上文提到,普什圖族人民非常重視家庭關系,認為血緣最重要。在阿米爾夫婦想領養孩子時,他的岳父立刻表達了疑慮:“我的孩子,關于收養……這件事,我不知道對我們阿富汗人來說是否合適”。家庭血脈觀念在普什圖族人心中根深蒂固、無法撼動。而當阿米爾得知這一消息時,震撼他內心的不僅僅是道德觀念,也不僅僅是一直以來父親高大形象的轟然倒塌,更深層的原因,是不可接受父親違背了家庭倫理這個現實。此處為小說的第二個重要的倫理節。“在我葬了他十五年之后,我得知爸爸曾經是一個賊!還是最壞的那種,因為他偷走的東西非常神圣:于我而言,是得知我有兄弟的權利;對哈桑來說,是他的身份。”在這種根植于普什圖族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庭倫理觀念的驅動下,阿米爾踏上了解救哈桑之子、他的親侄子———索拉博的路。自此,阿米爾解開了他的心結,走出了困擾他多年的倫理困惑,從而做出了正確的倫理選擇。在他的倫理意識里,向善的念頭幫他撥開了心里的迷霧。他的倫理成長和倫理選擇也映射出阿富汗人民內心對和諧的民族倫理觀的認同及渴望。此時,阿米爾做出的倫理選擇不再具有兩面性,對他而言,這是不二的選擇。雖然他內心依舊有惶恐、有膽怯,但是他還是毅然決然地堅持了自己的選擇。雖然解救索拉博之路并非一帆風順,但最終的結局令人欣慰。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阿米爾的“罪惡與懲罰”“行善與救贖”得到了最好的闡釋。他為自己犯下的罪惡深感不安,他把和妻子的不孕不育以及后來險些命喪阿塞夫的鐵拳之下都看作是對自己罪行的懲罰。而他“再次成為好人”之旅雖布滿荊棘,但在經歷了身心雙方面的洗禮磨煉之后,最終讓他達成了道德上的成熟和完善。在飽受折磨二十多年之后,他對“善行”的選擇才是真正能夠洗去他罪惡的做法。回家之后,他對索拉博的身世沒有諱莫如深,更沒有試圖掩蓋父親曾經犯下的錯誤,而是大方地承認了他與索拉博的血緣紐帶關系,并且要求家人也不要替他們的錯誤有任何的遮掩。此時,讀者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阿米爾,他不再是那個膽小懦弱的富家少爺,而是父親心中典型的勇士。小說的結尾處,作者用索拉博嘴角的一絲微微翹起的微笑象征著阿米爾對自己的救贖。這也揭示了作者通過阿米爾的惡行來警戒世人、又通過他的向善來勸導世人的意圖。
四、結語
卡勒德·胡賽尼通過主人公阿米爾在人生三個時期中所做出的倫理選擇給我們展示了“惡”與“善”并非二元對立這個道理。作品中,這三個時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過阿米爾的倫理選擇作為推動力朝前發展的。從阿米爾的掙扎與成長經歷可以看出,善與惡,不再是簡單的道德標簽,“善人”可以為惡,而“惡人”亦可向善。從文學倫理學的視角出發,不難發現,卡勒德·胡賽尼借助阿米爾的倫理選擇為讀者揭示了善與惡之間的倫理辯證關系,完美地體現了文學文本勸善懲惡的教誨意義。
作者:李一暉 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
- 上一篇:小說中的茶文化研究范文
- 下一篇:鄉土小說的審美取向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