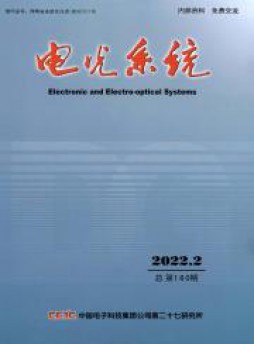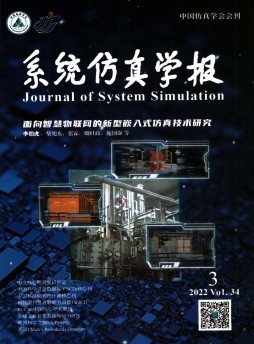盧曼系統下大眾傳播媒體如何影響社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盧曼系統下大眾傳播媒體如何影響社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問題的提出
如果將大眾傳播媒體簡單地定義為原則上所有人都可以進入的信息傳播場域,那么自從有了這種場域——早期為印刷品,后來增加了廣播、電視等電子媒體,今天則有了如電腦、手機等為載體的互聯網新媒體——人們關于社會、歷史和自然世界的信息和知識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這種媒體。一方面,人們依賴大眾媒體傳播各種信息和知識,以便了解社會和世界;另一方面,人們持續懷疑大眾媒體傳播的態度及其傳播內容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對很多人來說,大眾媒體背后似乎有一些隱蔽的幕后操縱者在控制和利用它們以實現某種目的。盧曼創建的社會系統理論旨在啟蒙社會。運用這一理論,他分析過大眾媒體這一特別龐大和復雜、表面上看并不那么“系統”的系統。他試圖回答的根本問題是:大眾媒體是如何影響社會的?而這個問題又被分解為以下問題:大眾媒體的“本值”或“自身行為”是什么?在認識了這種“本值”以后,使媒體顯得神秘的某種“秘密”是否還存在?他的基本論點是:媒體是現代社會功能分化產生的一種效果或后果,其既可以被認識又可以在理論層面被反思;其背后并無操縱者或者秘密。像所有其他系統一樣,媒體按照自身邏輯運行,即在自身密碼“信息/非信息”和綱領(節目、欄目)的基礎上生產和傳播信息。
二、大眾媒體的定義及其建構的世界真實
盧曼認為,大眾媒體應被理解為“社會中利用復制技術手段傳播溝通的所有機構”。在此,盧曼的理解顯然與一般大眾媒體理論有別:他不是將大眾媒體理解為信息傳播的機構,而是將其理解為傳播“溝通”的機構。正如下文將介紹和分析的那樣,盧曼認為,大眾媒體在以獨特的方式生產出信息后將其傳播給大眾,旨在引起受眾在日常世界中的溝通以及與媒體的溝通,從而影響社會。盧曼區分了三種大眾媒體。第一種是印刷品,包括圖書、雜志、報紙等;第二種是運用照相和電子復制技術大批量生產的產品,這類產品的受眾是不確定的;第三種是基于無線電的溝通傳播,但這種溝通指的不是單個參與者之間的電話通話,而是面向大眾的溝通,如廣播、電視等。在此,盧曼提出的一個基本思想是,只有在作為溝通載體的某種產品(如電視劇)被機器生產時,大眾媒體這一特殊系統才得以分化出來。盧曼提出這一觀點,進而將大眾媒體當作一個類似于經濟、法律、政治等系統的功能系統來分析。他認為,對大眾媒體這一系統來說,傳播技術是一種媒介,它使大眾媒體系統得以分化出來,就像貨幣這一媒介引發了經濟系統的分化一樣。在盧曼的理論中,媒介是構成形式的底物,而系統中形式的生產是由溝通的操作來完成的。通過這些溝通,系統的分化和閉合成為可能。每一個系統的操作方式都受一些結構性框架條件的限制。首先,在大眾媒體中,傳播者與受眾之間不發生在場者之間的互動。他們之間的溝通憑借媒體的傳播技術得以進行。傳播者可以與單個受眾互動,但他不可能與所有受眾互動。媒體溝通中這種直接接觸的中斷有兩種作用:一是溝通的自由度得以保持在較高水平,溝通的可能性得以大幅度增加或出現剩余。這種剩余只能在系統內部通過自組織和自身的真實建構得以控制和加工。二是溝通的可能性又受兩種選擇機制的限制,即媒體的傳播意愿和受眾的接受興趣。兩種機制都無法由某個機構集中調控。大眾媒體中用于生產溝通的組織機構能夠對受眾認可和接受的內容做出評估。在此基礎上,它們將自己的節目標準化和區別化,即發展出一些針對不同群體的節目(如電視臺下午四點播放家庭主婦喜愛的烹飪節目)。當然,這些節目不可能滿足所有個體的喜好,但節目的多樣性可以使每個個體從中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或對自己重要的內容來接收。傳播技術雖然是大眾媒體的基礎,其工作方式使大眾溝通得以結構化,但在盧曼看來,這種溝通屬于傳播技術領域的工作——印刷過程、電子設備的操作等,并不屬于大眾媒體系統的操作。大眾媒體系統的構成性要素主要是作用于這些機器設備工作的溝通過程并貫穿其中。盧曼稱技術性的機器設備為“溝通的物質基礎”,只有通過這些設備傳播的信息所引起的溝通,也就是這些信息被接收,才屬于大眾媒體系統的溝通。要理解盧曼的這種區分,就需要簡單認識一下他對溝通概念的定義。他認為,溝通是由三種要素構成的完整過程,即信息、傳遞和理解(或誤解)。信息是區分的操作結果;傳遞行動是將這一信息告知他者的行動;理解或誤解是接受者對這一信息的接受過程,它可以是理解也可以是誤解。當這三種要素都出現時,就形成了溝通。從這一定義出發,盧曼進一步揭示了大眾媒體的特征。在傳遞環節,大眾媒體面臨的一個問題是難以確定正在參與溝通的人群即受眾圈,而只能假定這一人群。在一次溝通完成之后,在大眾媒體系統內部和外部參與相關溝通的圈子就更難確定了。這種能力限制對大眾媒體來說反而是一種優勢。正是基于這種不確定性,大眾媒體往往將其援引性的溝通范圍設計得很寬泛,并且在溝通失敗或遇到反對時不放棄溝通,而是嘗試尋找潛在的受眾,挖掘更多的溝通可能性。如前文所述,人們今天對世界的了解基本上來自大眾媒體。但是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真實并非現實的真實,而是康德所說的“先驗的幻想”。盧曼引入觀察概念解釋了這一現象。觀察指的是做出區分后,再標示出這一區分的行動。要理解大眾媒體的操作,我們則必須以觀察者的視角,即二階觀察的視角來觀察大眾媒體。對其觀察的結果是:在這一系統中出現的是“對真實的二重化”,其所呈現給受眾的真實不是原本的世界真實,而是其觀察的結果;如果說世界真實是由一階觀察的活動或演化構成的,那么,大眾媒體所反映的真實則是二階觀察的結果,是其建構出的真實或關于真實的溝通結果。這種真實既可以是關于外部世界的,也可以是關于大眾媒體系統自身的真實(如大眾媒體系統內部的權力斗爭)。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無論是在古典真理問題的討論中,還是在人們對真理或真實的日常理解中,人們都會問媒體報道的內容真實嗎?盧曼認為,對一些被報道的對象(系統)來說,這個問題是可以回答的,因為他們了解原初的真實情況;而對廣大受眾來說,這個問題是無法回答的,因為對他們來說,媒體報道的就是真實情況。基于這一實際狀況,盧曼認為,以上問題可以排除在對大眾媒體系統的研究之外。要認識和研究大眾媒體,重要的是認識它的運作方式,即它是如何生產或建構真實的?盧曼的基本觀點是,包括媒體在內的所有社會系統都通過自身的操作建構真實;對它們來說,原初的真實不是存在于“外部的世界”,而是存在于認知操作中。在此意義上,盧曼稱其所主張的認識論為“操作的建構主義”。其核心內涵是:對操作的系統來說,世界是作為真實而存在的,并且是作為環境而存在的;但這個環境是現象學意義上的視域,對系統來說是不可及的,系統只能通過自身的操作來建構真實、認識環境中的一部分真實或者通過對建構真實的觀察者的觀察來建構自身的真實。要建構自身的真實,每個系統都要滿足一些條件。大眾媒體要滿足的條件為區分自我指涉和他者指涉、生產自身的密碼等。盧曼認為,要認識大眾媒體,就要將關于大眾媒體的理論置于關于現代社會的一般理論中。在他看來,現代社會是一個功能分化的社會,它是由諸多發揮著自身功能的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教育系統、法律系統等構成的。這些系統的績效能力能夠不斷提升,是因為它們自身在細分,并且具有操作性閉合和自我生產的自治性等特征。
三、大眾媒體作為功能系統的自我指涉和他者指涉
在盧曼關于一般系統的描寫中,區分和差異是兩個互相關聯的關鍵概念。當一個區分被做出時,比如當樹上的一只鳥被與其周邊的他物區分開來時,就出現了差異,即被區分物(如鳥與周邊他物)之間的差異。這種區分被盧曼稱為“操作”。而當被區分出的某物(如鳥)之外的萬物被忽視而此物(如鳥)被標示出時,就出現了觀察。觀察是由認識的系統(人和社會的系統如政治系統、法律系統、經濟系統、大眾媒體系統等)做出的。被觀察物之外的萬物變成了環境。在此物的某一部分(如鳥的羽毛)與其他部分區分開時,該部分以外的其他構成部分則隱退到背景中去了,變成了環境,但這個環境是鳥的觀察這一系統內部的環境。系統是在第一次觀察后出現連續的觀察時產生的,可以被稱為操作(區分)和觀察的連續統。當操作和觀察只關涉系統內部的事物(如鳥的構成、習性等)時,它們是自我指涉的。當它們關涉系統外的事物(如人類的生產活動)時,其指涉是他者指涉。在系統的操作中,每一次操作都是對上一次區分的“再進入”。再進入是跨越邊界的操作,它通過區分走出了上一次區分所形成的系統與環境的邊界,同時劃出了一種新的系統與環境的邊界。在操作只關涉系統內部的事物,即自我指涉時,這種邊界是系統內部的系統/環境邊界;而當操作他者指涉時,則出現了系統與其外部環境的邊界。系統的操作是對世界的觀察操作,在進行這種操作時,它不能同時觀察自身。系統對世界的觀察被盧曼稱為一階觀察,而對作為觀察者的系統之觀察則被稱為二階觀察,如傳媒學對大眾媒體系統的觀察就是二階觀察。在一個區分做出后,下一個操作是什么,這是不確定的。由于“我”的觀察總是在忽略他物的前提下進行的,所以這一系統不可能是完全意義上“確認客觀真相”的系統。這一系統的穩定性建立在兩個基礎上,即被觀察之物和被忽略之物(只有忽略他物才能觀察某物),因而具有“雙基穩定”的特征。在觀察的系統出現后,系統即生成了自己的時間,并且通過自身操作的序列消耗這一時間。每一次區分的操作所產生的不確定性都被后續的操作所分解。而通過這些操作,系統實現很多目標、完成很多事情。在此,系統在利用時間進行操作并且期待每一次操作都會引起后續操作。對大眾媒體來說,這意味著它總是在假設自身的溝通會引起后續溝通、每一次傳播節目會引起下一次節目的出現。因此,對大眾媒體來說,重要的不是呈現目前的世界狀態,而是自身操作的可持續性,也就是吸引受眾的能力。與所有其他社會系統一樣,大眾媒體系統也是一個閉合的系統。這種閉合性是由系統自身的操作所決定的,因為這些操作只發生在系統內部,是按照系統自身的邏輯進行的。同時,系統又是開放的,因為系統的操作往往需要從其外部環境中采集材料。對大眾媒體系統來說,用于溝通的主題往往來自其寓于社會內部的外部環境(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等領域)。在此意義上,主題代表著他者指涉。對大眾媒體系統來說,主題具有以下意義和功能。第一,主題將媒體采用的作品(稿件、影音作品等)捆束成多種分類單位,由此組織著媒體系統的記憶。在此基礎上,在正在進行的溝通中,辨別應保留和繼續報道哪個主題、應放棄哪個主題。在主題層面,大眾媒體系統自身在溝通中持續發生著自我指涉和他者指涉之間的表決。第二,主題是大眾媒體與其環境即其他社會領域進行結構性耦合的媒介。在選擇主題時,大眾媒體具有比其他系統(如政治系統、法律系統、經濟系統等)大得多的彈性和靈活性;它可以通過主題選擇而進入所有社會領域,而其他社會系統卻難以將一些主題提供給媒體并使其得到客觀的報道。第三,作為溝通媒介,主題既可以拓展社會的溝通,又可以加速這種溝通。盧曼認為,已經被媒體報道的主題具有與貨幣這一經濟系統媒介相同的功能。在一種貨幣作為交換媒介被社會接受后,不同的個體可以用它實現自己的各種交換目的(如購房、買菜、換外匯等)。同樣,在一個主題被報道后,人們可以將其視為一種普遍熟知的資訊用于實現不同的溝通目的。第四,媒體總是在區分用于溝通的主題與媒體自身的溝通功能。在功能優先的原則下,主題被選擇甚至被虛構。媒體的功能首先是傳播溝通、吸引受眾。媒體的一些固定節目,如天氣預報、晚間新聞等,在被證明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后,必須有持續的新聞填充進來。此時,為了滿足這一功能,媒體可能放棄一些新聞,也可能制造一些虛假新聞。
四、大眾媒體系統的密碼、綱領和信息生產
像所有其他功能系統一樣,大眾媒體要持續辨識自身操作的銜接性、生產和再生產系統/環境差異,還必須引入一種機制,即密碼。這一密碼是對信息和非信息的區分。對該系統來說,信息是正值,是其用于標示自身操作可能性的設計值。同時,要具有將某事物確定為“信息”的自由,它又必須具有將其他事物視為無信息價值的自由。無信息價值的事物可以被稱為反涉值,它對大眾媒體系統的運行也是不可或缺的;沒有這種反值,系統將陷入被信息淹沒的狀態,無法將自身與環境區分開來,從而無法減少復雜性、提高自身的績效即加工信息的能力。為了避免反值的復歸,媒體做了另一種區分,即對編碼和編程(制定操作綱領的過程)的區分。編程的結果是作為規則的綱領得出的。這種綱領(如新聞、娛樂節目)可以分解非信息的信息性悖論,有助于系統決定哪些事物可以作為信息來加工。因此,盧曼將密碼和綱領稱為雙重選擇機制。通過密碼,大量的信息流入系統;而通過綱領,這些信息被分類和分流處理。
五、討論
作為普通社會成員,我們已經能感覺到媒體無處不在的影響以及媒體傳播內容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但卻難以把握媒體的特質。盧曼運用其社會系統理論對媒體的分析無疑為我們認識媒體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重要的資訊。作為可以與經濟系統、政治系統、法律系統等相提并論的一個現代社會的主要功能系統,媒體按照自身的操作邏輯即信息/非信息之密碼和綱領(欄目分類)運行,生產和傳播信息。因此,媒體的傳播內容既來自外部世界又不同于外部世界。媒體生產的信息在持續刺激社會,使社會保持清醒,也在推動社會反省和改變自身。但是,這種刺激可能是脫離環境現實的,可能引起對其他系統的過度干擾和隨之而來的社會震蕩。而在后發展國家,由于功能系統(比如法律系統)本身尚處于演化和完善的過程中,各系統的建設可能并不同步,媒體的影響可能偏強,即超出其他系統的信息加工能力;也可能偏弱,即對它們的刺激不夠。在第一種情況下,媒體可能會過度干擾其他系統的運行,引起這些系統內部乃至全社會的混亂,即引起結構摩擦問題。在第二種情況下,媒體可能發揮不了應有的推動社會自我反省的作用而使社會傾向于故步自封、陷入僵化。如何避免這兩種極端情況的出現,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展國家協調各系統間的關系時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作者:秦明瑞 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