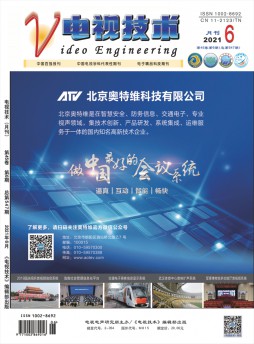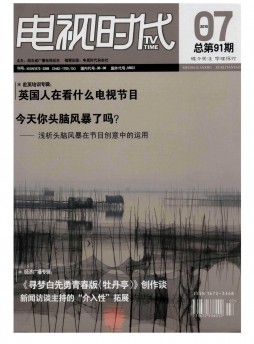張冰的電視電影劇作手法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張冰的電視電影劇作手法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自1992年新疆大學畢業分配到天山電影制片廠擔任場記、副導演,張冰并未感到自己的編劇特長,直至和著名的電影導演張鑫炎一起合作,張鑫炎認識到他的編劇天分,鼓勵他做最適合他的編劇工作;而后著名電影編劇王興東在幾天偶然的接觸中敏銳地注意到張冰講故事的才華,再一次鄭重其事地請張冰考慮投入到編劇的工作中;正逢此時,與張冰合作多年的導演金麗妮找到他,希望合作創作一部電影,鼓勵和機遇就這樣不期而至,張冰因而有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編劇的電影《會唱歌的土豆》,而這部電影成為預言張冰會不負編劇這一崗位的第一個佐證,它獲得了中國電影華表獎最佳兒童片獎。從那以后,張冰徹底投入到編劇的創作工作當中,以每年至少一部電影的速度進行創作,且在獎項上時有斬獲。其中,2005年,電影頻道出品了張冰創作的電視電影《男人上路》,獲得2006年度上海國際電視節最佳影片、最佳編劇入圍提名獎,2007年中國電影華表獎最佳數字電影獎、最佳編劇新人獎提名和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數字電影提名,以及2007年“百合獎”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男演員三個獎項。2007年,張冰創作了電視電影《暮鼓晨鐘》,獲得2008年“百合獎”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男演員三項大獎,其僅有的兩部電視電影作品在高層的評獎中都獲得了最高榮譽,可見張冰選擇做編劇既成就了個人的價值,也讓觀眾看到了更多更好看的電影,這對于張冰和觀眾而言都是幸運的事情。
張冰的電影和電視電影作品,并不以愛情題材或者歷史題材見長,而是專注于現實主義題材的創作,無論是創作《大河》、《買買提的2008》這樣的大銀幕電影作品,還是創作《男人上路》、《暮鼓晨鐘》這樣的電視電影作品,他都能夠進行實地考察和體驗生活,因此他的作品都更富有靈動鮮活的生活質感,在看待是拍攝膠片電影還是電視電影的問題上,張冰也自有個人的見解:畢竟膠片電影可以涵蓋更大的容量,同樣的90分鐘,膠片電影比電視電影會顯得更為厚重和宏大,但是又因為電視電影在結構和人物的設置上的要求相對來說要簡單一些,故事環境的單純反而能夠深入地挖掘出當今所謂大銀幕大制作比較容易忽視的元素,比如人性當中微妙的關系、矛盾沖突下隱藏的真情等。再看《男人上路》和《暮鼓晨鐘》,前者講述了發生在戈壁荒漠上父子之間的情感故事,后者則將視角轉到沿海城市膠片廠歷經的重大變革,在處理這兩部不同題材的作品上,張冰并沒有獨辟蹊徑別出心裁,反而是遵循著類型片的創作模式。前者是公路片,后者是中國特有的改革題材,但是在故事進行當中又顯現出與同類型影片的差別,使得這兩部低成本的電視電影作品,在當今淪為票房工具的大銀幕電影之外,讓觀眾們看到了真正屬于電影創作者的誠意之作。
類型片模式的運用
在類型片當中,尤以好萊塢戲劇式結構的影片為顯著,都普遍遵循著“開端→發展→高潮→結尾”這一布局。同時,如果我們將整部影片視為一個大系統,將大系統當中的開端、發展、結尾視為子系統,又會發現在每一個子系統當中,也包含開端、發展、高潮、結尾,在子系統當中的這些因素又可以繼續分割下去,因而形成了不同規模的敘事單元。在這些敘事單元當中,小的沖突推進子系統的故事發展,進而又形成大的沖突推動大系統故事的發展,沖突成為故事向前發展的動力,伴隨沖突推進的是人物關系的平衡狀態被不斷打破。沖突的層層推進、各種平衡的不斷打破成為影片的核心動力,而且在整個敘事體系中,由于功能上對各系統當中沖突的強度和力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形成了影片的節奏和韻律。由于受到制作條件和播出方式的限制,那些表現宏大場面和展示視聽奇觀的題材并不是電視電影表現的首選,反而那些敘事手法精巧、結構緊湊的影片更容易引起觀眾的興趣,而好萊塢戲劇電影的劇作結構恰好能夠滿足觀眾的這一需要,讓觀眾覺得“有戲可看”,《暮鼓晨鐘》即是一部這樣的影片。影片是當下仍是熱點的改革題材,涉及到國有企業破產重組這一話題,影片將視角先放在一個50年代建廠、生產工業膠片的老國企特種膠片廠上。這個膠片廠不僅有過輝煌的過去——為東方紅衛星三號生產過感光膠片,還擁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產業工人隊伍和兩項國家級核心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但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卻欠下了7000萬元的債務而走向了破產的邊緣。市領導請來“破產專家”章明來運作膠片廠的破產,章明到任后,歷經調查情況、聽取民意、查賬查債,發現了破產背后另有復雜的隱情——這當中有企業現任領導的以權謀私、政府內部官員的腐敗、不法商人對企業的覬覦。紛繁復雜的重重黑幕當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章明和膠片廠的命運始終牽動著觀眾的心。這當中編劇的技巧功不可沒。在這里試分析一下《暮鼓晨鐘》的劇作結構:
開端:章明應臨濱市婁副市長和國有資產管理局趙局長之請,到特種膠片廠任廠長,實際是來進行破產運作的。發展:章明進行調查發現重重黑幕,準備停止破產,恢復膠片廠的生產自救從而保護國有資產,但是受到各種阻撓,舉步維艱,最后落入吳亮和高宏達的圈套。
高潮:章明決定行使企業法人權力,將膠片廠抵押給國有銀行,并召開全廠職工大會發放拖欠工人的工資獎金和所有福利待遇,工人舉手表決要進行生產自救、保護國有資產。結尾:章明轉身離開膠片廠,劉大業、趙炳權、吳亮、高宏達等人得到應有的處理,婁副市長引咎辭職。這是影片情節模式的大系統,而在簡單地交代了故事背景以及開端之后,影片的發展部分又可以分為若干子系統,見表一。從表一不難看出,大系統的情節推動正是子系統的沖突構成的,子系統當中的沖突不斷被帶入到大系統當中,使得情境激化、懸念迭起。這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雖然他的出場看似漫不經心,在整部影片的大半部分都不見承擔大的劇情動作,但正是這個人物出乎意料地使整個劇情風云突變。這個人就是國有房地產公司的老總吳亮,他一直以章明的朋友自居,兩個人的見面也無非就是打打球喝喝茶,安慰勸解章明。當章明被資金搞得一籌莫展的時候,他主動伸出援手,以國有房地產企業和膠片廠聯姻的方式幫助膠片廠解決生產資金問題。然而出乎章明和觀眾意料的是,正是這個吳亮早已和高宏達達成了協議,作為國企的華龍集團即將被高宏達收購,膠片廠最終還是要落到高宏達手里。章明和膠片廠在倏忽而過的一絲曙光之后陷入了更大的危機,這也構置了影片最大的沖突和懸念——章明和膠片廠還有生產自救的路嗎?觀眾的心理在得到釋放之后反而被推入更大的期待當中——章明能否峰回路轉?章明決定以“不要臉”的辦法對付“不要臉的人”。他冒著犯巨大錯誤的風險,行使企業法人權力,將生產線抵押給了國有銀行,一方面保全了國有資產和新技術,另一方面用抵押來的貸款解決了拖欠工人兩年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待遇。而工人們也決定先用這筆錢恢復生產線,進行生產自救,守住國有資產——這才是全片最大的高潮。編劇張冰在進行布局時并不是將沖突均勻地散落下來,而是明暗交織、錯落有致,看似一條暗線卻潛伏著最大的危機,而將最后的懸念和高潮都留到了影片最后的1/6。這一沖突不僅是子系統的沖突,也是大系統的沖突,更加加大了懸念的落差以及解決之后所帶來的沖擊力,使得全片結局有了一個非常可觀的落點。屬于主旋律題材的改革開放故事的影片創作,很容易落入空泛和口號式的俗套,但章明卻將戲劇電影的經典敘事模式引入到主旋律影片當中,影片中沒有口號式的說教,也沒有臉譜式的人物,而始終致力于怎樣將故事講得跌宕起伏、引人入勝、激動人心,并透過這個故事將國企改革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充分剝離展示在觀眾面前,使得這部電視電影作品成為改革題材影片中最貼近現實的作品之一。
公路片的環境利用
如果說《暮鼓晨鐘》向我們展示了復雜的社會環境下波瀾壯闊的改革風云,《男人上路》則向我們講述了單純環境下發生的簡單故事,這種單純的環境正是公路片的特色——在公路旅行的單純環境中,完成那個生命體驗、思想變化、性格塑造。當中也有戲劇沖突,但更多的是完成心靈的交流。公路片在美國已經是很成熟的類型片。美國被稱為“裝在輪子上的國家”,可想而知,那些公路、公路上的汽車旅館、行駛在公路上形形色色的汽車和人會成為多少故事的載體和主角。
無論是《德克薩斯州的巴黎》,還是《末路狂花》,主人公無不懷揣著破碎的夢行駛在路上,但是盡管《男人上路》也以一段旅程作為敘事發展的背景,卻少了美國公路類型片的失落和憤懣,轉而講述了父子親情的回歸。講述父子親情的影片并不少見,但是將父子故事放置在公路片這一類型卻不多見。張冰認為,復雜的環境——比如城市——規則太多、視點太容易分散,對故事的束縛也更多,而在公路這種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人物塑造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故事的發展也更隨心所欲一些。從故事層面上說,《男人上路》講述了一個以“承諾”為主題,有關父子的故事。這對父子——莊大林與莊嚴在幾年分別之后,陌生得都幾乎令對方不認識了,父親發現兒子逃學、上網、虛榮、說謊……面對這個他幾乎不認識的兒子,父親莊大林決定帶他回油田,在那里讓他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盡管已經有了高速公路,但是莊大林還是帶著兒子走上了他每次看老婆孩子都走的同一條路,車里的錄音機放著那首和老婆同名的歌曲。旅途中,莊大林和兒子互相懲罰各自徒步了30公里,而途中搭載的曉月看出父子之間的癥結,一面對父親提出中肯的意見,一面又和兒子進行和風細雨式的談心。影片最后,當大林因為給生孩子大出血的曉月輸血而體力難支、汽車又拋錨在路上的時候,大林和兒子相互支持,又一次徒步上路,就是為了兌現承諾,將婚戒送給舉辦婚禮的徒弟。當看到徒弟的婚車,兒子拿著戒指使盡渾身力氣奔跑過去的時候,影片定格在一個成長起來、已經懂得承諾對于一個男人意味著什么的兒子身上。在一部作品當中,除了人物的語言和動作之外,時間和空間都是可以利用的因素,環境可以承載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動作,成為情感動作的隱喻因素,同時還能夠傳遞人物的內心情感。就故事發生的環境而言,《男人上路》散發出濃重的地方特色。莊嚴在物質環境優越的城市當中養成了各種各樣的劣習,而在廣袤粗礪的沙漠公路上,盡管沾上了一身塵埃,卻完成了心靈的凈化;莊大林在油田里是個敢做敢當的經理,在兒子面前卻是個不知所措的父親,除了收拾兒子別無他法,也是在這樣的公路上,他真正成為了一名父親。一開始劍拔弩張的父子二人,被困在沙漠公路上行駛的吉普車當中,觀眾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就被帶到父子關系的進展和解決上來。莊嚴獨自一人上路。一面是十幾歲的孩子獨自走在荒無人煙的路上,一面是在客棧擔心兒子而神不守舍的父親,影片將敘事集中在沙漠公路上,這條公路所具有的意義是多重的:兒子的叛逆、父親教育方式的極端,父子之間的矛盾。但這時,編劇巧妙地安排進一個重要的人物——曉月,這個還有一個月就要生孩子的老師,為了給丈夫一個驚喜,讓丈夫看到自己兒子的降生,獨自跑到油田來找丈夫。曉月的一言一行,無疑是父子關系最好的潤滑劑。通過曉月的舉動和談話,莊嚴意識到父親工作不容易、母親對自己的養育之恩,莊大林也認識到除了“收拾”,還更應該用“愛”來對待兒子。曉月和莊氏父子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對話,她告訴莊嚴孩子是怎樣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告訴大林應該怎樣對待孩子。這段對話發生在一小塊綠洲當中,曉月就像是一脈清泉滋潤了父子倆粗糙燥熱的心靈,讓父子關系現出平和溫暖的新綠。由此,我們可以領略到,編劇在設計故事場景的時候,是充分認識到環境在電影的隱喻式動作體系當中率先凸顯出來的作用的:城市——浮躁復雜,不能培養真正的男子漢——莊嚴沙漠油田——單純粗糙,具有男性氣質——莊大林,莊嚴綠洲——平和溫潤,雖然只是一小片,在沙漠當中卻最滋潤旅人——曉月這一組人物和環境的比對,使得該片盡管是公路片卻又青出于藍,不僅將人物、情節的推進和環境的變化有機地融為一體,還利用環境加強了人物的塑造。
人物的設置模式
《暮鼓晨鐘》和《男人上路》一個發生在東部沿海城市,一個發生在西部荒漠公路;一個講述國企改革,一個講述父子親情;一個是人物眾多的戲劇式電影,一個是故事簡單的公路片……看似題材跨度大到毫無可比性的兩部影片,但是因為都出自同一編劇——張冰之手,我們還是不難看出其中的共同之處,那就是人物的設置都采用了同一套路。前面說過,張冰是個擅長用老套式講新故事的人,這在他對人物的設置上同樣有所反映。這兩部影片的主人公,膠片廠廠長章明對于臨濱市和膠片廠來說,是個外來人;油田經理莊大林對于兒子莊嚴來說,是個外來人;女老師曉月對于莊氏父子來說,還是個外來人。這種外來人的模式不僅在寫改革家的題材當中常見,在講述父子關系的電影當中也屢見不鮮。俄羅斯影片《回歸》當中的父親就是個離家12年之久突然回來的外來人。外來人介入到原來的生活格局當中必然就會打破原有的格局和平衡,這其實是推進敘事發展的一個非常討巧的模式,問題是,怎樣將這種模式用出新意?幾乎所有寫改革家的作品都是“外來人”這一模式,大致就是一個企業瀕臨倒閉,來了一個人,這個人一般都是上面派過來的,因為這個人,企業又起死回生了。《暮鼓晨鐘》當中,章明作為一個外來人,卻并不是作為妙手回春的神醫被派過來,而是作為“破產專家”派過來的,這是一個顛覆。派過來之后先是被市領導認可而被工人難為,繼而又被工人認可,宣布不破產要力保膠片廠,這又是一個顛覆。當他說他之所以要這么保全膠片廠保全國有資產,就是因為以前他師傅跟他說的一句話“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工人是你最好的兄弟”,這是對以往改革題材的“外來人”模式最大的顛覆。以往的改革家,他們所有的舉動都是因為“外來人”這一特殊身份帶來的,他們或者手持尚方寶劍,或者自己是完人一個,而章明身上是帶有主旋律人物的共性的,比如他的正氣,但是這個人物在設置和塑造上更為立體和豐滿,這來自于編劇對這個人物深層次的精神世界和靈魂的挖掘,使得這個人物在主旋律影片或者改革開放題材影片當中成為最接近生活現實的人物。改革題材的正面人物很容易寫成一個言詞空洞的高大全式的人物,但是因為編劇賦予他豐富的內心世界,在表現內心世界的時候又充分調動臺詞的表現張力,將這一從老套路走出的“外來人”塑造得充滿新意。
而《男人上路》作為一部講述父子關系的公路片,同樣也走了“外來人”這一模式,但是思路卻是嶄新的——父子兩個人,兩個男人,到底是誰教育了誰?對于兒子莊嚴來說,久未謀面的父親是個外來人,對于父親莊大林,兒子莊嚴又何嘗不是?兩個人都走入了對方的生活,互相適應,也互相較勁,兩個人都要把原來屬于自己生活中或者性格上的一部分給拿掉,矛盾沖突由此而起。當父子倆鬧僵,又出現一個女老師做調和,矛盾沖突由此又得到解決。最后曉月臨盆,父親輸血救人,又要完成送戒指的承諾,父子兩人攜手解決了這后來的一連串矛盾。表面上看,作為“外來人”的父親教育兒子成長為信守承諾的真正的男子漢,其實父親又何嘗不是重新學習如何做一個合格的父親?以往講述父子親情的影片,尤其是這類大人教育小孩的影片,并不是真正平等的對話,而《男人上路》正是因為將父子二人同時放在了“外來人”的位置上,父子都是教育的人和被教育的人,在人格、社會關系的協調上都被放逐在一個平等的位置,這才實現了真正的平等對話。
章明和莊大林不僅是“外來人”,同時還是行進在崇高與平凡之間的平民英雄。早期電影銀幕上的英雄無不高大偉岸、充滿傳奇色彩,而當今的影壇英雄早已走下了神壇,電視電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保持了和電影同樣的步調。在這兩部影片的主人公塑造上,章明也會落入官商勾結的圈套,他最后采取保護膠片廠的手段也要冒著犯巨大錯誤的風險,但是他最后畢竟還是保全了膠片廠,成為膠片廠所有職工心目當中的英雄。而莊大林,盡管曾經以那樣極端的方式教育兒子,但是他也身體力行接受了兒子的懲罰,并且給曉月輸血,終于成為兒子心目當中的英雄。章明和莊大林依靠點滴平凡,構建了自己的英雄形象。“外來人”的設置,在文藝作品當中屢見不鮮,他們或者主動或者被動地改變著原有的格局,而后又形成新的格局,并在新格局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這兩部影片雖然引入了“外來人”這一模式,卻在敘事進行中不斷地進行顛覆,人物并沒有因為“外來人”這一模式而走向臉譜化,故事也未落入俗套,這不僅來自于編劇高屋建瓴的視角,也來自于張冰對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尊重。看張冰的兩部電視電影作品,可以領略到嫻熟的類型片編劇技巧的充分運用,他本人也表示喜歡具有戲劇張力的作品,喜歡比較機智的東西,因此在人物的塑造、臺詞的處理上或多或少都受到美國類型片的影響。但難能可貴的是,張冰并沒有完全照搬類型片的模式,也不一味地以好萊塢敘事模式為創作范本,而是在敘事構成和人物塑造上充分考慮到故事發生的環境和地域文化,以及題材的特殊性,從而使得《暮鼓晨鐘》和《男人上路》都成為同類影片當中的佼佼者,也成為電視電影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