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劍東編劇風格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黃劍東編劇風格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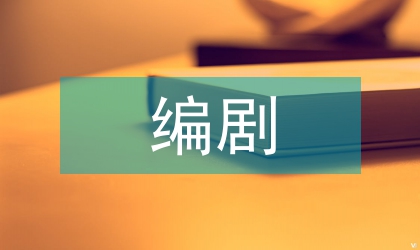
編劇黃劍東的第一部作品是2004年的電視電影《琴聲暖洋洋》,其后,他又創作了電視電影《北京童話》(2004)、《籃球寶貝》(2005)、《陸小鳳傳奇之幽靈山莊》(2006)、《烈火男兒之了不起的消防兵》(2008)、《菜園街醒獅會》(2010)。(1)寫過《百年孤獨》的拉美小說家馬爾克斯說過,任何作家的前五部作品都是自傳,這說明了藝術創作與藝術家的生活經驗和生命經歷的對應關系。黃劍東也有類似的表述,“劇作家和導演的第一個劇本是回到自己經歷的一個過程,是其生命的映照”。然而,他又說,“一個成熟的職業編劇要將自己的情感隱藏,于不動聲色的故事講述中傳達出人們可以理解的生命感悟”。藝術創作本身即是如此矛盾的體現,在收放之間,創作者的心路軌跡便可若隱若現地勾勒。不可否認,任何的藝術創作都是與現實對話的努力。本文試圖回到黃劍東藝術創作的起點——電視電影,通過對這些作品主題的選擇以及創作技巧的心得分析,去觀照藝術世界中那些常議常新的話題——文本與作者、創作與模式……
主題
(一)親情與家庭
東方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尤為重視親情與家庭、倫理與道德。中國電影也有很深厚的家庭倫理情節劇傳統。這從第一代導演鄭正秋到第二代導演蔡楚生到跨越第三代第四代的謝晉都是如此。他們或是向戲劇開掘,或是觀照社會,都縈繞著濃濃的親情和家庭觀念。這一傳統在馮小剛的《唐山大地震》中得到了極致的延續,該片取得六億多元的票房,賺足了觀眾無數的眼淚。足以可見,親情與家庭這一倫理主題并不會因時展而退卻它在人們心中的位置。相反,在人情淡漠、世態炎涼的社會風氣之下,其更能成為大眾內心的慰藉。在黃劍東的創作過程中,家庭和親情的觀念始終貫穿在其幾部作品當中。“每個人進入故事的角度都不一樣,我自己是從人到家。”個人成長的孤獨體驗以及日本的影視劇對黃劍東的創作主題影響至深。“日本的創作者非常喜歡寫人的孤獨,寫人對家庭、親情和愛的渴望,這是典型的島國心態,這也是我最喜歡宮崎駿電影的原因。《龍貓》寫的是姐妹倆在母愛缺失的環境下努力地生活,《再見螢火蟲》是戰爭背景下失去雙親的兄妹兩人的悲慘際遇,《千與千尋》則是失去父母之后的千尋歷經坎坷,最終救出父母,學會了成長。”縱觀黃劍東的幾部電視電影,除卻《烈火男兒之了不起的消防兵》中對家庭沒有直接的表現之外,其他幾部作品無論情節如何進展都隱含著親情與家庭的倫理主題。
《琴聲暖洋洋》講的是做律師的劉年工作不順,因債主上門而不得已關掉律師事務所時接到公安局的一個通知:同父異母的弟弟劉以風因涉嫌過失傷人而被關押。作為父親去世后弟弟唯一的監護人,劉年到公安局為劉以風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因為對父親感情不同的原因,盡管劉年做出了各種努力,劉以風非但對哥哥心懷記恨,而且還不肯配合對案情真實情況的了解。經過一系列的調查,劉以風并沒有犯罪。一場虛驚過后,劉年在父親的遺物中最終理解了父親,冰釋了兄弟兩人多年來的心中塊壘。《琴聲暖洋洋》以一樁傷害案的解決為線索,講述了兄弟之間的情意故事。如果說故事中的傷害案是個容器,其中真正裝的是親情。正如《唐山大地震》要講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內心的余震,地震只是32秒,而內心的余震卻延宕了32年,這種親情的難以釋懷恰恰是媽媽當初的一次無奈的選擇。兩部影片的成功,恰恰告訴我們,真正重要的是故事,而不是事故;是人性和人情的故事,而不是漂浮在外表的故事。與《琴聲暖洋洋》講述兄弟情意不同的是,《籃球寶貝》講述了女兒林曉研從最初的厭惡父親到體諒父親的一個親情回歸的故事。在家庭結構的設置上,父母離異;母親開著豪華車,住著別墅,父親則住在胡同深處的小四合院;與漂亮的母親相比,父親顯得木訥、窩囊、頹唐。所以,林曉研打心眼里看不上父親,只習慣稱之為“老林”。母親外出,她從豪華別墅住進“老林”的小四合院后,林曉研又被“老林”報名參加了籃球寶貝大賽。一場比賽過后,女兒認同了父親。《菜園街醒獅會》雖然以舞獅大賽為故事的線索,但是對主人公Ricky的背景介紹上,有意地設置他的信息——一家跨國公司的中層主管,人很獨,凡事講規則,冷血麻木;沒有朋友,沒有親人;跟家人從不來往,父親住在老人院十年沒去看過;換女友像換衣裳一樣,從不投入感情,甚至不認為人需要感情。這樣的一個人物在澳門賭博輸得身無分文后,偶然加入到菜園街醒獅會,他的生活與其中的各色人等發生了關聯,在這些人物的糾葛和感情的升華中,Ricky開始認識到生活的真諦,舞獅的過程讓他知道責任對每一個人的重要性,寬容是人們相處的基本。
我們可以發現,以上幾部影片的主人公的家庭基本都是破碎的,然而在家庭倫理情節劇的規范之下,創作者讓每一個人的情緒都找到了出口:劉年和弟弟通過父親留下的小提琴,二人合奏,完成了親情的回歸;林曉研通過父親“老林”暗中幫助的舞蹈造型繪畫,獲得比賽成功,感受了父愛;Ricky也是從菜園街的各個人物的家庭悲歡以及舞獅的整個過程中認識到親情的重要。最終,片中的各色人等都回歸到主流價值觀念的家庭中去。正如黃劍東所說,如果說我有什么創作慣性的話,那便是孩子離開了家,如何回去,如何與父母彼此接受的一個過程。
(二)青春和勵志
從電影中理解“青春”,我們有必要借用“青春片”這一類型概念。在筆者看來,“青春片”的概念基本包含如下兩個層面:青春的迷惑與懵懂、成長的陣痛與釋然。臺灣的“青春片”已經成為一個可供識別的標簽。已故電影大師楊德昌說過,臺灣電影只分為兩類——青春片和非青春片。言臺灣電影,必言青春片。近兩年來,臺灣電影勃興,出現大量青春片,像《單車上路》(2006)《、六號出口》(2006)、《練習曲》(2006)《、夏天的尾巴》(2007)、《最遙遠的距離》(2007)、《沉睡的青春》(2007)、《九降風》(2008)《、囧男孩》(2008)《、艋舺》(2010)等等。很有意思的是,臺灣的青春片多有同志情結,如《藍色大門》(2002)、《十七歲的天空》(2004)、《盛夏光年》(2006)、《刺青》(2007)、《渺渺》(2008)等。
以上的這些影片很少有勵志的成分,更多的是惆悵與迷茫,散發著淡淡的文藝氣息,囿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多贅述。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內地很少有“青春片”,個中原因與文化土壤有莫大的關系。本文中的“青春”概念更多的是反映片中人物所處的年齡段以及其中被概念化的情緒,所以與嚴格意義上的“青春片”概念不盡相同。從更為寬泛的意義來說,“青春”常常和“勵志”主題搭配,采用“團隊競賽”的外包裝形式。從故事的建構性來說,這種競賽本身符合戲劇的對抗性原理,參與其中的各個人物的性格缺陷在備賽和比賽的過程中暴露無遺,最終的比賽讓他們認識到團結與尊重的重要性。這一模式比較成功的電影有寫鋼廠下崗工人為求生存自組團隊跳脫衣舞的《光豬六壯士》(1997)、有講述五位高中男生水上芭蕾表演的《水男孩》(2001)、有講述胖女孩參加選美比賽并引發全家總動員的《陽光小美女》(2006),以及由五個“老弱傷殘”的非專業歌手組建樂隊的《海角七號》(2008)等等。以“青春和勵志”的尺度去觀照黃劍東的幾部電視電影,可以得到一個統一的敘事慣例:一是影片的主人公多為青春期或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二是黃劍東偏好對群像人物的塑造,因為在以競賽為總體模式的“青春與勵志”模式中,群像人物更能產生豐富的戲劇對抗性,從而讓故事內蘊更加立體。同時,從作者與文本的關系來看,“青春和勵志”也是對黃劍東個人性格的彌補,他創作的電視電影是一種讓他進入理想精神狀態的途徑。
《琴聲暖洋洋》中,弟弟劉以風不配合哥哥的法律調查,從親情上講是不能原諒哥哥的過往;從故事情節性上看,是因為劉以風想為自己心愛的女孩承擔法律責任。然而,事實上是受害者自己倒到墻上撞成重傷。劉以風的行為完全是一個尚未成熟的男孩硬要強裝男子漢的做法,是用青春捍衛愛情的一種稚嫩表現;而且劉以風是一個小提琴手,這樣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不羈青年與臺灣青春片的男主角無疑具有很相近的特質。
相對于《琴聲暖洋洋》,《籃球寶貝》、《烈火男兒之了不起的消防兵》《、菜園街醒獅會》的“青春和勵志”特征更為明顯。《籃球寶貝》中,林曉研作為一個高二的女學生,另類并叛逆。“假小子”的性格讓林曉研在學校小有名氣。她原本想參加籃球訓練營,沒想到“老林”卻給自己錯報了籃球寶貝。周萌萌的冷嘲熱諷讓林曉研決定組建自己的籃球寶貝隊,自任隊長,并招募了劉小菲、周童、于芳三名同學。人員齊了,但“紅翅膀籃球寶貝”卻因為五個人決然迥異的性格分分合合。最終,她們克服重重困難,從父親暗中畫出的舞蹈造型中獲得靈感,站到了比賽現場,感動了評委和對手。《烈火男兒系列》講述了一群消防兵為了消防事業貢獻青春的故事,每一集都圍繞著兩個人物或幾個對抗性人物展開故事敘述。在《烈火男兒之了不起的消防兵》中,王寶強飾演的消防兵龍大川因為表現突出,被認為是“了不起的消防兵”。連里為他報名了新一屆全國消防特勤訓練尖兵大賽。在進行比賽訓練的過程中,龍大川幾次跟班長發生沖突,在一次火警中,班長為了救他,壯烈犧牲,龍大川為此喪失信心。
幾經情緒疏導,在眾人期待的目光中,煥然一新的消防兵龍大川趕到全國消防尖兵大賽初賽的現場。《菜園街醒獅會》中的人物從表面上看不是清一色的青春少年,硬要與“青春”的概念發生關聯確實比較牽強。但是,從影片的情緒來看,做“青春與勵志”的闡述也說得通。影片中人物的日常生活圍繞“醒獅會”這一集體活動展開,參與其中的各式人等有著“青春的激情”,同時也貫穿著勵志主題。如上分析,本文所言的“青春與勵志”只是泛意義上的概念。作為一種總結式的表述,它不可能與既定的規則一一對位,也不能涵蓋經驗事實的方方面面,它更多的是將類型經驗與個人創作慣性做一次對照,以檢驗類型經驗和傳統范式的動態的可持續性。如此看來,如果說情節劇化和故事化是黃劍東電視電影創作的外在的敘事形式,那么它內里裹挾的則是兩部分——“家庭和親情”、“青春和勵志”。二者在某種程度上構成復調“,青春”的叛逆和迷茫多半表現在“家庭”關系上,“勵志”的表現使得“青春”男女回到主流價值觀念的軌道,從而回歸“親情”。從這個角度來說,雙主題互相映照,充分保證了敘事形式的平衡和內在的豐富性。
技巧
(一)人物建構
在故事主題上,黃劍東受成長經歷及日本影視劇的影響,重家庭和親情,喜青春和勵志;在戲劇人物的建置上,黃劍東坦言自己更多是受好萊塢和港劇的影響,“我基本上從一個人物出發,想出與之對應的一個或幾個人物,然后編織一個故事。而這幾個人物一定是完全不可能在一起,完全沖突化的角色設置,像火星撞地球的那種。總之,正和反,大和小,這樣的差異化組合方能產生戲劇張力”。著名編劇理論家悉德•菲爾德說過,“一切戲劇都是沖突。如果你已經清楚自己人物的需求,那就可以設置達到這一需求而要克服的種種障礙。他如何克服障礙就成為你故事的本身……沒有沖突就沒有戲劇,沒有需求就沒有人物,沒有人物就沒有動作”。(2)
在《琴聲暖洋洋》中,黃劍東最先構想出來的人物是弟弟劉以風,因為這是他夢想中的孩子的范本——灑脫不羈、不受世俗牽絆。因為有了弟弟這個人物,就需要建構出一個與之對抗的人物,于是哥哥劉年就被創作出來。在劇本的前幾稿,人物的關系建置中還有爸爸,在第四稿的時候創作團隊做出重大決定,讓爸爸這一人物死掉,這樣才會造成兄弟二人的不平衡性,故事的沖突才好繼續下去。《籃球寶貝》原名為《青春網事》,講述的是爸爸為了把女兒從網戀中解救出來,在網上扮演了知心姐姐,最后讓女兒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到真愛。然而,這一技術難度較大。黃劍東決定給原故事“找件衣服穿”,于是加上了一群性格和行為完全迥異的四個女生,讓她們參加一場比賽,而原本的父女情感變為一條副線,最終的情感落腳點一分為二——朋友間的團結合作和父女間的情感溝通。電影創作中,人物設置除了簡單的對抗性原則之外,深刻的編劇在創造主要人物時大多遵循“圓形人物”原則,所謂“圓形人物”,即是與扁平化的“類型人物”塑造相對的一個概念,力求展現一個人物的方方面面,使人物飽滿有力。編劇理論家多米尼克說,“為了能使人物在建構背景中栩栩如生,他必須是一個有過去的人,不論這一段過去和當前的情節有無關聯,它對現在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們必須了解人物的過去才能發現其與現在的關聯”。(3)悉德•菲爾德則有更為詳細的描述:“首先,確定你的主要人物。然后,把她或他生活的內容分為兩個基本范疇:內在的生活和外在的生活。人物的內在生活是應該從人物出生到現在這一段時間內發生的,這是形成人物性格的過程。人物的外在生活是從影片開始到故事的結局這一段時間內發生的,這是展示人物性格的過程。”(4)
悉德•菲爾德所謂的“人物的內在生活”與多米尼克說的“人物的過去”是同一個概念。編劇理論家之所以如此重視“人物的過去”,是因為它為主要人物的行動確立了心理依據。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心理學多從挖掘夢境和童年的記憶去分析人物心理,西方電影去回溯人物行動的動因的時候,往往都可以從童年生活得到求證。偉大的《公民凱恩》也將報業大亨凱恩的性格悲劇部分地歸結為被剝奪的童年造成的陰影,所以人人想知道的“玫瑰花蕾”原來是童年時的一只雪橇板下的標簽名。黃劍東的電視電影作品在設置人物時,同樣是將人物的“內在生活”和“外在生活”統一起來進行觀照。《琴聲暖洋洋》中的哥哥劉年在童年時是一個小提琴神童,父親為了完成自己的琴夢而離家出走,他痛恨父親,摔碎了自己心愛的提琴,發誓永不拉琴。這種童年的記憶成為他心中永遠的痛。同時,在對劉年的“外在生活”的表述上,編劇和導演也用盡心思。“不能丟掉生活質感與生活原態,用強調質感與原生態來沖淡故事的假定與人物性格的扁平,讓觀眾從一點一滴中相信故事與人物,否則影片再好看也不會感人。比如我們想強化劉年的事業不成功,生活無序,焦躁不安,過著狼狽不堪的日子。從開篇他駕車奔法院入手,我們就給演員提供了所有能想到的瑣碎細節,如收音機嘈雜的換臺聲中傳出的路況信息,插上點煙器的刮胡刀,反光鏡中亂蓬蓬的頭發與睡眠不足的雙眼,手在塑料袋里摸索著油漬漬的小籠包子,后座的袋裝牛奶用嘴撕開,副座上的卷紙與手機,惡聲惡語向別人催債的電話,撒謊敷衍別人催他的電話,還要換擋超車。他下車后向褲子里塞襯衣下擺,套上從來打好不解扣的領帶及西裝,還從后視鏡整整頭型,又記錯了案子,拿錯了卷宗,慌亂的腳步,這一切細節的設置都是為了幫助演員堆積出忙亂無序的狀態,增加生活質感,讓觀眾相信并接受他是一個倒霉律師。”(5)
《菜園街醒獅會》中,除了主要人物Richy之外,同樣對其他醒獅的各色人物做了“內在”和“外在”的處理。比如菜園街醒獅會的絕對主力阿黑,原來是澳門著名的大律師,因為崇拜曾經的醒獅之王黑仔才給自己取名叫阿黑。反面人物飛虎本是阿黑的堂弟,年輕時同在菜園街醒獅會,后來因為飛虎自視甚高,不肯再做獅尾,兩人斗獅,飛虎失敗。從那以后,飛虎把阿黑和菜園街醒獅會當成最大敵人……在劇作領域,能否成功地建構起一個豐滿而獨特的人物,已成為判斷劇作者藝術能力高下的最重要的標準之一。也正因此,故事和人物這一對創作起點的概念,往往成為困擾編劇的一大難題。太故事化,人物扁平,往往會陷入藝術平庸的質疑之中;太講究人物性格的豐富性,而缺乏故事情節性,則可能讓觀眾對電影敬而遠之。如何去平衡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成為創作界共同面對的課題。黃劍東電視電影作品中的人物建置既符合好萊塢電影的戲劇沖突原則,保證了故事的可看性,同時又掌握了人物“內在生活”和“外在生活”統一的原則,使得人物立體豐滿。既然說到人物建構,就不得不提及中國很多以人名命名的電影,它們的失敗也恰恰因此:人物采取的高尚行為完全無來由,單靠對白驅動,完全可能的真實事件被拍得虛假,喪失了本該可以感人又富教育意義的影片功能。
(二)人物關系建置
在確定了親情與家庭、青春與勵志的主題,設定了一個主要人物之后,對于創作者來說,接下來的任務便是選擇與之匹配的人物關系。親情與家庭自然離不開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青春勵志的故事也是多發生在青年人中間。可見人物關系的建置也可以共享某些普遍的敘事策略。對這種策略的把握和表述,其實也就是對此類劇作中的一系列關鍵元素的把握和表述。有人曾經總結過幾種人物關系的“基本配對模式”,該文作者將之劃分了三類,并指出其中普世的價值主題:“長幼模式——救贖/成長主題,異性模式——/慰藉主題;同性模式——認同/平等主題……在長幼模式關系中,這類影片在傳遞情感的同時,背后通常隱藏著長者獲得救贖或者少年得到成長的敘事。被救贖的長者通常都有自己的心結,但通過愛和救贖,他最終走出原來的陰影,重新獲得希望的生活態度。而少年在獲得長者之愛和教誨之后得到成長。”(6)
講述盲人上尉與高中學生之間的看護與被看護關系的《女人香》、游手好閑的賭徒陪伴缺失父愛的小男孩尋母的《菊次郎的夏天》、巴西車站替人寫信的自私冷漠的老太太帶領失去母親的小男孩尋父的《中央車站》、自私的弟弟拐走自閉癥的哥哥以求修改父親遺囑的《雨人》等影片無疑是這種模式的代表。電影《琴聲暖洋洋》同樣也很好地體現了這種人情關系模式理論。哥哥與弟弟的人物關系屬于“長幼模式——救贖/成長主題”。劉年因為童年的陰影,一直不能原諒父親,發誓永不拉琴。長大的他成為一名律師,由于藝術家的感性的性格,使他不屑做事務性的工作,雞毛蒜皮的小案子他更是不求甚解,所以他很失敗,富有才華,卻過著狼狽不堪的日子。他自我保護意識很強,凡事先想到自己,有些自私,多年的社會經驗使他變得事故、圓滑,掩藏了他心底的真誠與勇氣。他把感情埋在心底不愿去觸及,直到有一天他在弟弟身上看到了自己丟失多年的東西……通過琴聲,哥哥先消除了對父親的恨,又化解了對弟弟的誤解,找回了自己失去多年的真誠與勇氣。可以說,案件的處理讓哥哥獲得了救贖,也讓弟弟學會了成長。除了“長幼模式”之外,作為青春與勵志主題的電影大多都共享著“同性模式”,“同性模式更多地集中于社會個體的差異性與統一性的探討,這一過程常常被展示為一方向另一方的認同,由于這種認同常常是一個表面的社會強勢成員向弱勢成員的認同,因此又常常內在地蘊含著哲學意義上的平等主題”。(7)
《籃球寶貝》、《烈火男兒之了不起的消防兵》和《菜園街醒獅會》明顯是“同性模式——認同/平等主題”的絕好例證。《籃球寶貝》中的五個女孩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林曉研會打籃球、劉小菲從小跳芭蕾、周童有過練武學藝的經歷、于芳熱衷辯論,借鑒周萌萌的訓練,糅合自己的動作設想,等待林曉研“紅翅膀籃球寶貝”的是不歡而散。在林曉研自己都心灰意冷時,一幅漫畫寶貝造型給了林曉研靈感,并以漫畫靈感為啟發,重新召集回劉小菲、周童和于芳,完成了一組融芭蕾、武術、街舞、健身操的表演動作。大家認識到比賽是一個整體,如果只是孤軍奮戰,個人技術再高也終將失敗。這種尊重個體差異性和群體統一性的認識將《籃球寶貝》的“認同/平等”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在得知啟發他們的漫畫寶貝造型出自父親“老林”之手后,林曉研感受到濃濃的父愛,理解了父親,一個少女成長的軌跡被描繪了出來,這也是“長幼模式——救贖/成長主題”的一個表現。《烈火男兒之了不起的消防兵》的名字意有雙關。一是表示消防題材的電影,二是表現一群有火一樣情懷的熱血男兒。消防兵部隊是一個帶有強烈團隊精神的集體,強調的是“統一性”,于是消防兵們迥異的性格和互相碰撞的生活共同構成了這支消防隊的激情交響曲;《菜園街醒獅會》的群像描寫更是復雜。菜園街儼然是一個獨立的小世界,這個街里的每個人都跟醒獅會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古道熱腸、不肯結婚、會打鼓和打魚蛋的杏仁姐;充滿激情、菜園街醒獅會的絕對主力阿黑;“菜園街醒獅會”的精神領袖、喜歡跳“搓澡舞”的70歲的木老爺,以及菜園街醒獅會最大對頭潭山獅館的總教、36歲的飛虎等等。在兩個醒獅幫派爭奪“醒獅之王”的過程中,原本自私冷漠的Ricky領悟了生活的真諦,知道了責任對每一個人的重要性,寬容和平等是人們相處的基本。“我們這個戲,是觀念之爭,是觀念的交鋒,而交鋒的焦點就在于如何把榮譽和人性統一又如何說明榮譽的重要是建立在人性健全之上的。”(8)
總之,在類型片的創作上,建置人物關系有著既定的模式和套路,共享著成功的敘事策略。黃劍東選取的“長幼模式”以及“同性模式”完全是與其故事的“家庭與親情”、“青春與勵志”的主題貼切吻合。而且從通俗劇情片的角度來看,這兩種模式完全是國際通行、可以跨越文化鴻溝的人物關系的建置方法。當然,模式不是公式,作為一種經事實檢驗的富有其廣泛意義的人物關系形態,其注定具有某種開放性,也就是說,它具有以其基本范式為基礎,進一步產生具體劇作人物關系的空間。這些都需要我們結合更多的電影劇作事實,進行經驗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