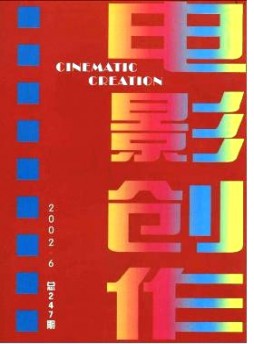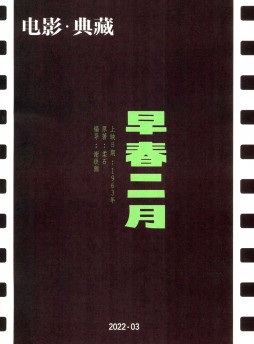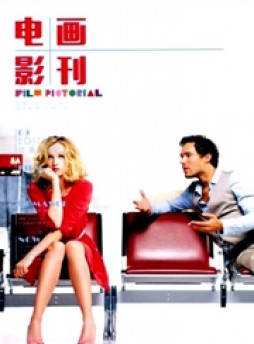電影作品音樂特色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電影作品音樂特色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李安的電影中,音樂落地有聲,極有存在感,他影片的配樂,已隱然成旁白,清晰地道出了每個角色心中無法言喻的多重情緒。《臥虎藏龍》和《斷背山》,曾讓李安的電影兩度奪得奧斯卡的最佳電影配樂獎,雖然那更多是音樂家的榮光,但在電影音樂評論家羅展鳳看來,“能夠令兩部電影音樂奪得殊榮,一點也不簡單,可見這位華人導演的確獨具慧眼,能為自己杰作找到好搭檔,錦上添花。”
唐人有詩云:“玉碗盛來琥珀光”,下面我們就從音樂切入閱讀,看看李安是如何為他的電影作品尋找適合的“音樂裁縫”的,以及他是如何以細膩敏銳的音樂感覺來講述電影故事的。
一、開場音樂
在李安的光影世界中,音樂一開場就要先聲奪人,抓住觀眾的注意力,成為引導觀眾情緒的主要因素,并將其帶到電影特定的環境之中,《臥虎藏龍》開始于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低沉緩慢、憂傷深沉的主題音樂,音色微微地發顫,仿佛一幅淡彩水墨長卷緩緩展開。雖然風景如畫,我們卻聽得到琴聲里殺機一線,仿佛提醒著觀眾江湖的險惡。俞秀蓮進京的時候音樂頗有些緊張,但是緊中有緩,仿佛在提示著好戲即將開始。
李安曾說,《斷背山》的音樂是那種教人要哭出來的樂聲,來自阿根廷草根配樂大師古斯塔夫·桑塔拉拉的音樂,就有這種教人哀傷的特質,當他“轉軸撥弦三兩聲”,讓“吉他的響亮,像一線光彩劃破長空”,就讓《斷背山》有了一個與眾不同的開場。
二、華人組合
李安沒有一個長期伙伴為他主理電影音樂,就像普列斯納之于基耶斯洛夫斯基,久石讓之于宮崎駿,相反,他每部電影都找來不同的音樂人合作,而對音樂人的選擇則顯現出李安的匠心獨具。
1991年,李安拍攝了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推手》,“《推手》是一部中、美班底混合的電影”,他聘請了作曲家瞿小松來完成影片的配樂,如果把這部影片的影像太極視作名詞,那李安需要它的音樂就是那個形容詞:靜寂。李安找到瞿小松,不僅因為他是中央音樂學院當年的“四大才子”之一,更因為他的靜——瞿小松被西方樂評人稱作是“寂靜大師”,他的音樂,有一種來自自然界的虛空味,最能體現人類同自然渾然無間的寧靜。影片《推手》開場,朱師傅在自家的客廳練著太極,這時音樂緩然而至,寂靜的音符仿佛是氣流動于朱師傅的指掌之間,進退均衡,圓轉如意。
三、中西合璧
李安的成長,同時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和美國商業文化的影響,因此他的電影美學成就在于他展現了一種理智與情感、東方與西方碰撞交匯中的生命體驗,他的電影作品中,同時打上了兩種文化的烙印,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李安曾說:“至今我每部片子的配樂,大都采用中西合璧的方式……東西合璧好像最能配合我的需要。”
中西合璧,是指以傳統民族器樂為主的民族樂加上以西方管弦樂為主體的交響樂,交響樂在塑造整體樂思上有優勢,而民族樂的材質源于自然,充滿了濃郁的鄉土色彩和溫暖的人情味,更具“神韻”,兩者在李安的影片中各司其職、各領風騷。
為了配合東西合璧的需要,李安向能跨越東西半球、融合多民族曲風的樂壇傳奇人物發出邀請,在為影片《與魔鬼共騎》配樂時,李安請到“當代第一魔笛手”雷恩·寇伯,他的演奏被形容為是“西方曲式與東方結構最誘人的結合”;與李安合作過三部影片的極簡主義配樂大師邁克爾·丹納,最擅長把東南亞的民族音樂和西方的交響樂搭配在一起。當李安希望在《冰風暴》中找到“原始的屬于大自然的呼喚”,他便找來了印尼的打擊樂器甘美蘭,甘美蘭音質的原始風味,與交響樂搭配在一起,讓人一曲難忘。
《臥虎藏龍》的音樂將東方音樂的藝術美感與西方音樂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堪稱是中西合璧的典范,影片中使用了在泰國、云南一帶的樂器巴烏,為影片營造感性及神秘氛圍,在飛檐走壁的一段又配上緊密有致的擊鼓聲,則充分烘托出緊張刺激的武打氣氛,是中國電影配樂中的極品。
擴展閱讀
- 1電影文化
- 2電影傳播
- 3電影現狀
- 4電影發展戰略電視電影
- 5深究傳統電影以及數碼電影結合
- 6電影海報設計
- 7電影類型思索
- 8電影文化闡釋
- 9英語電影欣賞設計
- 10電影中服裝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