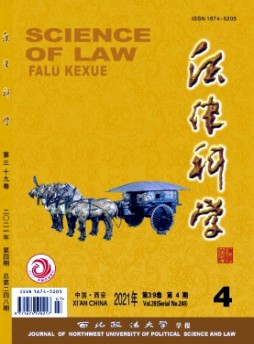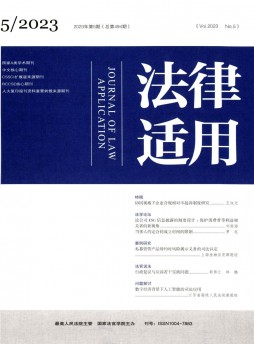法律文化視角下干部法治思維的制約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法律文化視角下干部法治思維的制約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提高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重要精神。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是集體本位,導致權力本位、人情優先、無訟的理念,現實中成為制約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重要文化因素。開展法制教育、推廣法治典型、營造法治環境,是促進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養成法治思維的未來路徑。
關鍵詞:
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制約;文化因素
法國學者孟德斯鳩認為,法治是一種精神、一種文化、一種經久不衰的風氣。法治實質上是一種思維方式,只要當每個人主動而非被動、時常而非偶然地用法治思維去思考問題的時候,這個社會就進入法治狀態了。當下的中國已經進入法治建設的關鍵時期,而阻撓我們法治進程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的法治意識和法治思維欠缺,即國民法律意識的缺失以及對法律缺乏足夠的敬畏。信訪不信法、信網不信法、信鬧不信法等諸多社會現實表面背后反映出的是信權不信法,遇事“找關系”而不愿意“走程序”成為一種普遍認同的規則,人們痛恨社會不公,但自己的權利糾紛又習慣于找政府解決不愿訴諸法律。我們必須反思,到底是什么力量讓法律規則在現實中失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們不愿理性地表達訴求?這些現象反映的還是權大于法,最終涉及領導干部如何用權的問題,是否權力法定、權依法使成為核心要素。可見,引領社會法治信仰的關鍵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從根本上消除此類現象,必須緊緊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培養領導干部法治思維,使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合理的預期,從而相信法律、相信規則,最終形成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而制約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因素是多重的,包括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等。筆者試圖從傳統文化層面探析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制約因素。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是集體本位
從古老的世界文明來看,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中國是東方文明的代表。愛琴海岸和黃河中下游地區存在著天然的地理環境差異。早在三千多年前,古希臘人與中國人在社會結構、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等方面呈現出巨大差異,從此也決定了兩大文明的歷史流向。這與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密不可分,古希臘土地貧瘠、高山多石、炎熱少雨的自然氣候天然不適用于農耕,而其得天獨厚的航海條件讓希臘人把目光投向大海,迫使古希臘人從事商業貿易。人口的流動性很快打破傳統的以血液為紐帶、以家庭為基礎的熟人社會,進入了一個以地域為基礎聚集的陌生人社會,動搖了血緣組織存在所需的長期定居的穩定性。人們開始遠離血緣控制,成為獨立的自由人,同時也失去了熟人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要重構陌生人之間的誠信,就需要建立一種自由、平等、獨立的理念和規則,實現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和演進,人們的契約精神、法治理念和規則意識逐漸形成。與古希臘相反,中華大地的中原地區具有天然的地域環境優勢,土地肥沃、氣候濕潤溫和,非常適合農耕生產,很快聚集了大面積的農業定居人群。中華大地以平坦的中原黃土地為中心,形成一個特殊的地域環境:北邊是無法耕種的遼闊草原,南邊是難以開墾的浩瀚森林,西部是不利農耕的高原,東部是無法跨越的大海,這種封閉的地理環境必然形成一種內向的、互相消耗的內墻文化。人們一直生活在集體中,一切社會關系都是通過血緣展開的,人們固定在血緣的網絡之中,世世代代過著簡單、重復的生活,家族是人們生存的唯一依靠。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必然導致有限資源的爭奪,也推動著部落向自我膨脹和集權化方向發展。生存的壓力迫使氏族部落必須提高管理水平,必要的時候聯合起來一致對外,逐漸形成一種集體本位的文化,從氏族到家族再到國家,每個時期都體現出集體本位,個體被維系集體的繩索越綁越緊,在集體面前,個人權利無足輕重。離開了集體,個人幾乎無法生存。西周時期的宗法制度把這種集體文化固化了,并且影響此后中國社會幾千年。宗法制度是一種以血緣為紐帶的制度,宗族成員的身份地位與權力分配完全是由家族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決定的,宗法制度的實質是國家的統治關系與家族的血緣關系合二為一。①法律與政治制度由宗法制度演變而來,宗法制的實質是一種血緣等級制,集體本位實質是權力本位、義務本位,壓制個人權利。從梭倫改革和商鞅變法的共同點來看,兩者都打破血緣和門第,消滅貴族世襲特權,廢除世卿世祿制。但各自體現的文化傳統不一樣,梭倫改革的理念是重商,以個人財產決定社會地位,尊重個人權利,體現個人本位;而商鞅變法的思路是重農抑商,以戰功、農耕論賞,以個人對國家的貢獻決定其社會地位,從而提高國家的控制力,其實質仍然是國家本位。
二、集體本位生成權力本位
西周的宗法制確立了血緣關系的遠近決定權力大小的規則,天子的嫡長子、長孫繼承天子之位,其兄弟只能是諸侯,諸侯的嫡長子長孫繼承諸侯之位,其兄弟只能是大夫。同樣,大夫的嫡長子長孫繼承大夫之位,其兄弟只能是士,以此類推。這樣就逐步形成了以權力為中心的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系。在宗法家族制度分崩瓦解之后,儒家通過對宗法制度的“忠”、“孝”兩個基本原則作出溝通性解釋: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延伸。同樣,家是國的細胞,君權是父權的放大,重新確立了宗法制度及其倫理道德與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體關系。此時的君臣關系也并非一種絕對化的權力服從關系。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孟子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③“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④到了漢代,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把神學、君權、父權、夫權結合起來并加以絕對化,提出了三綱五常理論,“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⑤認為君、父、夫具有一種天然的絕對權力,后來就逐漸演變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夫要妻亡妻不得不亡”。成功創設了家族本位與國家本位相結合的理論,影響中國政治法律兩千余年。國家本位實質是權力本位,權力本位就是官本位。因為權力大小決定地位、資源、待遇的分配,決定人的等級地位,這就容易導致權力崇拜。與法律至上、權利本位不同的是,中國人對人的崇拜勝過對神的崇拜,導致皇權專制,法律只是維護皇權的工具而已,不可能內化為人們心中的信仰與思維的慣性,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均受制于皇權、君權,從而使法律在中國長期處于權力的從屬地位,也形成了中國人“權大于法”的思維定式,培育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以權廢法的人治土壤。命令、指示、批示在今天依然很有市場,其實質是人治思維的慣性體現。當今社會,國人的骨子里仍然充滿著等級觀念,血液里流淌著權力思想,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在于擁有多大權力、享有多高級別。權力本位的觀念充斥著生活的每個角落,餐桌座位都是按照級別的高低與權力的大小進行排序。這種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在現實中必然產生一個問題,當權力與法律產生沖突時,應當如何作出選擇,這也是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的非常重要的制約因素,傳統的等級差別與現代法治思維的平等觀念形成巨大的反差。
三、集體本位形成人情優先
從人類文明進步史來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就是從血緣關系社會向契約關系社會的轉變,而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沒有真正突破這一邊界。以血緣為核心的集體本位觀念根深蒂固,在家庭關系中表現為按照血緣遠近決定親屬關系的親疏與地位。西周的五服制度把這種家庭血緣的親疏等級固化了。具體如下:第一等(斬衰):生麻布、最粗、刀砍、不縫邊;[三年,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父為嫡長子]第二等(齊衰):熟麻布、次粗、裁剪、縫邊;[一年,父未去世子為母、夫為妻、孫為祖父母…]第三等(大功):熟麻布、較粗、裁剪、縫邊;[九個月,男子為堂兄弟、女子為親兄弟、公婆為嫡長子之妻…]第四等(小功):熟麻布、較細、裁剪、縫邊;[五個月,為堂祖父母、外祖父母、舅舅…]第五等(緦麻):熟麻布、最細、裁剪、縫邊;[三個月,為岳父母、外甥、女婿…]從外在形式上來看,五服制度是按照血緣的遠近為標準,確立不同的喪服和守孝時間;從內容來看,五服制度實際上是用血緣關系的遠近來定親疏、別內外,把親屬關系分成不同等級。古代以男性血脈為中心進行分類,最終形成父子、兄弟、近親、遠親乃至朋友的五倫關系網絡。遵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倫理法則,以此維護社會及家庭的穩定、和諧、有序。用人倫關系來理解、調整家庭關系和國家政治關系,道德原則和規范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按照《禮記》的解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①古代官員處理案件遵循“人情”的理念,人情滲透到法律當中,具體表現為道德重于法律,如“原心論罪”,只要作案動機是善良的(符合道德規范),即使觸犯法律,也應該減輕或免除處罰,成為解決道德與法律這對矛盾的原則之一:“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心,立君臣之義以權之。”②即用父子之間、君臣之間的道德原則去評判案情。古代司法實踐中解決道德與法律沖突的原則還體現在“親親相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③
“親親相隱”鼓勵人們講究親屬之間的倫理情感關系,在宗法倫理和法律價值的沖突之間,優先維護宗法倫理和家族制度。當一個死刑犯的家中還有老人需要照顧時,只要皇帝下赦,則可以網開一面,允許其在家中“存留養親”。古代春秋決獄的實質是人情、道德決獄。在這種人情優先于法律的理念指導下,只要不危及皇權,貴族官僚的一般犯罪便可從輕發落。統治者為了體現仁慈之心可以對一般罪犯法外施恩,即恤刑,也可以對過失犯罪從輕發落,即宥過。恤刑與宥過后來逐漸演變成對情有可原的一般罪犯采取各種各樣的變通手法,減輕或免除其處罰。人情中體現的“情理”也就慢慢演變為個人的“私情”。人情味濃厚的社會里,法律的公平正義不斷受到損害。古代法律的基礎也在于人情,以維護人情為法律的重要使命,當法與情發生沖突或抵觸的時候,人們習慣于情重于法、以情變法。在社會觀念中,情是永恒的,法是可以變通的,這正是法外之仁、法外之刑在古代盛行的內在因素。領導干部在現實中決策或者處理各類問題的時候,也非常注重倫理道德,甚至導致重倫理輕道德法律規則,“無私”便“無畏”隱含對法律不存敬畏之心。這種思維慣性極大影響著中國法治建設進程。湖南嘉禾原縣委書記反思嘉禾事件的教訓時提出“無私也要有畏”,這對于當代中國的意義極為深遠。今天的中國已經從熟人社會逐漸發展到陌生人社會,因工作或生活集聚在一起的人們不再以血緣為紐帶,而是以地域為標準,法律規范理應成為人們共同遵守的規則。然而,社會現實并非如此,在血緣紐帶徹底瓦解的城市,人們千方百計建立各種擬制血緣的關系網,熟人社會、關系社會的印跡根深蒂固,老鄉會、同學會、校友會充斥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有熟人的地方辦事也確實更加方便。正如費孝通所說:“在這個社會中,一切普通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準來。”[1]六親不認仍然是一個道德上的貶語。人情在實踐中仍然具有深刻的影響力,時時處處體現“圈子意識”,情為至上,而“理”與“法”次之。尤其是在中國的基層社會,更多地停留在熟人社會階段,凡事都是先想到熟人,這種熟人社會為人治行政提供了土壤。在這種社會中,人們崇尚熟人關系的背后實質是崇尚權力、迷信權力,以權力信仰取代法治信仰。古代的人情規則直接體現在法律中,現在的人情規則掌握在人的內心里。由此必然導致另外一個問題,當法律與人情發生沖突時,領導干部應當如何作出選擇?人情成為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的重要制約因素。
四、無訟的價值取向引發厭訟
由于對自然的過度依賴,宗法時代以血緣為紐帶聚集而居,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使得社會成員共同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中,社會結構的顯著特征是家國一體,形成了以群體力量同大自然作斗爭的觀念,人與人的關系以是否符合情理為準則,不主張權利,只追求和諧,這正好迎合了封建統治者追求穩定秩序的目標。古人以“德主刑輔”的理念治國理政。儒家追求的是一種沒有紛爭的和諧社會,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①以“明德”、“循禮”追求“無訟”,現代應當是追求一個矛盾糾紛能夠得到公平處理的和諧社會。古代的國家治理是依靠道德教化,即采用道德和禮治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使人民各守本分,相安無事,形成一種禮教秩序。現代法治追求的是爭議和糾紛能夠在訴訟中得到終局解決,合法權利得到保障,從而使社會正義與公平得以實現,形成法治秩序。無訟一直是執政者追求的目標,古之圣賢舜就是一位息訴止爭的高手,以自己的言傳身教使得“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②使整個社會達到無訟的境界。地方長官通過裁判文書的形式,貫穿以道德教化平息紛爭的精神,寓教于判,使民眾重倫理道德,止訟息訟,決今日訟以止明日訟。與此同時,統治者宣揚“訟不可妄興”、“訟不可長”、“訟,終兇”等理念。興訟是道德敗壞的表現,是社會穩定的威脅,是陷人心于不古的權利之爭和使人格與族望掃地的惡行。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訴訟被認為是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績的表現。
崇尚無訟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厭訟、賤訟,以致訟師職業(古代的律師)為人們所鄙視,甚至被列為官府“嚴打”的對象,其嚴重后果就是人們不愿意運用法律維護權利。無訟的價值取向在于,民事案件調處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主渠道,包括州縣官府調處和民間調處,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調處制度,以調處息爭,從而實現無訟,在世界法制史上實屬罕見。當今社會,地方領導干部的頭腦里依然崇尚“無訟”觀念,一些矛盾糾紛和社會事件本來屬于法律問題,應該運用法治思維加以解決,而地方領導干部通常站在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運用政治思維進行解決,推崇“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妥協就是和諧”,要么花錢買平安,無條件遷就和退讓,要么濫用公權力,采用強制措施壓制權利。“穩定”成為一種政績,甚至把民眾上訪表達訴求也看成是影響穩定的事件,單純使用跟蹤盯梢、重點管理等行政手段,不注重權利保障和利益保護,強力壓制不僅沒有解決現有的矛盾,反而激發更大的矛盾沖突。“花錢買平安”只注重個案的解決而不顧社會普遍的公平正義,一旦出現傷亡事件,政府時常從第三方協調者轉變成了當事人,無原則地承擔法律之外的責任,從而破壞了人們對法律規則的一種合理預期,導致更多的人不相信法律。各自極端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獲取自己的非法利益,整個社會形成一種混亂局面,最終陷入“越維越不穩”的惡性循環之中。
五、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培養路徑
“一國的法治總是由一國的國情和社會制度決定并與其相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人民的主張、理念,也是中國人民的實踐。”[2]我國是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從傳統人治思維向現代法治思維轉變,必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領導干部是全社會法治思維的引領者、示范者,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養成也同樣是一個系統工程。
(一)以法治教育推動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養成法治理念、法律知識是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必備要素。領導干部學法知法是用法用法的前提條件,熟悉法律規范,把握法律原則和精神,有助于養成法治理念,進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工作。要培養領導干部法治思維,首先要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加強各級領導干部對法律知識的學習,黨委中心組學習法律常態化,以此促進領導干部形成法治理念。同時,通過實踐中鮮活的案例從正面學習經驗,從反面吸取教訓,不斷觸動領導干部的靈魂。要強化學習效果的運用,把學法懂法列入領導干部考核體系,要不斷規范領導干部法律知識考試的內容、方式及結果的運用,確保領導干部法治理念、法治思維能夠真正內化于心、外踐于行。
(二)以法治典型激勵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養成當前,培養領導干部法治思維至關重要又任重道遠。為此,必須注重樹立典型,推廣其典型事件,激勵典型人物,以點帶面,從而在全社會產生正面的示范效應。堅決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對那些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領導干部,必須嚴格依法追究責任。“對特權思想嚴重、法治觀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評教育,不改正的要調離領導崗位。”[3]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引導領導干部自覺養成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工作的習慣,使法治思維深入領導干部的內心,最終外化成一種行為———法治方式。在決策和執行中,必須做到“在合法性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地實現政治效益、經濟效益和道德效益的最大化”。[4]
(三)以法治環境促進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養成實踐證明,僅靠領導干部的自身努力來養成法治思維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營造一個有利于領導干部提升法治思維能力的外部環境,促進和保障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健全權力監督制約機制是依法行使公權力的前提條件,也是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重要保障。為此,一是要健全組織法制,厘清公權力的邊界,確保領導干部依照法定權限履行職責。二是要完善相關制度,健全程序規則,特別是規范領導干部決策權、執行權方面的法律程序(如行政程序法等),保證領導干部按照法定程序推進工作。三是建立科學的干部政績考核和選拔任用機制。充分發揮考核任用這個最管用、最根本的指揮棒,探尋推進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動力機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3]
將“法治狀況”納入領導干部績效考核和選拔任用標準之列,用一些可量化、可操作、可測量的指標來評價和考核領導干部的“法治狀況”。四是完善問責制度。注重問責主體、問責對象、問責程序、問責救濟等方面的制度完善,促使領導干部改變非法治的思維定勢和行為模式,逐步養成法治思維的習慣。
作者:萬高隆 單位:中共江西省委黨校 法學教研部
- 上一篇:儒家思想對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范文
- 下一篇:飲食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策略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