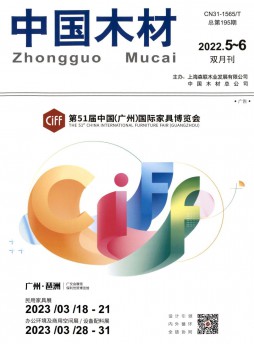中國古代文學功用思想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古代文學功用思想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荀子·樂論》),但同時也十分擔心藝術容易使人耽于享樂而墮落,所以節制藝術的娛樂性而放大其教化作用就成了首先要解決的一件大事。為此他們厘定了一個大原則,即“發乎情,止乎禮義”。孔子率先對文藝進行了一次大的清理,這就是刪定《詩經》,其審美標準就是“無邪”。其學說不排斥人性而又不放縱人性,“發乎情,止乎禮義”,凝聚了其在調和人的個性需要與其社會性需要之間的矛盾沖突的全部智慧:一面是活躍的個性,一面是社會的大秩序,兩者之間難以兩全其美,只好折衷以求。但在實際操作時,這個原則的分寸把握就難了,這就產生了后世或緊或松的不同局面:時而偏執于前,時而偏頗于后;走樣的時候多,和諧的時候少。筆者認為,在對待藝術的態度上,荀子的性惡論未嘗不較孟子的性善論來得合乎邏輯。如果人性本善,則何需禮、義、仁、智、信束縛呢?藝術本乎人心,有放縱人性中的卑劣之因素,如果放任自流,其結果將是“惑而不樂”,因此必須加以節制。荀子指出:“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荀子·樂論》)這就為情感的藝術戴上了理性的鐐銬。作為“道”的具體表現的禮也就此產生:“禮起之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也,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真是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且這一套禮儀也顧及人的心理需要,頗富人情味,入情入理,可謂中肯。以上各種功用主義思想最早胎育于早期社會對美的觀念。《國語·楚語上》中記載,楚國的政治家武舉在回答靈王問他新造章華之臺美不美的問題時說:“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陳伯海先生認為,武舉給美下的定義,是文獻錄存最早的有關美的解說,其內涵深烙著功利性色彩。孔子發表過類似的主張,《荀子》記載:“子貢問于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拍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起功而不德。為人下者其猶土也。”孔子以土為美的思想,正是一種功用意識的反映。孔子在解釋子貢提問君子為什么貴玉而賤珉這個問題時說:“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并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荀子·法行》)由此觀之,孔子是把萬物之善性和美聯系在一起,與其說在向我們申訴萬物因善而美的道理,毋寧說以此為比況向我們昭示君子以德為美。所以我們可以說孔子將“善與美”統一起來了。問題不應僅僅停留于此,應該看到,這種“美善合一”論對后世文學批評的影響十分巨大。在儒教成為國教之后,這種功用主義文藝觀也就基本上成為中國二千年封建社會最具有說服力的文學批評思想。回溯歷史,首先把孔子“美善合一”的功利主義思想理論化、系統化、政教化,并自覺運用于批評文藝的是荀子,后經揚雄、劉勰等人,把“明道”、“征圣”、“宗經”的文藝批評思想逐步臻于完善。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總體上是一部處理藝術與生活(政治)的關系史。這種功利主義的文學觀念,一旦被僵化和扭曲,其負面效應十分巨大。
首先,容易把文學變為政治的附庸,不宜于文學自身的獨立。文學批評容易走向非學術的政治批評,從而導致文學批評在非本質的層面上游離,很難冷靜下來作自身的、內在的本質建設。
其次,造成批評審美趣味的狹隘和單調。我們從孔子“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的態度中不難揣摩出,讀詩就是為了在實際生活、工作中用得上,不然就毫無用處,完全排斥藝術的娛樂、審美功能。這種急功近利的觀念顯然不是對待藝術所應持的中肯態度。再如韓愈曾寫過《毛穎傳》、《雜說》、《石鼎聯句詩序》等一類近似傳奇小說的作品,表現為重視從民間文學和對新興的文學體裁與表現方法中吸取滋養的積極態度。但卻遭到裴度的批評,稱之為“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這就極大地限制了題材、藝術形式、表現手法的多樣性、活潑性。在“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的重負之下,創作與批評的豐腴性被擠榨殆盡,只剩下莊嚴肅穆的道德意識,無法輕松,更不能放縱。
再次,在深層的文化心理上養殖了文學價值取向上的退避心態,即征古文化心態。韓愈在敘說自己文學創作的經歷時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這種征古文化心態促成了一代代聲勢浩大的復古浪潮,形成了中國獨具特色、橫貫古今的以復古為革新的文學發展模式。
最后,對文學批評自身的束縛。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學批評理論既豐富又單薄。所謂豐富,有浩如煙海的文學批評典籍為證,其詩話、詞話、言、紀事、詩品、典品、精義、廣記……可謂汗牛充棟。但與中國文學的實際相比,文學批評根深蒂固的道統思想和急功近利的功用思想,決定了在諸多的批評領域里無法客觀公正地深入研討,特別是對文學形成的研究尤顯冷落。中國的詩學批評理論較發達,但相形之下,散文理論、小說理論、戲劇理論等則難以望其項背。
再看敘事文學樣式,如小說、戲劇,可以說這是世界上最大最普遍的文學體裁,但中國文學批評對此一向較冷漠。《中國文學理論辭典》中關于小說、戲劇的詞條幾近于無,最具權威的郭紹虞先生的九十萬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竟一字不提小說和戲劇批評。造成這種偏失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最主要的恐怕還是與中國文學批評觀念中功用主義的道統思想有關。因為以“明道”為正統的文學觀念十分反感虛擬,從功用角度看,完成經國大業的、體現道統的東西怎么可能是那種荒誕無稽的奇門道術之類的虛妄之體呢?所以批評家們一開始就定下原則:“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揚雄《法言·吾子》)
從現存的資料看,第一個對屈原作品作評價的是劉安,而第一個對屈原作品中浪漫成份表示不滿的是揚雄,稱其為“過于浮”。在其《法言》之《重黎》、《問神》、《吾子》諸篇中,皆流露出不容浪漫虛擬的思想。他在批評司馬遷《史記》時認為,《史記》能夠秉筆直書,在《淮南子》之上,這就是“實錄”,但同時又批評《史記》的缺點在于“雜”和“愛奇”。他說:“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記麟止,不與圣人同,是非頗謬于經。”(《漢書·揚雄傳》)受其影響,王充也十分反感虛妄。他在《佚文篇》中明確表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在談到《論衡》的寫作目的時說:“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茍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論衡·對作》)王充之所以對“虛妄”如此深惡痛絕,實乃基于其文學的功用思想,他說:“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論衡·自紀》)要使文章有補于世,就必須“真實”,要能證之驗之。“故夫賢圣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論衡·對作》)對于兩漢功用主義的專制與霸道,羅根澤先生有段妙論,他說:“兩漢是功用主義的黃金時代,沒有奇跡而只是優美的純文學書,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運,然而詩經卻很榮耀地享受那時的朝野上下的供奉,這不能不歸功于儒家的送給了它一件功用主義的外套,做了他的護身符。這件外套,不但不是一人所作,亦且不成于一個時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即使在思想較活躍的南北朝時期,這種寄生于功用主義思想之下的對虛擬的反對也是激烈的。劉勰在充分肯定屈原的同時,對其浪漫色彩也不無微詞。在《辯騷》中說:“至于托云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日,目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
在《諸子》中又說:“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中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同虛誕。”為此,劉勰提出一個原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文心雕龍·辯騷》)在這種崇實尚用的批評氛圍里,視虛構獵奇的小說為“小道”而冷漠視之,也就不足為奇了。直到梁啟超以西方的眼光來審視小說,接連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論小說與政治之關系》的著名文論,才使小說的地位受到重視,而梁氏藉以推進小說發展的手段還是假借了傳統的功用思想。功用主義的批評觀念,由于囿于“明道”的神圣性,所以往往不容于趣味性、娛樂性和浪漫性,因而也就無視大眾消費的消遣心理,在崇高的使命感中忘卻了藝術的休閑功能。在俗文化粉墨登場的今天,在放縱與享樂成為時髦的今天,傳統文論思想對此必然手足無措,陷于危機實屬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