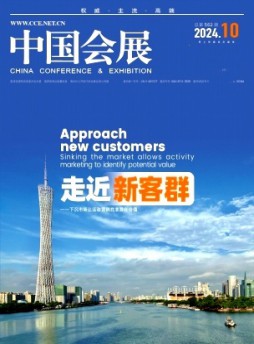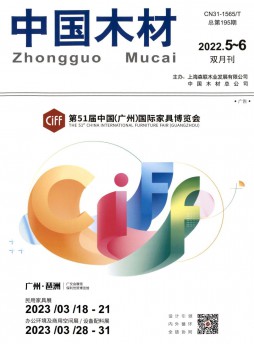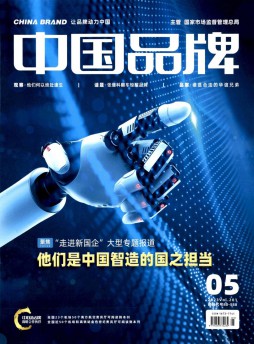中國意識形態現代思潮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意識形態現代思潮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概念的解析意識形態不僅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意識形態人類就無法維持自己的生存。我們既是各種意識形態的創造者,也是各種意識形態的創造物。作為一個在某種特定利益驅動下形成的包含著欲望、情感、表象的知識系統,意識形態是由理論到實踐、由觀念到行動的“翻譯器”和“催化劑”。
但我們總是把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混為一談。一種是“意識形態”(Ideologie),一種是“意識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來源、內涵、性質等方面存有本質區別,一味在二者之間進行“心臟搭橋手術”,不僅難免郢書燕說以訛傳訛,而且會過度強調意識形態的階級性,并極易造成亂貼“階級”標簽的粗暴學風。西方學者把意識形態作為考察社會的一個視角,在他們眼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與其說是兩種制度的對峙,不如說是兩大意識形態的對抗;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也是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與融合。20世紀6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成為社會科學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范疇。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的形成與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大陸)的出現及其政治意識的覺醒,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的解體,都是培育“意識形態”研究的適宜氣候與土壤。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識形態”一詞的濫用,不過同時又強化了它的語義威力。
“意識形態”是20世紀西方思想史上內容最復雜、意義最含混、性質最詭異、使用最頻繁的范疇之一,撒姆納曾經歸納、總結了10種意識形態定義,伊格爾頓歸納、總結了6種意識形態定義,其中都充滿了對立、矛盾和歧異。“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道德”、“倫理”等簡單概念不同,它是一個動態復合概念,表達的是一個動態復合過程,既包括歷史、社會和文化的深層互動關系,又包括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既包括主體的認知,又包括價值的評判;既是一個思維的過程,也是一個信仰的過程;既具有理論的性質,又具有實踐的品格。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無法用其他內涵清晰、外延明確的概念取而代之,因為意識形態絕非一個可有可無的“標記性術語”,而是一個無可替代的“實體性術語”。這個事實本身表明,“意識形態”這一術語的重要性是無可懷疑的,缺少了它,對學術研究來說,或者課題的性質有變,或者課題的范圍受限。在這種情況下,對“意識形態”的概念構成、諸種定義、歷史背景、哲學框架進行考察,對“意識形態”各種意義、各種用法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省思,對“意識形態”進行“知識考古”,無疑有益于澄清圍繞“意識形態”問題引發的各種混亂。意識形態是由“意識形態家”創造出來的,而“意識形態家”來自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不僅擁有“知識”,而且能在“知識”的基礎上創造、傳播、發展、闡釋某個特定的價值體系——他掌握的是一個知識系統,但這個知識系統包含著人類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認知、理解、評價等諸種心理因素。他們或者維持現狀,或者批判現實;或者著重建設“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傾盡全力建構新世界的藍圖。意識形態的分類有許多種,有人分為描述意義、貶義、褒義上的意識形態,有人分為主流意識形態和非主流意識形態,有人分為具體意識形態和整體意識形態,有人分為認識論意義、社會學意義、心理學意義、文化心理學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無論哪種分類方法,它們都只能把握問題的某個方面或某個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學術研究的第一步,而定義事物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實體性定義,它著重認定事物靜態的本質;一種是功能性定義,它著重描述事物動態的功用。不同的歷史時期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實體”:18世紀末以前的意識形態通常以宗教信仰(巫術、宗教、神話、傳說)為載體,19世紀初之后的意識形態通常以學術思想(思想、學說、理論、觀念)為載體。即是說,意識形態本質上是某種并不特定的事物(“體”)呈現出來的功能(“用”),能夠發揮意識形態這種“用”的“體”在不同的時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術、宗教、神話、傳說,在現代則是思想、學說、理論、觀念。任何思想、觀念、意識、理論、學說、見解……都既可以是純粹的學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識形態,只要它發揮了意識形態的功能。意識形態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區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反映現實,界定情境;第二,面對現狀,指引方向;第三,社會動員,付諸行動。意識形態,也只有意識形態才能發揮這樣的功能:認識世界的面目,闡明現狀的意義,指引前進的方向,提供解決危機的方案,強化民眾的團結,進行必要的社會動員。它既能綜合性地滿足人類認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類對世界的感知、態度與行動,并為人類生活提供適當和適度的行為模式。意識形態具有“反映現實,界定情境”、“面對現狀,指引方向”、“社會動員,付諸行動”的社會功能;同樣,舉凡一切觀念、信念、教條、理論、哲學、世界觀、價值、意見、神話、烏托邦,只要具有了這樣的功能,均可以稱之為意識形態。
2、歷史的探源意識形態理論得以產生的基本動機是去除意識上的蒙蔽——“去蔽”,并確立科學的觀念意識。雖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類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識形態的存在。從歷史發展看,“意識形態”概念史可以大致劃分為五個階段:特拉西階段、馬克思階段、曼海姆階段、列寧階段、西方馬克思主義階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創造了“意識形態”一詞并將其置于認識論的基礎之上,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識形態問題從認識論的基礎上置于歷史社會學的基礎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識形態問題從歷史社會學的基礎上置于知識社會學的基礎上,列寧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識形態的貶義色彩(意識形態成了階級斗爭和階級對抗的盛大典禮,成了每個階級用以武裝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在于他們從文化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角度開展了深入細致的“意識形態批判”。
“意識形態”是特拉西在18世紀末的首創,他用“意識形態”一詞命名一個新學科——觀念學。馬克思采用了“意識形態”這一概念分析19世紀德國哲學,使“意識形態”概念史發生了革命性轉折,因為馬克思內在地否定了意識形態在反映現實、揭示真理方面的“無能為力”或“倒行逆施”。在馬克思那里,意識形態就是“虛假意識”或“錯誤觀念”,它源于社會角色的階級立場:不同的人由于在經濟生產中所處的位置和利益關切點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觀念”——既包括真實觀念又包括虛假觀念,意識形態是特定的社會階級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而扭曲真實的現實關系的結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實寫照。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意識形態的,還有兩位歐洲早期的社會學家——默斯卡和帕萊托,他們研究意識形態問題的途徑與馬克思并不相同,卻得出了和馬克思極其相近的結論,并因此被人稱為馬克思的復仇女神。
曼海姆在兩種意識形式之間作出區分:一種是沒落階級的思想偏見——“意識形態”;一種是新興階級的思想觀念——“烏托邦”;同時他在兩種意識形態之間作出區分:一種是具體意識形態,一種是整體意識形態。具體意識形態是個別人的觀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飾個人的私利;整體意識形態是特定歷史時期或特定社會團體的意識形態,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觀,確定理論思維的總體構架和主體的認知態度。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整體意識形態,因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個時代或一定團體的思維結構、一個社會的主體的認識態度是怎樣形成的。曼海姆之后,蓋格爾把意識形態看成是以“理論”的形式掩飾著的原始情感、審美情趣和價值判斷,這樣,意識形態的精神分析便漸漸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對意識形態理論的透視,使我們發現了另一片生機勃勃的新天地。
從社會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意識形態,成為曼海姆之后意識形態研究的一個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識形態的虛假性并不表現在它是某個特定階級出于利益的考慮而對現實所作的扭曲,而是來自個體與團體無意識間的“自欺”,是人類為了撫慰心靈的傷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藥”。威廉·萊希在《法西斯主義的群體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義的起源、結構與功能等問題,對精神壓抑、意識形態、社會現實三者相互關系進行了透徹分析。弗洛姆認為意識形態是“純粹的幻想”,“意識形態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種幻想下面的真實狀態。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理論頗具特色。資本主義的長盛不衰,迫使盧卡契、科爾施、葛蘭西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現實,以便解開當代資本主義“垂而不死”、“崩而不潰”、“滅而不亡”的秘密。他們較為一致的看法是,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幾經波折大難不死,原因很簡單: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還沒有覺醒,因此他們無法肩負起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使命。只有重視意識形態問題,才能使無產階級形成自覺的階級意識,才能在革命斗爭中獲得勝利。但隨著20至30年代早期壟斷資本主義的鞏固,盧卡契和科爾施直接激發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努力宣告失敗,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界再次明白了“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樸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展開批判。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爾都塞、伊格爾頓和法蘭克福學派。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是具有獨特邏輯和獨特結構的表象(形象、神話、觀念或概念)體系,人們需要意識形態,是因為它能為人類體驗世界確立某種模式,沒有這種模式人類就失去了認識世界和體驗世界的可能性。阿爾都塞還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這與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密切相關。伊格爾頓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的傳統,以“意識形態”一詞對西方種種文化現象進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義的還是“法蘭克福學派”,他們認為只有進行“意識形態批判”,剔除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神秘因素,才能復活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馬爾庫塞認為,科技的進步和工業的發達不僅沒有使意識形態走向終結,反而使它以一種新穎獨特的方式得以強化,并以無形的力量支配著人們的一言一行。雖然法蘭克福學派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問題上,也是苦無良策。在這方面,哈貝馬斯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以“意識形態批判”著稱于世,因此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實質上是“意識形態批判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一致之處在于,他志在社會批判;與馬克思主義的歧異之處在于,他雖然注重理論的實踐性,但無力因而也無意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只是試圖建立一種超越性觀念,以消除他所謂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際”。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具有濃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視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在形式上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概念,但在內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處:經歷了啟蒙主義的精神洗禮之后,任何意識形態都可能以一定的學術思想為根基,任何學術思想都不能排除發揮意識形態功能的可能性。由學理到思想,由思想到價值,由價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動……便是學術思想發揮意識形態功用的步驟和過程。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識形態史,這與中國近現代特殊的社會現實有密切關系。近代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危機時代孕育危機哲學,近代以來的社會思潮都以“危機哲學”為核心和基石。中國危機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現實危機,亡種、亡國、亡教是中國人面臨的滅頂之虞;二是文化危機,情境上難以界定,精神上流離失所,乃其典型表現。中國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時代,解決危機是全體中國人的當務之急。這就不難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訂對于現代中國來說是多么急迫;也不難理解,為什么在現代中國一切學說、理論、思想、觀念都在發揮意識形態的功能,都高度意識形態化了。一切學說、理論、思想、觀念,只有為解決中國危機“獻計獻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無關乎解決中國危機的學說、理論、思想、觀念都將被棄之如敝屣。
一方面,傳統的經學、史學、理學逐漸式微,這不僅因為它們無法應付西學的挑戰,而且因為它們對處于危機中的中國局勢束手無策,在“反映現實,界定情境”、“面對現狀,指引方向”、“社會動員,付諸行動”方面完全無能為力。另一方面,我們從西方引進的現代學術思想無一能夠逃脫被意識形態化的命運——我們并沒有接收西方現代學術思想博大精深的學理,沒有顧及孕育、產生它們的具體文化環境,只是一味在“經世致用”的驅策下對其予以“生吞活剝”。我們特別注重每一種學術思想的社會含義及其解決具體問題的可能性,對其學理漠不關心。這種華而不實、逐流而不探源的學風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學術傳統,今天我們在面對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時,依然還在接受這種“傳統”的“賜福”。
科學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在中國所能發揮的功能還是相當有限的。科學主義或許可以在“反映現實,界定情境”方面發揮一定功能,但在“面對現狀,指引方向”、“社會動員,付諸行動”方面卻是無能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闡釋職能,卻無力解決任何現實問題。它可以解釋自然現實,甚至可以隱喻性地分析社會政治問題(討論民族救亡大業),解釋人的生理現實和精神現象,但究竟如何進行民族救亡,它既無切實可行的方案,也無實現這方案的綱領步驟,“社會動員,付諸行動”更是無從談起。作為科學主義之一種,進化論之所以成為一種持續發生影響的思想主流,就是因為它同時具有幾項功能:第一,解釋當時中國的險惡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應付三千年未見之變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為變法維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論根據。但它最終為馬克思主義所取代,其原因顯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危機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變中國近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無當。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可以彌補它的缺陷,它能告訴我們如何組成政黨,如何進行階級斗爭,如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如何打倒帝國主義,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為變法維新、民主革命的理論依據,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議題是以變應變,變到最后的結局將是如何?我們不知其詳。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的理論依據是十分完備的,它對人類社會的分期,對共產主義的構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國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進化論已經成為時代之必然。第四,馬克思主義能夠為中國及中國人尋找自身的意義,而進化論卻做不到。在進化論那里,人只是受難者和犧牲者;在馬克思主義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價值與光輝全都體現在解放全人類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實踐之中,因而能夠引發強烈的革命激情。第五,進化論一方面強調物競天擇是進化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又強調人力可恃,二者之間的矛盾一直沒有很好解決,這使中國人困惑;進化論中不可避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使得一向鐘情于傳統道德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感到矛盾: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愛。他們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學說,另一方面又時刻受到西方的威脅。中國接受進化論的歷史就一直是這樣矛盾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成功地克服了這樣的矛盾,在許多外力條件的作用下,贏得了中國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從這個角度說,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絕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滿足了中國的現實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國現實土壤之中。只要它還能多方面地滿足中國的現實需要,還能深深根植于中國現實的土壤之中,它就會永遠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論的批判不僅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識形態史,而且一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也是一部意識形態史——文學的意識形態化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所謂“文學的意識形態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會形勢之下,在某種特定利益的驅使之下,讓文學發揮著意識形態方面的功能。我們文學理論所強調的文學的“認識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實也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功用,因為強調文學的“認識作用”就是要求文學發揮“反映現實”、“界定情境”的作用,強調文學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學發揮“指引方向”、“社會認同”、“社會動員”、“情感溝通”的作用。我們有這樣的批評傳統,孔子所謂的“興觀群怨”,就把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極其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出來。從理論上講,文學能不能發揮意識形態的功用取決于許多因素。要而言之,這首先取決于文學自身是否具有發揮意識形態功能的潛質,其次取決于社會需要的內容與性質,一個危機重重、動蕩不安的社會不需要“楊柳岸曉風殘月”式的抒懷,一個平安富足、安樂祥和的社會也不需要“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式的悲壯。現在看來,無論就文學的性質而論,還是就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現實而言,文學的意識形態化都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一個沉痛的事實,也是一個無奈的感慨。
化約和確立假想敵是學術思想發揮意識形態作用的一個重要步驟。化約就是簡化,意識形態在反映現實、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極強的簡化、詮釋功能。中國近代啟蒙主義者失望于現實的政治專制,因而遷怒于政治專制的文化心理基礎,把這個文化心理基礎化約為中國傳統文化,把中國傳統文化化約為傳統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約為宋明理學,把宋明理學化約為幾個腐儒鄉愿式的標語口號(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簡化的典型表現。孔子的地位在現代史上的變化可以表明假想敵的確立對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性。維新初期孔子名聲還很不錯,后來譚嗣同認為兩千年來的封建專制是“秦政”,為之服務是“荀學”,可它們“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荀學”,把“荀學”當成封建舊禮教、舊思想、舊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掃地”的是康有為。維新失敗之后,變法維新的意識形態——康有為的“托古改制”論的合法性已經漸漸消失;袁世凱復辟打出了孔子的旗號,想以此為專制復辟尋求合法性,康有為甚至要“定孔教為國教”,這不僅使孔子之學進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發起知識分子批判儒學的政治與道德熱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個時代的標志和象征。
革命既是一個消解意識形態的過程,也是一個制造意識形態的過程。革命的對象之所以成了革命的對象,首先是因為它居于統治地位,是主流思想或主流意識形態。清末文學界的三大革命表明,隨著中國形勢的日益惡化,以“學”為核心的實用主義標準深入學者之心。一切古典的情趣,一切個人的愛好,一切心性的陶冶,因為無關乎時代變革之大局,漸漸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日益受到攻擊,人們視之為“聲色之累”,害怕的是“玩物喪志”。從形式上看,文學革命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語言革命”和“文體革命”。在“語言革命”方面,啟蒙主義者把文言文看成是封建統治階級推行愚民政策的工具,把白話文看作啟迪天下民智的工具;把文言文看成舊文化的寫照,把白話文看成新文化的代表。正是在這個符號化的過程中,學術問題被意識形態化了。在“文體革命”方面,小說、雜文社會地位的上升與八股文社會地位的下降相映成趣。八股文本來只是一種特別的文體,雖然免不了內容空泛、形式死板的缺點,但作為一種文體,自然也有其存在的權利。雖然對八股文的蔑視和批判與八股文的生死相始終,但只是到了“五四”時期,它才被賦予了強烈的“文化意味”——八股文不再是一種文體,也不再是統治階級取士的一種方式,而是一種文化傳統、一種文風,一種奴性的、說體面話的、無定見的生活方式。那是一個讓人氣惱而又不知該向誰撒氣的時代,是一個深受黑暗社會之苦而又不敢直言專制之害的時代,憤怒的知識分子們不知該遷怒于誰,便向著中國傳統文化開了火,把中國傳統文化當成了一切罪惡和黑暗的淵藪,進而又把文言文、八股文當成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和全盤人,并向其發難。“五四”新文學觀念的高度意識形態化不僅集中表現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中,而且更集中地表現在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中。
有人反對把一切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的意識形態化——反對把學術、文學、藝術……轉化成思想、潮流、精神、主義,反對把學術、文學、藝術……都當成政治宣傳、文化教育、開發民智的工具,反對一切學術、文學、藝術……的社會化、政治化、革命化、工具化。但在那個危機重重的時代,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新時期以來的種種“意識形態批判”和“意識形態建設”同樣無功而返,也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