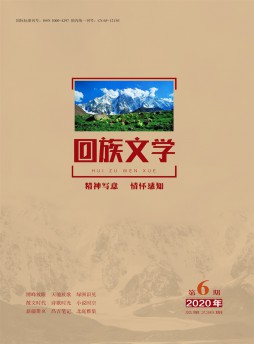文學形態與社會文化變遷的關系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形態與社會文化變遷的關系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國的“革命文學”是“五四”落潮之后精神上“左”傾的知識分子尋求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另一形態。柯仲平作為革命激流中的一名“人民詩人”,與同時代的革命作家們一樣,裹挾著個人意氣與宏大目標的話語構成了其革命文學的基本狀態。在當時,他的詩歌創作充滿著政治化和大眾化的革命主流特征,同時也汲取了民間文藝,尤其是歌謠和說唱文學,以一種民眾性的反叛和激進的姿態,表達著對所處時代的焦慮和體驗。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說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社會革命文化變遷深深地影響了這樣一種革命文學形態的生成。柯仲平初涉現代文化盡管是在邊遠的云南小鎮,但當時近代中國正處在個人主義、革命理念、浪漫主義相糅合滲透的社會時期。所以,柯仲平初入詩壇,懷抱的是那個時期特有的民眾情緒和飽滿的革命情懷。由此,便生成了帶有政治色彩的“人民性”革命詩歌,這樣的文學現象很典型地反映了近現代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特征。可以說,在文化變遷與文學形態的演變路上,詩人柯仲平與時代經歷了一個感同深受的過程。
20年代初期,柯仲平以一個青年學生的身份步入文壇,恰逢“五四”運動時期。這場運動雖說是一場高級知識分子自上而下的啟蒙運動,但是隨之而來的群眾的參與和“群眾運動”的興起,卻有效地促成了知識分子個體意識和個性解放得以表現的形式。柯仲平向來都是熱情傾注的,在老家廣南的成長期間,他就擁有了最初的敏銳感受力,從年少奔赴昆明讀書開始,在他身上沒有出現過一絲一毫回避政治革命的癥結。第一次登臺演講時,他表現出了浪漫主義的天性,又因為對其他學科的排斥,學習的個性極大地造成了柯仲平與文學藝術不解的關系。所以,他到了北京后,決心走詩歌的道路絕非偶然。但當他全身心投入到藝術創作中的時候,其實對藝術運動沒有保持足夠的關注,而是更多地接受了社會革命運動。他在1927年的講演稿《革命與藝術》中有過這樣的陳述:“創作是自然地為時代所限制,也就是時代要求藝術必為時代表現的意思。”①
“藝術能使革命力向更深更偉大的去處猛進。”②“革命時代的藝術就好比狂風暴雨熱戀著海洋。”③“有誰不承認有宣傳的藝術也可以,但他無權利阻止用藝術宣傳革命。”④這些文字說明了柯仲平自覺地接受了共產主義的藝術觀,當然這與他一開始就接觸了馬列主義分不開。著名劇作家田漢同時期有一個論斷:“相信每一個作家只應該作詩不應該作宣傳。”柯仲平的表現與此觀點剛好相反。柯仲平不僅積極宣傳他對新興的共產黨的認知,還以現實社會秩序本能的反抗者的身份,全身心地關心著政治,正義感逐漸進入到他的藝術活動和創作過程,并最終凝聚于成果中。因此,他從創造社轉向“左聯”,不斷把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帶到創作中,這樣的文學選擇目標性很明晰,不管詩人在主觀上是否明晰地意識到,都難于避開這種目標趨向,對于柯仲平這樣沉浸在革命文學進步理念的知識分子,投入革命創作不僅是外部的時勢釋然,更多的還是詩人主體內部深層的原因。就創造個性而言,柯仲平屬于偏向主觀抒情的浪漫主義詩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對于壯烈的場面、人生無出路的苦悶、社會命運的焦慮的表述、詩歌形象的設置,都可以看做是詩人自己的生命體驗和對現存秩序的反抗。尤其是在“紅色的三十年代”,無論是中國、遠東、前蘇聯的文化界還是文藝界,到處都充溢著浪漫的革命的激情。這種特定的歷史情勢,對敏感的柯仲平來說不能不是個刺激。而這個刺激又恰好應和了他自身對藝術追求的轉變。
一方面,譴責國民黨背棄底層勞苦大眾;另一方面,視“求真”為其藝術的首要目標。他對于藝術的理解定格為作品應該代表民眾的根本利益,并真正為人民大眾代言。在柯仲平看來,這是檢驗文學“真”的唯一標準。柯仲平選擇了文藝,走宣傳化道路,毫無疑問,這是符合他的思想個性與藝術特質的,也是符合當時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后來,當柯仲平經歷了煉獄之災,且得到了黨組織的營救,這個非同一般的歷程相當于完成了他的藝術的一次政治化洗禮。他覺得自己已經完全成為革命的一分子,在精神上也有了依附,從此以后,他毫不猶豫地將流浪者的憤懣自然地轉化成了激越的時代使命感。同時,為了汲取理論的營養,他大量閱讀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并用這些理論思考詩歌與革命斗爭的聯系。又因為受到其中的教條主義和政治實用主義的影響,柯仲平越來越看到了藝術與階級的相關因素,也更加看重詩歌藝術的煽動性與宣傳性。所以在詩歌創作時,他對革命的理性理解逐漸蓋過了個性化的抒情。閱讀柯仲平這個時期的詩,結合其創作的歷史條件和創作動機,不難讀出其詩歌在配合時勢宣傳階級斗爭意識和民族自由獨立精神的認同關系。
40年代,中國文學處在戰火的洗禮之中。樹立良好的文學政治形象成為當時不成文的“文藝政策”,作家向政治趨附,作品向政治化轉移,是當時一種普遍的自覺行為。奔赴延安的柯仲平,積極投入到解放區萬事待舉的氛圍中,而且,比起當時國民黨虛弱殘忍的文藝政策,解放區文化顯得更有自信和更有遠慮,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被賦予了更強烈的革命政治色彩也是必然了。此時的柯仲平詩歌創作,因為對政治理解的純粹性得到了的肯定,在“神人共憤”的時代里,柯仲平很難平靜地進行自主創作,于是自覺選擇了積極投身革命和主動為政治服務的功利寫作道路。與當時大多數“以文抗戰”“以筆從戎”的作家的創作觀一樣,柯仲平一定程度地避開了自由作家們的被“誤讀”的煩惱,但也迫使他的詩作走向了單調和缺乏創造性的“群眾文化”道路,同時,詩歌的藝術生命也不得不逐漸游離于世界文藝思潮之外。口語化、激情化、大眾化成為當時革命詩歌共同性和連續性的追求,文學在這個時候需要完成的任務就是在文藝領域里闡釋與貫徹的文藝思想,這樣的話語選擇和文學形態的生成,不得不說是詩人對現實政治感同深受的結果。
到了50年代,隨著新中國革命的勝利,社會的文化特征從表面看來進入了一種轉型,很多作家認為文學的革命話語形態似乎應該做一些新的調整了。所以,柯仲平這一時期在他的詩歌創作上進行一些突破,如1954年寫的《劉志丹》一詩,他試圖在客觀描述上做一些嘗試,但即便是在對革命的虔誠膜拜范圍里進行的創新,依然使柯仲平遭遇了一次劫難。這個事件說明了“組織化”文藝體制在更加緊迫地制約著文藝者們的創作。在建國17年間,新中國建設作為一場革命直接地具體地規定著文學藝術的實踐與創作,這種導向不能說能夠真正與藝術創作規律內在相洽,但意味著按照先前的思維方式寫出來的作品肯定也不總是成功的,或者說被組織認可的。他對劉志丹部隊的刻畫和對所掌握資料的使用上的不解和困惑正好說明了在正統文化中異己的個人的自發性抒寫,則會顯得危險,稍不小心,就會滑向被改造的界定之中。事實上,這是當時的普遍性的評價方法,從政治文化心理來說,創作和批評的動力和源泉不是順應自己的信仰,而更多的是來自外部的教誨。在這個意義上,前文所列舉的柯仲平的自我批判和創作自覺以及他對思想的實踐,從理論層面和政治情感的層面仍然無法達到真正的精神突破,相反,他會將這一切視為實現那個政治信仰所要經歷的歷史過程,這必然導致他從理智上、情感上努力去接受它。也就是說哪怕經歷了改造與被改造,對于柯仲平來說,即便是在個別的事件上有異議,但創作的任務與事實毫無矛盾。這樣的選擇,是符合他的思想水平和歷史真相的,遵從革命政治對于柯仲平來講從生存到心理都是一種不斷形成的精神范式,甚至是一種生存的寄托。
聯系中國20世紀的現代文化變遷,革命文學所表現出的特征之一在于:比起以往的任何時期,此時的知識分子既要為引領人民的進步思想擔當鼓動,宣傳的作用,又不得不進行某種選擇,畢竟這是一種文學生存的尺度。從文學創作實踐上說,每一個敢于對整個人類前途思考的作家,在參與這一革命話語的形成過程中,其自身的身份認同便不得不陷入危機,即他們將處于政治權利、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及其文學規范的復雜糾葛之中,最終邁不出革命文化時代給他們帶來的矛盾宿命。柯仲平的感覺是敏銳的,情感是豐富的,但是他對于人生缺少觀察。社會絕不是單純的,人性也是復雜的,如果不能設身處地去體驗觀察,怎么能尋求到真實的理解和認知呢?所以他的詩歌根本來不及進行從容構思和精選意境,要說藝術技巧,也是先有了判斷定勢再去抒情,使得這些詩作往往卡在一個感染與被感染的磨合點上無法自拔。而且詩中的政治理念也過于直露,有些簡直就沒有詩意。因為宣傳的需要,政治理念便顯得膚淺,缺乏詩人主體的再透視和詩人特有的獨特意蘊,這些急就章,就只能達到與時代同呼吸,與時代共命運的意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具有轟動效應,但時過境遷,當那種鋪天蓋地的政治環境不復存在的時候,這些即興之作便隱退了,這正是他們這一批現當代作家面對歷史的有情和無情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