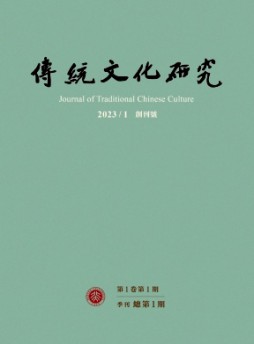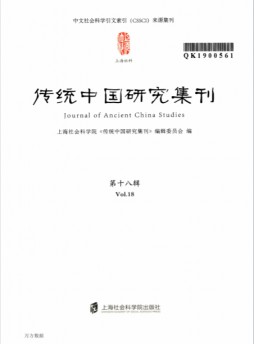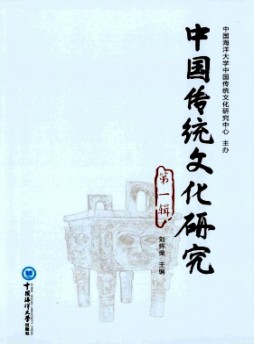傳統文學透視的宏觀批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傳統文學透視的宏觀批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本文作者:石麟單位:湖北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
一中國傳統文學,如果從文化層面進行最粗線條的劃分,似可分為“廟堂文學”、“山林文學”、“市井文學”三大部分。所謂廟堂文學,實際上也就是正統文學,亦即封建社會的主流文學;所謂山林文學,也就是隱逸文學,基本上處于非主流的地位;所謂市井文學,當然指的是大眾文學。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廟堂文學是以統治階級思想為核心的群體意識的反映,山林文學則更多地反映了作家的個體意識,而市井文學則是另一種群體意識)))傳統文化在廣大民眾中積淀的結果。
中國傳統文學雖然可以大體作以上三大部分的區分,但三者之間的關系卻并非全然的涇渭分明,而是相互間既有交叉,又有融合的。同樣,對于某一位作家而言,他也不可能一輩子只從事上述某一部分的文學創作。有時候他會從事廟堂文學的寫作,有時候他又會進行山林文學的構造,有時候或許也會染指市井文學。有的作家甚至會同時進行多種層面的文學創作。從文體的角度看問題,則各種文體都可作為上述三大層面之文學創作的載體,但也有一定的側重和偏向。如辭賦,寫廟堂的作品最多,寫山林者次之,寫市井者極少;如詩歌,則廟堂文學、山林文學并重,只有民歌或擬民歌才寫市井;至若詞曲,大致上三者平分秋色;戲劇、小說創作,則市井第一、山林第二、廟堂第三了。
一個饒有意味的事實是,無論是廟堂文學、山林文學抑或是市井文學,都共同具有“輝煌”、“墮落”、“反思”三種創作狀態,并且這三種狀態有時相反相成,有時相輔相成,有時竟是一種“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奇特態勢。
二廟堂文學的輝煌是持久的,然而,這種持久的輝煌卻建立在更為持久的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礎之上。進而言之,支撐輝煌的廟堂文學構架就是諸如忠、孝、仁、義、剛、正、廉、明等傳統倫理道德的精粹。忠君愛國、孝養雙親、關心民瘼、信義待人、不屈不撓、正直無私、廉潔自律、明辨是非,以及要求建功立業、施展懷抱的人生追求,,這一切,難道不正代表著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崇高精神嗎?將這一切用詩詞歌賦等各種形式表現出來,難道不是一種民族精神的輝煌再現嗎?《詩經》的周人史詩,屈原的《離騷》《九章》,孔夫子的《論語》,太史公的《史記》,那建安風骨,那正始哀音,左思的《詠史》詩,劉琨的《扶風歌》,陶淵明的“金剛怒目”,鮑明遠的《擬行路難》,李、杜、高、岑的吟詠,韓、柳、歐、蘇的文章,辛稼軒的氣吞萬里,陸放翁的鐵馬秋風,還有岳武穆、文文山、元好問、張養浩、于少保、陳子龍,,這些作家,無一不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筆下的作品,大多是時代的最強音。毫無疑問,正是他們用手中的筆、眼中的淚、心中的血,創造了廟堂文學的輝煌。
讀諸葛亮的《出師表》而不下淚者不是忠臣,讀李密的《陳情表》而不下淚者不是孝子,讀夏完淳的《獄中上母書》而不下淚者,此人大概既不是忠臣又不是孝子。這是一種情結、一種積淀,一種超越時空的民族精神、人文精神。這里有憂國憂民的情懷,有思鄉思親的情緒,有正大光明的氣質,有義無返顧的氣概,,而這一切,又正是輝煌的廟堂文學之所以輝煌的底蘊。在封建社會的中國,這種精神深深植根于每一個正常的人、尤其是人格健全的知識分子的心田。千千萬萬的正常的封建時代的中國人,從小所接受的就是這種傳統的教育,有生以來就生活在這種傳統文化的濃厚的氛圍之中。他們將這種正常的思想通過正常的方式表現出來,所締造的難道不恰恰是廟堂文學的輝煌嗎?
然而,當廟堂文學無比輝煌的同時,它的墮落也已悄然開始,甚至可以說,這墮落的根子就埋藏在輝煌的泥土之中。而這墮落是沿著兩道軌跡前行的,一是歌功頌德,二是矯飾人情。
歌功頌德本來也沒什么不好,但是,由對國家、民族、日月山河、英雄人物的歌頌轉而成為對君王、上司、達官貴人的歌功頌德,卻無疑是廟堂文學最大的墮落。在這里,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去一一列舉那些枯燥無味的“作品”,只看一點兒最極端的例子就足夠了。明代洪武年間的文人吳伯宗這樣寫道:“唐堯虞舜今皇是”,“萬歲聲呼山動搖”。“江海小臣無以報,空將詩句美成康”。如此“詩句”,難道還不能體現廟堂文學的極端墮落嗎?
除了對君王們進行直接歌頌而外,廟堂文學之歌功頌德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就是將傳統封建道德推向極致并加以大力的歌頌和鼓吹。忠君愛國在這里變成了對君王的愚忠,孝養雙親在這里變成了割股療親一類愚昧而又殘忍的行為,至于夫妻間的感情,則更是演變成為夫死守節乃至以死殉夫的婦女單方面必須履行的極端不人道的義務。總之,一切正常的人際關系都被冰涼、殘酷而又極端偏頗的忠孝節義的道德信條所代替。我們且不說那多如牛毛的“家訓”、“律條”、“烈女傳”、“忠義傳”等等,因為那些東西根本就不是文學作品,不在本文所論之列。我們也不說那些流傳并不廣泛的理學家們表彰忠孝節烈的詩歌散文作品,因為它們在廣大讀者心目中、在古代文學史上并未造成多大的影響。我們只對宋元以降同時興起的理學思想和戲劇藝術相結合的產物)))表現封建倫理道德的戲曲劇本略作分析,便可發現情況有多么嚴重。自元末高則誠在《琵琶記》中提出“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的標準之后,明代文人利用戲曲作品來宣揚教化、訓誡人心之風便愈演愈烈。有的要求樂戶女兒要“立心貞,出言準,守清名,志堅穩”,“到身后標題個烈女魂。”(朱有火敦《香囊怨》)有的高標作戲曲要“備他時世曲,寓我圣賢言”,“若于倫理無關緊,縱是新奇不足傳。”(丘浚《五倫全備記》)這便是戲曲作品中為數不多的“廟堂”之作,而且是走向墮落的廟堂之作。
輝煌的廟堂之作所表現的往往是人們的真情實感,而墮落的廟堂之作則往往以矯情代替真情。這樣,就造成了“人品”與“文品”的極不協調,乃至極大的矛盾。因為屈原、杜甫忠君愛民的詩篇流傳千古,因而人人都想寫一點《離騷》《北征》那樣的作品,于是乎,“今之學子美者,處富貴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無病曰病。”(謝榛《詩家直說》)這種矯情的表演便出現在既缺乏生活感受又要顯得大義凜然的無聊文人們之間。甚至有些品行極其低劣的人,也在其詩文作品中擺出一副關心國家、關心人民的悲天憫人的架勢。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先讀兩篇作品:
“泥污后土逾月余,四月雨至五月初。七日七夜復不止,錢王舊城市無米。城中之民不饑死,亦恐城外盜賊起。東鄰高樓吹玉笙,前呵大馬方橫行。委巷比門絕朝飯,酒壚日征七百萬。(方回《苦雨行》)“農田插秧秧綠時,稻中有稗農未知。稻苗欲秀稗先出,拔稗飼牛唯恐遲。今年浙西田沒水,卻向浙東糴稗子。一斗稗子價幾何?已直去年三斗米。天災使然贗勝真,焉得世間無稗人!”(方回《種稗嘆》)如果我們不知道宋末元初的方回是何許人,大概會產生一種錯覺:這大概是一位杜甫的繼承者吧。那么,就讓我們來看看方回究竟何許人也。據《癸辛雜識別集上》載:“方回,字萬里,,其鄉處專以騙脅為事,鄉曲無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齒。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敢歸。老而益貪淫,凡遇妓則跪之,略無羞恥之心。,,知嚴州,未幾,北軍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為必踐初言死矣。遍尋訪之不獲,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韃帽氈裘,跨馬而還,有自得之色。郡人無不唾之。遂得總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皆入私囊。”就是這樣一個大節有虧小節損的“稗人”,居然寫出了那樣一些關心民瘼、憂愁亂世的詩篇,居然在自己的詩篇中大聲疾呼“焉得世間無稗人”。這種貌似奇特的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絕不止一個方回,如潘岳、阮大鋮等等,均乃如此。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這些作家自覺不自覺地以矯情的方式在掩蓋著自己的劣行。毫無疑問,這也是廟堂文學的一種墮落。
當廟堂文學逐步墮落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御用工具或無聊文人的矯情載體之后,自然有人會對這一切進行反思,并且,一部文學史也正是在不斷的反思、不斷的反撥中才得以前進的,廟堂文學當然也不例外。廟堂文學的反思的立足點主要體現在對傳統道德、傳統學術的懷疑與否定方面。泰州學派對宋明理學提出了懷疑,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之學又對明人的游談無根進行了批判。至于忠孝節義等傳統道德,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懷疑和否定。黃宗羲在《原君》中居然敢說出“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話,真乃石破天驚。被封建士大夫奉為人生信條的“文死諫、武死戰”,卻被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賈寶玉之口說成是“胡鬧”,真是對傳統道德的大不敬。如此等等的悖逆言論,在明末清初以降的文人那兒可謂屢見不鮮。正是在這種懷疑傳統、否定傳統的思潮的影響下,才會出現吳敬梓、曹雪芹、龔自珍、魏源、黃遵憲、粱啟超、譚嗣同、章太炎、鄒容、秋瑾這樣一些反思型的作家以及他們所留下的極具啟示力的優秀作品。從而使廟堂文學不僅沒有走向徹底的敗落,而且展示出黑暗王國的一線新的曙光。
三山林文學也有它的輝煌,它是長居于或暫居于草野的文人的心靈的歌。許多古籍中所記載的隱士是山林文學的文化原型,老莊哲學是山林文學的理論基礎,逃避現實而又未能真正忘情于現實是山林文學作家的心理矛盾,貶謫罷官是山林文學締造者們的經常性待遇和創作誘因,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山林文學創作主體的心靈慰藉,而美麗的大自然則是停泊這些痛苦靈魂的寧靜港灣。
在先秦兩漢的文學作品中,我們雖然也能找到山林文學的片斷,但真正有代表性的山林文學作品卻誕生于兩晉以降。陶淵明、謝靈運、謝玄暉、王績、王維、孟浩然、劉禹錫、柳宗元、林逋、蘇軾、朱敦儒、辛棄疾、楊萬里、范成大、馬致遠、張養浩、貫云石、劉因、王冕、唐寅、王磐等,他們或以寧靜清虛的心態來對待窮愁潦倒的生活,或以深入細致的描繪來展現如詩如畫的美景,或在對山山水水的描摹中顯示出無比深邃的哲學思考,或在對花花草草的勾畫中體現了無比崇高的人格追求。這里有懷才不遇的牢騷,也有參透萬物的曠達;這里有農家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有洞天福地的朦朧憧憬。這里還有貶謫情結、遺民情結、憫農情結、游子情結,,所有這一些,他們用詩、用詞、用曲、用賦、用長篇、用小品,總之是用一切文學樣式來表現。正是這一切,構成了山林文學的輝煌,哪怕是潛藏在深山僻野間或士人心靈深處的輝煌。
山林文學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充分體現作家的個體感情和創作個性。表面上看,這些作品創作于山林之間,并以山林作為描寫對象,而實際上,作品卻融化在作者心中,甚至可以說寫的就是作家自己。正因如此,他們無須戴上假面具,也無須刻意追求什么社會效果、藝術效果等等“身外之物”,而只是原原本本、真真切切地寫來。這里有陶淵明的《歸園田居》,也有大小謝的山水吟詠。這里還有許許多多的或描摩山水田園或抒發人生感受的的賦作辭章,如《江賦》《游天臺山賦》《閑居賦》《恨賦》《別賦》《桃花源記》《北山移文》。這里還有那人生的哲理探尋和深沉嘆息,如《春江花月夜》如《代悲白頭翁》。在這里,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充滿禪趣,意境空靈;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則充滿生機,淳樸自然;就連豪邁的李白和沉郁的杜甫也偶爾到山林中“反串”。在這里,還有韋應物、劉長卿的山水之作,還有劉禹錫、柳宗元的貶謫文學,還有自《水經注》發脈、至柳宗元《永州八記》而發揚光大、直至明清兩代而盛傳不衰的山水游記作品,還有宋詞、元曲、明清詩歌中歌頌山林抒發感情的成千上萬的心靈的樂章。對于山林文學的作家們而言,這一切都是他們心靈的自白,也是他們與“自我”的對話。充分真實化、充分個性化,同時,也充分孤獨化、充分理想化。正是這一切,造就了山林文學的無比輝煌,哪怕是潛藏在心扉胸臆中的輝煌。
是的,充分的孤獨化和充分的理想化造就了山林文學的輝煌。但是,過分的孤獨化和過分的理想化又造成了山林文學的墮落。郊之“寒”、島之“瘦”、姚合之“峭冷”,已經開始了由幽靜的山林向著冷寂的深淵的下滑,而滑到“幽深孤峭”的鐘、譚那兒,則已到了“獨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鐘惺《詩歸序》)、“必孤行于古今之間”(譚元春《詩歸序》)的地步。這樣的詩,實在不知道還要寫它做什么!過分的孤獨化,所磨滅的不僅是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的靈性,更是人的生活熱情、百靈之長的靈性。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特點就是群體性與個體性相結合,文學的根本任務也就是要恰當而真切地表現或反映這種結合,只是不同的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各有其偏重而已。過分地強調群體性,是造成廟堂文學墮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過分地強調個體性,則容易造成山林文學的墮落。
超越可能性的理想其實就是幻想,是麻痹自己而又麻痹他人的幻想。在古老的中國,幻想往往又與宗教、迷信、崇拜緊密相連。而這些幻想反映在山林文學的作品之中,就是那些消極避世乃至追求長生、尋求解脫的游仙詩、玄言詩、禪悅詩、冥悟詩,更不用說還有那些代佛、道立言的宗教之作、迷信之作如“傳燈錄”、“證道書”一類的東西了。游仙詩的淵源雖可追尋到《離騷》,但那是一種積極的“游仙”,或者說,是借游仙表現作者心靈的遠游,屈原可從來沒有離開、也沒有想到要真正離開塵寰世界。魏晉以降的游仙詩的作者們,才真正幻想著高蹈輕舉、一步登天。稍后,玄言詩也不甘示弱,從老莊那兒借來了“物我同游”,從釋子那兒借來了“虛心靜照”,更加上士人們既有閑又有錢、既離塵且脫俗,于是淡乎寡味而又清高孤傲地“玄乎”了一個時代。用幻想代替現實、以玄言描述世界、這恐怕已接近山林文學的盡頭。但是,比起那些用長篇敘事的方式來演述宗教、迷信的戲曲作品而言,游仙詩、玄言詩之類,又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了。號稱“萬花叢中馬神仙”馬致遠,給我們留下的七個劇本中竟有四個是“神仙道化”劇。而元代的神仙道化劇竟是一大科,并影響到明清兩代。就連湯顯祖這樣杰出的戲曲家,在他的“臨川四夢”中竟也有一夢“佛”、一夢“道”,夢到了那遠離塵世的虛無縹緲的世界。
在山林文學經歷著朝過分孤獨化和過分理想化兩大方向墮落的時候,也有一些作家在這一最能表現文人自身情緒的園圃中苦思、沉吟。并且,在新的起點上進行了新的嘗試。在何景明“領會神情”認識的影響之下,在謝榛“自然妙者為上”理論的影響之下,在李贄“童心說”的影響之下,由晚明而及清代,形成了“性靈”一派。從“公安派”的“獨抒性靈”到袁枚的“性靈說”,不僅使許多作家的文學觀念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而且還直接影響了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山林文學的創作。晚明的小品文,堪稱中國文學史上最具真性情同時也最富于創作個性的一批作品。晚明的游記作品,亦堪稱純情的作家與純潔的大自然緊緊擁抱的結果。這里也有逍遙、也有放任、也有清高脫俗、也有自命不凡,但無論作家們心靈的航船向何方漂移,總是沒有脫離塵寰世界。而且,在許多晚明小品文、游記以及此后的詩歌作品中,還有不少在抒發性靈的同時,含有深邃的人生哲理,那就更是山林文學中的珍品了。
山林文學,是封建時代文人心靈的驛站,但這驛站絕非建立在九霄云外,而仍然是悄然屹立在人生的旅途之中。
四市井文學的輝煌源自市井,因為它是“市井”文學。從《詩經》到漢樂府,再到南北朝樂府、到唐代的聲詩和詞,其中有不少市井之作。但市井文學的鴻篇巨制卻毫無疑問地產生于宋代。關于宋代市井文學發達的原因,過去有著多方面的探討,如城市經濟繁榮、市民階層壯大等等。但我認為有一個重要因素不可忽視,那就是宋代的城市格局的改觀。相對于唐代比較封閉的坊市分離制的城市格局而言,宋代那種開放性的流線型的城市建筑格局應該對市井文學的繁榮有著不可低估的推動作用。更兼之與唐代實行宵禁的制度相比,宋代不僅不搞什么宵禁,甚至是鼓勵人們夜間消費,瓦舍勾欄動輒容納數以萬計的顧客,有的茶肆酒樓則幾乎通宵達旦地服務。在如此肥沃的市井文化的上壤之中,市井文學的花朵為什么不能開得絢爛多彩呢?
在宋元話本、元人雜劇、明清傳奇、明清章回小說、擬話本小說以及明清民歌時調中蘊涵著大量的市井文學作品。正是這些作品,創造了市井文學的輝煌。而市井文學輝煌的最主要標志就是在這些作品中體現了與傳統思想大異其趣的市民意識。宋元話本中寫得最多也最精彩的是男女愛情故事,而且是市井男人與市井鬼女的愛情,《碾玉觀音》如此,《志誠張主管》如此,《鬧繁樓多情周勝仙》亦乃如此。因為現實世界中的戀愛不自由,因此就出現了如此多的市井中的人鬼之戀,市民們就是這樣想問題的。元人雜劇中亦多愛情故事,表面上看,多半寫的是公子小姐之間的愛情,但實際上反映的仍然是市民趣味。《西廂記》中崔鶯鶯之“驚夢”,《墻頭馬上》中李千金之私奔,《倩女離魂》中張倩女之離魂,都是在千金小姐的面貌掩蓋之下的市井婦女行為的真實寫照。
愛情,在封建時代,是統治者不準談、文人偷偷談、而只有市井小民才敢于公開談的一個話題,故而才在市井文學中有如此多的愛情之作。更為重要的是,在對待愛情、婚姻、婦女的態度上,市井小民們自有與封建士大夫們截然不同的觀點。“三言”中有兩個名妓)))杜十娘和莘瑤琴都希望從良,都在選擇對象。其結果,杜十娘選擇了貴族公子李甲,因而怒沉江底、月缺花飛;莘瑤琴則選擇了市井小民秦重,因而夫妻和合、花好月圓。這兩篇作品似乎在告訴讀者,真情不在貴族公子們那兒,真情在市井之間,在市井小民之中。這里所表現的難道不正是一種市民趣味嗎?難道不是市井小民們希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能夠被人們所了解、所宣揚、所歌頌的一種歷史性的要求嗎?更有甚者,市民階層不僅希望在市井文學作品中表現自己的生活情趣,而且更渴望在這些作品中體現他們對愛情生活、婚姻生活、婦女問題的新的道德評判。《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的蔣興哥就是這種道德評判的一個形象載體。當蔣興哥得知妻子王三巧有了外遇以后,一是自己承擔了部分責任:“只為我貪著蠅頭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丑來。”二是委婉而體面地休妻:“本婦多有過失,正合七出之條,因念夫妻感情,不忍明言,情愿退還本宗,聽憑改嫁。”三是被休之妻再嫁時居然送去禮物:“興哥顧了人夫,將樓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連匙鑰送到吳知縣船上,交割與三巧兒,當個陪嫁。”這些行為,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思想基點之上,那就是把女人、哪怕是犯有過失的女人、哪怕是犯了在封建時代男人尤其不可原諒的過失的女人當作“人”來看待。這其實是一種人道情懷,一種在達官貴人不曾有、在封建衛道士們不曾有的人道情懷。尊重人性、尊重生活、尊重感情、尊重生命,這些市井小民們新型的倫理道德觀念在明清兩代的市井文學作品中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小說如此、戲曲如此,民歌時調集《掛枝兒》《山歌》《夾竹桃》《霓裳續譜》《白雪遺音》中成百上千的作品,更是如此。
市井文學輝煌的標志絕不僅僅是反映愛情生活的作品,那市井百態、那江湖風波、那每天開門離不了的七件事、那形形色色的三百六十行,,其間酸、甜、苦、辣,澀,應有盡有。要想知道這市井生活的五味瓶究竟有多少內容,你可以去讀柳耆卿的詞,去讀關漢卿的曲,去讀《水滸傳》,去讀《金瓶梅》,去讀“三言”“二拍”,去讀元明清的雜劇、傳奇,去讀陳鐸的《滑稽馀韻》,去讀那些寶卷、彈詞、子弟書。那里面會讓你明白,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日常生活,什么叫市井中人的日常生活。市井文學的墮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宣揚封建迷信,二是鼓吹封建道德,三是欣賞畸形性欲。明清章回小說和擬話本小說中都有大量宣揚宗教迷信的低劣之作,長篇的如《掃魅敦倫東度記》《陰陽斗異說傳奇》《天女散花》等,短篇的則有《雨花香》《通天臺》等集子中的許多作品。所有這些,都體現著市井文學的末流向著世俗宗教迷信的墮落。鼓吹封建倫理道德的作品在明清通俗小說尤其是擬話本小說中大量存在,只要翻開《石點頭》《型世言》《西湖二集》《八洞天》《娛目醒心編》等擬話本集,你就會發現,在這里,愚蠢的、反科學的、令人觸目驚心的或啼笑皆非的,總之是各種各樣的忠、孝、節、烈、仁、義、友、信應有盡有,而且毫不含糊。至于色欲描寫,更是某些市井文學作家的拿手好戲。在某些戲曲作品、甚至是比較優秀的戲曲作品中已開始出現過分的色情惡謔,到了小說創作、尤其是晚明小說創作中,這種不良傾向愈演愈烈,乃至不可收拾。《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有一定篇幅的色情描寫是人所共知的,而情況更為嚴重的作品則有:章回小說中的《浪史》《肉蒲團》《繡榻野史》《濃情快史》《昭陽趣史》《株林野史》《杏花天》等等,擬話本小說中的《宜春香質》《弁而釵》《一片情》《歡喜冤家》等等、這些作品、或寫女色、或寫男風,真是人欲橫流,體現了人的原始動物本能的一面。
市井文學的反思并不是由市井小民來完成的,而是經過了市并小民的思想積累之后再由那些窮愁潦倒而又富有真知灼見的文人來完成的。這些人在物質生活方面往往極端貧窮,而精神領域卻極其富有。如董說、如李玉、如孔尚任、如吳敬梓、如曹雪芹、如李汝珍,,直到梁啟超。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世界觀也大不一樣,但卻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都對社會、人生、歷史、現實有著深刻的思考,并且利用最為通俗的文學樣式表現出來。“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綠玉殿如今變做-眠仙閣.哩!,,只是我想將起來,前代做天子的也多,做風流天子的也不少。到如今,宮殿去了,美人去了,皇帝去了!,,這等看將起來,天子庶人同歸無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塵。”這就是一個生活在社會下層的知識分子在國之將亡的時候,發自內心深處的一種預感和悲哀,寫到作品之中,就是董說的《西游補》。褒揚忠臣、反抗權閹,最有力量的是誰?是市井小民。市井小民所發動的蘇州民變,代表了社會前進的動力。將這種思考搬上戲曲舞臺,就是李玉等蘇州派作家創作的時事劇《清忠譜》。思考,來自豐富而痛苦的現實生活;表現,卻在那通俗而動人的市井文學之中。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是孔尚任的《桃花扇》,高呼“一代文人有厄”而批判八股取士制度的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創造了一個“女兒國”,在那里寄托了作者懷金悼玉的歷史悲哀;李汝珍也勾畫了一個“女兒國”,在那里卻寄托了作者男女平等的朦朧理想。至若梁啟超等人,則干脆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公開提出要依靠市井文學來改造社會、移風易俗、改變人們的世界觀。市并文學發展到這個時候,才真正顯示了它巨大的威力和無盡的潛力。因為它所反映的已不僅僅是過去、現在,而且指向了恒遠的未來。
五廟堂文學、山林文學、市井文學的劃分不過是我們為論述問題的方便而采取的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嚴格而言,任何類別的區分都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或者說,有許多文學作品并不能僅僅屬于哪一類,而任何一位作家也不大可能一輩子只寫某一類作品。陶淵明不僅有“悠然望南山”,也有“刑天舞干戚”。白居易不僅有“新樂府”的創作,也有“閑適詩”的撰寫。蘇東坡則處廟堂而憂其民,處山林而思其君。關漢卿的戲劇常以市井文學的方式反映重大的歷史問題,社會問題,而他的散曲則更多一些山林文學與市井文學相結合的趣味。蒲松齡則既寫堂堂正正的廟堂文章,又寫雅俗共賞的《聊齋志異》,還寫了充滿世俗意味的俚曲小戲。至若《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僉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這些通俗小說中的偉大作品,則更是市并文學、山林文學、廟堂文學諸多因素的結合,只不過各有其側重點而已。
對傳統文學進行文化批評,是一件饒有意味的事,也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原本就深深扎根于該民族傳統文化的泥土之中,而文學研究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要研究其民族性。不注目于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學的影響而孤立地研究傳統文學,其結果,只能是喪失其民族性。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學,無論是廟堂文學、山林文學抑或是市井文學,都擁有過各自的輝煌,也曾出現過各自的墮落,最終,也都醞釀著各自的反思。對于中國傳統文學而言,輝煌的極端往往是墮落,墮落的盡頭往往是反思,而反思,又往往意味著新的輝煌的即將到來。廟堂文學、山林文學、市井文學均乃如此,三者之間的關系亦乃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