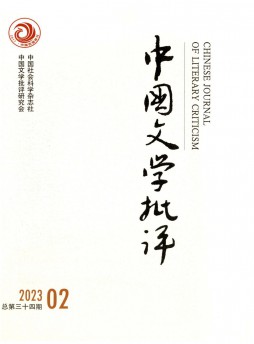文學(xué)批評類型的轉(zhuǎn)換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文學(xué)批評類型的轉(zhuǎn)換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公共性
傳統(tǒng)學(xué)者屬于書齋型文人,他們雖然在與友人的書信來往中闡發(fā)文藝主張,探討某一文學(xué)理論,但他們的書信文論相對較私人化,流通渠道僅限于數(shù)個好友之間,甚或乃至結(jié)集出版文集時,才將它們收錄其中,為世所悉。反之,由于報刊傳媒的發(fā)展,相當(dāng)一批五四學(xué)者以“文”謀生,他們從事翻譯、編輯、職業(yè)撰稿人等工作。受此職業(yè)特點(diǎn)的影響,書信這一傳統(tǒng)的文體也成為批評家們公開宣傳新思想、論爭新觀點(diǎn)的重要工具。五四以來,采用書信形式發(fā)表于各大報刊的文論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如:錢玄同的《致陳獨(dú)秀》發(fā)表于《新青年》第3卷第1號;胡適、錢玄同的《通信:論小說及白話韻文》發(fā)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1號;劉半農(nóng)的《復(fù)王敬軒書》發(fā)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3號;林紓的《就本刊登二古評批〈荊生〉給本刊主筆的信》發(fā)表于《每周評論》第15號;魯迅的《致傅斯年信》發(fā)表于《新潮》第1卷第5號等。借助于報刊這一現(xiàn)代形式的“公共空間”,書信體批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開放度。首先,通信成為開展文學(xué)批評的重要途徑。
這些書信文論或是一封或是一組,通信之人可以是兩人或兩人以上,借通信而展開的討論由于參與者眾,其影響力自然也大。從文學(xué)批評實(shí)況看,像胡適關(guān)于“八事”的《寄陳獨(dú)秀》來信一經(jīng)《新青年》第2卷第2號刊登后,即刻成為評論界的熱點(diǎn)。陳獨(dú)秀回信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礎(chǔ)上胡適撰寫《文學(xué)改良芻議》一文。該文在《新青年》發(fā)表后又引起錢玄同的關(guān)注,他也給陳獨(dú)秀寫了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見。陳獨(dú)秀收到后將錢信以及自己的回信一并刊登在《新青年》上。錢胡兩人也有書信往來,他們之間的書信《通信:論小說及白話韻文》同樣刊于《新青年》上。爾后參與論爭的來信越來越多,既有新文化統(tǒng)一戰(zhàn)線同仁們平心靜氣的切磋,也有新文化運(yùn)動者與林紓之流的復(fù)古主義者之間針鋒相對的辯論,隨著討論的維度不斷拓寬,新文學(xué)觀念也日臻完善。其次,以傳播媒介來公開表達(dá)意見,是“公共空間”的顯著標(biāo)志。借助報刊這一“公共空間”,書信體批評不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傳統(tǒng)的書信體批評缺乏普通民眾的參與。民眾的缺席導(dǎo)致文學(xué)理論傳播通道的單一,而文體往往需要在雙向的傳播與幅射的過程中不斷更新發(fā)展。五四時期倡導(dǎo)使用的白話大大降低了書信寫作的門檻,再加上許多報刊雜志為了擴(kuò)大影響,紛紛開設(shè)讀者“通信”欄目,使越來越多的平民讀者成為文學(xué)批評的新生力量。1915年9月《新青年》(時名《青年雜志》)創(chuàng)辦之初,即設(shè)“通信”一欄,“以為質(zhì)析疑難,發(fā)舒意見之用。”
《新青年》從創(chuàng)刊號直至1921年,每期都有讀者來信,甚至一期刊登的讀者來信有時多達(dá)25封。同樣,《小說月報》、《創(chuàng)造季刊》、《新潮》等刊物都曾開辟“通信”欄目,其中不少來信所闡述的問題與文學(xué)理論批評有關(guān)。這類通信可以說是文學(xué)批評發(fā)展的隱形推手,“我之文學(xué)改良觀”、“寫實(shí)主義”、“自然主義理論”等問題就是通過這些欄目擴(kuò)大影響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黃紹衡讀者致沈雁冰信。該信刊于《小說月報》第13卷第6號,黃紹衡于信中催促《小說月報》盡早開辟創(chuàng)作批評欄。于是《小說月報》便從第13卷第8號起開辟“創(chuàng)作批評”欄目,促使批評迅速擴(kuò)大影響。因此,五四的書信體批評具備了古代所沒有的公共性,對某一文學(xué)觀念或某一理論問題的研究往往依托某一報刊作為平臺,仰賴一批信友的相互交流合作。
趨時性
受時代大潮的影響,五四時期的文學(xué)批評不像古代那樣相對囿于較純粹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具有鮮明的趨時性。五四初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卻未能清除傳統(tǒng)舊思想的荼毒。于是,新文化的先驅(qū)者掀起“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xué),提倡新文學(xué)”的聲浪。受此時代氣氛感染,很多作家在與友人的通信里熱衷于討論如何建設(shè)新文學(xué)等問題。許多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話題都是在通信中誕生的。胡適在1916年8月19日答朱經(jīng)農(nóng)的信中就提出了著名的“文學(xué)八事”。錢玄同的《致陳獨(dú)秀》一文從語言進(jìn)化的角度論證白話取代文言的歷史必然性。錢玄同與劉半農(nóng)的雙簧信《文學(xué)革命之反響》明確提出新文學(xué)的目標(biāo)“三大主義”。宋云彬與錢玄同的通信《“黑幕”書》對代表舊文學(xué)的黑幕小說展開猛烈的批判,斥之為“殺人放火奸淫拐騙的講義”[8]70。可見,五四時期的書信體批評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十分敏感,始終呼應(yīng)新文學(xué)的時代訴求,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具有鮮明的趨時性。概言之,五四時期,書信這一文體盡管在格式上沒有較大創(chuàng)新,但舊瓶裝新酒,這一“容器”根據(jù)時代和現(xiàn)實(shí)的需要容納新思想,成功轉(zhuǎn)換成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新文化載體。
序跋體
序跋是一種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文體,姚鼐在《古文辭類纂》分文章為十三類,“序跋”列第二。凡經(jīng)史子集,詩文圖書之類皆可寫序作跋,因此序跋體文論在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僅小說而言,丁錫根所編的三冊本《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一書所收小說及說部總集凡537部,所收序跋約1300余篇。即便是在傳統(tǒng)批評范式日漸衰微的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史上,序跋類文論依舊成果豐碩。例如1941年王冶秋選編的《魯迅先生序跋集》所收集的序和后記等,共有134篇,而附記、譯名、附續(xù)記等還沒有列入,共約25萬余言。胡適所寫序跋數(shù)量不亞于魯迅,他曾說:“從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間,我以《序言》、《導(dǎo)論》等不同方式,為十二部傳統(tǒng)小說大致寫了三十萬字(的考證文章)。”
其他作家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等人所寫的序跋數(shù)量也很多。從文體學(xué)角度觀照,五四時期的序跋既有繼承也有創(chuàng)新。在題名上基本沿用傳統(tǒng)的序言、小引、前記、題辭、跋、后記、附記、附注等;語言上多采用明白曉暢的白話,根據(jù)現(xiàn)代語法遣詞造句;內(nèi)容上有自敘寫作緣由、抒發(fā)感慨、理論歸納、學(xué)術(shù)介紹等;體式上既有文情并茂的漫談,也有結(jié)構(gòu)縝密的評論。相較而言,五四序跋寫作在理論內(nèi)涵、思維方式、批評方法方面有了質(zhì)的飛躍,顯現(xiàn)出鮮明的現(xiàn)代特征。
相對而言,傳統(tǒng)序跋體批評大多比較“微觀”,拘泥于對單個作家的作品或數(shù)個作家的合集點(diǎn)評,在縱深層次的理論問題方面探索有限。五四批評家則常常以高屋建瓴之態(tài)探討作品與社會生活的聯(lián)系,考察作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理論價值等。魯迅的《吶喊•自序》在按照慣例闡述寫作的緣由和目的外,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鐵屋子”的理論,使得該序言成為研究魯迅思想的重要文獻(xiàn)資料。其譯文序跋也常對所譯小說的引進(jìn)意義和思想價值加以總結(jié),表達(dá)了作者介紹“他人之心”、“轉(zhuǎn)移性情,改造社會”的思想。魯迅在1920年前后之所以翻譯俄國作家阿爾支跋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幸福》、《醫(yī)生》等作品,正是看中阿爾支跋綏夫的“流派是寫實(shí)主義,表現(xiàn)之深刻,在儕輩中稱為達(dá)了極致”,并在《工人綏惠略夫》譯后記里對“現(xiàn)代人”的兩面性進(jìn)行入木三分的揭露,對某些評論家認(rèn)為作者“誨淫”和“誘惑青年”的謬論進(jìn)行反駁。而錢玄同的《嘗試集•序》雖是為胡適《嘗試集》作序?qū)崉t是一篇提倡“言文一致”的理論文章。他認(rèn)為“做白話韻文,和制定國語,是兩個問題。制定國語,自然應(yīng)該折衷于白話文言之間,做成一種‘言文一致’的合法語言”,主張“為除舊布新計,非把舊文學(xué)的腔調(diào)全數(shù)刪除不可”,嚴(yán)厲批判了歷史上那些獨(dú)夫民賊和文妖們對“言文一致”進(jìn)化大勢的破壞。其他諸如瞿秋白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郭沫若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和耿濟(jì)之的《屠格涅夫〈前夜〉序》、楊振聲的《〈玉君〉自序》等都能于具體作品外解讀出更多帶有普遍性的理論思想,這類深度批評為文學(xué)研究提供了新的闡釋張力。
而且傳統(tǒng)序跋篇幅一般較短,用的是文言文,對著者身份、著述內(nèi)容、作序緣由的介紹著墨較多,分析評騭常憑個人感悟、體驗(yàn)的方式,缺乏邏輯嚴(yán)密的演繹論證。像杜牧的《李賀集序》一向?yàn)槿朔Q道,文章前兩段主要闡述作序的起因和心情,第三段使用“云煙綿聯(lián)”、“水之迢迢”“春之盎盎”、“秋之明潔”、“風(fēng)檣陣馬”、“瓦棺篆鼎”、“時花美女”、“牛鬼蛇神”等象喻之辭概括李詩的整體風(fēng)貌,但序中對李賀詩風(fēng)的點(diǎn)評仍然是感性判斷多過理論辨析。而五四時期的序跋文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還保有傳統(tǒng)感性批評的痕跡,不少批評家卻在傳統(tǒng)體式框架上引用西方批評理論進(jìn)行解讀,精神分析法、社會學(xué)方法、平行比較法等常成為五四批評家的它山之石。如魯迅在《〈幸福〉譯后記》里評價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短篇小說《幸福》時就使用了弗洛依德理論中的“無意識”和“本能”兩個概念。鄭振鐸在《〈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中應(yīng)用比較的方法以理性的思維從“真”與“乏真”、“人”與“非人”、“平民“與非平民”、“悲劇”與“團(tuán)圓主義”四個方面對中俄文學(xué)進(jìn)行比較,邏輯嚴(yán)密。
可見序跋雖是一種傳統(tǒng)的批評文體,卻增加了許多新質(zhì),不僅容量拓展,而且思想性和理論性得以提升。五四的序跋文論不僅是我們理解作家創(chuàng)作思想、藝術(shù)理念的重要憑證,而且還是我們追溯五四文藝思潮、文藝流派、文藝論爭生成的歷史現(xiàn)場的重要依據(jù)。特別是那些數(shù)量較多的譯文序跋,是五四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是國人了解世界文藝潮流、域外文學(xué)的重要窗口。
論文體
中西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二者之間存在許多差異,其中,最明顯的區(qū)別在思維模式上。中國傳統(tǒng)思維習(xí)慣憑借經(jīng)驗(yàn)和直覺從整體上把握對象的內(nèi)在本質(zhì)和規(guī)律,所以較為直觀和感性。因此,詩話、詞話、評點(diǎn)、序跋、書信成為中國古代重要的批評文體。而西方思維則具有濃郁的理性和思辨色彩。習(xí)慣以實(shí)證和邏輯推導(dǎo)來把握世界,因此,條理分明、論證充分的論文體在西方文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晚晴時期,西學(xué)東漸,梁啟超、王國維、嚴(yán)復(fù)等人在文言文舊語言的框架中,“別求異邦于新聲”,對文學(xué)批評文體進(jìn)行改良。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以嚴(yán)密的邏輯,科學(xué)的方法、系統(tǒng)的理論,成為當(dāng)時文壇的新風(fēng)標(biāo)。至五四,論文體的寫作已蔚然成風(fēng),最確鑿的證據(jù)就是以“論”為題的文論不斷出現(xiàn)。如《文學(xué)革命論》、《論“黑幕”》、《論短篇小說》、《再論戲劇改良》、《歷史小說論》等。其他雖沒有冠以“論”字的文章同樣在思維方式、篇章結(jié)構(gòu)方面顯示出與傳統(tǒng)批評文本的巨大反差,具有明顯的現(xiàn)代特征。
首先從思維方式上看,五四時期的文論多屬于理性文本。究其緣由,與科學(xué)主義思潮的興起有關(guān)。鴉片戰(zhàn)爭后裹挾而入的西方科學(xué)精神正潛移默化地改變國人的思維習(xí)慣。科學(xué)、民主是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一面大旗,陳獨(dú)秀在《新青年》發(fā)刊詞《敬告青年》一文中“謹(jǐn)陳六義”,其六便是“科學(xué)的而非想象的”。同時,五四作家的知識結(jié)構(gòu)較為全面,中西兼?zhèn)洹TS多學(xué)者是在國內(nèi)新式學(xué)堂完成中學(xué)(中等科)和大學(xué)本科(高等科)教育。部分學(xué)者還曾遠(yuǎn)涉重洋、負(fù)笈游學(xué)。魯迅學(xué)過地質(zhì)和醫(yī)學(xué),周作人攻讀過海軍技術(shù),郭沫若學(xué)醫(yī),胡適學(xué)農(nóng)業(yè),張資平學(xué)地質(zhì),成仿吾學(xué)兵工,郁達(dá)夫?qū)W經(jīng)濟(jì)。這種求學(xué)經(jīng)歷使他們在夯實(shí)的傳統(tǒng)人文知識底子上融入了現(xiàn)代科學(xué)的因子,對他們的理性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種思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評論的文體風(fēng)格。具體而言,他們不再拘泥于詩話、詞話、序跋、書信之類的傳統(tǒng)文體,而是選用了重邏輯、重推理的論文體。以茅盾的《評四、五、六月的創(chuàng)作》為例。論文中,作者首先采用調(diào)查歸納法對1921年四、五、六三個月的小說進(jìn)行調(diào)查歸類,按照題材劃分為六種:(A)描寫男女戀愛的。(B)描寫農(nóng)民生活的。(C)描寫城市勞動者生活的。(D)描寫家庭生活的。(E)描寫學(xué)校生活的。(F)描寫一般社會生活的。并統(tǒng)計上述六類題材的篇數(shù)為:(A)七十篇以上(B)八篇(C)三篇(D)九篇(E)五篇(F)二十篇左右。在此基礎(chǔ)上,茅盾對各類題材逐一解析,得出結(jié)論:“為創(chuàng)作而創(chuàng)作,實(shí)是當(dāng)今大多數(shù)創(chuàng)作者的一個最大的毛病;現(xiàn)在的許多戀愛小說便是極好的例證。”從論證方式來看,茅盾自覺運(yùn)用歸納、演繹、統(tǒng)計、反證等方法,證明其論點(diǎn)的科學(xué)性與客觀性。
其次從篇章結(jié)構(gòu)看,較符合論文體的寫作規(guī)范。中國傳統(tǒng)批評文論雖能評出許多言盡意未盡的精妙之處,但往往失于零碎。這種結(jié)構(gòu)很難切合新文學(xué)理論建設(shè)的需求。于是,西方的文論模式對中國文學(xué)批評文體的轉(zhuǎn)換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胡適的《論短篇小說》堪稱此方面的典范。該文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什么叫做‘短篇小說’”。胡適先對“短篇小說”進(jìn)行界定,接著分別論述短篇小說的兩個重要條件“事實(shí)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個方面”和“最經(jīng)濟(jì)的文學(xué)手段”,并輔以莫泊桑的《最后一課》和《二漁夫》、都德的《最后一課》和《柏林之圍》等作為立論依據(jù)。在此基礎(chǔ)上,胡適在第二部分“中國短篇小說的略史”中,詳盡梳理了先秦諸子寓言至明清白話文言短篇小說的發(fā)展歷程,并進(jìn)而分析白話短篇小說發(fā)達(dá)不久便中止的兩層原因。第三部分的“結(jié)論”則由最近世界文學(xué)的趨勢得出要救治中國小說不講“經(jīng)濟(jì)”和記死帳的弊病,不可不提倡短篇小說這一定論。整篇文章縱橫開闔、結(jié)構(gòu)完整,論述嚴(yán)謹(jǐn),注意各個論點(diǎn)、論據(jù)間的邏輯關(guān)系、講究論證方法,充分體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文論迥異的文體風(fēng)格。
文體是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其生成、發(fā)展、衰亡既受到社會歷史文化的影響,又受其自身嬗變的內(nèi)在規(guī)律所制約。無可否認(rèn),詩話、詞話、評點(diǎn)等中國古代批評文體雖然具有鮮明的特色,但“這種批評形式的依附性使之永遠(yuǎn)也不可能成為一種真正獨(dú)立的文體,不構(gòu)成一種知識門類,無法具有現(xiàn)代批評學(xué)的那種知識的自足性與生產(chǎn)性(即‘生題能力’),最終不能超越傳統(tǒng)文論的樊籬”。因此,必須對中國傳統(tǒng)批評文體進(jìn)行改革,才能有所發(fā)展。當(dāng)代美國學(xué)者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在《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一書中認(rèn)為科學(xué)發(fā)展的過程,實(shí)質(zhì)上是不斷摒棄舊范式,創(chuàng)建新范式的過程。同理,文學(xué)革命也是一個以新范式取代舊范式的過程。五四時期的批評家對序跋體、書信體進(jìn)行現(xiàn)代改良,使之成為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活動的重要文體,避免了像詩話、詞話、評點(diǎn)那樣被淘汰的宿命。同時,他們也效法西方,引進(jìn)了論文體,使文學(xué)批評思維方式、語言使用、批評技巧等方面表現(xiàn)了中西文化合流的一上述三種文體共同促成了中國文學(xué)批評文體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
作者:宋向紅單位:莆田學(xué)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