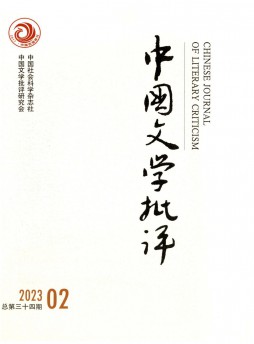文學批評的建構主義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批評的建構主義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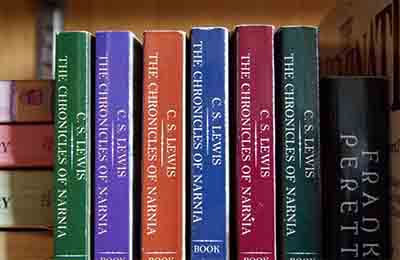
一、文學批評中的建構主義
人天生好奇,喜冒險探索,熱衷于發現真相,快樂于歸納出事物的規律,這就是建構活動。弗洛伊德在他的《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中指出,孩子最喜歡的最投入的活動是游戲和玩耍,每一個孩子在做游戲時的行為就像一位作家,他在游戲中創造著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在用自己喜愛的新方式重新組合他那個世界里的事物[2]421。孩子如此,成人也一樣愛建構。傳說中國上古圣王伏羲喜歡仰觀天象俯察地理,漸有所悟而畫出八卦,后周文王把八卦兩兩相疊,形成六十四卦,完成了《周易》,從此《周易》成了可以上測天,下測地,中測人事,預測未來,決策國家大事的圣書。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建構都很熱鬧,在文學批評領域建構也不冷落。孔子廣泛收集西周至春秋民間的詩歌,篩選編輯為《詩經》,評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從此“思無邪”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標準之一。亞里士多德熟讀荷馬史詩,遍觀古希臘的悲喜劇,構寫出《詩學》這一煌煌巨著,成為西方文學批評的源頭之一。文學批評里的建構首先發生在“空白地帶”,在他人尚未涉足的地方你首先開墾播種,你就能有所建樹,孔子和亞里士多德就是這樣做的,而現在所謂的“填補空白”也即此意。早期的社會中,處女地甚多,建構也就容易遍地開花。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你爭我鳴,各執一詞,對文學也就有了儒、道、墨、明、法家等各派學說,對我國之后的文學寫作和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集大成者當推劉勰。劉勰的時代儒家盛行,他起初有志于鉆研孔子的學說,通過注釋儒家的經典來弘揚儒學,但他很快意識到在這方面自己無法超越漢代的大儒馬融、鄭玄,于是就轉念另覓出路。他覽讀了當時的很多文論,如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的《翰林論》,發現這些文章的議論雖不乏精彩,但都失之短小簡略,言之不全不透,令人難窺為文的堂奧。他潛下心來,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歷時五年多,下筆三萬七千多言,終于構建成宏大縝密、體系完備的文論殿堂《文心雕龍》。王運熙和顧易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贊道:“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劉勰的《文心雕龍》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總結了南齊以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豐富經驗,論述比較全面,體系比較完整,開創了我國文學批評的新紀元。”
在西方,文學批評的建構也是先從空白處、從旁人未所涉獵的地域開始的。古希臘的柏拉圖率先在當時頗空蕩的文學批評園地栽下第一棵大樹———《共和國:卷十》,文中柏拉圖指出詩人巧言令色,用煽情的語言編織謊言來蠱惑人心,使人們情不自禁而失去理智,擾亂了社會次序,動搖了共和國的根基,因此必須把詩人驅逐出共和國。這里柏拉圖態度鮮明地構建了文學批評的政治和道德標準,為后世的文學創作和批評豎起了一根標桿。有批評家說,如果按英國哲學家懷特黑德(A.N.Whitehead)的說法,西方哲學史是對柏拉圖哲學著作的一系列腳注,那么我們也可以說西方文學批評史是對柏拉圖《共和國:卷十》的一系列腳注[2]1。但文學批評園地里的空地多著呢,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所栽的大樹不遠處栽了一棵幾乎同樣高大的樹《詩學》,他說,詩人確實在撒謊,因為他表達的是想象的世界,而非現實的世界,批評家該研究的是詩人為什么能把謊撒的那么圓滿,那么動人,給人以那么多的愉悅。這樣亞里士多德著手總結藝術發展的規律和創作的原則與技巧,為文學批評構建了一根美學標桿。之后文學批評園地中的林木越來越多,它們大多或者圍繞著柏拉圖的樹而長,強調作品所反映的哲理和道德,或者圍繞著亞里士多德的樹而生,偏重論析作品的技巧與風格。這時弗洛伊德來了,他在這兩個理性主義性質的派別領地的空隙間栽下一顆樹,用精神分析學說解釋文學藝術問題,撰寫了許多有關文藝創作、文學批評和美學鑒賞方面的文章,如《作家與白日夢》《摩西與一神教》《夢的解析》《圖騰與禁忌》《精神分析引論》等,提出了不少精辟和前衛的藝術觀點和批評見解,建立起弗洛伊德文學理論,開拓了非理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新天地。現在隨著多元化和網絡化社會的到來,文學批評園地開始擁擠起來,傳統的哲學道德批評法和歷史傳記批評法依然根深蒂固,俄國形式主義批評、新批評、神話原型批評、結構主義批評和精神分析批評雄風仍在,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批評、后結構主義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后現代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文化批評、性別批評、現象學批評、闡釋學批評、“對話”批評、生態批評等紛紛登場各顯神通,園地內似乎人滿為患。然而社會永遠在發展,生活永遠在變化,文學批評園地會永遠不斷地擴展,建構主義永遠能找到新的用武之地的。
除了尋找新空地“無中生有”之外,在原批評傳統的地圈內施肥澆水、固本培元或嫁接新枝以促使該傳統綻發新芽也是一種建構主義活動。一種文學批評理論和模式的建立不是朝夕之間一蹴而就的事,而是需要批評家盡畢生之力,甚至幾代人前赴后繼才能做成的。如現象學的創始人愛德蒙•胡塞爾(EdmundHusserl)一生投入哲學研究,在1907年出版了《現象學觀念》,1929年出版了《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斬釘截鐵地指出“一切實在事物都必須按其呈現于我們心中的面貌而作為純粹的現象加以對待,這是我們可以由之開始的唯一絕對材料”,并由此出發構建了懸擱法、還原法、意向性以及主體間性等理論來分析人們心中的純粹想象,為現象學批評奠定了基礎[4]。在胡塞爾現象學理論的基礎上,德國美學家莫里茨•蓋格首先將現象學運用于美學研究,對人的美學感受加以現象學闡釋。蓋格之后,德國美學家R•歐德布萊希特(RudolfOdebrecht)等人進一步對藝術價值的審美活動加以現象學分析,他們代表了現象學美學的主觀方向,即注重主體的能動性。隨后H•呂采勒(Hein-richLutzeler)等人將注意力集中在藝術作品的本體分析上,而發展了現象學美學的客觀方向。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波蘭美學家羅曼•英伽登(RomanIngarden)受胡塞爾和蓋格的影響,在藝術本體論、藝術認識論、藝術價值論方面深化了現象學美學的研究。1953年,法國美學家杜夫海納(MikelDufrenne)出版了《審美經驗的現象學》,把現象學美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然而真正將現象學理論作為自己的基礎,全面直接應用現象學理論于文學批評的首推日內瓦學派,他們提倡以一種“居中性”的態度對作者的意識經驗進行“內在”批評,從而“直觀”到作者的意向性意識和潛伏的經驗模式。至此,現象學文學批評才從理論到實踐真正名副其實,顯然,在使現象學批評生根發芽、爾后枝繁葉茂、最終開花結果的過程中,每一個參與的論者和批評家都是建構主義者。
從內部促使某種批評傳統茁壯成長和發展是建構的一種途徑,感到某種批評傳統已僵死沒落無可挽救或與己見解不合無從調和,而從中破門出另立門戶也能是一種建構的途徑。在精神分析批評中,弗洛伊德作為前驅提出了意識、前意識、無意識的心理結構論,自我、本我、超我的人格論和作品是作家的白日夢理論。榮格起初曾與弗洛伊德合作,深得弗洛伊德器重,被視作繼承人。后來兩人間漸生分歧,最終無法彌合,于是榮格離開了弗洛伊德并對其理論進行批判性的修正。弗洛伊德說的是個體的無意識,榮格將之擴大為集體無意識;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是個體的人格因素,榮格則推出人格面具、阿尼瑪、阿尼姆斯和陰影四個原型來個體的人格。榮格構建的集體無意識論和原型論經過充實發展為影響不亞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評的神話原型批評。在中國類似的例子是黃庭堅與蘇軾。蘇軾是宋代重要的文學家,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黃庭堅是“蘇門四學子”之一,師從蘇軾得到提攜后出名,但不久他發現自己與蘇軾在旨趣和技法上有很大不同。蘇軾主張文章當“有為而作”,要求“言必中當世之過”,而他認為詩歌是個人情性的表現,不該用以批評朝政,議論是非;蘇軾崇尚自然,反對雕琢,落筆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而他推崇熟讀古書,規摹古人,遵守法度,做到“無一字無來處”。后來他就另辟蹊徑,別立門戶,構建了“點鐵成金”、“脫胎換骨”法,終成江西詩派的開山鼻祖,在中國文學史上后與蘇軾并稱,他的詩論盡管有不足之處,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占了一席之地。建構主義文學批評的核心是批評家主體的主動構建,但因為他的構建活動發生在他所處的社會大環境中,他就不得不妥當處理他與客體的關系,不然他的構建活動將一無所成。按照前述的建構主義原則和方法,批評家首先必須找到他的個人興趣愛好與他所在的文學批評語境的需求的契合點,選定現實的目標,找到可墾殖的空地或請求進入某個已開墾的場地開展他的構建主義的批評活動。其次,在這種構建性質的活動中,由于文學批評的互文性,他必須與其他批評家有所接觸和交流,若有人志同道合能與之同干則更好,而對與己志趣不同的人,也盡量做到“道不同,相與謀”,因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諧地與觀點相異的人進行思想碰撞,能促使自己全面地看問題,克服自己的短處,從而更有效地構建和創新。再次之,進行建構活動必須得有合適的工具,這工具可根據需要因地制宜自己制作,也可借用他人制造的現成工具。如今批評界各種各樣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爭奇斗艷,各逞其能,各放異彩,我們若能海納百川,不拘一格,采擷眾家之長而綜合用之,我們的建構主義批評定能得心應手取得事半功倍的結果。這幾點其實是建構主義原典精神的重申,只是在文學批評領域的具體化落實而已。
二、文學批評中的解構主義
解構主義批評首先是一種閱讀策略,在閱讀文本時專注于發現文本的內在矛盾,然后給以顛覆性的解釋,解構其所表達的論點,代之以新的合理的說法。德里達對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的解構性閱讀為這策略樹立了一個經典性的榜樣,使人們從此對解構主義有了具體深刻的印象。索緒爾在書中說,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的口說形式,書寫語言只是為了表述口說語言而存在以方便研究,這樣他明確地規定了語言的口說形式高于書寫形式的等級次序。但德里達質疑道,口說的語言一出口即消失,見不到,抓不住,如何研究?即使現在有設備能記錄下來反復播放,依然是只聞其聲不見其形而無法進行分析。德里達在《論書寫》一書中比較對照了口說語言與書寫語言的異同,指出兩者的區別在于媒介形態不一,前者為聲波,后者為文字,聲波稍縱即逝,而白紙黑字清晰持久,所以書寫語言作為研究的對象遠比口說語言穩定牢靠。就此德里達解構了索緒爾所規定的次序而確立了語言的書寫形式高于口說形式的新等級次序,他成功的解構性閱讀使解構主義在批評舞臺上勝利地亮了相。文學批評領域的解構性閱讀則是由美國耶魯學派的主將保爾•德曼首先身體力行發揚光大的,他對愛爾蘭詩人葉芝的《在小學生中間》一詩尾部的四行詩的分析也堪稱經典范例。原詩行如下:“0chestnuttree,great-rootedblosso-mer,/Areyoutheleaf,theblossomorthebole?/0bodyswayedtomusic,0brighteningglance,/Howcanweknowthedancerfromthedance?”此詩的最后一行在傳統讀法中是無需回答的詰問句,其意是舞蹈美妙絕倫,舞者技藝非凡,舞與人兩者渾然一體,猶如樹葉、花朵和樹身構成整樹一樣不可分割,表達了形式與內容、創造者與創造物有機統一的觀念。然而德曼質問道:為什么不可把最后一行看作是期盼答案的真實問題,問者迫切希望知道舞者與舞蹈究竟有著什么關系,兩者在何種情況下會和諧一致或互相別扭?這一問就問出一個有關藝術創作和欣賞的美學問題了。實際上把葉芝的最后一行詩當作設問句處理是較為簡單、無須深思的傳統讀法,而當作真實看待則能導出一連串復雜細致的思考和探討,打開了一條新的思路,得到了一個傳統閱讀法不可能獲得的結果。德曼的范例給我們的啟示是,在文學批評領域內我們應該擺脫傳統思維的囚禁,采取積極的解構姿態,對被奉為法規、恭敬地領受的文學理論和模式進行審視與批判,以能別開生面,有所建樹。很明顯,解構的目的不是要拋棄傳統,德里達并不全盤否定索緒爾的理論,德曼也沒有武斷地認為對葉芝的詩的傳統讀法毫無價值。解構主義追求的是打破傳統話語權的一統天下,讓新思想新方法有發展的機會和成長的可能。
解構主義對傳統閱讀的顛覆為文學批評帶來了勃勃生氣,它的解構精神得到廣泛的吸納而不斷催生新花。解構主義的又一個卓越貢獻是把文學文本高踞于批評文本之上的傳統局面顛倒了一下。人們習慣稱文學是皮,文學批評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批評是老二,長期處于奴婢地位。但耶魯學派的哈特曼在《荒野中的批評》一書中指出:“文學評論會跨越界線變得如同文學創作一樣苛求……批評必須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重新構筑語境的力量,它不應被視作他物的附庸。”這意味著不再是批評依附于文學,而是文學因批評而獲得理解和賞識。不惟如此,高超的解構主義批評甚至能使被作者有意無意掩蓋的或他自己都未曾意識的意圖得以昭示。對此德里達有過深中肯綮的解釋:作家運用語言遵從邏輯進行寫作,而此語言和邏輯的自身體系、規則與活力按其本義是作家無法完全控制的,他只有讓自己按照某種模式在某種程度上被該體系控制后才能運用它們。而讀者的閱讀總是指向作者使用語言模式時他所掌握的與未掌握的部分之間的關系,但對此種關系作者缺乏意識。此種關系不是明與暗或強與弱的定量分布,而是批判性閱讀應該產生的一種意指結構。
換言之,作家用語言創作,而語言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和多義性,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并不能完全主宰他所使用的語言的意義,作品一朝分娩后他更是失去了對作品的控制,于是作品的意義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于讀者對作品的解讀。傳統的文學批評對“作者未能完全主宰作品”這一點缺乏足夠的認識,往往聯系作者的生平和歷史背景,依照作者自陳的意圖、追隨著他的思路去分析作品挖掘意義。與之對照,解構主義批評常抓住作者未曾意識到和未能主宰的部分做文章,以揭露深藏于作品的意指結構,解構主義對作品的解讀不但能引導讀者大眾,而且還能啟發作者,加深他對自身的認識,促進他今后的創作。德里達和哈特曼的論說提升了文學批評的地位,使之與文學創作平起平坐,甚至指導后者,大張了文學批評的志氣,值得為之擊節贊賞!文學批評的解構主義有其發生的動機和動力,這已在前面與建構主義一起簡論過,但解構主義可能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動力,即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所指的“影響的焦慮”。布魯姆的《影響的焦慮》論述的是一個詩人的成長過程,但他論著的內容和精神也適用于分析文學批評家。他說:詩人之“自我”(ego)的形成是一個無意識的、不可逆轉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前驅詩人的形象無時無刻不存在于后來詩人的“本我”(id)之中,兩者之間的關系類似佛洛伊德“家庭羅曼史”之父子相爭關系,詩人慢慢感受到前驅詩人影響的壓迫而引起的深刻焦慮,其心理歷程是:年輕詩人被一位老詩人的力量所俘獲,然后產生一種詩歌視野上的共鳴,緊接而至的是年輕詩人的沉默對抗。布魯姆認為為了走出前驅詩人的影響陰影,年輕詩人必須竭力掙扎,盡其所能去爭取自己的獨立地位,以求名載詩歌史之冊。他采取的策略會是用各種方法有意和無意地對前人詩作進行“誤讀”、“修正”和“逆反”,推倒前驅詩人這偶像,屆時這已解放、擺脫了焦慮的年青詩人才能把自己表現為真正的詩人。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這是一個“戀父———弒父———升華”的過程和規律。美國詩人暨詩論家威廉斯(W.C.Williams)的成長過程就是這樣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慕名拜龐德為師,在龐德的影響下,開始充滿激情地投身于意象派詩歌運動,以龐德首創的意象主義原則指導自己的詩歌創作,后來成功地以意象派詩人的形象登上詩壇。但他很快就感到他在無可避免地被龐德所同化,自己的個性在龐德的影響下漸漸消蝕,他的焦慮由此產生。于是威廉斯開始用各種方法有意和無意地對龐德的詩作進行“誤讀”、“修正”和“逆反”,并于1917年在自己的意象主義詩集《致需要者》中一語雙關地喊出了這樣的口號:“詩歌要活下去,必須注入不同樣的東西,不循規蹈矩,必須進行微妙的、難以察覺的變革。”他通過對意象派的核心概念“意象”的修正使美國意象派詩歌從“現代”躍向“后現代”,也通過對龐德的“意象”的“誤讀”和“逆反”成功地擺脫了龐德影響的陰影,顯示出敢于同傳統決裂一薄前人的氣概。后來他將矛頭直指龐德,批判其意象的主體性,而強調詞語的客體性,確立了“思想只在物中”的詩學思想,并以之為指導原則創建了客體主義詩派。現在,美國幾乎所有主要詩歌創作派別,無論是黑山派、紐約派,還是自白派,都聲稱他們借鑒了威廉斯詩歌創作的理論和實踐。威廉斯的客體派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詩歌的創作方向———詩歌民族化,因而他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美國本土詩人之一”,是“惠特曼以來美國最具有‘本土’意識、堅持走詩歌創作民族化道路的詩人”。至此威廉斯終于如愿所償鳳凰涅槃般走出了一條與龐德大相徑庭的詩歌創作道路,他的成長過程雄辯地證明,面對強大的圈地為王的傳統,若欲有所創新和建樹,必得先用解構主義利器開辟出一片土地來。文學批評園地中的解構主義并非單純只是一種批評方法,它更應該被理解為“實踐智慧”,即一種通過解構實踐最終促成建構的智慧。杰拉爾德•L.布倫斯在他的《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和闡釋學》一書中這樣說道:“人們并不把解構主義純粹當作一種方法運用,它不是可以隨意地拾起、放下或玩弄之物。必須把它理解為‘實踐智慧’,即一種能使幫助人們應對某種局勢的智慧。我是說,我們似乎總是困于傳統的羈縛之中無法擺脫,而解構主義正是我們對付這種局限生活的一種途徑。這就是為什么說解構主義爭論的并非知識和真理問題,它所爭論的是權力和權威問題。解構主義并不著眼于解決這個問題,而只是以某種方式與它相處。”
按此種見解,文學批評的解構主義是一種實踐智慧,它遵從批判的策略,實行策略性的批評。它認為文學批評語言內在的歧義性決定了語言所表達的知識和所闡釋的意義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不確定性和可解構性。任何文本都自以為代表真理,企圖確立自己的權力和權威,企求把內在的異己力量抹殺或遮蔽,從而能以統一的聲音和面貌對外。文學批評的解構主義旨在證明,如果對已被接受為正統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仔細檢視其細節的話,或許另一幅圖畫會呈現在我們眼前。解構主義并不認為它自己所展示的新文學批評圖畫更有真理性,但它針對權力和權威壓制差異造成知識和真理一統天下的幻象提供了一套戳穿幻象揭露矛盾的有效法則,指明正是文本對權力和權威的渴望埋下了它自我顛覆和解構的種子。解構主義在這一點上是比較有自知之明的,它首先承認自己無法提供更徹底更正確的真理,同時承認自己的文本也是用語言寫成,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具有被解構的可能性。這樣,舊的權威文本被解構了,新的文本獲得了權力,而這新的權威文本接著又成了批評的對象被解構,更新的文本獲得了權力……文學批評園地就在這種解構—建構—解構—建構生生不息的綿延中永遠充滿生氣和活力,這也許就是文學批評的“反者道之動”吧。
三、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協同運行
文學批評的各種理論和方法按其功能的本質大體可分成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兩大派,這里對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理解已超越技術層面而進入理念層面了。那么建構主義與解構主義兩派孰先孰后,孰重孰輕,彼此有何關系?人們的一般感覺是建構主義在先,解構主義在后,因為若沒有先建構,將無物可供解構。但實際上兩者的關系如同道之陰陽,是同生共存,貫穿始終,協力運行于文學批評的園地里的。太極圖明白地顯示,陰與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擁為一體,流轉舞動,永不止息。建構主義與解構主義也是彼此進入,由始至終互相促動的。一種文學批評流派在建立之初,無論是原始資料的搜集和篩選,還是基本原則的斟酌與敲定,都得經過建構和解構的反復運作;在這一流派的發展壯大階段,也得時時灌澆施肥和修剪枝葉,給原則充實新內容,給方法提供新實例,同時隨時芟除引起歧義的論點和導致謬誤的方法。所以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應該不分先后輕重而應協同運行,就如劍有雙刃,缺一不成寶劍,文學批評有了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雙刃于一劍,才能為繁榮社會文化和發展文學藝術作出貢獻。然而在人類社會中,畢竟終極目標是建構,解構的根本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建構,不然社會就不能進步,歷史也不會發展。在文學批評中,最終目的也是建構,而解構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人們常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破就是立,“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晉•韓康伯《周易•系辭上》注),此之謂也,中西方文學批評史都證明了這一點。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緒論中勾勒道,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文學觀念演進期,一是文學觀念復古期,又一是文學批評完成期。從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學觀念演進期,這一時期的批評風氣偏于文,重在從形式上去認識文學;從隋唐到北宋,是文學觀念復古期,這一時期的批評風氣又偏于質,重在從內容上去認識文學;從南宋一直到清代是文學批評完成期,這一時期才以文學批評本身的理論為中心,而文學觀念只成為文學批評中的問題之一。
從這簡略的勾勒和豐富的全書中我們都能清晰地體會到一部文學批評史就是一部文學批評通過不斷的建構解構向前演進的歷史。顏元叔在他翻譯的《西洋文學批評史》的代譯序“西洋文學批評的幾個重鎮”中指出:文學批評的對象有四,即作家,作品,讀者,與時空。文學批評處理這四個對象的各別本身,也處理其間互相的關系。我們可以把作家、作品、讀者排列在同一水平上,時空則包容了全體。于是,文學批評討論作家與作品的關系,作品與讀者的關系,讀者與作家的關系,時空與作家或作品的關系,時空與讀者的關系:這些都是外在關系。假使文學批評專事研討文學作品本身,這便是企圖處理文學的內在關系。文學批評的活動,大抵周轉于這些區域之內。他又說,文學是一種現象,文學批評是對這個現象的探索與研究。各代的人,各地的人,因其不同的習性、需求與條件,作了不同的研究探討,獲得不同的結論。這正顯示各代各地的人對文學的積極關懷,積極要求文學對他們的生命有所助益。文學批評便是文學與人生相接觸,閃耀而出的火花[12]。從他的代譯序和全書看。西方文學批評圍繞著作家、作品、讀者和時空四要素之間的關系不斷探索思考,總結出種種理論,從古希臘的模仿說到中世紀的諷喻說,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縱觀西方文學批評史,我們不難發現這也是一部不斷建構解構的文學批評嬗變史。中外文學批評史無可否認地表明,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誰擯棄對方,誰就不能成就自己,而當活躍的解構主義與沉著的建構主義默契地聯姻時,文學批評就能源源不斷地開辟新的研究領地,發現新的創作規律,發明新的解讀方法,書寫文學批評史新的篇章。
文學批評的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在第一層次是一種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作為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解構主義已為大家熟悉和應用,而建構主義尚有待于更深入的認識、理解、接受和運用,這里倘蒙有識之士關心出力,使之得以進一步理論化、體系化和方法化,則將是建構主義之大幸,文學批評之大幸,人們將為之額手相慶。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在第二層次是一種批評的理念和智慧,這種理念和智慧施之于文學批評園地則能通觀文學批評活動,從建構什么和解構什么的角度來考察和促進各個批評流派的理論、方法和實踐的發展;施之于社會和人生,則能幫助我們明智地去面對世界和度過人生。建構和解構性質的文學批評活動古已有之,只是多處于散布和無組織狀態,而在現當代則發展成為有相當理論體系和活動規模的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但當今社會生活豐富,文藝創作繁榮,而文學批評卻相對滯后。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把建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既視為理念和智慧、又當作理論和方法來振興文學批評是非常必要和十分有益的,值得我們大家認真看待并積極參與。
作者:武新玉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
- 上一篇:勃蘭兌斯的文學批評分析范文
- 下一篇:文學批評的文化認同與價值建構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