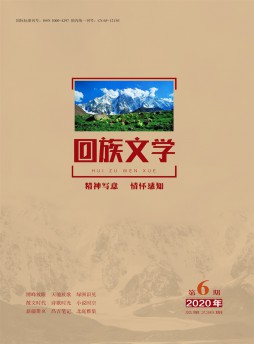文學翻譯功能對等原理運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翻譯功能對等原理運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的提出和發展
尤金奈達是美國著名的語言學家、翻譯理論家,當代翻譯理論的主要奠基人。在中國,奈達的翻譯理論在當代西方翻譯理論中影響最大,其核心是功能對等理論。
1.1、動態對等他的動態對等理論,在《論對等原則》一文中得到了明確闡釋。文章一開頭,奈達就提出:沒有哪兩種語言史完全一致的,無論是對應符號被賦予的意義還是這些符號排列為詞組和句子的方式,既然如此,就有理由認為語言之間不存在絕對的對等。這樣,也就不存在完全精確的等同。翻譯整體影響可能接近原文,但細節不可能完全等同(謝,2008)。既然沒有“完全等同”,因此翻譯所要追求的就是最接近的對等物。奈達進一步把劃分了對等的兩種不同類型:一是形式對等;一是動態對等。形式對等關注信息本身,包括形式和內容。在這樣的翻譯中,譯者關注的詩與詩、句與句、概念與概念的對應。而與形式對等不同的是,以動態對等為導向的翻譯不那么關注譯語和源語在信息上的一致,而更關注動態的關系,即譯語接受者和譯語信息的關系應該和源語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存在的關系相同。在于Taber合著的《翻譯理論與實踐》中,奈達進一步說明動態對等的含義。他認為,“所謂翻譯,就是在譯語種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源語的信息,首先是意義,其次是文體。”(郭,2000)。
1.2、功能對等由于奈達“內容為主,形式為次”的思想受到誤解,各種各樣只翻譯內容,而不注重形式的自由譯都被冠以“動態對等”的名義。所以奈達在后來的《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論圣經翻譯中的功能對等》一書中,把“動態對等”改為“功能對等”。所謂語言的“功能”,就是“它在使用過程中所發揮的不同的語言作用”(葛,1994)。同時他也強調,功能對等的翻譯,在追求信息內容對等的同時,也要盡可能達到形式對等。在《語際交際的社會語言學》中,奈達認為,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過分強調形式對應會抹殺原文的文化意義。稱職的翻譯者應該把語言看做交際的工具。翻譯只能達到“功能對等”,或者是“實際上的交際對等”(郭,2000)。
文學翻譯與其他翻譯之所以不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學以文字為物質手段,構成一種表象和想象的形象,反映現實生活,表現了藝術家的審美感受。因此,對文學的翻譯,除了準確以外,還要考慮到文字的鮮明生動,力圖轉換和移植原文的意境和風格,表現出作品的審美價值。此外,文學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寫照。文化差異和語言特色造成了文學翻譯中某些不可譯的因素。因此,譯文是永遠不可能達到與原文完全對等的效果的,譯者能做的就是追求相對的“近似值”。這與奈達的對等理論是相一致的。《紅樓夢》以其豐富的語言和文化內涵列居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首。本文試從霍克斯與閔福德的英譯本探討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在文學翻譯上的應用。
2.1、語意對等奈達的功能對等十分強調翻譯的傳情達意,形式是次要的。為了避免翻譯失誤,譯者就要正確理解原文在源語文化中的特定意義,并在譯語中找到最接近最自然的對等語。例1.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居然鬼嚎的一般……霍譯:Byeveninghervoicebegantogrowhoarseandshesoundedmoreandmorelikeacroakingharpy.(馮,2008)趙姨娘粗俗愚蠢自私,人人厭惡。“鬼嚎的一般”帶有明顯的貶義。簡單譯為ghost是無法表現出這么強烈的感情色彩的,因此霍譯用另一個西方人十分討厭的形象“harpy”來代替。哈比是希臘羅馬神話中的鷹身女妖,生性貪婪,饑餓且疲憊不堪,她們碰過的一切東西都會變得污濁惡臭。可見harpy一詞的感情色彩非常符合趙姨娘,也更易于譯語讀者對人物的定位。
2.2、風格對等《紅樓夢》語言質樸自然,含蓄凝練,準確表達了作品的思想主體,尤其是生動的對話賦予了每個角色不同的性格特征。字字珠璣,趣味盎然。例2.張王氏哭稟:“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里住,十八年頭里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為小人家里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里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里打發人來叫俺……”霍譯:(馮,2008)張王氏是農村婦女,話語中多夾雜土語,如“娶女人”、“沒得養活”、“當槽兒”等等,因此很難找到合適的對等語。霍譯根據張王氏的身份和特征,在語音和語法上做文章,讓她聽起來就像英國北部帶有濃重鄉音的村婦,很好地再現了原文口語化、地方化的風格。其主要方式就是吞音,包括所有詞首的元音和h音,如“’bout”(about)、“’im”(him)等,所有詞尾的后鼻音,如“helpin’”(helping)、“comin’”(coming)等,連讀中的個別音,如“may’t”(mayit)、“Yeronner”(YourHonour)等,以及不規范的語法。
2.3、文化傳遞奈達認為,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語言在文化中的角色以及文化對詞匯和習語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Nida,2001)同時,功能對等理論追求的是譯語接受者和譯語信息的關系應該和源語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存在的關系相同。但是,文化差異的客觀存在決定了讀者反應之不可能相同(郭,2000),如中國婚俗中的“紅蓋頭”就不可以翻譯為“weddinggown”。而且,即使是“雨后春筍”和“togrowlikemushrooms”,在記憶圖式的原型反應也是不同的。文化詞的翻譯困難正是功能對等理論在文學翻譯上的局限性所在。例3.寶釵笑道:“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一些,咱們也算是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霍譯:(馮,2008)《論語•顏淵》中“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對孑然一身、孤立無援的感嘆。這個典故在英語中很難找到相對應的習語,若意譯為“lamentyourlackofabrother”,則失去了原文的文化底蘊和通過對話進行人物塑造的機會。霍譯不拘泥于形式,把“司馬牛之嘆”的內容補充出來,既向譯文讀者傳達了原文的文化信息,又展現了兩位女子博古通今的氣質,達到了翻譯的目的,在另一層面上實現了“功能對等”。可見,在文化詞匯的翻譯上,“功能對等理論”仍然是適用的,但是,不能太執著與現成的“對等語”甚至濫用,而應該打破局限,對譯文做整體考慮,用不同的方式達到共同的“對等”目的。
3、結語
本文試用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分析了霍克斯與閔福德的《紅樓夢》英譯本的部分例句,測試了該理論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雖然它在文化詞句的翻譯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是可以用不同方式進行彌補;完全不同的對等翻譯對源于不同文化的文學作品來說是不可能的,但大致的對等是可以實現的。譯者可調整自己的翻譯策略,盡可能表現原作的內涵、風格和文化,給譯文讀者帶來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