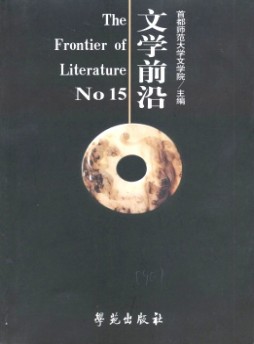文學(xué)翻譯作品的風(fēng)格再現(xiàn)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文學(xué)翻譯作品的風(fēng)格再現(xiàn)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本文從闡釋風(fēng)格的概念出發(fā),分析文學(xué)作品中風(fēng)格的可譯與不可譯之爭,并站在可譯性的角度,從風(fēng)格的多樣性出發(fā)分析作家風(fēng)格及陶詩風(fēng)格,以及從語言層面,即遣詞、修辭和音韻三方面分析汪榕培在英譯陶詩時如何再現(xiàn)它的風(fēng)格。
【關(guān)鍵詞】文學(xué)翻譯;風(fēng)格再現(xiàn);汪榕培;英譯陶詩
“風(fēng)格”一詞剛開始出現(xiàn)時,在我國并不單單指作家或作品的風(fēng)格,也指人的風(fēng)致、風(fēng)度、品格、氣格等。風(fēng)格亦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風(fēng)格包括時代風(fēng)格、民族風(fēng)格、階級風(fēng)格、流派風(fēng)格等,而狹義的風(fēng)格是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形式的有機(jī)統(tǒng)一中所顯示出來的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總特點(diǎn)。(王明居,1990)本文通過分析作家風(fēng)格和作品風(fēng)格,討論汪榕培英譯陶詩時如何再現(xiàn)其作品風(fēng)格。
一風(fēng)格的可譯與不可譯
風(fēng)格的可譯與不可譯在我國翻譯界一直有爭論。一方面有學(xué)者認(rèn)為風(fēng)格虛無縹緲,無法把握,如我國翻譯家周煦良先生認(rèn)為作品所特有的感情色彩和藝術(shù)特性是不可譯的,他認(rèn)為風(fēng)格好像只是在無形中使譯者受到感染,而且譯者也是在無形中把這種風(fēng)格通過他的譯文去感染讀者的。(李玉梅、王蕾,2009)另一方面,部分學(xué)者認(rèn)同另一種觀點(diǎn),即語言是風(fēng)格形成的基礎(chǔ),不同的語言因其社會環(huán)境、民族特點(diǎn)而具有特殊性,但同時所有的語言都是對人類實(shí)踐的反應(yīng),是思想的表達(dá)手段,語言是有共性的。筆者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的風(fēng)格是可譯的,而詩歌作為文學(xué)體裁中的一種,其風(fēng)格也是可譯的,倘若譯者能準(zhǔn)確把握作品風(fēng)格和作家風(fēng)格,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再現(xiàn)詩歌的風(fēng)格,而作家風(fēng)格的形成與他的時代背景、家庭環(huán)境息息相關(guān),因此譯者在翻譯前需對作家的人生經(jīng)歷有所了解。
二陶淵明的人生經(jīng)歷及其詩歌風(fēng)格的形成
陶淵明的一生主要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出仕前,即29歲前,在儒家思想有所作為的影響下,他意氣風(fēng)發(fā),想為國效力,實(shí)現(xiàn)政治抱負(fù)。第二階段是時仕時隱階段,即29歲到41歲,歷經(jīng)13年之久,此時的他徘徊在歸隱和出仕之中。在受儒家思想影響之余,他還深受道家思想影響,主張隱居,要無所為,一切順其自然。他出仕時懷念田園風(fēng)光的美好,歸隱時又關(guān)注時事,等待時機(jī)想有所作為,但總是以失望收場。第三階段是辭官真正歸隱田園階段,他淡泊名利,不為五斗米折腰。
三陶詩英譯的風(fēng)格再現(xiàn)
由于“文學(xué)是借語言文字來作雕塑描寫的藝術(shù)”,因此整部作品的風(fēng)格,集中體現(xiàn)在語言風(fēng)格上。本文將分別從遣詞、修辭、音韻三個方面對陶詩英譯的風(fēng)格再現(xiàn)進(jìn)行分析。1.從遣詞看陶詩英譯的風(fēng)格再現(xiàn)作者年近半百,歸隱田園8年后對少年時光的回憶,當(dāng)年意氣風(fēng)發(fā)、積極樂觀,擁有一番雄心壯志,體現(xiàn)的是慷慨激昂的風(fēng)格。一方面,原詩中“自”字表現(xiàn)出作者的快樂是由內(nèi)心自發(fā)出來的,從側(cè)面強(qiáng)調(diào)了這種快樂不是周圍環(huán)境或事物所能左右的。汪榕培在翻譯時用“overwhelm”這個詞來再現(xiàn)這種快樂。“overwhelm”作為動詞,有“(感情上)使(某人)感到不可自持”的意思,若汪榕培用“befilledwith”來代替“beoverwhelmedwith”則失去了強(qiáng)調(diào)這種快樂是無須理由、油然而生的意味,也就無法準(zhǔn)確體現(xiàn)作者積極樂觀的人生態(tài)度。另一方面,原詩第三句中的“猛志”是指壯志,但當(dāng)我們初看譯文,發(fā)現(xiàn)它被譯成“aims”,那種雄心壯志的意味便蕩然無存,我們無法體會到作者年少時的志向到底有多大,但當(dāng)我們繼續(xù)讀下去便會豁然開朗,體會到譯者的良苦用心,譯者用“seizethestar”即“摘星”這一具體的行動來體現(xiàn)只可意會的豪情壯志,遣詞方面可謂是恰到好處,妙趣橫生。綜上所述,譯者能較準(zhǔn)確地再現(xiàn)原詩中慷慨激昂的風(fēng)格。
2.從修辭看陶詩英譯的風(fēng)格再現(xiàn)
陶淵明詩歌中采用頻率相對較高的修辭手法是明喻。如《雜詩十二首•其一》的前兩句:“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這兩句采用了明喻的修辭手法。陶淵明起筆便感嘆人生無常,認(rèn)為人的一生宛如塵土,無根蒂,隨風(fēng)飄散。很明顯,第二句中的“如”字便是明喻的提示詞,將人生比作塵土。汪榕培將其譯成:“Humanlifeisrootlesslikeagale.Floatinglikethedustalongatrail.”(汪榕培,1999)第二句用了英文中的比喻詞“l(fā)ike”,很好地對應(yīng)了原詩中采用的明喻修辭手法。陶淵明在感嘆人生無常時用明喻,同樣,在感嘆生命短暫時也采用了相同的修辭手法。如《飲酒二十首•其三》中的“一生復(fù)能幾,倏如流電驚”汪譯為“Nomatterhowlonghumanlifewilllast,asswiftaslighteningitwillsoonbepassed”(汪榕培,1999:197)。用“as…as…”的結(jié)構(gòu)表達(dá)“和……一樣”,同樣使用比喻詞,將生命的短暫比作閃電,倏然間就消失了,因此再現(xiàn)了原詩隱約悲憤的風(fēng)格。
3.從音韻看陶詩英譯的風(fēng)格再現(xiàn)
飲酒二十首•其五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首詩是典型的田園詩,雙數(shù)行押韻且押的都是平聲韻。如雙數(shù)行的韻腳喧、偏、山、還和然的韻母分別為uan、ian、an、uan和an,而韻母an、ian和uan同屬一韻部,中間并無換韻,一韻到底。而且它們的聲調(diào)都屬于平聲,讀起來聲韻和諧。本詩采用樸素的語言描繪了再平常不過的田園景象,畫面感十足,再加上和諧優(yōu)美的吟誦節(jié)奏,體現(xiàn)了陶詩的恬淡閑遠(yuǎn)風(fēng)格。我們知道漢詩無一例外都要押韻,汪榕培為了保持漢詩的韻律美,從而從吟誦節(jié)奏和音樂美上向原詩靠近,他在英譯時采用了抑揚(yáng)格五音步的韻律,因而和原詩一樣也押了韻。首先,詩的每一行包括10個音節(jié),5個音步對應(yīng)原詩中的5個漢字,整齊劃一;其次,采用了aabbccddee的押韻方式,即每兩句最后的單詞押尾韻,如-en,-ind,-sure,-ther等;最后,吟誦上一輕一重,抑揚(yáng)頓挫,音調(diào)和諧優(yōu)美,再加上樸素簡單的用詞再現(xiàn)了原詩恬淡閑遠(yuǎn)的風(fēng)格。
綜上所述,一方面,風(fēng)格的概念從不同角度理解便有不同的范圍,可大可小,可深可淺。特別是作家的個人風(fēng)格更是如劉勰所說,受“才、情、學(xué)、習(xí)”等主客觀原因的影響,具有多樣性的特點(diǎn)。另一方面,雖文學(xué)翻譯作品風(fēng)格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在當(dāng)今仍是一個爭論,但大多數(shù)學(xué)者用其實(shí)際行動以及翻譯作品證明詩歌風(fēng)格的可譯性,在可譯性的基礎(chǔ)上,詩歌風(fēng)格可通過語言層面,即從遣詞、修辭和音韻三方面來再現(xiàn)。
作者:羅彤;廖昌盛 單位:贛南師范大學(xué)外語學(xué)院
- 上一篇:淺談文學(xué)翻譯中的文化誤讀范文
- 下一篇:淺談早期的文學(xué)翻譯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