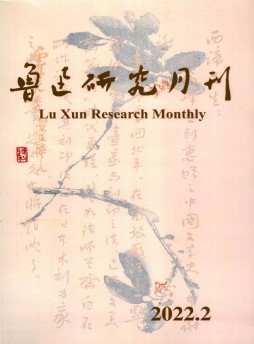魯迅小說中女性人物描寫體現文化背景探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魯迅小說中女性人物描寫體現文化背景探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五四時期,對舊道德、舊傳統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討伐,婦女問題在這次思想大震蕩中占據了突出位置,對婦女的討論出現了空前的高漲。魯迅小說里、雜文里曾經多次表現婦女的生活,描寫婦女的遭遇,控訴婦女的命運,《祝福》、《傷逝》、《離婚》便是其反映婦女問題的力作。
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對自己的小說有過一段說明,他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者的主意。”顯然,對病態文化的批判,以及對在病態文化濡染下女性主體意識的喪失和女性生存慘相的展示,始終貫穿在其女性主義文學作品中,以此揭示社會變革的必要性。
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以來運演的是“父子型”文化模式,女性作為一種文化存在,從自然存在到社會存在到精神存在,都處在“被人看”、“被人用”的角色地位,她們僅僅作為人妻、人母、或“玩物”、“附屬品”等角色進人父系制的家庭秩序,以絕對服從以盡其工具意義上的角色職能,以倍守封建的父權文化和封建禮教的“規范”作為自己的職志。中國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家庭等各個領域處在無權的被人擺布的地位。自從儒教宗師孔子提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男尊女卑思想后,一代又一代儒家文人都在注釋、擴充和強化這一思想,使得女子在這一強大的父權文化覆蓋下漸漸迷失了自我,女性被制度化、道德化地全面剝奪了人權,他們的卑屈地位成了封建專制制度的一部分,是維系中國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顯著特征之一。魯迅正是站在反封建文化的高度,以“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美學追求,塑造了祥林嫂、子君、愛姑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以此表現父權文化栽害、濡染、重壓下的女性屈辱、悲慘的悲劇命運。
對于理解父權文化下女性“非人”化的生存慘相,《祝福》無疑是最具有代表性和認識價值的。《祝福》講述的是辛亥革命前夕江南農村一位勞動婦女祥林嫂命運多并的故事。作為一個處于社會最低層的農村婦女,祥林嫂所受封建父權文化的重壓及其濡染是至深的。父權文化規定下的女性性別角色意識和父權文化套在女性身上的其他精神枷鎖在其身上都得到了集中而鮮明的體現。她對社會把女性角色固定為‘、女兒—妻子—母親”三重復合的理想女性標準視為天經地義,對封建的父權文化意識“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好女不嫁二夫”的“從一而終”的節烈思想深信不疑。作品正是通過祥林嫂悲劇的一生,揭示了父權文化毒害因襲下的不覺醒農村婦女喪失既定角色后的走投無路。
同所有的農村婦女一樣,祥林嫂一向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盡其女人的角色職能獲得婦女最起碼、最“正常”的生活,但因命運的多并,使她最終喪失了其固定的角色地位,這是祥林嫂的第一重悲劇。但更為重要的是,她缺乏“人”的觀念的理性自覺,對封建思想的毒害而不自知,反而無意識的維護,并著意以封建禮教的標準塑造自己,但依然不被社會所承認,這是第二重悲劇。祥林嫂最初是被迫嫁給一個比她小十歲的丈夫,在父權支配下她承認了這個不合理的婚姻。但不久丈夫死去,使她第一次失去了“人妻”的角色地位。在那個時代,出了嫁的女人永遠是丈夫的附屬品,即是男人死了也還是他遺留下來的附屬品,所以她本想格守禮教的規范而守寡,“扎著白頭繩”,愿意為丈夫守孝。她的出逃,固然是對“嚴厲的婆婆”的逃避,也是對自身不幸環境的逃避,她在魯家“整天的做,似乎閑著就無聊”,固然是勤勞能干,但也是失意后孤獨感的寄托。所以,盡管丈夫的死,談不上對她有精神上的沉重打擊,但“寡婦”的身份無疑使其心理蒙受濃重的陰影。“從一而終”的思想使她抵死反抗再嫁,但最終還是給夫家捆綁回去,像一頭牲口似的被賣到山坳里。祥林嫂再嫁賀老六后,盡管有違初衷,但一切都已注定,于是慢慢對其第二個丈夫有了好感。對自己的骨肉、精神寄托—阿毛有了感情。可以說,這是的祥林嫂又一次獲得了自己作為女人的角色,重建了心理上的平衡。但不幸的是,第二個丈夫又死于傷寒,兒子阿毛又被狼銜去。阿毛的死對她是致命的一擊,這種浸透骨髓的悲哀,使她變得精神失常。因為她擔著“失節”的罪名而獲得的生活希望徹底成為泡影。她反復述說阿毛的故事,表露出對自己也曾和別的女人一樣“有過兒子,做過母親”的自豪和失子的負疚自責,當然更是心靈受到重創后心理變態的“失語”。
對于祥林嫂而言,再嫁、喪夫、失子使她喪失了封建文化對女人規定好了的角色職能和理想存在樣式。妻子、母親、“好女人”做不成,但終究還要生存下去,夫家趕她出門,擺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重回魯家“作穩了奴隸”,盡其“被人用”、“被人奴役”的角色,以求得蔽體裹腹之需。但在滲透著濃厚的封建禮教思想的社會環境中,她這種地位也不能保住,因為她被視為“不干凈的女人”。盡管她順從于封建文化的戒規條律,試圖用“捐門檻”贖罪,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最終還是在禮教和神權的束縛下,最低層次上的愿望也不能得到滿足。這次打擊,使其精神徹底崩潰。各種角色喪失后的祥林嫂“百無聊賴”、既沒有了人身歸屬,又沒有了精神寄托,走投無路,只有結束自己的生命,以希望“與家人見面”,在陰間繼續其角色職能,把人間未竟的希望寄托與虛無。
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對漫長的中國歷史下的女性文化存在的畸形作了有力抨擊,對女性因受封建禮教的因襲濡染的生存慘狀作了深刻分析。《祝福》其實就是其思想的形象寫照。正如魯迅其他作品揭示腐朽文化因襲下的“國民性”一樣,《祝福》揭示的是中國婦女長期以來因襲心理狀態下的惰性,意在“揭除病苦,引起療救者的注意。”透過祥林嫂悲劇的一生看出,封建社會的女性存在本是“非人”化的,但廣大的婦女們卻缺乏自我意識,不對父權文化進行反抗,而恰恰是把封建禮教、封建的女性觀和性別角色定位內化為自己的義務,以當時的社會道德為道德,以當時的普遍觀念為觀念,這正是祥林嫂悲劇意義的深刻所在。
在五四時期或五四高潮和落潮時期,知識女性是文學中數量最多、影響較大的一類形象,這類形象的一個顯著標志是暴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惡,表現了知識女性“自我觀念”的覺醒。但是魯迅的《傷逝》卻是借助子君“夢醒后無路可走”的“人生最大的悲劇”,表現了女性生存的艱窘和慘象。
無疑,子君是“自我觀念”覺醒的知識女性形象,她不顧封建禮教的束縛,不顧封建文化濡染下的遺老遺少老東西小東西之流的敵視和狠裹的目光,不顧她“在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親”的干涉和反對,甚至不顧和家庭斷絕關系,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鮮明的帶有沖決封建文化約束的“五四”時代的色彩。這是被“五四”時代個性解放思想喚醒了的年輕知識女性向傳統的父權文化發出的挑戰,是意識到自我價值和尊嚴、認識到“女性也是人”的表現。
但是,在這種男權文化氛圍相當濃重的社會里,女性沒有與男人平等的地位、獨立的人格、獨立的經濟能力,女性即使覺醒,命運也不會有什么改變的。正如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中說:“她除了覺醒的心,還帶了什么去?”的確,以后,社會部分職業向婦女開放,農村婦女由于經濟破產流亡到城市,被工廠主雇用,為的是她們工資低,少數知識女性則被當作“廣告”、“花瓶”,以迎合男子一貫玩弄女性的卑鄙心理。中國婦女仍然在被歧視、被損害、被侮辱的生活中掙扎。魯迅在《關于婦女解放》一文中說:“……她們從閨閣中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是又成為給大家開玩笑,發議論的新資料了,”“這是因為他們到了社會上,還是靠著別人的‘養’,就得聽別人的嘮叨,甚而至于侮辱,”所以“這并未改革的社會里,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是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并無兩樣。”既然社會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在政治生活中,女性沒有與男性平等參與社會的權利,在經濟生活中,女性沒有與男子同樣的就業機會和報酬,女性就不可能真正的有路可走。所以“必須地位同等之后,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消失了嘆息和苦痛”。
因為如此,始于“戀愛自由、婚姻自主”而“覺醒”了的子君,也只能在達此目標后而止步,從而使她雖沖破舊的束縛,卻走向了另一種依附。她和許多犯了時代病的“五四”青年一樣,并未將反封建、反傳統的理性覺悟內化到心理深層中去,真正成為價值規范,傳統的女子治內的思想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依附意識還影響著她。所以她心滿意足地承擔了家務勞動,并為此“傾住著全力”,把所有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涓生身上,把涓生的懷抱視為生命的港口,在小家庭的金絲籠里“麻痹了翅膀,忘卻了飛翔”。這種“捶著一個人的衣角”生活的依附性無疑給她的命運播下了悲劇的種子,所以當涓生面臨失業時,她變得異常的怯弱和消沉,最終還是在生活的壓力下,重回父親家里而孤獨的死去。
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中說過:娜拉走后,“或者也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魯迅在《傷逝》中正是懷著無限愛護和惋惜的心情,以涓生的悔恨和悲哀,反映了父權文化下男女不平等社會中“覺醒”女性無路可走的悲劇命運,更批判了父權文化影響下女性的思想中因襲的傳統重負、封建奴性和弱者意識,以此揭示出時代轉型期女性悲劇生成的歷史、文化、道德倫理和自身原因,以及女性解放的舉步維艱。
魯迅談到《離婚》時說:“這里的愛姑,本來也富有反抗性,是能夠都記下的,可是和《傷逝》里的子君那樣,還沒有長大,就被黑暗勢力壓壞了。如果說子君的悲劇是在揭示父權文化濡染下女性覺醒后無路可走復歸依附的話,那么《離婚》所揭示的就是女性為了自身的地位和尊嚴而向父權斗爭的失敗。
男權社會里,婚姻歷來便是男權至上。男子擁有選擇、占有直至拋棄的權利,女性從屬于男人、受制于男人,男人掌握著“休妻”的權利,而女性又無獨立的經濟地位,只能任男人擺布而忍辱負重地以男人的意志為中心活著,倘若男人有了新歡,一紙休書便能將舊人掃地出門,所以自古以來,我們多聽到棄婦們悲悲切切的哀婉之聲,多看到女性生存的沉重與慘痛。
同是農村婦女,愛姑的性格不同于祥林嫂。她潑辣能干,具有反抗性。她要求婦女有獨立人格,與丈夫平起平坐,她不能忍受妻子的地位被剝奪,反對丈夫納妾或與人餅居。丈夫與小寡婦私通,她就罵丈夫是“小畜生”;公爹偏袒丈夫,她就斥之為“老畜生”;并且表示“我一定要給他們顏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縣里不行還有府里呢。”她把夫家鬧得雞犬不寧;地主慰老爺出面調停,她也拒絕接受;連七大人也不放在眼里。她的反抗的確給人耳目一新、酣暢淋漓之感,使我們看到中國女性反抗封建夫權的精神氣概。但最終還是在浸染著濃厚父權意識的“七大人”們的壓力下被迫屈從,宣告了女性為命運而抗爭的失敗。透過這些,我們可以看出,二十年代的中國,雖然已不是一紙休書便可以結束一次婚姻的時代了,但是封建的父權意識依然禁錮著人們的頭腦,女人依然處于卑賤、被人擺布的地位,毫無獨立的人格和尊嚴。盡管表面看來,愛姑的離婚是那樣的“公正”而“堂皇”,最后夫家再加十元錢,愛姑也愿意,雙方和和氣氣分手。但十塊錢里卻透著愛姑的屈辱和無奈,包含著“七大人”們對婦女地位、人格和尊嚴的踐踏。因為愛姑的離婚,說到底不是自由離婚,而是買賣離婚。
對愛姑來說,離婚是不幸的,在貞操節烈思想依然深重的社會現實中,女性被拋棄,實際上等于生命的終結。因為女子還依賴男子生活,女子再嫁還受社會鄙笑:男子可以另求新歡,逞其“自由”,而女子只有屈辱和苦痛。作品正是通過愛姑抗爭的失敗,深刻揭露了封建禮教和夫權制度的罪惡,反映了男女不平等社會中女性的悲慘命運。同時我們也看到,愛姑反抗的失敗,也是其骨子里的奴隸心態所導致。因受父權文化的濡染,因依然被“傳統”深深禁錮著,她的反抗自始至終是那么蒼白無力。她用封建社會傳統的倫理教條為思想武器來反抗男權社會,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用她自己的話說,她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啊!那么容易嗎?”而且自從嫁進夫家后,“真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可見其反抗父權文化的理論依據還是封建禮教,并不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主體自覺。她反抗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維護封建的綱常倫理,維護住“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為紐帶的婚姻家庭關系,其結局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在舊中國,婦女處在社會的最低層,從婦女角度人手,更能揭示封建文化的腐朽和封建制度的罪惡。《祝福》、《傷逝》、《離婚》先后從三個層面上表現了女性在父權文化濡染下的生存慘相,以此指明社會改革和婦女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