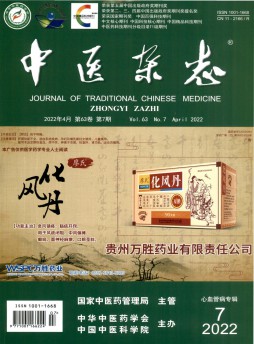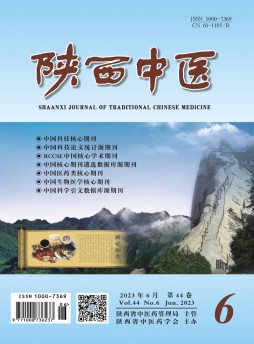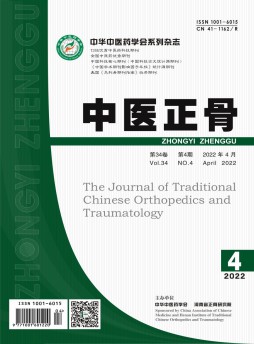中醫(yī)古籍中道家語言文化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中醫(yī)古籍中道家語言文化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中醫(yī)體系建立后,道家、中醫(yī)用語在優(yōu)化重組中傳承文化
醫(yī)籍用語的產(chǎn)生不僅有語言本身的內(nèi)部因素和外部語言因素,還有更廣泛的社會因素,文化發(fā)展導(dǎo)致文字、語言的差異。中醫(yī)古籍用語受到時代用語習(xí)慣的滲透、影響。“晉唐時代,社會治亂相間,政權(quán)頻繁更迭,社會哲學(xué)思想錯綜交替,出現(xiàn)了儒、道、佛紛爭并存的局面。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中醫(yī)學(xué)不可避免地深受這3家文化思想的沖擊和影響。”[2]至遲晉唐后,中醫(yī)用語通過優(yōu)化、重組道家用語,形成中醫(yī)用語特色。研究道家用語的社會背景對醫(yī)籍用語的影響可以使研究視角更加開闊,綜合社會和文化因素,向文化學(xué)角度延伸探討中醫(yī)古籍道家用語的產(chǎn)生、演變。不論從語言學(xué)角度入手來研究文化,還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語言,都可以對中醫(yī)古籍道家用語現(xiàn)象進(jìn)行新的文化闡釋。
1.1醫(yī)家用語在道家語言傳承基礎(chǔ)上的超越自道家思想創(chuàng)興及至?xí)x唐,尤其唐代皇族崇尚老子,道家在唐展達(dá)到鼎盛。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道家、醫(yī)學(xué)關(guān)系也更加密切,但隨著中醫(yī)自身學(xué)術(shù)體系的不斷健全與完善,道家用語融入后被更多地賦予中醫(yī)自身學(xué)術(shù)內(nèi)涵,醫(yī)籍用語形成自身特色,道家用語痕跡變得模糊。孫思邈將醫(yī)學(xué)理論與養(yǎng)生實(shí)踐結(jié)合,《千金要方•食治》:“若能用食平疴,釋情遣疾者,可謂良工,長年餌老之奇法,極養(yǎng)生之術(shù)也。夫?yàn)獒t(yī)者,當(dāng)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后命藥。”孫思邈對食治與藥治的利弊得失分析透徹,指出藥治應(yīng)在食治無效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這顯然是醫(yī)家食治在道家食療養(yǎng)生基礎(chǔ)上的醫(yī)學(xué)闡述。歷代醫(yī)家都以道家養(yǎng)生文化思想為基礎(chǔ),從食療、本草、養(yǎng)生一體化汲取道教藥補(bǔ)養(yǎng)生思想。元代《飲膳正要》服蒼術(shù)方取自《抱樸子》,《抱樸子》中南陽文氏服蒼術(shù)后效果超常,但葛洪仍將蒼術(shù)視為下藥。道家中上藥、中藥多為金屬礦石類藥物,認(rèn)為草木類補(bǔ)益藥只能延年不能成仙屬于下藥。醫(yī)家雖然也吸收道家藥食養(yǎng)生思想,但從醫(yī)學(xué)本體出發(fā)更為理智。醫(yī)家汲取發(fā)揮的多是地黃、蒼術(shù)、茯苓、遠(yuǎn)志、菖蒲、天門冬等草木類藥物對人體治療時的補(bǔ)益功效,道家強(qiáng)調(diào)神仙必有、長生可至等養(yǎng)生觀念并沒有為醫(yī)家接受,醫(yī)家更多是選擇性繼承道家有效藥物的養(yǎng)生經(jīng)驗(yàn),“道醫(yī)相融”兩者互相融合促動。
醫(yī)家經(jīng)典中很多中藥都是道家摸索而形成的經(jīng)驗(yàn)。《抱樸子•仙藥》列上百種藥物,《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本草綱目》收錄了茯苓、麥門冬、枸杞、天門冬、黃精等道家養(yǎng)生常服食藥物,這些藥物同時也成為后來常用中藥。《素問》有四烏賊骨一藘?nèi)阃琛⑹朝煼斤装胂臏?《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將薏苡仁、大棗、芝麻定為上品藥;張仲景《金匱要略》有飲食調(diào)養(yǎng)(禁忌)專篇;孫思邈更是提出“食療不愈,然后命藥”。道家以食療補(bǔ)充人體元?dú)猓浜蠚夤Α?dǎo)引來延年益壽;中醫(yī)食療更注重臨床,以食療調(diào)和陰陽來防病祛疾,藥食同源孕育了中醫(yī)藥文化根基。食療在隋唐達(dá)到興盛,與道家學(xué)說在這一階段的影響力增強(qiáng)有關(guān)。隋唐道家、醫(yī)家同時對食療研究推進(jìn)下,醫(yī)家與道家食療理論逐漸融合,形成五味相調(diào)、性味相勝、以類補(bǔ)類和所宜所禁等觀點(diǎn)。金元四大家劉完素把理學(xué)運(yùn)用到醫(yī)學(xué)領(lǐng)域,其水善火惡論表現(xiàn)出歷代醫(yī)家對道家哲學(xué)思想的基本態(tài)度:以道為本、從道推衍。劉完素在道家“上善若水”基礎(chǔ)上,在《素問玄機(jī)原病式》中結(jié)合醫(yī)理進(jìn)一步提出“水在火下不能制火,為未濟(jì)也。是知水善火惡”,“水善火惡”也是中醫(yī)用語超越道家用語的典型體現(xiàn)。
1.2道家用語文化基因與中醫(yī)用語同化現(xiàn)象中醫(yī)方劑名稱也常常包含道家文化基因。中醫(yī)中一些藥物以“丹”命名,如紫雪丹、至寶丹、紫金丹等;一些方劑稱真人真君所授,或者名稱中兼有神仙、真人、真君等道家人物名稱或道家專用術(shù)語,如八仙膏、玉真散、乾坤一氣膏、呂祖一支梅、紅鉛造化丹、梅花五氣丹等。道家記述經(jīng)驗(yàn)成就有時會大量使用隱語,道教神仙家的外丹術(shù)在唐代達(dá)到極盛,同樣在唐代隨著外丹養(yǎng)生副作用被醫(yī)家所詬病,由盛至衰,道家用語隱語變得晦澀難懂。雖同為“丹”命名的藥物,在醫(yī)藥、文化傳承上加大了難度。“唐代醫(yī)家中僅孫思邈等少數(shù)人將丹方用于醫(yī)學(xué)。”[6]唐代雄黃廣泛應(yīng)用于急救、齒科、外科等。孫思邈《太清丹經(jīng)要訣》有“造赤雪流珠丹法”,從方名看令人費(fèi)解,其核心內(nèi)容為提煉雄黃,用于治療瘧疾以及心痛牙疼。《千金要方》卷12“太一神精丹,治客忤、霍亂、腹痛脹滿、尸疰惡風(fēng)、癲狂鬼語、蠱毒妖魅、瘟瘧,但是一切惡毒無所不治方”,其有效藥用成分“雄黃和雌黃均是含砷的硫化物”,用于治療瘧疾。《千金要方》卷11太一神明陷冰丸、卷12耆婆萬病丸、仙人玉壺丸以及卷24太一追命丸均用到雄黃。藥名雖然都是中醫(yī)常用丹、丸方,如果缺失道家文化背景,理解其用藥成分就很困難。道家用語在醫(yī)籍傳播使用過程又被中醫(yī)用語同化。與《千金》同時期的醫(yī)籍,一些相同或相類方藥在表述時已經(jīng)完全脫離了道家用語的影響,用語方面一目了然,為后世中醫(yī)用語所沿襲。如同樣用雄黃療牙痛,《外臺秘要》卷22殺齒蟲方五首中必效殺齒蟲方:“雄黃末,以棗膏和為丸,塞牙孔中,以膏少許置齒,燒鐵篦烙之,令微熱,以差止。”
2中醫(yī)體系完善過程中,中醫(yī)用語對部分道家語言文化基因的揚(yáng)棄
“道教醫(yī)藥學(xué)大致包括3個部分的內(nèi)容。其核心部分是仙藥、本草、醫(yī)方、針灸等,大致范圍相當(dāng)于世俗的中醫(yī)學(xué)和中藥學(xué)。道教醫(yī)藥學(xué)的中間層部分是導(dǎo)引、按摩、氣法、辟谷、房中、存思、飲食療養(yǎng)及起居禁忌等,這是靠自我攝養(yǎng)和調(diào)諧精、氣、神來防病抗病的技術(shù)。道教醫(yī)藥學(xué)的外層部分是符水、藥簽、祝由、祭祀、齋醮等調(diào)整社會環(huán)境和心理環(huán)境的治療方法,具有強(qiáng)烈的宗教特征。”道家用語玄妙的神秘色彩,隨著中醫(yī)傳播過程大眾化的需求,部分文化基因被曲解丟失。醫(yī)學(xué)文化基因是醫(yī)學(xué)文化系統(tǒng)內(nèi)部的遺傳密碼,在醫(yī)學(xué)理論、治療方式和保健習(xí)俗方面維系著醫(yī)學(xué)認(rèn)同感。最初巫、道、醫(yī)文化基因同源,從道家文化角度理解中醫(yī)用語中一些被曲解、丟失的道家文化基因便有跡可尋。宋明理學(xué)把儒釋道在哲學(xué)上融為一體,實(shí)現(xiàn)了根本性的突破。宋以后主流醫(yī)家否定咒禁術(shù),雖然官方機(jī)構(gòu)里還有書禁科、祝由科,但已微不足道。咒禁術(shù)在中古時代的萎縮體現(xiàn)在操用者規(guī)模的收縮與固定、適用疾病范圍的縮小等方面。至明代,隨著道家思想的逐漸衰微,這一類用語更加難以理解,從醫(yī)籍不同朝代的校訂重刊中可以發(fā)現(xiàn)其脈絡(luò)線索。唐代王燾《外臺秘要》匯集了大量歷代醫(yī)學(xué)文獻(xiàn),版本有宋本和通行本明版。宋本:“又云:覆臥傍視,立兩踵生腰,以鼻內(nèi)氣,自極七息除,腳中弦痛,轉(zhuǎn)筋酸疼。”“生腰”,明版作“伸腰”;又,宋本:“又云:端坐生腰,徐以鼻內(nèi)氣,以手持鼻,除目暗淚出。”“生腰”,明版同樣改作“伸腰”;宋本:“養(yǎng)生方導(dǎo)引法云端坐生腰,徐徐以鼻內(nèi)氣,以右手捻鼻。”
“生腰”,明版亦作“伸腰”。宋版《外臺秘要方》中“生腰”,明本均作“伸腰”。明本所改從字面義更淺顯易懂,且“生”“伸”音近。“生腰”原為道家修煉語,后人漸為生疏,而文中“生腰”義即伸腰,明本中以俗語校改。“生腰”在《朱子語類》卷一二一也有類似用法,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zé)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jiān)強(qiáng)’,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才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yǎng),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可知,在道家修煉時有“生腰坐”與“死腰坐”2種,“生腰”已為后世生疏,醫(yī)籍及校訂多改作“伸腰”。“死腰”更為冷僻,在醫(yī)籍中逐漸被棄用。宋本《外臺秘要方》:“東向三禹步,即以手左攪取水。”“三禹步”,明版作“三兩步”,應(yīng)是明本重訂時對道家詞語的誤讀而造成的錯改。明版中改作“三兩步”,從字面義似乎更好理解,實(shí)際已丟失了本條文化精髓。不僅明代學(xué)者會誤讀富含文化含義的詞語,這也是歷代包括當(dāng)今解讀古醫(yī)籍均需注意的一點(diǎn)。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禹步三,勉一步”,放馬灘秦墓《日書》甲種也有“禹步三,鄉(xiāng)北斗質(zhì)畫地”,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及《養(yǎng)生方》也多次提到“禹步”“禹步三”。道教著作東晉葛洪《抱樸子》記載2種禹步法都是三步,沿襲了《日書》中的“禹步三”。禹步最原始最重要的功能是消災(zāi)去病、驅(qū)除鬼魅,《五十二病方》中“禹步三”都是用來治療諸如狐魅、蟲蛇咬傷、贅疣、癰瘡之類疾病,《抱樸子》指出“凡作天下百術(shù),皆宜知禹步”,《普濟(jì)方》卷二六九:“禁病則皆須禹步。”先秦人尊崇禹,因而巫效法禹步,漢晉也有所反映。禹步即巫步。
后來禹的含義逐漸淡化,至北宋,張君房《云笈七簽》稱禹步“一跬一步,一前一后”象征“一陰一陽”,兩足相承如丁字,“變象陰陽之會”,三步九跡應(yīng)合著“三元九星,三極九宮”的“大數(shù)”。三元指天、地、水;九星指四方及金木水火土五星;三極指天、地、人;九宮指八卦宮和中央宮。禹步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不斷地變更,愈來愈復(fù)雜化,與原始禹步的含義相去甚遠(yuǎn),以致明代重新校刊《外臺秘要》時徹底曲解這一道家用語用義。雖然現(xiàn)存最早醫(y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有“禹步三”“祝曰”等,但祝由在《內(nèi)經(jīng)》中基本被排斥,至葛洪《肘后方》卷三中又出現(xiàn)“祝法”,隋代醫(yī)藥行政中出現(xiàn)咒禁科(祝由科),《隋書•百官志》載設(shè)“祝禁博士二人”;《唐六典》載“太醫(yī)署有……咒禁師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共20人,為數(shù)不少。宋以后咒禁仍得以存續(xù),但沒有隋唐受重視。這一類道家用語在漫長的中醫(yī)傳承過程中出現(xiàn)表述反復(fù),取決于道醫(yī)的外層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被中醫(yī)文化吸收借鑒。這類道家用語多數(shù)在后世中醫(yī)學(xué)用語中消退,導(dǎo)致了這類道家語言文化基因被曲解。成熟的道家思想對中醫(yī)影響非常大,形成2者歷史上相互融合的格局。中醫(yī)是以術(shù)載道的醫(yī)學(xué)體系,中醫(yī)對道家思想的吸收主要從人體生命疾病治療角度進(jìn)行揚(yáng)棄。道家與中醫(yī)的關(guān)系經(jīng)歷了由哲而醫(yī)、由醫(yī)而哲,哲理、醫(yī)理彼此促進(jìn),共同發(fā)展完善。
作者:張繼沈澍農(nóng)單位: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基礎(chǔ)醫(yī)學(xué)院
- 上一篇:中西方宗教文化論文范文
- 下一篇:鴉片戰(zhàn)爭前后的語言文化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