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民事檢察權的正當性與適當性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析民事檢察權的正當性與適當性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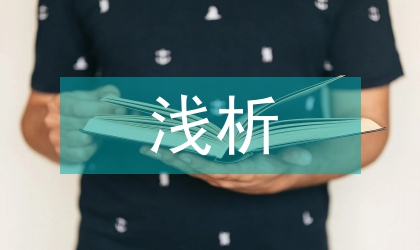
民事檢察權是《憲法》規定的法律監督權在民事訴訟中的具體表現形式,考察其正當性需追溯民事檢察權的歷史淵源,了解其從哪里來;解析其在既定法中的靜態配置,定位其現在的層次與地位。
(一)民事檢察權的歷史變遷
回顧民事檢察權在民事訴訟中的變遷,首先需要拾掇我國民事訴訟制度不同歷史時期的普羅透斯之臉。①根據訴權、審判權、檢察權地位的不同,筆者將我國民事訴訟模式的實踐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超職權主義時期、職權主義時期、當事人主義時期和政策呵護下的當事人主義時期(也可稱為準當事人主義時期)。
1.超職權主義時期(1949-1966年):啟蒙期
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和《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這些法規確定了公開審判、巡回審判、陪審制等審判原則和制度,對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提出了要求。而后,檢察院組織法中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可參與民事訴訟。該時期受蘇聯法律體系模式影響較大,法院和檢察院在民事訴訟中的主要任務是依職權查明事實,法院、檢察院有權代表國家對當事人的各項處分權進行監督,不受當事人處分和請求范圍的限制。但是,限于當時階級斗爭的形勢和檢察機關自身的條件,從全國范圍看,檢察機關參與民事案件的業務開展極少,與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所起的作用相比,民事訴訟中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忽略。
2.職權主義時期(1978-1997年):起步期
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以一個條文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沒有明確抗訴的范圍;198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設立了民事行政檢察廳,實務界重新關注檢察監督問題。1991年《民事訴訟法》增加了兩條關于抗訴的規定,正式確立了檢察機關的抗訴監督制度。而后,各地檢察機關陸續設立民事行政檢察部門,逐步開展民事抗訴監督,其中標志性的案件是1991年新疆伊犁市哈薩克自治州人民檢察院提出的“張某與茍某購銷合同糾抗訴案”和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提出的“富陽村民夏某訴公安局治安行政處罰抗訴案”獲得改判,相繼成為全國首例民事、行政抗訴改判案例。但該階段民事訴訟還是傳承糾問式模式,人民法院需依職權查明案件事實,追求客觀真實,并主導民事訴訟整個過程。檢察機關的抗訴監督處在混沌的摸索階段,抗訴數量不多,監督職能未能充分發揮。如繼民事行政抗訴首例改判后,當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僅受理民事行政申訴2361件,立案644件,結案572件,抗訴9件[3]。
3.當事人主義時期(1998-2006年):質疑期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成熟,學界對市民社會的理論和西方民事訴訟法理念的學習和研究亦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個體權利得到強化。1991年《民事訴訟法》實施后,理論界開始反思職權主義的民事訴訟模式②,對西方純粹的當事人主義表現出了較高的熱情。在學術界的理論呼應下,最高人民法院相繼于1998年、2001年和2002年出臺《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的改革問題的若干意見》、《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人民法院法官袍穿著規定》等,從理論、輿論、實踐、著裝等方面不斷強化審判獨立、民事意思自治、法官自由心證等理念,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2000年間相繼頒布10多個司法文件,規定對人民檢察院提起的對執行程序中的裁定、先予執行裁定、破產還債程序裁定、民事調解書的抗訴不受理。以法律無明文規定為由,拒絕檢察機關抗訴以外的其他監督形式。限制民事行政檢察權的行使和約束當事人訴權的表達。①相反的是,在此階段,民事檢察權在民事訴訟中活動范圍和活動強度不斷擴大,監督效果逐漸呈現。如2003-2005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對認為確有錯誤的民事和行政判決、裁定提出抗訴33340件,人民法院審結18908件,其中改判9919件,調解結案3013件,提出再審檢察建議9943件,人民法院采納4401件[4]。但是,伴隨著檢察監督的深入,對民事檢察權強行介入私權,破壞訴訟平衡,影響法院裁判的穩定性等質疑聲和加強檢察監督、創新矛盾化解機制等呼聲此起彼伏。然而,在協作化解社會矛盾的共同政治壓力和多方原因推促下,檢法兩家加強了交流與對話,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監督的對抗性。
4.準當事人主義時期(2007-2012年):完善期
近十年跳躍式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分層加劇,引發了大量深層次的利益糾紛,司法產品的供需矛盾突出,純粹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在面臨大量社會矛盾時疲態頓顯,國家干預成為一種現實的需求。與此同時,國家在社會科學方面做了重大變革,陸續提出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等概念,繼而大力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在深入司法改革等多項重大政策引導下②,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4年頒布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審判;2007年對《民事訴訟法》局部修改,緩解“申訴難”、“執行難”;最高人民法院倡議能動司法,創新矛盾化解機制,并于2008年相繼出臺《關于適用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有關舉證時限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和大量司法解釋,增架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之間的橋梁,弱化訴訟時效的法定性,增加訴權保障措施。在此階段,理論界關于民事檢察權的存廢爭論逐漸平息,熱點轉為如何規范和完善民事檢察權。實務界的溝通亦取得階段性的共識。典型的如2010年檢法兩家簽訂《關于對民事審判活動與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若干意見(試行)》和兩高三部會簽《關于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加強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③,就民事檢察監督的理念、原則、范圍、方式、手段、效果、協作等作了全方位的協調,并就執行監督進行了試點,民事檢察權隱現出訴訟監督向社會監督延伸的態勢。如檢察機關督促相關部門起訴以維護國有資產、支持弱勢群體起訴以維護社會公平、檢調對接合力化解社會矛盾、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④等等,形成了以抗訴為中心的多元化監督格局。可以說,這一階段的民事檢察權經歷質疑之后,逐漸顯露了其應有的面貌,并發揮了諸多正面的制度效應。2006-2011年抗訴數量維持在10000-15000件之間,再審檢察建議維持在5000-10000件左右。⑤又如,2010年全國檢察機關提出12139件抗訴案件外,對認為裁判正確的44021件申訴案件予以息訴;辦理督促起訴33183件,支持起訴21382件;查辦涉嫌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員2721人[5]。
(二)民事檢察權的靜態配置
民事訴訟普通程序大致的路徑是受理-開庭-裁判-執行,該路徑其實是訴權、審判權、行政權相互滲透,相互抗衡、相互演變之內核在不同階段的表現形式。①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4條“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規定,民事檢察權對訴訟活動的監督,形式上是對訴訟活動參加人的訴訟行為、訴訟形式、訴訟內容、訴訟結果及實現予以監視、督促,本質上是對訴權、審判權、行政權的監督。因此,如果說民事訴權作為溝通公權和私權的橋梁,在本質上可看作為國家權力向民間私權空間的涉入[6],那么民事檢察權巡檢的就是該橋梁的有無、是否通暢以及維護是否到位。
1.訴權監督
訴權是指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和應訴,請求法院以國家審判權保護其實體民事權益的權利。②對訴權的監督包括制約與保障兩方面,制約是指民事主體怠于行使訴權或者濫用訴權時的國家干預,保障是指訴權不能行使或無力行使時的救濟。
(1)督促起訴
民事督促起訴是指檢察機關為保護國有資產或公共利益,督促有關國有資產監管部門或國有單位及時提起民事訴訟,通過法院判決確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行為無效,返還被侵占的國有資產,給予受損害的公共利益法律上的救濟,對違法者一定的民事制裁[7]。實踐中,浙江檢察機關在2002年開始試點督促起訴,著重辦理涉及土地出讓、財政專項資金出借、公共工程招標、重大環境污染等領域的國資流失或公共利益遭受損害案件,2009-2011年共提出民事督促起訴3179件,避免和挽回損失76億余元[8]。對于檢察機關督促起訴職能權能,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并無明文規定,但是可以在該法第13條“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中找到權源,即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不能逾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禁區。
(2)支持起訴
《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該條文帶有一定的道德宣示功能,并沒有明確具體的程序和主體。但社會弱勢群體的重大利益是否能夠得到有效保護涉及到整個社會公平與否,民事檢察權作為一種公權力,針對社會弱勢群體因訴訟成本高,法律維權能力不足時,應提供必要的法律幫扶,以保障其訴權。
(3)公益訴訟
《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條文對檢察機關提起民事訴訟沒有拒絕,也沒有授權,留待將來法律進一步明確,但實踐中多地檢察機關進行了嘗試。筆者認為公害案件,是典型的外部不經濟,即一些人的生產或消費使另一些人受損,而無法補償受損者,此時需要國家干預。就民事訴訟而言,公害案件損害的是公共利益,由檢察機關從訴權監督的角度提起公益訴訟,可以將抽象化的公共利益主體具體化。
(4)虛假訴訟調查
虛假訴訟又稱訴訟詐騙、訴訟欺詐,一般認為是指民事訴訟的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合謀編制虛假事實和證據向法院提起訴訟,利用法院的審判權、執行權,非法侵占或損害國家、集體、公民的財產或權益的訴訟行為,屬于典型的濫用訴權。針對虛假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3條明確“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第56條、第112條、第210條分別設置案外被侵權人救濟制度、虛假訴訟的懲戒措施、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因此,對虛假訴訟的調查,是民事檢察權以國家干預的形式,保障民事訴訟發揮權利救濟和糾紛解決的正當功能,進而維護法律秩序和尊嚴的重要職責。
(5)訴權恢復
訴權恢復是指訴權被屏蔽后的回歸,民事檢察權針對審判權拒絕接受訴權觸碰的情形,應作出必要的約束措施,防止選擇性司法。《民事訴訟法》修訂前,針對當事人的起訴,人民法院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和壓力,通過司法解釋或者會議紀要形式,對某一范圍的案件不予受理,或受理后不立案;收取訴狀后不受理不給答復;以判壓調;超范圍判決等。對此,《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保障和便利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第50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93條、第96條、第122條突出了調解自愿原則,賦予當事人自由處分實體和程序權利。尤其是第123條規定針對訴權被屏蔽現象專門進行了規定,如人民法院應當保障當事人依照法律規定享有的起訴權利,不予受理的應當出具裁定書等等。上述為保障訴權而增加的條文,能否被遵循,需要民事檢察權的監督。
2.審判權監督
民事檢察權對審判權的監督,包括判斷權和指揮權的監督,其直接的法律依據除《民事訴訟法》第14條外,是第208條第三款“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審判監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審判程序中審判人員的違法行為,有權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檢察建議”的規定和第200條、第209條的規定。
(1)訴訟指揮權監督
社會沖突的司法救濟,決定了訴訟的對抗制性質,同時,民事訴訟的私權性質決定了當事人自主性。民事訴訟雖然是解決私權糾紛的程序,但訴訟程序卻并不僅僅是當事人私人的事情,民事訴訟中的平等和對等原則決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對實質性平等和社會公正的追求必然要求法院要對訴訟進行管理[9]。確實,訴權與審判權在民事訴訟中是呈膠著狀態的,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不僅包括對糾紛的判斷,還包括對訴訟程序和規則的依法執行、管理、指揮。典型的如:訴訟保全措施、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審判人員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為的監督。
(2)糾紛判斷權監督
訴權所代表的私權,在司法場域內通過與審判權的對話和抗衡,從而披上國家強制力保障的外衣,是私權沖突化解的傳統模式,也是審判權演繹的主要表現形式。因此,根據既定的程序,依法認定訴爭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作出裁判,化解糾紛,是我國審判權正確表達的題中之意。根據權力制衡的原理,民事檢察權的現實職責就是保障這種糾紛判斷權的良性運行,否則公民保護私權、防衛公權的能力會被剝奪,公權力禁絕私人暴力的正當性基礎隨之動搖。①
3.行政權(執行權)監督
審判程序的結束只意味著當事人的實體權利獲得了法律上的確認,權益的真正實現還有賴于當事人的自動履行或法院的強制執行。在檢察機關有權對刑事執行、行政執行進行監督的前提下,離開民事執行監督,檢察監督的完整性、系統性將會被破壞。對此,《民事訴訟法》在235條賦予檢察機關對民事執行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的權力。
二、民事檢察權的適當性
制度主要依賴一種規范性基礎要素,包括價值觀和規范。所謂價值觀,是指行動者所偏好的觀念或者所需要的、有價值的觀念,以及用來比較和評價現存結構和行為的各種標準。規范則規定事情應該如何完成,并規定追求所要結果的合法方式或手段[10]。《民事訴訟法》對民事檢察權的靜態配置,是一種應然設計,但應然的制度設計并不意味著會產生必然如是的結果。民事檢察權實踐中如何正確運行以維護司法公正,做到既防止審判權行使的恣意和失范,同時又不侵犯私權,涉及到民事檢察權在實然層面如何動態理性演繹,即民事檢察權實際運行中需調整理念、完善機制以及規范手段。
(一)調整理念
1.從“私權救濟”向“公權制衡”轉變
民事檢察權與審判權一樣,是一種公權力,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是以國家系統暴力為威懾的指令性信息;具有膨脹性力量,一直運行到極限;有自我尋租的基礎;容易被人異化[11]。民事訴訟場域中,民事檢察權參與后,呈現兩大公權力(民事檢察權、審判權)對應一個私權利(訴權)的格局。公權力的固有特征致使民事檢察權成為一把雙刃劍:向左干涉審判權引起公權械斗,向右侵犯訴權窒息意思自治。因此,劃定權力的邊界是權力運行前的首要任務。當前實踐中,民事檢察權一般以私權救濟作為切入點,強健私權對抗審判權的體格,突出了審判權與訴權相克的一面,而忽略了相生的一面,或者說侵犯了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常見的如沒有當事人的申訴,主動依職權抗訴;對一審不上訴案件的抗訴;對再審改判數量的追求;協助申訴人調查取證等等。為順應新《民事訴訟法》,民事檢察權應從“私權救濟”轉向“公權制衡”,權力運行目的是制衡審判權,監督審判權是否合理指揮、管理訴訟過程,是否依法判斷糾紛、兌現判斷結論。對私權的救濟應通過對審判權的監督間接予以維護。如:訴權監督方面,督促起訴、支持起訴、虛假訴訟查處、調解過程及結果的監督,應以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為標準;對審判指揮權、執行權監督應以明確的規范為依據,考量審判權、執行權是否違反訴訟規則;對判斷權的監督應在當事人窮盡救濟程序后才可依《民事訴訟法》第200條在規定范圍實施,且不應逾越自由裁量權的邊界。
2.從“實體糾錯”向“解紛止爭”轉變
民事糾紛是平等主體間人身、財產權益失衡,當事人尋求途徑改變從而導致社會秩序不穩定的狀態。解決糾紛就是對這種狀態的矯正或徹底改變,而民事訴訟為糾紛解決的重要手段。從民事訴訟解決的效果來看,可以分為四種情況:(1)利益失衡狀態得到公正解決,當事人也接受此狀態并放棄其它努力;(2)利益失衡狀態沒有得到公正解決,但當事人接受了此種狀態,并放棄以其它途徑解決的努力;(3)利益失衡狀態沒有得到解決,當事人依然尋找其它途徑改變這種失衡狀態;(4)利益失衡狀態雖然得到公正解決,但當事人依然不接受此狀態而繼續尋求其它解決途徑[12]。對前兩種情況,應當視為糾紛已經得到解決,而后兩種情況則不能認為糾紛已經得到解決。民事檢察權在審視審判權是否失范時,應考慮這種失范是否獲得私權的諒解,因此出現第(2)種情形時,民事檢察權不應機械參與實體糾錯,避免重新激發矛盾,除非涉及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因素;對第(4)種情形,則應維護審判權威,配合審判權做好當事人的服判息訴工作;只有在第(3)種情形,民事檢察權才可介入訴權、審判權場域啟動再審程序,或者以其他監督形式緩解訴權對審判權的不滿。
3.從“靜態邏輯”向“動態經驗”轉變
在討論民事檢察權應有的作用時,必須考慮其運行成本。畢竟作為一項公共政策,面對當前轉型期間司法需求劇增的趨勢,缺乏成本意識的司法制度最容易產生功能不全的問題。《民事訴訟法》在司法權的分配上對民事檢察權進行了全方位的布置,民事檢察權伴隨訴權、審判權從受理至執行。但是,司法從來是經驗性的,并不能靠純粹的邏輯演繹,制度應然功能的發揮受制于社會生活的變化、私權個體的多樣性要求、制度發揮的成本等因素,應然與實然經常會出現分離。《民事訴訟法》對執行監督、公益訴訟、檢察調查權、檢察建議的范圍、方式、手段只作原則性的規定,并沒有對其效力及外延進行明確,一方面是因為民事訴訟活動因訴權的意思自治千變萬化,無法逐一設置大前提。另一方面,更多的是考慮民事檢察權沒有先例可遵循,其行使的深度、廣度存在諸多變量,與訴權、審判權磨合的成本、時間缺乏反饋信息,而30年來民事檢察權運行的司法實踐僅能滿足應然方面的設計需求。因此,民事檢察權運行的方式、手段,只能在公權力制衡的原則指引下,通過實踐收集數據,整合信息,不斷調整其運行的軌跡和速度,不能過度剛性。典型的如民事檢察權中的抗訴和檢察建議,其本質是一種程序權,并不對實體權利義務進行分配,類似同行業的評價和規勸,而不是取代和顛覆,更為甚之,這種評價和規勸應保持必要的歉抑,選擇適當的時機和方式。我們需要考量動用多少資源、凝聚多大的同行輿論,才能制肘審判權的恣意,進而找到公正與效率的最佳結合點。當如麥考密克所言:“一種旨在認識法律現象———而不是停留在一種靜止的對可能的體系中的邏輯關系的概括描述上———的法律理論必須研究規范體系在其社會現實中的實際存在。不考慮社會現實———它與規范的存在主義相對應———的法律科學是不可思議的。”[13]
(二)完善機制
《民事訴訟法》將檢察監督從事后的審判監督擴大到訴訟過程監督,將訴訟及執行活動全過程納入監督范圍,為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規定了3個月的審查期限,對公權力輸出社會承諾的質量、效率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需求。為了解決司法服務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在現有資源不可能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只能在服務程序上進行改良,進行存量更新。筆者認為,順應《民事訴訟法》對民事檢察權的要求,當務之急是建立檢察一體化機制,解決效率問題;推行專業化審理,解決質量問題。
1.構建一體化辦案機制,提高效率
(1)一體化辦案機制的概念
一體化模式分為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縱向一體化指利用檢察機關上下級的領導關系,以有權對外發生效力的檢察院為主,統一調配下級院辦案資源,取消下級院的行政審批程序,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彌補地域的物理距離,實行信息溝通的即時性。如:針對二審生效判決的抗訴監督,從立案到抗訴需動用3級檢察機關9名辦案力量。實行一體化機制后,全省民檢部門的人員歸省院統一調配,省院或市院指定一名屬地檢察人員辦理案件,結案后直接給省院處長或組長審核后報分管檢察長批準,全程動用的人員在3-4名左右,可節約50%的檢力。橫向一體化是指同一檢察院內設機構之間的一體化,檢察機關的公訴權、偵查權、抗訴權、建議權等對內而言是專業的分工,對外均歸屬同一檢察監督權,由檢察長行使。因工作的需要,可以統一調配信息資源、人力資源、手段資源,分工而不分家。
(2)一體化辦案機制的必要性
首先,傳統的辦案模式無法適應3個月的審查期限。修訂前的《民事訴訟法》沒有期限的規定,實踐中一個二審抗訴案件受案至結案在檢察系統內部運行的時間跨度少則半年,多則2年,各省級院承受巨大的積案壓力。新《民事訴訟法》實施后,超過期限未辦結的,辦案壓力之上將增加當事人的責問。其次,信訪局對檢察資源的必然性損耗。《民事訴訟法》增加再審抗訴的前置條件和取消二次抗訴,改變原先院長啟動、申請再審、檢察抗訴三門并開的格局,將抗訴監督設置在糾紛法律解決的程序末端,信訪解決的前哨,成為實至名歸的第二信訪局。即:如果人民法院審監庭、立案庭等部門是理性的,申訴案件的前置程序增加了當事人向檢察機關申訴的成本,過濾了部分再審案件,案件數量在檢察機關環節減少的可能性增大,但剩余的糾紛繼續運行,剛性增強,檢察機關化解的壓力增加。如果人民法院審監庭、立案庭是不理性的,糾紛數量未經過濾,直接涌向檢察機關,檢察環節的案件數量將大幅增加。無論案件數量增加還是減少,檢察機關作為信訪前沿服務平臺的地位已是大趨勢。再次,偵查局對檢察資源的可能性消耗。《民事訴訟法》擴大檢察監督的范圍,涵括訴訟全過程,尤其是對人監督和事中監督,需要動用調查權采集信息,核查客觀情況。而民事調查權的大量運用,可能將民檢部門演變為繼反貪局、反瀆局之后的第三偵查局。進而言之,若調查權出現濫用,容易異化為刑事偵查權向私權領域滲透,引起訴權、審判權主體的不安,導致檢察權過剩,背離法律監督的初衷。
2.實行專業化辦案模式,提高質量
(1)專業化辦案模式的概念
專業化辦案是指在縱向一體化的前提下①,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中確定的十大第一級案由,將民檢部門人員進行專業分組,專門辦理對應的民商事案件,在專業知識的人才儲備上與人民法院業務庭保持相對一致的辦案模式。
(2)專業化辦案模式的必要性
首先,民商法的特征需要專業積累。民商法直接反映紛繁復雜的社會交易和變遷,博大精深,浩瀚如海,更新迭出,民行干警辦理的民商案件雜而多,很難對某一類型案件深入鉆研,掌握其前沿理論和規則變換的軌跡,更難以總結類案監督的經驗。經過若干年對某類案件的審查和跟蹤學習,能提高監督的能力和監督的質量。其次,監督權威的樹立需要業務精通。司法并不是自動售貨機,投入大前提和小前提就能產出結論,在糾紛解決的過程中,不僅涉及規范的適用,還牽涉訴訟心理、社會習慣、自由心證等隱含的因素,如果沒有熟練的業務能力和專業的法律儲備,監督過程將引起被監督者的對抗情緒,產生內心的不信服,進而損害檢察權威。再次,引導輿論監督需專業號召力。如前文所述,民事檢察權是一種程序權,不是審判權,作為公權力其與審判權處于相互制衡的地位,并無凌駕審判權的職能。根據博弈原理,抗訴或建議類似同行業內的規勸和評價,并不具有強制力,若要增強這種規勸的實效,仍需引導更多的同行,以同行或社會共識的輿論壓力勸阻失范的權力,動搖其正當性。而號召同行的能力,取決于號召者在行業內的權威,專業、公平、無私等品格和能力。
(三)規范手段
《民事訴訟法》第210條規定了檢察機關因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的需要,可以向當事人或者案外人調查核實情況,但沒有規定調查權的范圍、程序、形式、效力,結合該法67條“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取證,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的表述,民事檢察調查權應具有一定的強制力。根據民事檢察權的性質、目的、任務,調查權應歸依民事訴訟協商、和平屬性,不宜過度剛性而混同于刑事偵查權,除非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審判人員違法。關于調查權的范圍、程序、形式、效力,最高檢應盡快出臺司法解釋,解決調查權在程序上的正當性。在此之前應以省級院為單位制定試行的規范性文件,以統一操作規范。
1.范圍與程序
調查的范圍應包括申訴案件的證據調查和違法調查,前者指案件可能損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當事人在原審中因客觀原因不能收集證據,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調查收集;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或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未經質證的情形。后者包括審判人員、執行人員、訴訟參加人、案外人可能影響公正司法的行為及其性質、情節、后果。程序上應設置被調查人救濟機制及內部審批機制,防止濫用。
2.形式和效力
調查的形式可以包括詢問當事人及證人;查閱、調取、復制書證;現場勘驗、委托鑒定、委托評估、約談法官等,但不得限制被調查人的人身自由或者財產權利,不得以傳喚方式在辦案區域進行詢問,不得妨礙人民法院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涉及刑事犯罪的,可以動用刑事偵查權的手段和方式。效力方面,在審判監督程序中,類似于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取得證據的效力,經庭審質證后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檢察人員可對當事人提出的異議進行說明;在其他程序中,檢察機關依法定程序調查的證據材料,當然具有其法定的效力。(本文作者:胡金龍、張劍鋒單位:浙江省溫州市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處)
- 上一篇:文明縣城創建方案范文
- 下一篇:法學教育改革路徑探索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