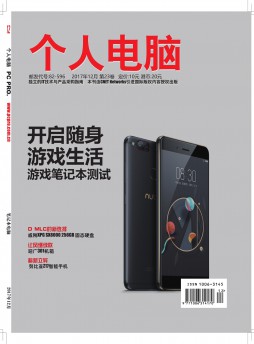個人國際法主體地位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個人國際法主體地位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
關于個人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有三種不同的觀點。其一認為國家是國際法的唯一主體,個人不是國際法主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國際法的客體。其二認為個人是國際法的唯一主體,因為國際權利義務歸根結底都要由個人來享受或承擔。最后一種觀點認為,國家是國際法的基本主體,個人在某種限度內可以成為國際法的主體。第二種觀點過于絕對和激進,筆者主要討論第一種觀點和第三種觀點。
二
在具體討論個人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之前,回顧一下國際法主體的涵義是很有必要的。韓成棟、潘抱存主編的《國際法教程》中是這樣規定的,“所謂國際法主體,就是指那些能夠直接承受國際權利與義務的國際法律關系參加者”。在具體說明這個定義的涵義時,該教程指出,國際法主體必須構成國際社會中地位平等的實體,自然人和依據國內法所設立的法人在國際關系平面上不具有與國家相等的地位,所以不是國際法主體。該定義雖使用了“國際法律關系參加者”字眼,但實際上它仍然沒有脫離要求國際法主體是國際關系特別是國際政治關系參加者的傳統觀念。事實上,在國際社會中法律地位平等的實體只能是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國際組織的法律地位是不相同的,更不用說視國家與正在爭取獨立的民族和交戰團體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不合理性,后者不過是一種過渡形態的暫時的有限的國際法主體。當然,它們在國際立法上都有大小不等的參加權,都是立法性國際法主體,它們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范圍大小是各不相同的。
最近王鐵涯先生主編的《國際法》對國際法主體是這樣定義的:“國際法主體是指獨立參加國際關系并直接在國際法上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并具有獨立進行國際求償能力者”。(注:王鐵崖主編:《國際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頁。)這一定義預先排除了那些不能獨立參加國際關系但能直接在國際法上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且有獨立國際求償能力者成為國際法主體的可能性。這種國際法主體概念與否認個人直接承受國際法上權利義務從而成為國際法主體的理論以及認為國際法上的客體為國內法上的法律關系的理論相聯系。他們認為“個人作為國際罪犯受到國際法懲處這一事實也只能說明他們是國際法懲處的對象,并恰恰說明他們是國際法的客體”。
我們不妨類比一下,個人作為國內罪犯受到國內刑法懲處這一事實,也只能說明這些人是國內刑法懲處的對象,并恰恰說明他們是國內刑法的客體。上述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趙廷光教授指出,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是確定的,一方只能是實施犯罪行為的犯罪人,另一方只能是國家。(注:趙廷光主編:《中國刑法原理》(總論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頁。)國家作為處罰者,始終處于主導地位,但它并不能將犯罪人降格為客體。
再回到他們的觀點上來,假如國家觸犯嚴重的國際罪行如反人道罪反和平罪而被國際法懲處這一事實是否能如他們推理那樣,“恰恰說明國家是國際法的客體呢?”這種國際法客體國內法主體的理論不符合國際法作為法律在法律關系主體上應表現出的一致性與統一性,與一般人的理念相去甚遠,難以令人接受。其實,不是個人是國際法的客體,而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國際刑事法律關系構成國際立法法律關系的客體。個人在具體的國際刑事法律關系中構成與國家不相對稱的法律關系主體。
持該國際法主體觀點的人也否認個人能直接取得國際法上的權利,他們認為個人依條約取得國際法上的權利不過是國家間的權利義務。實質上,他們混淆了國家與國家之間以權利義務關系為特征的國際立法過程與個人依所立法律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從事法律規定的行為而成為該國際法律關系主體這一事實。個人可以援引條約中“明確的無條件的不需國內或其它補充立法”的規范作為權利主張的依據,而在個人引用經轉化的國內法規范主張權利時,它的源頭仍在國際條約。況且,這一定義并不足以排除個人成為國際法主體的可能性。根據已生效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我國于1996年5月批準)第153條規定,在國際海底區域實行“平行開發制度”,為此公約第187條和附件六第38條還作了相應規定,允許個人和國家一道參加國際海底區域的勘探和開發活動,允許他們進入國際海洋法庭海底(爭端)分庭成為訴訟當事方。顯然,個人和國家嚴格遵照《海洋法公約》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進行開發活動,不能認為國家參加該開發活動是參加國際關系,而個人(法人)在相同情況下參加開發活動就不是參加國際關系,個人(法人)獲準成為國際訴訟當事方,他們就有主動開啟訴訟程序,實現國際法賦予他們的權利和承擔國際法可能加之的義務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一種完全的國際訴訟能力,當然包括獨立國際求償能力。按照前述定義,此種情況下個人的國際法主體地位不應被否認。
有的學者從國際法律關系角度來定義國際法主體。葉叔良先生認為“國際法主體就是國際法律關系主體,也就是在國際法上享有權利(包括訴訟之權)和負擔義務和責任者。”(注:李浩培:《國際法的概念和淵源》,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頁。)李浩培先生則指出,“國際法主體是其行動直接由國際法加以規定因而其權利義務從國際法發生的那些實體”。(注:黃炳坤主編:《當代國際法》,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3頁。)這一概念非常靈活,它繞開了傳統的國際關系參加者的定勢要求,直接以國際法的有關規定判斷何為國際法主體。這一概念即包括了傳統的國際法主體如主權國家又能容納二戰后逐步確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國際法主體地位,同時也不排除直接由國際法所調整的某些特別關于個人的法律關系中個人成為國際法主體的可能性。例如,國際組織與其雇員關于勞動合同的糾紛都是由相應的行政法庭來解決的,法庭在判決中只能依據國際法包括國際組織的內部“行政”管理法來處理案件。雇員與國際組織的勞動合同關系已經脫離了所有國家的管轄權,直接成為國際法調整的內容,雖然這種關系類似國內法上的勞動法律關系,但事實上它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國際法律關系,而雇員作為該法律關系的主體是無庸質疑的。
三
從國際法律關系角度看,個人作為國際法主體必須能夠直接承受國際權利義務。個人能夠直接承受國際法上的義務在紐倫堡軍事法庭審判中明白無誤地確立起來。該法庭指出,“……國際法對于個人和對于國家一樣,使其負擔義務和責任,這點久已為人們所承認,……另一方面,《憲章》的精神是,個人負有其在本國所加服從之上的那種國際責任,違反戰爭法規的人,在其依照國家授權行動的時候,如果國家授權越出國際法所定的權限者,不得享受豁免”。聯合國大會于1946年12月11日通過第95(1)號決議,肯定了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及其判決體現的原則。二戰以后,聯合國參予制定了關于國際犯罪的公約,并積極編纂《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法典》。最近建立的專門性國際刑事法庭正審理波黑戰爭中違反國際法應負國際刑事責任的個人,判決了一批戰爭罪犯,重申個人可對國際法直接承擔義務的立場。
個人也可以直接取得國際法上的權利。國際常設法院在關于但譯問題法院管轄權案件中發表咨詢意見,指出“國際法并不阻止個人直接取得條約上的權利,只要締約國有此意圖。”(注:LouterpachtColleetellPapers.Voll.P142.)現在的國際實踐有將共同或類似國內法規范上升為協定國際法的統一實體法規范的趨勢,從而個人以往從單邊涉外法律取得的權利上升為以條約形式規定的國際法上的權利。某些國家以國際習慣法或其參加的國際條約作為國內法的一部分的作法,也賦予本國公民國際法上的權利。
國家賦予公民法權利要求個人擔當國際責任是有原因的。就個人承擔義務來說,最古老的恐怕是對破壞海洋自由的海盜的懲治,海盜被認為是人類的公敵,不授予沿海國捕獲海盜的權利,不從國際法上禁止個人作海盜行為,就無法保持公海上的秩序。到現代,又出現了大規模針對國際社會和平安寧以及秩序的穩步和平演進的犯罪如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侵略戰爭罪,施行這些罪行的有國家也有個人,而國家的犯罪行為也是通過個人完成的。這些罪行動搖了國際社會的基礎,危害了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不加諸犯罪人以國際法上的責任不足以懲誡后來者。這是個人成為國際法責任主體的主要原因。此外,原屬一國國內的普通犯罪的跨國化、國際化同樣危害著國際社會的利益。這些行為都是個人(法人)所為,依任一國內法他們都應負刑事責任,因而國家之間不難在這方面達成共識,以條約、國際習慣的形式規定此等人的法律義務。
至于國家為何依條約賦予個人以國際法上的權利,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這種依條約享有的國際法上的權利是締約國國內法所承認的,或者在條約的過渡安排后可以有效保護的,以條約形式承認這些權利,有利于保護處于另一或另幾個締約國的本國公民的正當利益。在用盡當地救濟手段后,可以借助較客觀公正的國際司法機關解決爭議問題。
其次,承認個人在條約上享有一定的權利并不會削弱國家對個人的最終控制和保護。在多大范圍和何種程度上落實個人在條約上的權利是由國家決定的,同時國家對國際法庭的影響比個人的大得多,它可以派遣專案法官,影響國際法庭的組成,在法庭上熟練地運用程序規則。從實踐上看,國際司法機關的裁決并不一般地有利于個人。
最后,有的國家將一部分權利交給了一體化國際組織,該國際組織深刻影響著締約國個人的權利,作為救濟手段,國家以條約形式賦予個人向國際行政和司法機構申訴、訴訟的權利。尤以歐盟法院的實踐為典型,個人可以起訴成員國,執委會也可以起訴特定個人和成員國及歐盟其它機構(除歐盟法院ECJ和CFI)。
四
國家賦予個人以國際法上的權利是否意味著國家承認在此權利范圍內個人享有國際法主體地位呢?阿庫斯特指出,國家可以賦予個人以國際權利來承認個人是國際法主體,國家也可以通過不給予個人任何國際法上的有效權利來防止個人取得國際人格。(注:阿庫斯特:《現代國際法概論》,汪暄、朱奇武等譯,1981年,第86—87頁。)勞特派特指出,“許多國內法體系所采用的以國際法為國內法一部分的學說,分析起來也是一種因素,足以表明國際法可以直接適用于個人,而個人在這個限度內就成為國際法的主體。”(注:富學哲:《國際法教程》,第64頁,引勞特派特修訂之《奧本海國際法》。)上述兩種觀點似乎認為只要國際法賦予個人以直接的權利,個人就可在以此限度內成為國際法主體,而不問此等國際法上權利之實現形式。葉叔良先生則指出,要證明個人是國際法律關系主體,個人在國際法上權利義務之實現要能夠通過訴諸國際法庭或仲裁庭形式。“如果我們能夠證實一方面個人享有國際法(包括國際習慣和條約)上的權利,并得以個人以自己的名義不通過其本國或本國國內法直接訴諸于國際性法庭或仲裁庭、主張或并行使國際法上的權利,他方面個人又負擔國際法上的義務,怠于履行義務時,直接負擔國際法上的責任,那么個人是國際法上之主體應該被證實。”(注:黃炳坤主編:《當代國際法》,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3頁。)
個人在多大限度內成為國際法的主體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主張個人是國際法主體的學者的看法不大一致是很正常的。一般來說,在葉先生這個驗證公式所闡明的限度內,個人普遍被認為是國際法主體。我國在實踐中也出現了傾向于承認個人在有限范圍內享有國際法主體地位的作法。我國早已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并于1996年批準了已生效的該公約,于是我國不得不面對公約中關于個人(法人)在國際海洋法庭海底分庭的起訴權的規定。1990年我國加入了《關于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議公約》,依該公約規定,締約國可以和其它締約國國民達成協議,將由投資產生的爭議提交公約設立的調解與仲裁國際中心。我國批準并加入該公約主要是為了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它在客觀上也起著保護我國海外投資的作用,賦予了我國個人(法人)利用該公約對另一或另幾個締約國提起仲裁程序,保護其自身正當利益的國際法上的權利。批準和加入該公約表明我國認真考慮與個人一同參加國際仲裁程序的必要性以及對他國國民可享有國際法上的權利之承認。
這種態度的轉變在學說上有所反映。李浩培先生指出,個人是國際法的部分主體;個人的部分國際法主體地位依賴于各主權國家的意志;由于一些主權國家以條約規定個人具有部分國際法主體地位,個人才取得這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