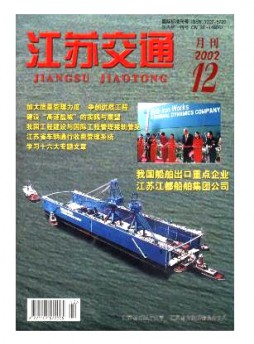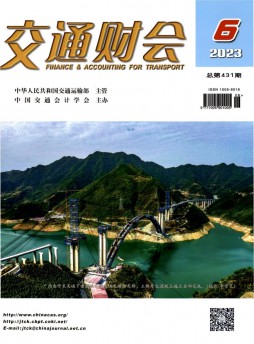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處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處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筆者有幸拜讀《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可訴性》一文,從中受益非淺。但在贊同作者大部分觀點的同時,筆者對其中的一些觀點也有自己不同的認識。為了使觀點能夠更加鮮明充實,所謂“真理越辯越明”,本人有意針對作者的一些觀點提出自己的一點不成熟的認識,以供讀者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該文的主要觀點
為了使讀者能夠了解該文的主要觀點,在此先對該文做一個概括。該文分三部分:
1.“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性質(zhì)”。作者認為,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完全符合具體行政行為所應(yīng)當(dāng)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屬于公安機關(guān)的法定職責(zé),是某一公安機關(guān)在某特定時間,就某特定的交通事故依職權(quán)作出的一種行政行為。該認定只適用于該交通事故及有關(guān)當(dāng)事人,它能夠產(chǎn)生行政法意義上的法律效果,有可能成為公安機關(guān)對違章者作出行政處罰的依據(jù)。作者進一步指出,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屬于行政確認。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不直接確定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不產(chǎn)生實際的法律效果,而只是交通違章行政處罰的先決條件。
2.“行政行為可訴性的思考”。該部分的內(nèi)容可概括為如下幾個要點:(1)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包括法律上的可訴性和事實上的可訴性,它是確定某一行政行為是否屬于行政訴訟受案的范圍的雙重標準。關(guān)于法律上的可訴性,作者認為,除了明確排除的抽象行政行為、國家行為、內(nèi)部行政行為和終局行政行為以外,其他的具體行政行為都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關(guān)于事實上的可訴性,作者指出,事實上的可訴性是以行政行為是否對原告的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了實際影響作為確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最終標準。(2)在確定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時,綜合考慮被訴行政行為法律上的可訴性和事實上的可訴性是許多國家的通常做法。目前,我國行政法學(xué)界和司法界在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上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只重視行政行為法律上的可訴性,而忽視了事實上的可訴性。(3)行政行為可訴性的可變性。作者認為,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行政行為的作出是一個過程,形成該過程的行政行為可進一步分解為幾個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階段性行為”;行政行為既可以作為一個整體,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同一個法律效果,各個階段性行為也可以單獨對相對人的某個方面的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不同的法律影響,因此,行政行為的可訴性隨著行政行為的階段性和法律影響的相對性而有所不同,行政相對人針對不同階段的行政行為及對自身權(quán)利義務(wù)的不同影響,可以提出不同的訴訟請求。
3.“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實例分析”。在該部分中,作者認為,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具有法律上的可訴性,但對其事實上的可訴性要區(qū)別對待、具體分析。(1)如果公安機關(guān)不履行對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法定職責(zé),具有事實上的可訴性,當(dāng)事人可以不作為為由,向法院起訴,請求責(zé)令公安機關(guān)履行法定職責(zé);(2)如果公安機關(guān)在作出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過程中程序違法,則使相對人的程序權(quán)利受到影響,相對人可以此為由提起撤銷之訴;(3)相對人單獨就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內(nèi)容提起訴訟,則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者認為,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未產(chǎn)生實際影響,是一種不成熟、未完成的行政預(yù)備行為;在一般情況下,總是先有交通責(zé)任認定,然后才有對事故責(zé)任的違章行為的行政處罰。在行政處罰作出之前,相對人與認定之間不具有提起行政訴訟所必須具備的法律上的利害關(guān)系。作者還認為,如果法院對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內(nèi)容進行實質(zhì)性審查,并作出判決,不僅有悖于行政訴訟法關(guān)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有關(guān)規(guī)定的精神,而且必然與相關(guān)的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發(fā)生矛盾。在因交通事故提起民事?lián)p害賠償訴訟中,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僅作為民事訴訟證據(jù)的一種形式,只有經(jīng)過庭審質(zhì)證、認證,才能決定是否采信;在刑事訴訟中,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也不能直接作為對肇事者定罪量刑的事實依據(jù),人民法院也要重新審查后才能決定取舍。
二、筆者的幾點認識
近階段,因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而引起的行政案件越來越多。法院在審理這類行政案件時,往往會遇到公安機關(guān)的一定抵觸。公安機關(guān)認為,對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公安行政機關(guān)有終局裁決權(quán),不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人民法院無權(quán)對其進行審理。因此,在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作為被告的公安機關(guān)往往無故缺席,造成案件審理的被動。關(guān)于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可訴性問題,理論界仍存在爭論,實踐中各地的作法也不盡相同。有的地方法院不受理該類案件。該作者在上文中關(guān)于此問題的相關(guān)觀點對于解決實踐中的一些不明確的、不統(tǒng)一的作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指導(dǎo)意義,其中的一些觀點不乏獨到之處,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但筆者也對作者的一些觀點有不同的認識,在此不防由感而發(fā),提一些不成熟的觀點,以供探討。
1.關(guān)于行政行為法律上的可訴性和事實上的可訴性問題。該文作者認為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具有法律上的可訴性,但由于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未產(chǎn)生實際影響,不具有事實上的可訴性,因此,相對人單獨就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內(nèi)容提起訴訟,則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對此觀點筆者不敢茍同,不可否認,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包括法律上的可訴性和事實上的可訴性,但是,不能以行政行為事實上的不可訴性來否定其法律上的可訴性。法律上的可訴性是確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明確的、最先依據(jù)的標準,事實上可訴性,只是法律上可訴性的補充,只有在無法確定行政行為法律上的可訴性的情況下,才能通過其事實上的可訴性來確定其最終是否可訴。法律上的可訴性和事實上可訴性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之所以存在事實上的可訴,是由于行政訴訟法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無法作出窮盡規(guī)定所致,判斷某一行政行為是否具有可訴性,應(yīng)首先以法律明確規(guī)定為標準,如果法律沒有明確性規(guī)定,則可通過事實上的可訴來解決。反之,如果法律明確規(guī)定某一行政行為具有可訴性,則不必要再考究其事實上的可訴性,更不能以事實上的不可訴來否定法律上的可訴。法律上可訴性是法律明確賦予人民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權(quán),以事實上的不可訴性來否定法院的審查權(quán)不妥。筆者認為,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既然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在我國有關(guān)法律并未對此類行政行為作出明確的排除性規(guī)定的情況下,其具有可訴性是毫無疑義的,不能以其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未產(chǎn)生實際影響,即事實上的不可訴性來否定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
2.關(guān)于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是否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實際影響的問題。該文作者認為,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不直接確定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不產(chǎn)生實際的法律效果,而只是交通違章的行政處罰的先決條件,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未產(chǎn)生實際影響。筆者認為,如何確定某一行政行為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是否產(chǎn)生實際影響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判斷某個行政行為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是否產(chǎn)生實際影響不應(yīng)以行政行為是否直接確定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為標準。如果某一行政行為已經(jīng)直接確定了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其當(dāng)然也就影響了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還有去考究其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是否產(chǎn)生影響的“實際性”的必要嗎﹖筆者認為,在行政審判中,判斷或者需要考究某一行政行為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是否產(chǎn)生實際影響時,該行政行為須存在下列情況:(1)該行政行為沒有直接確定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理由不再贅述。(2)該行政行為“已經(jīng)”影響到了相對的權(quán)利義務(wù)。雖然,行政行為沒有直接確定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但是,由于該行政行為的實施或其他原因,已經(jīng)客觀上存在了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影響的事實,即已經(jīng)實質(zhì)改變了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3)該行政行為將來“肯定”會影響到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雖然,行政行為沒有直接確定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行為實施過程中也沒有實際影響到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但,一旦行政行為的結(jié)果得到確認,則肯定要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影響。就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而言,雖然沒有直接確定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但是,由于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是確認當(dāng)事人事故責(zé)任的一種行政確認行為,它的實施效果不在于“認定”過程中,而在于“認定”之后。在當(dāng)事人的事故責(zé)任得到確定之后,將成為公安機關(guān)對責(zé)任人進行行政處罰、受損害方提起民事?lián)p害賠償訴訟和人民法院對肇事者定罪量刑的有效證據(jù)和事實依據(jù)。因此,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是一種肯定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影響的具體行政行為,不能以其沒有直接確定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為由來判斷其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未產(chǎn)生實際影響。新晨
3.關(guān)于行政行為的“變數(shù)”問題。從該文第
二、三部分可見,作者將行政行為割裂開來,認為行政行為在某一個階段是可訴的,在另一個階段可能是不可訴的。認為公安機關(guān)不履行對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法定職責(zé)或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程序違法時具有可訴性,而相對人單獨就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內(nèi)容提起訴訟,則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筆者對此有不同認識,且不說這種將行政行為割裂開來的作法是否妥當(dāng),在審判實踐中就無法操作。如果將一行政行為分為幾個階段,認為某一階段可訴,另一階段則不可訴,也就是講,對一個行政行為,一部分可由人民法院來審查,另一部分則要由其他部門來處理,那么,行政行為作為一個整體對相對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所產(chǎn)生的整體法律效果如何解決﹖最終該由哪一個部門來裁決呢﹖筆者認為,行政訴訟的最終目的,即其立法宗旨,是實現(xiàn)司法權(quán)對行政權(quán)的限制,行政法律規(guī)定行政行為的可訴性,應(yīng)是就行政行為的整體而言的,人民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應(yīng)是全面性,包括行政行為實施的始終及其產(chǎn)生的法律后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xiàn)司法權(quán)對行政權(quán)的限制,否則有悖于行政法律的立法精神。
另外,就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而言,當(dāng)事人就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的內(nèi)容單獨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進行實質(zhì)性審查并作出判決,與相關(guān)的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并不矛盾。在因交通事故提起的民事?lián)p害賠償訴訟和刑事訴訟中,可以直接引用法院的生效判決所確定的內(nèi)容作為證據(jù),不必要再經(jīng)過庭審質(zhì)證、認證就可以采信。況且,在民事或刑事訴訟中再回過頭來調(diào)查交通事故當(dāng)時的責(zé)任,很難保證其真實準確性。由此也可見,對交通事故責(zé)任進行及時、準確、有效的認定,對相關(guān)當(dāng)事人而言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