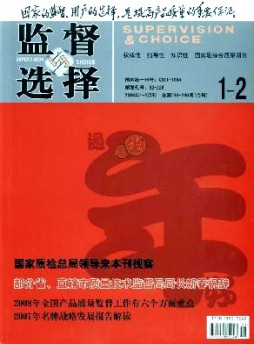監督過失罪設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監督過失罪設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要:我國《刑法》中,業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主要體現為分則第二章的各種責任事故犯罪,但職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則被第九章的玩忽職守犯罪所替代。司法實踐中,許多原本屬于職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的犯罪,或者被認定為“領導責任”,不追究刑事責任,或者以玩忽職守論罪。為了矯正這一缺陷,我國《刑法》應當在職務關系領域專設“監督過失罪”
關鍵詞:監督過失;領導責任;玩忽職守
一、監督過失罪內涵的界定
(一)監督過失的理論源起
監督過失的概念包括狹義的監督過失和廣義的監督過失。所謂狹義的監督過失,是指處于指揮、監督地位的行為人(監督人)怠于履行監督義務,致使直接行為人(被監督人)的行為發生危害結果的情況。廣義的監督過失,指狹義的監督過失之外的包括管理過失的過失。①管理過失是否屬于監督過失,學者持不同觀點。②本文姑且回避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僅在狹義上討論監督過失問題。
監督過失理論最早由日本學者提出,其產生有著深遠的社會背景。上個世紀中后葉,戰后的日本經濟處于迅速恢復并急速膨脹的時期,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新技術的廣泛運用,同時帶了來新的社會問題,環境公害問題日益凸顯,各類重大責任事故頻發。大多數責任事故中,直接行為人因存在罪過而需追究刑事責任自不必待言,但是在生產經營中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管理者和組織者,因過失未盡監督管理義務應否追究刑事責任呢?若不予追究,顯然于情不合、于理不符。但予以追究又缺乏法理依據,因為按照日本當時的過失犯理論,過失構成犯罪的條件之一就是行為人對結果預見義務之違反(舊過失理論)或者對具體的結果避免義務之違反(新過失理論),而高新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背景下,認定行為人對具體危害結果有預見可能性或者避免可能性非常困難。為了破解這一“囚徒困境”,日本判例法突破傳統,在危懼感說(新新過失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監督過失理論,其以1973年“森永公司奶粉中毒事件”最具代表性。③在這起致多名嬰兒砷中毒的事件中,高松高等裁判所最終以業務過失致死傷罪做出有罪判決。該有罪判決旗幟鮮明地采用了過失犯理論之危懼感說,認為對藥店將“松野制劑”作為磷酸氫二納出售雖然是不能預見的,但是在購入了與預定不相同的物品時,使用這種物品應當有不安感,這種不安感就是對危險的預見。自此以后,監督過失理論在日本刑法學界得到廣泛探討。
(二)監督過失的表現形態
監督過失在日本刑法理論中僅體現在業務關系中。業務過失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兩個范疇,廣義上的業務過失包括狹義上的業務過失和職務過失。狹義上的業務過失一般是指發生在特殊業務中,行為人由于“怠于業務上必要的注意”④,使犯罪事實發生的場合。職務過失側重于指公職人員在對國家事務管理過程中,由于疏忽大意、不負責任的原因,給國家和社會的利益造成嚴重損失,依法應受刑事處罰的情形⑤。關于監督過失的適用范圍,日本刑法理論中有一種比較一致的認識,即“監督過失是一定業務活動關系中的過失犯罪,在業務活動關系以外不存在監督過失”。⑥因此,日本刑法理論中的監督過責任不存在于職務關系領域,僅體現為業務關系中對負有監督管理責任的生產經營管理者的責任。
監督過失在我國《刑法》中不僅體現在業務關系領域,也體現在職務關系領域。監督過失理論介紹到我國是晚近之事,關于我國《刑法》對該理論是否有所體現的問題,學者有不同看法。有的學者持否定說,認為“我國目前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實踐中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監督過失責任的存在”⑦。不過總體來看,大部分學者持肯定立場⑧。本文贊成肯定說,并且認為我國《刑法》對監督過失理念的體現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刑法》第134條“重大責任事故罪”、第135條“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等條文中,相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管理人員、實際控制人、投資人等,對直接從事生產作業行為人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都直接地體現出監督過失理論。不難看出,這些條文中的監督過失責任,都屬于業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犯罪。第二個方面,第408條“環境監管失職罪”、第409條“傳染病防治失職罪”等條文中,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及“從事傳染病防治”等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為嚴重不負監管責任,由被監管人的行為導致發生重大事故的,除被監管人承擔刑事責任外,監管人也應承擔刑事責任。這明顯也蘊含著監督過失理念。不過這類監督過失屬于職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
盡管上述兩類監督過失責任在我國《刑法》中都分別表現為一定的具體罪名,但它們與這些罪名之間的關系還是有所區別的:前者中的各種行為屬于業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他們與監督過失之間屬于具體與抽象、特殊與一般的關系,二者在形式上和內容上是統一的;后者中的各種行為屬于職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但卻被冠以各種玩忽職守的罪名,如下文所述,監督過失與玩忽職守有著本質差異,所以,這是一種訛誤,有張冠李戴之嫌。基于此種區別,立法上應當對這兩類監督過失犯罪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一方面,出于立法經濟性和延續性的考慮,我國《刑法》應當保留這些罪名;另一方面,出于名實相符的考慮,我國《刑法》應當將這些監督過失犯罪從玩忽職守罪中獨立出來,單獨設立新罪名,即“監督過失罪”。
由上述可見,本文所主張的“監督過失罪”,僅限于職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專指那些負有直接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公職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被監管者的行為發生重大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公共衛生等事故,致使公私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
二、我國設立監督過失罪之現實必要性
我們先來考察一則案例。該案是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新窯煤礦“1215”特大爆炸事故案。2007年12月5日23時15分,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瑞之源煤業有限公司新窯煤礦井下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導致105人遇難、數十人受傷。事故發生后,相關責任人、瑞之源煤業有限公司(原新窯煤礦)和被告人王東海、王宏亮等19人被依法提起公訴,臨汾市市長李天太等人被追究行政責任。⑨這起震驚全國的特大責任事故的處理結果在我國當前類似事故的處理中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從這些事故處理來看,在我國實踐中,對于事故負有直接監管職責的國家公職人員,要么不認為是犯罪,僅以追究“領導責任”、科處行政責任了事;要么認為構成犯罪,卻以玩忽職守罪論處。那么,這兩種方式能否實現預期規制效果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一)“領導責任”不能替代刑事責任的追究
首先,“領導責任”有悖于罪刑均衡原則。根據日本刑法理論,監督過失理論是建立在
危懼感說之上的,行為人的“注意義務”要高于普通過失犯,其責任也應當重于普通過失責任⑩,這已是刑法理論的基本共識。所以,以“領導責任”替代刑事責任的做法,似有包庇“領導者”之嫌。同時,同樣處于監督者的地位,同樣存在監督過失,也不應只由生產經營管理者承擔刑事責任而國家公職人員僅以承擔“領導責任”了事。可見,以“領導責任”替代刑事責任,會導致“責任倒掛”的現象,易生“頭部無罪而手腳有罪”⑾之弊,違背罪刑均衡原則。
其次,“領導責任”不利于各類安全責任事故的防范。2007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廳披露了《檢察機關立案查處事故背后瀆職犯罪情況報告》。該報告列舉了礦山責任事故中瀆職犯罪的七種表現形式,并指出,此類事故的發生,與負有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采礦安全生產監管過程中放棄監管職責,乃至濫用職權的瀆職犯罪行為密不可分。高檢院瀆檢廳負責人分析認為,預防和減少重大責任事故、重大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必須特別注重查辦事故涉及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職務犯罪⑿。因此,如果僅以“領導責任”替代刑事責任的追究,容易造成某些地方主管部門對責任性質的模糊認識,不利于從源頭上防范和杜絕各類責任事故的發生。
(二)玩忽職守不能替代監督過失
既然“領導責任”不足以替代刑事責任,那么應當追究何種刑事責任呢?當前普遍采用的追究玩忽職守罪的做法是否合適呢?對此,我們持否定觀點,認為相關負有直接監管職責的國家公職人員的行為應當屬于監督過失犯罪,而玩忽職守與監督過失有著本質區別,以前者替代后者,實有張冠李戴之嫌,有違罪刑法定原則。二者區別大體如下:
首先,基本構造的差異。玩忽職守罪屬于普通的職務過失犯罪,其基本構造一般可以表述為:公職人員的玩忽職守行為→危害結果;而職務關系中監督過失的基本構造則是:公職人員的過失+被監管企業或者從業人員的行為→危害結果。可見,在監督過失犯罪中,事故和危害結果的發生,并非公職人員直接作為或者不作為造成的,而是介入了被監管者的行為,即危害結果的發生是由被監管者的行為直接導致的,只是監管者沒有對被監管者盡到監督義務,這其實是一種過失的并行競合現象。監督過失罪的這種獨特構造是其區別于一般過失犯罪的象征性標志,也是監督過失罪與玩忽職守罪在其他方面差別之濫觴。
其次,因果關系的區別。監督過失罪中的因果關系屬于多因一果,其在判斷方式上與玩忽職守罪有所不同。從形式上看,玩忽職守罪中,行為人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關系相對明顯,比較直觀地符合“如果沒有”(sinequanonorbutfor)⒀的判斷標準。而監督過失罪中,監督者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并沒有直接、必然的聯系,前者僅僅為后者的發生提供了起較大作用的客觀條件,這種條件相當于相當因果關系中的原因:監督者無過失,不意味著被監督者的行為一定適法,危害后果一定不發生,反之亦然。不過,即便如此,行為人的監督過失行為,也已經包含了“危險實現”的內涵,盡管有被監督者行為的介入,仍然可以認定因果關系的存在⒁。根據刑法中“被允許的危險”理論,“如果禁止所有危險,社會就會停滯”,安全責任事故經常發生的領域屬于高風險行業,所以,必要的風險在這些行業中是被允許的⒂。但是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風險被允許的前提是要求相關人員負有高于一般人的注意義務。如果行為人違反了這種注意義務,則行為所致的危險就不再是被允許的危險了。如果經中間項行為的促進,這種危險在危害結果中被實現了,那么,監督過失罪中的因果關系也就最終得以形成。
再次,注意義務的不同。過失犯罪都是對一定注意義務的違反的行為。從我國《刑法》第15條關于過失犯罪概念的表述來看,包括玩忽職守罪在內的通常意義上的過失犯罪中的注意義務屬于結果預見義務。但監督過失理論以危懼感說為基礎,認為在食品、藥品事故、工廠等爆炸事故以及醫療事故等現代型犯罪中,“所謂預見可能性,并不需要具體的預見,僅有模糊的不安感、危懼感就夠了”⒃。危懼感說將注意義務理解為結果避免義務⒄,所以,監督過失中的注意義務應屬于結果避免義務。
三、我國設立監督過失罪之理論可行性
我國學者對監督過失的理解,大多以日本刑法理論作為參照。如前所述,日本刑法理論不承認監督過失在職務過失犯罪中的適用。受日本刑法理論的影響,在各類安全責任事故犯罪中,我國學者對監督過失的討論,往往也只是限于業務過失的范疇。這種情況,導致實踐中對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新窯煤礦“1215”特大爆炸事故等案件中國家公職人員的這種處理方式。我們認為,這是一種訛誤,監督過失不僅適用于業務關系中,也同樣適用于職務關系之中,在職務關系中設立“監督過失罪”并不存在理論障礙。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職務過失與監督過失的關系。在刑法理論中,依據職務過失犯罪主體承擔的職務不同以及職責權力指向范圍的不同,職務過失犯罪的表現形式可以劃分為決策過失、管理過失以及監督過失⒅。因此,監督過失原本就是職務過失的一種具體形態,理應存在于職務關系之中。
其次,從國外實踐及理論來看,監督過失的適用也并不限于業務關系領域。以德國為例,在德國的刑法理論中,原則上行為人只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但是在例外的情況下,也對他人的某種違法行為承擔責任,其根據就是因為對他人的行為具有特定的監督義務,因此才負監督責任。這種監督有兩種形態:⒆企業組織中的監督責任;⒇公務員的監督責任。而公務員的監督責任,根據德國法的規定,公務員已經知道或已經預見到他人犯罪時,有阻止他人犯罪的義務,對此種義務之違反即是監督過失21。
另外,在日本,監督過失理論最早是從業務過失的判例中發展而來的,此后,學者對監督過失的討論一直局限于業務關系領域,這可能是受其《刑法典》第211條“業務過失致人死傷”規定影響的結果。日本的這種實踐及理論,即使在日本,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因此并不具有普適性,不能作為界定監督過失適用范圍的唯一理論依據。
摒除這種理論障礙之后,我們發現,我國《刑法》中,除了“玩忽職守罪”這一罪名之外,分則第九章中還有很多具體罪名實際上也屬于監督過失罪。首先,最為典型的就是第408條“環境監管失職罪”,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一般并非是由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于這些人員的嚴重不負責任,疏于監管,導致被監管的企業或者相關從業人員的行為引發了事故,完全符合狹義上監督過失犯罪的基本構造。其次,第409條“傳染病防治失職罪”等條文中,傳染病傳播或者流行等事故的發生,可能是由于被監管者的過失或者故意所致,如果監管者未盡到法定監管義務,其責任也符合狹義上監督過失的基本構造,屬于職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犯罪。
(二)信賴原則的適用
盡管我們主張在職務關系領域設立“監督過失罪”并不存在理論障礙,但是,監督過失理論是在過失理論的危懼感說的基礎上提出的,確有擴大過失犯罪成立范圍之虞。在日本,盡管有判例承認危懼感說,但該說也因之遭到一些學者的批評22。因此,“監督過失理論又要自覺地進行自我限制,避免罰及無辜”23,這主要是指信賴原則的適用。所謂信賴原則,是指當行為人(在監督過失中即是指監督人)實施某些行為時,如果在可以信賴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夠采取相應的適當行為的場合,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適當的行為而導致結果發生的,行為人對此不承擔過失責任的原則。關于監督過失中是否適用信賴原則的問題,刑法理論中存在著較大爭議,在日本,人們傾向于采取肯定立場24,我們采取肯定說,認為信賴原則對于限制監督過失的適用范圍有著重要的意義。
根據監督過失的邏輯,如果處于指揮、監督地位的人存在指揮、監督的不適當,或者不實施為了避免結果發生的管理行為的不作為的情形,就要對他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因此,企業內部的管理者、監督者要對導致事故發生的直接從業人員的行為承擔監督過失責任;負有監管職責的公職人員要對肇事場礦企業的行為承擔監督過失責任。相應地,該公職人員的上級機關或者公職人員也對該公職人員負有監督職責,按理也應當承擔監督過失責任。依次類推,責任將會無限向上延伸,這顯然是很荒謬的。所以,縱向上,監督過失責任必須限定在一定范圍內。信賴原則從分擔過失責任的基本思想出發,基于社會活動中行為人相互間的責任心以及社會連帶感,在彼此能夠信賴的范圍內,不要求行為人在行為時考慮到他人應注意的義務,即免除行為人預見他人實施不法行為而避免危害發生的義務。因此,信賴原則將義務和責任阻截在對安全責任事故負有直接監管職責的公職人員層面,可以適當地限制監督過失責任成立的縱向范圍,能夠有效地消解在職務關系領域設立監督過失罪的另一理論疑慮。
四、我國設立監督過失罪的立法構想
(一)命名為“監督過失罪”的理由
確定罪名,需要遵循合法性、科學性與概括性的原則,應充分發揮罪名的概括功能、個別化功能、評價功能、威懾功能25。據此,我們認為將本罪定為“監督過失罪”,反映了犯罪行為的本質屬性,能夠有效地和其他犯罪相區分。刑法理論中,提及“監督過失罪”這一概念,人們便會很自然地聯想到“監管者行為+被監管者行為→危害結果”的這一特殊構造,就會很容易將本罪與普通的玩忽職守罪區分開來。同時,由于業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犯罪在《刑法》分則第二章已經體現為各具體罪名,采用本罪名,也不會導致本罪與業務關系中的各種監督過失犯罪罪名相混淆。
(二)構成要件的設定
從犯罪主體方面看,本罪主體應當界定為“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其一,本罪主體必須是“人員”。業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監督者、管理者承擔監督過失責任情況大多是發生在單位犯罪中,換言之,某些情況下,認定監督過失犯罪之成立,須以認定單位犯罪之成立為前提26。依此邏輯,如果要追究職務關系中公職人員的監督過失責任,有時也需要以該公職人員所在的國家機關構成單位犯罪為條件,這個結論不符合現實情況。因此,在職務關系中適用監督過失,必須界定責任的橫向邊界,將責任限定在“人員”范圍內。其二,本文中的監督過失罪是專指職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犯罪,本罪應當是身份犯。綜合上述兩點,我們認為本罪主體界定為“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比較合適。
從犯罪的主觀方面看,監督過失罪是過失犯之一種特殊形態,所以本罪主觀方面應當是過失無疑。但如前所述,監督過失理論是在過失犯之危懼感說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所以其“注意義務”的內容有別于玩忽職守等普通過失犯:不是預見由自己的行為直接發生犯罪的結果,應當采取避免該結果的措施的義務,而是預見由自己的行為能引起被監督人的行為產生犯罪的結果,應當采取避免該情況的措施的義務27。
從犯罪的客體看,如前所述,本文所指的“監督過失罪”專指職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犯罪,所以,本罪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監督管理活動,或者說國家機關相應的監督管理職責。這一點,本罪與濫用職權罪__和玩忽職守罪相一致,因此,本罪應當歸于瀆職罪這一類罪當中。
從犯罪的客觀方面看,本罪的客觀行為表現是負有監督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怠于履行或不正當履行監督職責,致使被監督者實施了一定的行為,導致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因此,監督過失是一種不作為型的過失,行為構成犯罪的前提需是行為人負有相應的作為義務28。另外,根據過失犯理論,過失構成犯罪應當以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為要件,因此,監督過失罪屬于結果犯,只有發生了監督者的中間項行為并造成國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損失,才能成立犯罪。
(三)立法設計及條文表述
首先,建議在《刑法》第15條第一款后增設一款,規定“監督過失”的概念,該款可表述為:“處于指揮、監督地位的監督人怠于履行監督職責,致使被監督人實施了發生危害社會后果的行為的,是監督過失犯罪。監督過失犯罪,既包括業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犯罪,也包括職務關系中的監督過失犯罪。”在《刑法》總則中規定“監督過失”的概念,可以明確監督過失犯罪與普通過失的界限,也可以為在分則相關條文中規定和司法實踐中適用監督過失犯罪提供總則性指導。
其次,建議在《刑法》分則第九章“瀆職罪”中設立“監督過失罪”,作為專指職務關系中監督過失犯罪的獨立罪名。具體做法,可以考慮在第397條第一款后增設一款,規定:“負有直接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發生重大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公共衛生等事故,致使公私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獨立的監督過失罪罪名的設立,一方面可以涵蓋職務關系中各種具體的監督過失犯罪,避免立法的繁瑣,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司法機關在安全責任事故等犯罪中適用監督過失追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刑事責任提供統一的依據,避免無法可依或者張冠李戴的尷尬。
另外,為了避免“監督過失罪”成為又一個“大口袋罪”,本罪立法可以借鑒玩忽職守罪的經驗29,先概括設立一個“監督過失罪”,待到時機和立法技術成熟之后,再考慮將一些發案較多、社會危害性較大、行為特征比較鮮明、典型的行為樣態分離出來,單獨規定罪名、罪狀和法定刑,同時保留“監督過失罪”的概括規定作為兜底,防止遺漏。新晨:
注釋
①參見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69頁。
②參見彭鳳蓮:《監督過失責任論》,《法學家》2004年第6期。
③具體案情請參見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第二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40頁。
④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第266頁。
⑤參見謝文鈞:《外國職務犯罪立法特征淺析》,《當代法學》,2001年第1期。
⑥侯國云:《過失犯罪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5頁。
⑦韓玉勝、沈玉忠:《監督過失論略》,《法學論壇》2007年第1期。
⑧參見李蘭英、馬文:《監督過失的提倡及其司法認定》,《中國刑事法雜志》2005年第5期。
⑨參見新華網:《山西洪洞“1215”礦難13名犯罪嫌疑人被批捕》,/nuwscenter/2007212216/content27259081.htm,2007年12月16日。
⑩參見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第266頁。
⑾韓玉勝、沈玉忠:《監督過失論略》,《法學論壇》2007年第1期。
⑿參見王新友:《〈檢察機關立案查處事故背后瀆職犯罪情況報〉解讀》,/shownews.aspx?newsid=275,訪問時間2007年5月22日。
⒀參見趙秉志主編:《英美刑法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1頁。
⒁參見廖正豪:《過失犯論》,臺北:臺灣三民書局,1993年,第231頁。
⒂參見呂英杰:《監督過失的客觀歸責》,《清華法學》2008年第4期。
⒃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第二版),第240頁。
⒄參見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第256頁。
⒅參見謝文鈞:《論職務過失犯罪的形式》,《當代法學》2001年第2期。⒆參見謝文鈞:《論職務過失犯罪的形式》,《當代法學》2001年第2期。
⒇參見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第256頁。
21陳偉:《監督過失理論及其對過失主體的限定———以法釋[2007]5號為中心》,《中國刑事法雜志》2007年第5期。
22參見西原春夫:《交通事故和信賴原則》,成文堂,1969年,第14頁。
23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二版),第510~514頁。
24參見韓玉勝、沈玉忠:《監督過失論略》,《法學論壇》2007年第1期。
25參見川端博:《刑罰總論講義》,成文堂,1997年,第214頁。
26參見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第二版),第242頁。
27參見高銘暄:《刑法專論》(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52~8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