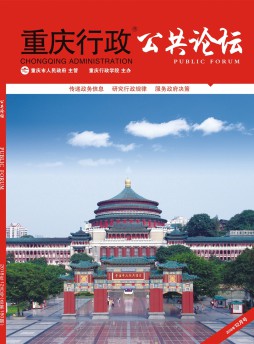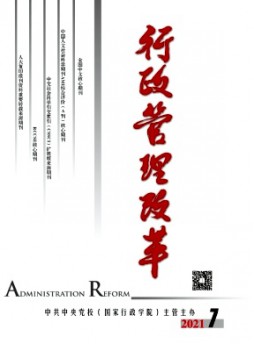行政執法協商和解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行政執法協商和解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為順應現代行政民主化之發展趨勢,促進行政主體積極靈活地對社會公眾的多元化需求作出反應并提供優質服務,在行政執法中不僅不應禁止和解,而且還應積極倡導和鼓勵和解。協商與和解之理念引入行政執法,不僅意味著在行政法的實施過程中,行政主體應當立于平等之地位,積極地與行政利害關系人展開對話、交流、協商與溝通,力爭在雙方達成基本共識的前提下作出行政決定,甚至以雙方合意即行政契約的方式達成法定的行政目標;而且意味著在行政決定的執行以及行政契約的履行過程中,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也應當進行充分的協商與和解,力爭以和平、高效之方式達成法定目標。
一、在行政執法中引入協商與和解之正當性
基于行政意志優越于私人意志、行政是法治而非自治、行政主體對其所享有的法定權力及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無權處分的傳統認知,協商與和解理念長期以來被視為私法之專利且被排除在行政法殿堂之外。相應地,行政執法也僅僅被詮釋為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即行政主體適用法律作出的具有強制約束力的命令,是行政主體的單方意志。①然而,應當指出的是,傳統行政法理論對協商與和解的反對,實際上建立在一個并不正確的假定之上,這個假定就是:法律對行政主體該如何行為的指令是明確而具體的,行政主體的任務在于遵循立法者的指令行事,不能將自己的意志摻雜在法律實施中。在這一假定之下,行政主體似乎完全受到立法者的控制而沒有任何自由,沒有資格或能力“處分自己的權利”,自然也沒有協商與和解的資格。
現在的人們已經認識到,法律僅僅為行政主體的活動劃定了大體范圍,而沒有指明行政主體采取行動的每一個細節。事實上,立法者根本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維護公益及增進人民福祉,乃最基本之國家目的,但法律甚少可能對于公益與福祉之實現,在各種行政措施之領域,提供恒久之價值判斷標準或作巨細無遺之規定,故行政機關不僅須對國家目的之實現,選擇具體及直接之措施,在立法機關未提供價值判斷之標準時,行政機關亦有責無旁貸之判斷義務。”②法律應當得到嚴格執行,但法律并不是鐵板一塊,更不會如同數學那樣完全可以量化。行政主體在行政法的實施過程中享有很大的裁量權;在行政法的實施中,行政主體融入了許多自己的價值判斷和事實認知,所有這一切已經不再是什么秘密,而是一個客觀事實,更是現代社會的客觀需要。一旦我們摒棄了不真實的前提性假定,協商與和解理念在行政執法中的引入就不應受到反對。而且,行政主體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與行政相對人的個人利益之間的可交換性,為協商與和解在行政執法中的引入提供了關鍵性的條件。
在現代行政條件下,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是一種既沖突又一致的關系,這為雙方的交換提供了前提。利益關系是人們之間為了追求和實現自己的利益而結成的一種社會關系,對抗或合作是利益關系的兩種主要形式。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關系也不例外。一方面二者表現為一種沖突關系,因而需要法律來進行調節,而如何對這種利益關系進行調節就是行政法的功能之一。另一方面二者之間除具有對抗性外還具有一致性。社會之所以要從個人利益中分離出公共利益,就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個人利益和安全,調節各社會成員占有的個人利益,促進個人利益的進一步發展,而不是要剝奪或消滅個人利益。③因此,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總體上是一致的、統一的,它們可以互相轉化、相互依賴、互相包含,③這種一致性無疑為二者的交換提供了可能性,也為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進行協商與和解提供了條件。
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妥協和交換可以達到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為在行政執法中運用協商與和解提供了動力。現代行政的實施過程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爭過程,而是共同合作的交涉過程。現代行政關系主要是一種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兩種利益在行政關系中是并存的并且具有互惠性,行政關系的形成與發生并不以犧牲行政相對人的私益為代價,行政機關實現行政職能并不排斥行政相對人在行政關系中追求其自身的私利。在行政法的實施過程中進行利益交換或交易,既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維護,也不妨礙私益的實現。
然而,傳統行政對權力與強制的過分倚重以及對行政意志優越性的過分強調,在一定程度上助成了行政主體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心理。行政主體的優越意識嚴重制約了其以平等姿態與行政利害關系人進行協商、溝通與對話。更為關鍵的是,傳統行政法理論在根本上將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置于相互對立與斗爭的關系結構中。在這一關系結構中,行政主體以命令者的身份出現,而行政利害關系人則以命令的服從者即行政之客體被迫卷入行政法的實施過程中。行政主體既無意識也無動機與行政利害關系人進行平等溝通和協商;行政利害關系人則要么在強力壓迫下無奈地服從,要么采取各種方式與行政主體進行周旋、抵抗。如此,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之間根本無法開展有效的溝通與合作。為改變這種狀況,就有必要在行政執法中引入協商與和解,變革行政執法的方式,將談判、協商、溝通、交流作為行政法實施的基本方式和過程。
總之,在行政執法中引入協商與和解,意在實現協商、合意、和諧之精神與行政執法的融合。通過協商淡化行政權力的命令與服從色彩,增添行政法人情、理性的光輝;通過合意來弱化行政執法過程中的對抗與沖突色調,增加民主、協作的音符;通過強調和諧來消除行政關系中的懷疑和不信任意識,建立信任與合作的新關系。
二、作為行政執法方式的協商
協商,首先是一個人際交往中的各方立于平等之地位就有關事務進行信息互通、溝通與對話、說服與談判的過程。它旨在最大限度地尋求共識、協調行動、預防和避免沖突,進而實現彼此間的互信與合作。協商,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協商往往受到法律較為嚴格的規制,在協商的形式、步驟以及結果的形式等方面具有嚴格的要求;而非正式的協商相比較而言較少受到法律的規制,基本上采取當事人意思自治主義。在結果上,正式的協商往往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約為追求目標,非正式的協商并不一定追求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約,而往往追求彼此間的默契和互信,即達成君子協定。
在民主理念、服務理念、契約理念等的支配下,現代行政法在本質上應當是對人民真實需求以及滿足此等需求之方法的記載和表達。行政法的實施過程,也就是不斷滿足人民的現實需求的具體過程。在此過程中,作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行政主體與作為私人利益代表者的行政利害關系人之間,就有必要進行充分協商,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協商,以實現雙方利益的協調和最大化。換言之,在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之間建立起長期、穩定的信任與合作關系,為實現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協調發展所必需,而平等協商則是信任與合作關系得以建立的不二法門。因為通過平等協商之過程,不僅可以最大限度地緩和行政沖突、達成共識,能夠以和平的方式高效地達成法定的行政目標,更重要的是這一過程本身就充分彰顯了現代公共行政的平等和民主本色。也就是說,無論協商的最終結果如何,即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之間能否達成共識,只要行政主體主動地與行政利害關系人進行談判、協商和溝通,就能夠充分地顯示出行政主體對行政利害關系人的主體地位、自由意志、正當利益的承認和尊重。僅這一點,就能夠拉近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之間的距離,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和尊重,也有助于建立和維護政府與人民之間長期穩定的信任與合作關系。客觀現實一再表明,缺乏平等協商、交流過程的行政執法,必然會演變成官僚行政,甚至是赤裸裸的暴政。行政主體如果不能立于平等地位與行政利害關系人進行有效的協商與溝通,那么,它必然會因嚴重脫離人民而不知人民之真實所思、所需,更不能為人民提供優質的服務,至多只能根據自己的片面認識作出武斷的決定,并且依靠強力推行。如果行政主體不能為行政利害關系人提供充分的協商、交流機會,那么,行政利害關系人必然因不了解行政主體意欲何為、依據什么以及怎樣作為而任意猜疑,對行政主體所作的行為根本不予信任,更不會主動配合。如果行政關系真正發展到這一地步,那么,行政法就很難得到有效實施,法定的行政目標更無有效達成之可能。
作為一種行政執法方式,協商應當貫穿于整個行政過程,即從行政程序正式啟動到行政主體作出行政決定或者雙方達成行政契約,直至行政決定的完全實現或者行政契約的完全履行,甚至在行政程序正式啟動前,行政主體和行政利害關系人也完全可以就相關問題進行商討,實現信息交流并達成共識。
首先,在正式行政程序啟動前進行協商。行政程序,是行政法實施的動態過程。為了確保行政主體在充分的信息基礎上做出合理、合法的行政決定,正確地行使法定權力或履行法定職責,各國法律都以保障行政利害關系人的參與權為基點對行政程序作出了繁簡不一的規定。然而,此等行政程序在具體個案中是否有必要機械地運行以及具體如何運行,則有具體問題具體考量的余地和必要。在正式行政程序啟動前,如果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各方都能夠善意地、本著誠實互信的態度,平等地進行溝通、協商,就一定能夠找尋到各方都能夠接受的方案。這樣,不僅能夠簡化、或者加速正式行政程序的運行,從而節約行政成本和社會資源,提高行政效率,而且能夠以令各方都比較滿意的方式解決行政問題,避免行政糾紛的發生,節約行政行為的執行成本,減少行政爭訟,最大限度地在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之間建立起長期、穩定的信任與合作關系。
其次,基于協商作出行政決定。傳統行政過分倚重權力與強制,行政法主要以行政主體作出單方命令并以暴力相威脅或直接使用暴力強迫行政利害關系人服從行政命令的方式而得以實施。然而,實踐已經證明,這種單純或主要依賴強權與暴力的行政執法方式的效果并不如人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損人類夢寐以求的法治的美德。現在,人類正在嘗試通過協商而作出行政決定并期望行政利害關系人自覺服從行政決定的行政執法方式,以此真正彰顯法治的本質即基于人們的同意而進行統治。基于協商而作出行政決定的實踐,在各國已經比較普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大有取代傳統行政執法方式、后來者居上之勢。例如,在美國,“為了避免縱向命令型管制和正式的行政法律程序的局限,人們發展出解決創新性的管制問題的各種形式的彈性機構——利益相關人網絡。”⑤通過多種方式與公眾溝通、管制協商、合作安排、討價還價等,這樣,“在參與者之間為了解決管制問題而在協商的基礎上建立了準契約性的關系”。⑥行政主體在作出行政決定前與行政利害關系人進行充分協商,將未來的行政決定建立在充分協商和最大限度的共識之上,不僅能夠體現以人為本的現代行政理念,而且能夠降低行政決定的執行成本,預防和減少行政爭訟,節約社會資源。
再次,以行政契約方式達成行政目標。行政契約是行政主體為達成法定的行政目標而與行政利害關系人進行平等協商、意思表示一致而達成的協議。它在現代公共行政領域的廣泛運用,充分顯示了協商式行政執法方式的強大生命力,也預示了協商式行政執法方式在未來公共行政領域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這是因為協商不僅滿足了人類對尊重和理解的渴望,而且與建立服務性政府、企業性政府的現代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相一致。
最后,行政決定之執行以及行政契約之履行中的協商。行政決定的作出和行政契約的達成,雖然是行政程序的關鍵性環節,但它并不是行政程序的終結。對行政法所追求的目標而言,行政決定的實現和行政契約的履行則顯得更為重要。作為行政執法方式的協商,不僅在行政決定的作出或行政契約的達成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行政決定的執行或行政契約的履行過程中同樣不可或缺。基于客觀現實的發展變化,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即使在行政決定或行政契約所確定的實體權利義務不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前提下,權利義務的實現方式并非一成不變。況且,基于客觀現實的發展變化,變更行政決定或者行政契約所確定的實體權利義務也完全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即使在行政決定作出或者行政契約達成以后,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彼此間保持順暢的溝通與協商,對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的最大化滿足而言也是絕對必要的。
三、行政執法中的和解
通常而言,和解是雙方或者多方主體間就某一爭議進行協商、談判,進而達成諒解和共識的過程與結果,它是當事人之間和平地化解糾紛或者爭議的一種方式。在行政法上,由于行政主體的特殊角色(被假定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及其優越地位,存在著行政主體將其單方意志強加于行政利害關系人的可能,因而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之間的糾紛或者爭議在行政程序運行的整個過程中隨時都可能發生,加之行政裁量權的客觀存在,和解作為一種化解糾紛或爭議的方式,在行政法領域具有廣闊的應用空間。
(一)行政和解契約
行政契約作為現代行政方式之一種,已經獲得普遍認可,和解契約即是一種典型的行政契約。行政主體可以運用和解契約追求法定的行政目標。在嚴格意義上,行政法上的和解契約,即是指在行政法的實施過程中,當事實、法律觀點不明確且此等不確定狀態不能查明或者非經重大支出不能查明時,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就此等不確定狀態進行協商而達成的協議。從域外立法來看,盡管基于行政法治原則的拘束和對行政主體販賣公權的擔憂,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行政程序法對和解契約的應用規定了較為嚴格的條件,但從原則上來說,和解契約作為行政執法之方式還是得到了立法者的肯定。《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4條規定:“公法范疇的法律關系可以通過合同設立、變更或撤銷,但以法規無相反規定者為限。行政機關尤其可以與擬作出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簽訂公法合同代替行政行為的作出。”第55條規定:“第54條第2句意義上的公法合同,經明智考慮事實內容或法律狀況,可借之通過相互讓步消除存在的不確定性時,可以簽訂。但以行政機關按義務裁量認為達成和解符合目的者為限。”⑦基于這一立法,德國學者毛雷爾認為:“和解合同是通過相互讓步來消除合理判斷中的事實或者法律問題的不確定狀態。其條件是:(1)存在著有關事實狀況或者法律觀點的不確定狀態;(2)這種不確定狀態不能查明或者非經重大支出不能查明;(3)通過雙方當事人的讓步,可以取得一致的認識。”⑧
和解契約之所以獲得人們的肯認,是因為行政執法中常常存在一些事實或者法律不確定的狀態,此等不確定狀態也許是由人類的認知能力有限而無法查明所造成,或者是因查明這些情況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因而基于經濟的考慮而不應當去查明。但是,這些事實或者法律的確定是行政主體作出行政決定的前提,因而它需要由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通過協商而獲得確定。如果不承認和解契約,那么,面對事實上或法律上的不確定狀態,行政主體的選擇只能是,要么因證據不足而純粹不作出行政決定,要么在事實不清、法律依據不明的情況下作出充滿爭議的行政決定。這兩種選擇都不利于行政法的實施和法定行政目標的達成。如果因事實不清或者法律依據不明確而純粹不作出行政行為,那么,行政法自然就無法得到實施,法定的行政目標自無達成之可能;如果行政主體強行單方決定并予以執行,則極有可能導致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之間的沖突、對立,進而可能引發訴訟。這對行政主體與行政利害關系人之間良好的服務與合作關系的建立根本沒有益處。相反,如果引入和解機制,行政主體就可以本著真誠互信的態度,平等地與行政利害關系人進行充分協商、溝通和對話,力爭彼此間能夠就關鍵性問題達成共識和諒解,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解決所面對的問題,最終實現雙贏。
德國和臺灣地區的行政程序法對和解契約的規定,是極其嚴格的。但是,若撇開這種嚴格的限制而從本質上考察的話,作為行政執法方式的和解契約是廣泛存在的。隨著現代行政的民主化程度增強,各國行政實踐中普遍存在這樣一些行政行為,即雖然在形式上表現為行政主體的單方行為,但在本質上是和解契約。因為行政主體在作出這些行政行為之前,已與行政利害關系人進行了充分的協商和溝通,并就行政行為的實質內容達成了共識。
(二)執行和解
根據一般的行政法理論,行政行為的執行是指負擔行政行為的實現。也就是說,當行政主體作出了為行政相對人設定義務的行政行為時,該行政行為就存在執行問題。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負擔行政行為一般是通過義務人自覺履行義務而得以實現的,但是,當義務人逾期不履行義務時,行政主體可以依據法律授權強制義務人履行義務。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行政主體只能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無論是由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還是由行政主體強制執行,都存在執行和解的可能性。為便于討論,本文僅涉及行政主體強制執行中的和解。
從程序角度看,執行和解的程序既可以由負擔行政行為的義務人啟動,也可以由負責執行的行政主體啟動,執行和解程序的啟動,既可以是在法律或者行政決定所確定的自覺履行義務的期限內,也可以是在義務人收到強制執行告誡通知時,甚至可以是在正式強制執行的過程中。依據一般的法律程序,負擔行政行為的強制執行程序,必須在法律或者行政決定所確定的義務人自覺履行義務的期間屆滿以后才能啟動。而且,行政主體在正式采取措施強制執行以前,必須履行告誡義務。但是,法定的強制執行程序是否啟動,并不影響執行和解程序的啟動。執行和解程序,可以在從負擔行政行為的作出到義務的最終履行的整個過程的任何時候啟動。當然,行政主體作出的強制執行告誡通知,常常是引發執行和解的因素之一。
從和解的內容來看,行政執行和解主要涉及如下內容:(1)義務的減免;(2)義務標的的變更;(3)義務履行方式的變更;(4)義務履行期限的變更;(5)義務履行主體的變更;(6)強制執行中代履行費用的負擔。原則上,只要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不影響法定目標的達成,行政主體就可根據客觀情勢的變更而與行政利害關系人就上述內容進行和解。
從結果來看,行政執行和解有可能達成和解協議,有可能達不成和解協議。如果達成了和解協議,基于誠實信用原則,雙方應當積極履行所達成的協議,而不應當隨意反悔。如果行政主體反悔,行政利害關系人可以通過行政爭訟程序尋求救濟;如果負擔行政行為的義務人反悔,行政主體仍然可以啟動強制執行程序,執行原負擔行政行為。如果無法達成和解協議,那么,行政主體仍然可以依法強制執行原負擔行政行為。
精品推薦
- 1行政訴訟法論文
- 2行政年終述職報告
- 3行政事業單位會計論文
- 4行政處罰法論文
- 5行政人事工作計劃
- 6行政爭議論文
- 7行政管理相關工作
- 8行政管理案例分析論文
- 9行政人事工作匯報
- 10行政哲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