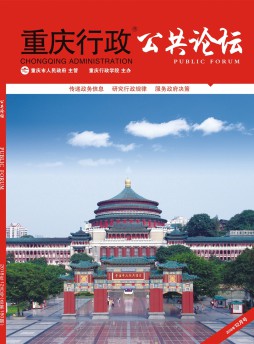行政強制執行權缺陷及成因剖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行政強制執行權缺陷及成因剖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我國現行的行政強制執行權配置即不一概把行政強制執行權授予人民法院,也不一概把行政強制執行權授予行政機關,而是在行政機關和人民法院之間進行一定比例的分配。即把行政強制執行權主要配置給人民法院,只把少部分行政強制執行權配置給行政機關的方式,行政法學專家應松年教授將其概括為這樣的一句話“: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自力執行為例外”。[1]但由于我國在進行行政強制執行權配置時,缺乏總體的理論設計和統一的指導思想,因此現行的配置方式存在明顯的缺陷與不足,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面:
(一)政強制執行權的配置缺乏明確、統一、合理的標準行政強制執行權在什么情況下由行政機關執行,在什么情況下由人民法院執行,這在我國現有的法律中并沒有明確的規定。而只是在《行政訴訟法》和新《司法解釋》當中對行政機關和人民法院的執行權限作了初步劃分,即行政機關在法律和法規明確規定有強制執行權時方能自行強制執行,否則一律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然而法律、法規又以什么樣的標準來判斷那些行政強制執行權由行政機關執行,那些行政強制執行權由人民法院來執行呢,這仍然不清楚。對此,理論上確立各種不同的配置標準。然而,這些標準很多僅僅只是學者根據現有有效法律、法規規定所作的一種學理上的分析。“目前并沒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且這種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的標準本身又沒有一種裁量判斷的客觀尺度和具有客觀、公正性的判斷主體,導致實際執行中出現諸多弊端”。[2]
(二)非訴行政強制執行行為性質不明確,不利于相對人的救濟從機關的性質上我們知道,人民法院行使的是司法權,即判斷權。行政機關行使的是行政權。我國現有行政決定的強制執行存在由行政機關自行執行,或者訴訟后法院強制執行,或者非訴申請人民法院進行強制執行。在非訴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的情況下———行政機關提出申請,法院進行合法性審查,在作出肯定性判斷的基礎上,再由法院去實施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此時法院的合法性審查行為行使的是判斷權無疑,但是法院實施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的行為究竟是行使行政權的行政行為還是行使司法權的司法行為呢?由于理論研究的不足和立法的滯后性,對此很難解釋清楚。人民法院應申請的非訴執行行為因其經過法院的非訴訟審查且由法院執行,“已不是原來的行政行為,對其不服的,亦不能請求行政復議;因為其不是行政訴訟,一般不進行口頭辯論,相對人和相關人的權益往往容易被忽略;因為其不是行政訴訟,對其不服的,亦不能提起上訴。”[2]因此,對此給相對人造成的不利,相對人很難獲得相應的救濟。雖然在我國的現行體制下,相對人還有唯一的申訴途徑,但在現實中基本上難以達到“救濟”的水準。
(三)與行政行為效力原理及其規則嚴重脫節
關于行政行為效力原理的通說認為,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并自告知、受領或附款規定之日起,即具有四種效力:公定力、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其中,執行力最具有現實意義,它對于行政行為內容的實現起著決定性作用。行政行為效力原理在我國實體法上的主要表現是《行政訴訟法》第44條有關“起訴不停止執行”的規定。然而,現行行政強制執行卻與其嚴重脫節。依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4條的規定,一般情況下,人民法院在訴訟過程中,對被告申請強制執行的不予執行,只在極少數特殊情況下才可以先予執行。可見“,起訴不停止執行”實際上只適用于行政機關自力執行的情形。但由于在現行體制下,行政機關自力執行所占比重極小,因而上述原則已處于被“擱置”的狀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85條規定:“人民法院認為執行具體行政行為,確有錯誤,經院長批準,不予執行,并將申請材料退回行政機關”。這就意味著被退回的行政行為就失去執行力了。然而,行政行為的效力除非被有權機關撤銷,其一直有效。這樣,一方面行政行為具有公定力、確定力、拘束力;另一方面行政行為卻沒有執行力。這不僅對行政管理不利,也違背了一般行政法原理。
(四)致使司法與行政的角色錯位,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
從當前中國的現實來看,我國各級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審判任務日益繁重。并且“執行難”成為法院生效的判決的“權威”的一大挑戰,在這點上法院本身的生效判決尚且難以執行,更何況由行政機關申請的行政強制執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司法機關根本沒有足夠的精力去審查、執行大量的非訴行政案件。同時司法的內涵應當是“司法機關依法對爭議所作的具有法的權威的裁判”,其本質是“權威裁判”。[1]換言之,人民法院始終扮演的是一個消極、中立且無偏私的裁判者的角色。然而,我國目前對行政強制執行權配置上,把絕大部分的行政強制執行權配置給人民法院,這使法院對行政機關的支撐功能遠遠超過了監督功能“,法院成了政府機關的執行部門,司法權力與行政權力又形成一股合力來對付行政相對人,實際上否定了行政訴訟制度存在的基礎。”[2]毫無疑問,這本身就是對司法與行政角色的一種錯位。其在我國行政訴訟制度運行環境尚不盡人意的情況下,這無疑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且對于司法權威的樹立也是一種不利。
二、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權配置形成的原因
我國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權配置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是受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將執行權視為司法權的認識
該認識的實踐依據源于刑事和民事執行制度。改革開放之初,在我國關于強制執行的法律規定僅限于刑事和民事訴訟法,而刑事強制執行和民事強制執行是由法院或在法院的指揮下實施的。因而強制執行權一直被實際上視為是司法權,應該由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行使而不應由行政機關行使。
(二)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控制和約束
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使涉及到對人身權、財產權的強制措施的采取,需要由法律予以嚴格的控制,尤其需要有完善的行政強制執行程序的約束。而在現行行政強制執行體制形成之初,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剛剛起步,行政法制頗不健全,人們對于行政法和行政程序知之甚少。因此,無法從行政法理論和當時的行政法律中找到可以控制行政強制執行權濫用的有效途徑。《民事訴訟法》規定了審理行政案件適用該法。在這種情況下,將行政強制執行權賦予法院,也就成了防止行政強制執行權濫用同時又能夠找到法律依據的惟一途徑。
(三)法院地位和威信的提高
法院地位和威信的提高及當時法院執行的有效性也促使更多的法律選擇將行政強制執行權賦予法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由于法律不健全和傳統觀念的影響,行政機關主要依政策辦事,在行政執行環節上,表現為手段不多,力度不夠,威信不足,而法院基于其地位和威信由它出面執行有利于彌補上述不足,達到實現具體行政行為之目的,這促使更多的法律選擇將行政強制執行權授予法院。
(四)模仿效應
在某一法律首先規定將行政強制執行權授予法院后,其他法律便產生了模仿效應。至《行政訴訟法》頒布,基于行政強制執行的現實,不得不確立了“以申請法院執行為原則,行政機關自力執行為例外”的行政強制執行體制。既在行政強制執行權的配置上把絕大部分行政強制執行權賦予法院來執行。從以上的幾點因素我們可以看出,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權配置體制的形成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它并非出于理論上的嚴格設計,而是缺乏審慎的價值思考與判斷的。這也就決定了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權在配置上并非合理,其在運行的過程中必然會引發諸多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思索和解決。
精品推薦
- 1行政訴訟法論文
- 2行政事業單位會計論文
- 3行政年終述職報告
- 4行政處罰法論文
- 5行政管理相關工作
- 6行政爭議論文
- 7行政人事工作計劃
- 8行政管理案例分析論文
- 9行政人事工作匯報
- 10行政哲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