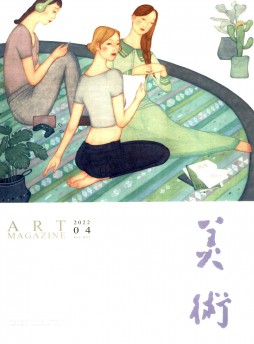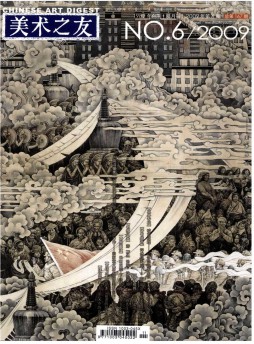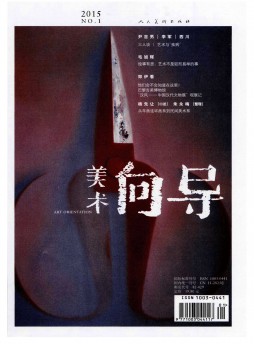美術發展史的歷史意義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美術發展史的歷史意義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從狂飆突進到潛心于民族文化
陽太陽在廣西美術發展史上產生影響,要從1937年返回桂林辦學算起。在這段時期,他的“初陽美術學院”像暗夜中的一道閃電,雖然微弱,盡管爾后就被黑夜掩住,但已經在廣西文化的土壤中播撒下一粒粒種子,為接下來的萌發孕育了新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爆發,促使他放棄赴法深造,回到故鄉桂林。在這段時間,他的繪畫風格有著顯著的變化,他1937年的國畫《農舍》,以及1938年所做的《古樹榕蔭》《桂林文昌橋》《花橋》等作品雖然只與油畫《煙囪與曼陀鈴》《海邊裸女》等相隔幾年,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人文取向。日后漓江畫派中常用的一些元素,如洋溢著濃厚鄉土氣息的百姓家常諸如民居、舟船、青石板道路、石橋、香蕉樹、牲畜等都已在畫作以主體地位呈現出來。由于陽太陽是一位喜歡大膽嘗試新鮮畫風的畫家,所以他接下來的繪畫題材也不局限于廣西山水。如代表作之一的油畫《沙原上的船》(1939年)就帶著現代主義的余音。但就是這么一幅超現實主義色彩極為濃重的油畫,在其內涵卻已經移向民族化的建構———不再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開始了對民族苦難的沉思,因而也獲得了超越早期歐化風格局限的人文底蘊。抗戰時期,陽太陽曾于桂林建干路一間二層小樓里創立私立學校“初陽美術學院”。過去學者對這段歷史多是從教育史的角度來考慮,其實還可以從藝術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如果深入其脈絡來理解陽太陽藝術創作發展演化的思想歷程,就能發現這段歷史雖然屬于漓江畫派前史的范疇,實際上在廣西本土美術的文化自覺意識發展史上卻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孟超曾總結出“初陽畫風”為“有生活”“有時代激情”“富有詩意”“富有創造性”等③。這些與后來的漓江畫派有濃郁鄉土味和時代朝氣這些特征雖還有一些差別,但發展的脈絡已經較為清晰。特別是身處那個國家危亡、仁人志士以身報國的大時代潮流之中,陽太陽的這種本土化主體意識順應了新的時代趨勢。此外,這個時期興起的強調走近大眾、走進生活、走入時代,對一直以來士大夫氣息濃重的中國繪畫傳統也有著重要的矯正作用。據昔日學生林楊回憶,當時學院十分重視組織學生外出寫生,規定每學期要外出遠足寫生一次,曾經組織學生去過陽朔、興安、蘇橋等著名風景名勝寫生作畫。此外,也經常組織學生到附近農村、工廠去深入人民生活,體會我國人民勤勞儉樸的本色和收集民間豐富多彩的民族形式的藝術④。后來由于桂林因日軍入侵而進行了大疏散,初陽美術學院也解散了。等到1947年,陽太陽在廣州試圖重整旗鼓,但最后終難實現桂林時期的輝煌。這段艱難時期,陽太陽夫人開的桂林米粉店倒是給過著清貧生活的一家些許補貼和安慰。這種窘境除了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末期的民生凋敝之外,其實也跟初陽美術學院與桂林文化環境的根基斷離有著密切關系———廣州是嶺南畫派的優勢地盤,雖然高劍父極為欣賞陽太陽的才華而聘其為廣州市立美專的教授,但繪畫環境早已不是昔日的桂林勝景,奇山已難搜,如何打草稿?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促使陽太陽思考自己繪畫的地域化、風格化問題。任何革新,終究是要在依托傳統的堅實基礎上進行的。藝術傳統之所以為傳統,就在于其為數十年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不斷試錯、對照、革新、積淀中最終得出的,所以革新不是與過去一刀兩斷,而是把握住時勢流變的脈絡,順時而動,將時代精神與文化傳統結合起來,這樣的藝術才能在深厚底蘊的基礎之上引領潮流。陽太陽在美術史上的建樹,恰恰表現在這種對時代脈搏的把握上。
二、在畫卷中建構廣西鄉土意境
20世紀50—60年代是陽太陽一段創作的高峰期,這段時期他的繪畫開始呈現出鮮明的地域藝術特征,以桂林山水風貌為題材的作品相繼涌現,這正式表明他歷經探索,終于走上了以繪畫形式來表述文化自覺意識的創作道路。這個時期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水彩畫《漓江木排》,該畫1955年參加蘇聯國際青年藝術節并獲得造型藝術獎,蘇聯的主要美術刊物《造型藝術》上專門加以刊載并配發評論。周楷教授認為:“《漓江木排》在陽太陽的美術創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是他從抗日戰爭以來探索外來藝術形式民族化,形成自己鮮明的個人風格取得成功的顯著標志。也是他在藝術上轉向以風景畫創作為主的開端。”⑤不過我認為,水彩畫《漓江木排》的確是陽太陽那個階段最為突出的作品,但這幅畫不是憑空出世的,除了初陽美術學院時期的積淀之外,《漓江木排》前后他就畫有不少桂林鄉土題材的畫作作為鋪墊了。而這都是昔日他回應中國繪畫面對的三重困境的歷史性延續。水彩畫《漓江木排》創作于1954年,同年他的《桂林象鼻山和解放橋》獲選“全國水彩、速寫畫展”。1961年深入百色地區寫生,《靖西之春》(油畫)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該畫抓住靖西最為優美的石山,配以富有生活氣息的竹木、梯田,描繪出一派祥和的山鄉風光。有意思的是,他畫的是靖西,但選的卻是靖西山石中與桂林山石精神氣質最為契合的平地起山的類型。1963年他五十四歲,與同仁們一道沿著漓江寫生作畫,創作了系列水彩畫《漓江》《塔山朝暉》《漁村》《漓江初霽》和國畫《碧蓮山道》等。只是突如其來的“”浩劫打斷了他的創作進程,批斗的紛擾和抄家導致他創作陷入停頓。在那個極左年代,陽太陽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受批斗,家中多年的書畫、畫稿也因此佚失。但這沒有磨滅他的意志,反而為后來如朝陽一般噴薄的新時期繪畫做了鋪墊。通觀陽太陽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繪畫,我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同一類型的畫面,他畫了一次又一次。
1954年他創作了水彩畫《漓江木排》,該畫以大幅桂林奇峰占滿畫面左側,右側是順流而下的漓江之水,水上有一彎木排隨著水流向畫面前方飄來。這幅水彩最重要的特點是開始在水彩繪畫中滲透水墨畫的筆法,在云繞群山的施墨上,具有強烈的中國氣派。而1956年,他又推出了油畫《漓江之曉》,該畫與水彩畫《漓江木排》在構圖上非常相似,以至于讓后來一些評論者在不經意間誤認為是同一幅畫。油畫《漓江之曉》最大的改進之處,在于強化了對山石嶙峋的刻畫,凸顯了桂林山石的獨特造型。而且他還把水面所占比例擴大,以便在水中畫出山的倒影。1972年他以中國畫形式畫出《煙雨漓江》,仍然是山石、竹排的構圖,不過多了變電站和信號站等,該畫畫面感似乎不夠強烈,缺少整體的力度感,倒是其中云霧的營造頗為成功。直到1989年,他還又以近似的構圖再畫了一幅油畫《漓江之晨》,這次重視的是對云霧的渲染。如此對近似的畫面落筆,必有其用意。早在20世紀40年代日軍入侵的艱難歲月里,由于各種繪畫原料的匱乏,陽太陽已經開始嘗試“土法自造”顏料。如周楷教授就曾提到:“由于處在戰爭的環境中,油畫工具材料的來源困難,也促使他更多地采用水彩畫。他作水彩畫重意境重氣韻,力求情景并茂,水色交融,習慣使用毛筆、水彩畫顏色與中國畫顏料混用并善于使用墨色構成了一套獨特的水彩畫技巧。”⑥在最初,這是不得已為之的方法,但或許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他開始發現其中筆墨轉換的獨特趣味,于是有意識將中西繪畫方法融合為一。結合他1963年所畫的系列水彩畫《漓江》《塔山朝暉》《漁村》《漓江初霽》,可以看出其中的脈絡。在這些系列水彩畫中,他嘗試用筆墨暈染的方法畫水彩,又嘗試用水彩的豐富色調來探索國畫用色的多樣性。其實我們可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他對三重困境的探索上,他事實上一直在試圖以西畫的用色、構圖糾正中國傳統水墨畫的陳舊蕭條,又試圖以中國水墨筆法突破西方寫實主義繪畫的局限,而且還要在過程中針對現代主義帶來的民族虛無主義迷茫,強調繪畫的民族風格,力圖在豐厚的民族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中建構新形勢下的民族藝術方面的精神面貌。他曾言:“用感情揮灑的畫面,比現實更高更寬闊、更真實,就是意境。家鄉的山水有無窮的意境,愛得越深,意境也就越深。”
陽太陽少年時期師從桂林資深畫家帥礎堅,筆下桂林山水自是練筆的必備。待他日后學習西畫成名,最終旅日歸國重畫桂林,是一種更高層次上的精神復歸。從年輕到資深,陽太陽的題材和畫風幾經變化,但那顆不懈探索的心從未改變。他以厚重的創作,來具體回應前述的20世紀初期中國繪畫面臨的三重困境問題,力圖在畫作中對年輕時代就開始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新中國成立初期,陽太陽在水彩畫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他并不停留于此,而是開始把主要的戰場轉向國畫。在20世紀50到60年代這段時期,從他的國畫作品中可以明顯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因為從具體用筆到施墨,他在不斷從各個角度進行民族化、地域化的深入探索。在1951年,他畫的《桂林花橋》似用的是逆鋒枯筆配以中鋒重墨來畫山石、樹木,畫作墨色凝重如鋼筋鐵骨,講求的是構圖的力度。而《南溪橋畔》落筆相對傳統持穩,左山折帶皴,右山斧劈皴,而且偏重以寫實手法勾勒樹木、石橋、山貌,在中國水墨構圖中融入了西畫焦點透視。而《桂林山水》則畫風轉為偏向寫意,山頂以積墨渲染,再用帶牛毛皴味道的斧劈皴來畫山石,這使得他所描出的山形,自由酣暢,遠看頗似整座大山都振翼起舞,隱約中似乎有西方未來主義的韻味。桂林是喀斯特地貌,以奇峰突起的石山居多。陽太陽在這些山水畫中都用了表現石山的斧劈皴,似乎并非偶然。或許他試圖將傳統技法揉以現代氣質,探究以新的精神氣質表現桂林山水的獨特韻味。而且1951年的這批畫作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在用色上頗費了一番心思,土黃色的石山正是廣西喀斯特石山的典型色征,他又以藍色點染樹林,這是桂北習見的晨霧色調。1962年的《碧蓮峰下》《碧蓮山道》《清江詩意圖》等走的都是這一路數。經過“”的中斷,他探索的勁頭卻更足了。1979年的《桂林山水最宜人》《陽朔白沙即景》試用青綠山水來鋪陳桂林勝景,這是在用色方面的復歸,又有所創新。作為對比,傳統青綠山水往往失之于浮華乃至匠氣,而陽太陽嘗試援以水彩的湛藍入中國畫,用綠顏渲染樹木的蒼翠,于是創造性地畫出了鄉土氣息濃郁的“青綠山水”。把世家氣派的青綠山水畫得鄉土味十足,這也可謂當代創舉。鄉土味入畫的風格,在后來漓江畫派的畫作中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如黃格勝的畫作,就具有相當深厚的民本風范,以八桂大地的人文底蘊深深打動觀者。
三、從“被表述”到“自覺表述”
學者黃偉林在研究“漓江畫派前史”時,考據出其實歷史上有不少藝術家和歷史文化名人曾以桂林山水為題材進行繪畫創作,從米芾到齊白石、徐悲鴻,再到關山月等,在不同時期畫出了各具特色的畫作⑧。他還提出“:抗日戰爭期間,桂林成為舉世矚目的抗戰文化城,除了徐悲鴻、關山月,中國一批杰出的繪畫大師如黃賓虹、傅抱石、李可染、張大千云集桂林。人們發現,此時中國山水畫的題材重心,逐漸從江南轉移到了嶺南。”⑨不過我想補充一點,那就是抗戰時中國山水畫關注的重心確實移到了嶺南,尤其是桂林,但之后實際上卻逐漸退潮。以桂林山水為題材的畫家不少,但他們畫桂林山水的作品如齊白石的《獨秀峰》《漓江泛舟》,徐悲鴻的《漓江春雨》《青厄渡》《漓江兩岸》等卻都并非他們的代表作,在繪畫史上的歷史地位也不是特別高。而且畫家們關注的也僅僅是桂林山水,對廣西的其他秀美風光和人文風情則大多忽視,偶有,也只是浮光掠影。說得不恭敬的話,抗戰之前,歷代文人關于八桂大地的奇山秀水,與其說是欣賞,還不如說是往往持獵奇的態度。可見,在沒有廣西地域文化的自覺意識的情況下,桂林題材、廣西題材至多也只是國內外藝術家作品中的陪襯,屬于游記性質的邊緣作品。若想擺脫這種窘境,廣西藝術家就必須以文化自覺意識,將這種“被表述”的被動處境一變為“自覺表述”的主動狀態。手指只有捏成拳頭才有力量,藝術家需要有明確的流派藝術的意識去凝聚力量。陽太陽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有意識地號召創建具有廣西本土地域特色的畫派,群策群力,而非單打獨斗。據學生蔣振立回憶,當時在開學典禮上,陽太陽先生就在作報告時以激昂高亢的聲音說“:我們身在天下第一山水的桂林,生活在天然畫廊的漓江畔,漓江兩岸聚居的十多個少數民族所創造的豐富悠久的民族民間文化是我們的乳汁。我們比之外地畫家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應該創造出獨特的藝術。我們要創造‘桂林畫派’。”⑩陽太陽在作品上的探索,與以文化自覺的高度號召成立本土畫派是同步進行的,有繪畫實踐,有開展的理念,還有具體的實施工作。他的不斷呼吁,為后來以黃格勝為代表的新生力量創立漓江畫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小結
以陽太陽為代表的老一輩畫家,經過了20世紀初的反叛中國傳統的狂飆突進思潮,抗日戰爭的國家危亡時刻,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現代民族文化復興,“”極左浩劫的洗禮,新時期的探索之途等一系列的歷史性時段,千錘百煉,在廣西繪畫的文化自覺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最初時,他只是在藝術社團中做輔助性支撐工作,但隨著歲月的歷練,他逐漸走向歷史前臺。從被動走向主動,從跟隨走向自覺,從淺稚走向成熟,最后成為新的青年一代的引路人。他從最初的純粹西式油畫見長,到鐘情于滿含水墨雅韻的水彩,再到融水彩色調入畫的水墨,以及晚年帶有抽象極簡意味的水墨,擺脫了中西隔閡的藩籬。真力彌滿,萬象在旁,他的繪畫到了晚年,已經達到了萬物皆備于我狀態,再不追求什么刻意的畫種模式的門戶之別,笑看寫實寫意的人為區隔,而是信手拈來,畫風多元。這,即是所謂歷經滄桑之后的大自在。
作者:簡圣宇單位:廣西藝術學院教授
- 上一篇:土司制度歷史地位新論范文
- 下一篇:遠程審判方式的探索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