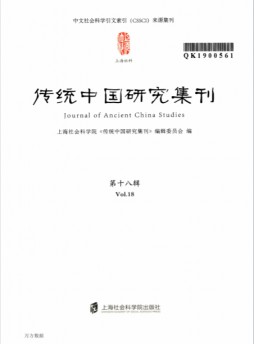傳統四維審美人格教育哲學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傳統四維審美人格教育哲學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重視以“善”為核心的德性涵養,陶冶仁善人格
仁善是生命之根,是審美情感的源泉,是人類生生不息的追求。中國傳統教育哲學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仁善”哲學。
(一)儒家的仁善人格表現為以“仁”為核心“仁”即仁愛,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把“仁”提升到做人的道德層面。孔子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范集于一體,形成了以“仁愛”為基礎的倫理思想結構,包含孝、弟、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仁愛在行為上表現為施利和寬容。施利就是開放博愛的胸懷,充分考慮和顧及他人的利益,盡可能多地施利于他人,對天下之民惠之以利。寬容表現為一種寬厚的情懷,《論語•陽貨》中提到“能行五者①于天下,為仁矣”。[3]寬容還表現為以待自己的態度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愛的終極價值取向是培養“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內圣”指對內修己,通過內在修身養德,達到內心精神生活的熏然慧慈,臻至極善,從而明智而圣善地立于社會人群、家國天下、宇宙萬物之中。“外王”指成就外在事功,達濟社會,踐行和承擔社會責任,“齊家治國平天下”。通過內外兼修,“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天下”,澤潤社會,贊化蒼生,達到美善圓融,從而完成仁善人格的陶塑。仁愛的結果是最終達到一種施仁成樂的“樂生”狀態。樂生者的心靈始終處于一種快樂的歡欣狀態———“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4]仁愛之人總是時刻與快樂相鄰,離快樂比憂郁更近,正所謂“仁者不憂”。在仁愛者那里我們看到生命不息地流淌,感觸到發自內心的由衷之樂。
(二)道家老子的仁善人格表現為“厚德載物”的自然情懷在老子心目中,大自然厚德載物,是仁善人格的化身,大自然有仁厚和博大的胸懷,不間歇地博施善行,哺育贊化著人。老子在《道德經》里多次用“水、溪澗、山谷”等來托比大自然溫和包容、質樸純厚的情懷。他說“上善若水”,意謂上善的人,就應該像水一樣溫和包容,涵養美德。他由衷地贊美溪澗、山谷孕育和乳養萬物而綿綿若存的偉大,《道德經》第二十八章中提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5]這要求人們學習澗溪和山谷質樸仁厚的美德。《道德經》第六章中提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6]谷即“虛下”、“不滿”、“不冒沖”,他用女性生殖器“牝”作為谷神的象征,贊美谷神孕育萬物而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的偉大,倡導人們要以谷神為道宗,學習其守虛和綿厚的胸懷。
(三)道家莊子的仁善人格表現為德性修煉的圓滿莊子的仁善人格主要是指超越了生命外在形體的精神人格,表現為一種德性修煉的圓滿所達到的純粹的精神本我的美善。如果說儒家的仁善人格還有一些外在的附麗、修飾和渲染,如禮儀道德規范、華美袍服的包裝,那么莊子的仁善人格則更純粹、更至美,臻于神化和圣化。莊子的仁善人格有兩種,一種是道德修煉到極致,精神完全脫離了形體或者說沒有了外在形體的真人和神人。在莊子那里,真人和神人已修煉到了與天齊,能夠“天”、“人”不分的境界。他們氣象強大,能量無極,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并照。如莊子在《大宗師》里講的真人,其智慧與大道已融為一體,真人的氣象是“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登高不憟,入水不濡,入火不熱”。[7]真人不倚眾凌寡,不自恃成功雄踞他人,也不圖謀瑣事。登上高處不顫栗,下到水里不沾濕,進入火中不灼熱。莊子在《逍遙游》里講的神人更是如夢如幻、縹兮緲兮、吸風飲露、乘云駕霧、凝神定氣間,使萬物不受害而年年五谷豐登,德澤萬方。另一種是尚有形體,但身體殘缺不全的人。莊子世界里的殘疾人雖然身體殘疾,但瑕不掩瑜,其內在德性的人格魅力熠熠生輝,令人傾慕。如莊子在《莊子•德充符》里講過一個故事,魯國有個受過兀刑被砍掉一只腳的人,名叫王駘,跟從他學習的人與孔子的門徒相當。他立不能行教,坐不能議事,弟子們卻空懷而來,學滿而歸。這是為什么呢?言外之意,是他的德傾倒了眾弟子。
二、推崇澹泊寧靜超功利的真性情,陶塑恬淡人格
恬淡是一種超脫了世俗功利的審美情感,體現為一種內心樸素的真性情或澹泊恬適的超然之情。在恬淡中,心境有一種清涼的歡欣,生命拋卻了功利的喧囂和聒噪,達到了釋然的極致。
(一)儒家的恬淡人格表現為安貧樂道和豪邁執著儒家的恬淡人格不是消極地遁隱,而是以一種積極的姿態迎接人生的挑戰。儒家君子在生活上可以安守清貧,但精神上卻豪邁執著,勇擔大義。孔子力倡積極進取的恬淡精神,提出“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他認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即便生活清貧簡樸,“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也會樂在其中。顯然,在孔子那里,恬淡是超功利的,是人之本然的自然流露。君子憑借這種自覺的恬淡,欣然坦蕩、無私無愧地行走于天地間,何來戚戚然。
(二)道家老子的恬淡人格表現為寡欲和不爭老子的恬淡人格主要表現為寡欲和不爭。《道德經》第十二章中提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8]這段話幾乎成了老子恬淡人生哲學的集中體現和警世圣典。老子高度概括了人與財物名利的辨證關系,并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為隱喻,說明功名利祿如飄風驟雨,來去匆匆,告誡人們要學會舍棄。他反對為名利歇斯底里爭搶的行為,要求人們修身養性,拭凈心靈的泥沙與塵垢,做回真實的自我。老子提出要向嬰兒學習“滌除玄覽,專氣至柔”,[9]凈化欲念,斫卻和清除心靈的蕪穢和鄙障,保持嬰兒一般的無邪、柔靜和恬然自適。
(三)道家莊子的恬淡人格表現為精神的忘我與蝶化莊子的恬淡人格表現為一種精神完全超脫世俗功利牢籠束縛的蝶化精神,精神世界的云卷云舒、鳶飛魚躍才是他所殷殷向往的。1.看淡功名利祿,物我兩相忘。莊子視功名利祿為浮云,他坐在云朵上看世界,胸中有一種蒼茫與浩瀚的大氣象。莊子認為人僅是蒼茫宇宙間一匆匆過客,功名利祿都是儻來之物、身外之物。《莊子•繕性》提到,“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10]只有擺脫世俗高官厚祿的羈絆,內心才能實現自適、自洽、自足、自樂,這要求人們服膺天地大道,拋棄世俗功名利祿的束縛。2.持守心靈的攖寧,達到釋然的極致。莊子要求人們擴充自己的精神,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強調心靈之鄉才是人們終極的眷注。在莊子看來,生活應歸于自然,應陶然忘機,忘掉成心、機心,最后達到形若死灰槁木,心如定云止水的境界。他主張修身養性,要求人們忘記自己,忘記生命,外化而內不化。莊子提出該境界修煉的辦法是“坐忘,心齋”。“坐忘”就是“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11]即擺脫形體和感官智巧的束縛,與大道相合為一。“心齋”就是“聽止于耳,心止于符”,[12]即內心保持寂靜和攖寧。
三、倡導含斂守虛精神操守的養成,陶鑄謙遜人格
謙遜人格表現為含斂守虛,不張揚不外露,深斂外在情感而不作任何思慮,謹慎地持守心中的一點靈氣用以通達外在事物,心胸坦蕩遼闊,心境虛靜篤定,澄澈而無雜繞,快活并富有生氣。
(一)儒家的謙遜人格表現為以“和”為精魂的君子人格對于謙遜人格,孔子在其撰述的《尚書》中早就提出“滿招損,謙受益”的濟世良言。謙遜在儒家那里是一種“和”的氣象。儒家的謙遜人格主要表現為以“和”為行為特征的君子人格。如果說“仁愛”是儒家君子人格的內在品質,那么“和”則是儒家君子人格的外在行為表現。1.“和”的本質是和諧。和諧有兩層意思:一是“中和”之意。如《論語•雍也》提到“質勝于文則野,文勝于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也”。[13]二是與人為善,與人和睦相處。如《論語•衛靈公》中提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14]《論語•為政》中也提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15]2.“和”的繩墨是“禮”。“禮”即溫和、含蓄、不自滿,包括三層含義:一是溫和。溫和即謙和、謙讓、不過激。如《論語•顏淵篇》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論語•先進》中的“過猶不及”。[17]二是含蓄。含蓄即內容飽滿卻不自我賣弄,如《論語•里仁》里的“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18]《論語•子路》中的“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19]三是不自滿。表現為在日常生活中嚴于律己,自省自律,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20]“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21]個人學習方面不斷修習,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二)道家的謙遜人格表現為含斂守虛與謙卑退讓的天地人格老子和莊子站在大宇宙觀的境界思考天地萬物運行的規律,最終參悟出天地萬物所秉具的天地人格規律,即含斂守虛與謙卑退讓。關于含斂守虛的美德,老子在《道德經》里多次提到,要求人們含斂守虛,戒驕戒滿,如《道德經》第四十五章中的“大成若缺,大盈若沖”;《道德經》第五十六章中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25]《道德經》第八十一章中的“善者不辨,辯者不善”。[26]老子不僅頌揚含斂守虛的美德,而且還進一步從正反兩方面說明有無此美德的利弊關系,如《道德經》第二十二章中提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27]意思是不自以為能看見,所以看得分明;不自以為是,所以是非昭彰;不求自己的榮耀,所以大功告成;不自以為大,所以為天下王。《道德經》第二十四章中指出,“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28]意思是自以為是的人,是非總是辨不清楚;自我顯露的人,反而不能自明;自我夸耀的人,事業不會有成就。他要求人們含斂鋒芒,韜光養晦。莊子在《知北游》里更是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為天地含斂守虛的美德唱了一支大氣磅礴的贊美之歌,其中隱喻著對人的要求,他深刻了悟人應明白自己在天地間的處境,認為天地、四時、萬物都那么深沉含蓄而不言,更何況人呢?他還指出:“夫昭昭生于冥冥,有倫生于無形。”[30]言外之意是說天地萬物的生長都遵守“大道”的法則,從冥冥中產生光明,從“無”中產生“有”,要求人應學習“大道”的寧靜守虛的美德。關于謙卑退讓的美德,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四章中說:“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衣養萬物而不為主,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31]意思是說大道如水般奔騰不已,浩浩蕩蕩,無時無刻不在哺育著萬物,萬物依靠它而生生不息,充滿生機,而大道從不居功恃傲,自高自大,總是很謙卑,正因為它始終不自以為大,才真正成為最偉大的存在。他要求人們學道精神,培養遼闊的境界和無私的胸懷。
四、強調生命存在與靈魂棲遲的詩意性,陶養浪漫人格
浪漫人格體現為生命主體超越外在世界的束縛,逍遙地寢臥,藝術化地生活,心靈自由地馳騁與飛翔,性靈中的真性情得以釋放,從而由現實王國走向理想的自由王國。
(一)儒家的浪漫人格體現為藝術人格儒家非常重視藝術教育,倡導以藝術教育來陶冶人的情操。“六藝”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內容。孔子尤其力倡君子要通過音樂和詩歌藝術陶養身心,在藝術的熏陶中完成自我生命的審美。《論語•八侑》中提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意思是說音樂是穿越人心靈的天餉,一開始五音齊鳴,排山倒海,跌宕昭彰;接著小河流水,九曲回腸;繼而涓涓溪流,緩緩流入人的心田。孔子還充分肯定了詩歌在情與理上的教化功能,《論語•陽貨》中提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他對詩歌的疏瀹身心功能和社會教化功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孔子認為人格修養的最高境界是一種自由的、臻于詩意的藝術境界,而不是嚴謹的道德境界。《論語•述而》中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顯然,在孔子的道德大熔爐里最終冶煉出的不是充斥著“之乎者也”道德禮教的嚴苛與沉悶,而是謙和、儒雅與詩意,人格修養最后在藝術的氤氳中完成。孔子向往的生活是“曾點氣象”,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35]生命個體在詩情畫意的自然山水中沐浴身心,于清風中翩翩起舞,然后唱著歌歡快地歸去,不亦樂乎。生命完全超越世俗的名韁利鎖,進入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翕動的審美境界。
(二)道家的浪漫人格體現為超然人格莊子的浪漫人格體現為超然人格,超然人格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超然人格的最大特點表現為精神上的“傲然展翅”和人與自然共生共游。莊子的內心世界堪稱大宇宙、大周天,他身在人間,心在太虛,“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乘風御氣,傲睨萬物進行著精神的巡天遨游。莊子在《逍遙游》里講述的一些故事無不充滿浪漫神奇的色彩。在“鯤鵬圖南”的故事里,鯤鵬傲然展翅,水擊三千里,扶搖羊角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游北冥南冥。這是何等的恢弘氣象和磅礴氣勢。在“列子御風”的故事里,列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御風而行,行云流水,進入化境。這是何等的優游自在、無掛無絆,這又是怎樣的空靈與曼妙。2.童話般的精神世界。莊子的超然人格還表現為一種童話般的天真與爛漫。他用奔騰的靈思和奇譎的妙想,為世人建構了一個詩意浪漫的童話精神世界。《莊子•齊物論》里的“莊周夢蝶”、“乘瓠而游江湖”等寓言故事堪稱寓言中的寓言,靈妙中的靈妙,簡直是天下奇聞,令人匪夷所思,而又拍案叫絕。不僅如此,在莊子童話般的心靈世界,勞動也變得那么富有激情而有滋有味。莊子在《莊子•養生主》講了一個“庖丁解牛”的故事,說的是有一個姓丁的廚師替梁惠王宰牛,心神交融,游刃有余,手所接觸的地方,肩所靠著的地方,腳所踩著的地方,膝所頂著的地方,都發出皮骨相離聲,刀進刀出,如歌如舞。在莊子心中,勞動也不那么乏味,而是如同從性靈中呼之欲出,充滿詩意,簡直就是一種藝術的享受,真正臻于儒家所提倡的“游于藝”的境界了。誠如紀伯倫所言,“在你工作的時候,你是一把管笛,從你心中吹出了時光的微語,變成音樂”。3.對待生死疾病的超脫。莊子的故事里有許多描述他對待生死疾病的觀點。如《莊子•至樂》里寫道,莊子的妻子死了,惠子過來吊唁,莊子盤膝而坐,敲擊著瓦盆唱著歌。此舉動令常人不可思議,但恰恰說明了莊子能欣然面對生老病死的開朗與曠達。《莊子•大宗師》還讓我們看到莊子對待身體疾病的樂觀自適,“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意思是說,如果疾病使我的左臂變成雞了,那么就讓這只雞打鳴司晨與司夜去吧。如果把我的右臂變成彈丸,我就用它去獵獲鴞鳥。如果化我的屁股為車輪,把我的精神變作馬匹,我就乘著這駕馬車出行,誰還需要再另行套車去呢!可見,莊子無時無刻不在享受著生命的天餉!21世紀是物質文明輝煌鼎盛的時代,也是人類精神渴望回歸的時代。溯洄于歷史的河流之中,我們恍若看到,老子正于混沌與杳冥中,舞動著思想的狐步,恍兮惚兮,縹兮緲兮,用神奇的玄思、神性的思辨、藝術的語言、鴻蒙的詩意澆灌著他的天地人格。莊子正鯤鵬展翅,帶著永恒的鄉愁,心游萬仞,翱翔于天地間,放飛著他的超然人格。孔子還是那么一往情深,在鄉野,在桑陌,在陋室,或是恂恂教言,孜孜不倦,或是御琴鼓瑟,弦歌不斷,熔鑄著他的君子人格。他們以其智慧光芒福潤天地蒼生、蕓蕓眾生,陶冶著我們的思想和情感,啟迪著我們的心靈。
作者:丁紅玲單位:山西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 上一篇:學習和研究教育哲學論文范文
- 下一篇:學習支持服務的遠程教育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