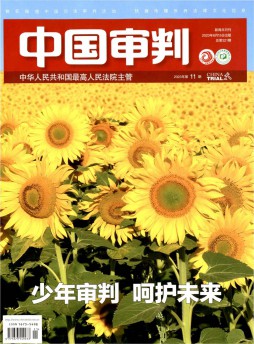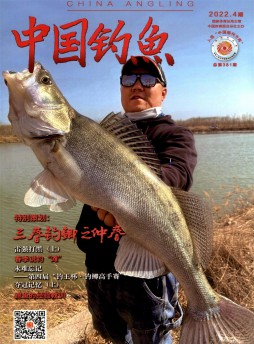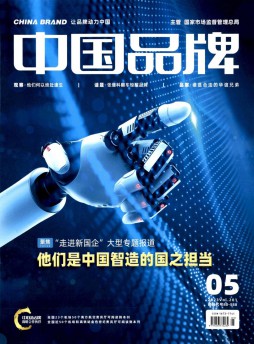中國修辭學學科建設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修辭學學科建設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學科自身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根源
學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受社會和學科內外對對象學科價值和地位的體認和評價的影響。對于修辭學的學科形象,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直到今日,一直眾說紛紜,毀譽交加。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諸如“困境”“缺席”“失語”“邊緣化”“弱勢”等關于修辭學科現狀和趨勢的種種負面聲音,不但出自學科內部,也源自學科外部,雖然未必盡如事實,但也絕非空穴來風。歷史和現實的諸種因素共同作用,已然導致學科環境趨于惡化,學科隊伍建設、成果建設受阻,學科整體形象受損。新世紀以來觀察、思考、評論中國修辭學學科建設和發展問題最深入的學者之一無疑是譚學純。他以大量事實和數據,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國修辭學科面臨的生態窘境:“修辭學科生態系統中,同行學術認同的理想形態和現實形態產生了矛盾”,小同行信心不足,出現“去修辭化”(離場和換裝)與修辭學科“空心化”趨勢,導致自我認同危機和悲觀情緒放大。在他看來,學科所謂的“弱勢特征”,結構性弱勢大于學術性弱勢,體制性弱勢強化了學術性弱勢,學術性弱勢又加劇了結構性弱勢,固化了體制性弱勢①。“多種原因造成的學科弱勢特征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弱勢-邊緣’的學術心態,以及由此滋生的學科自卑;可怕的是,面對強勢學科壓力的自我迷失。”②字里行間充溢這學科自省和學科自尊。吳禮權分析修辭學科重要性未受到應有重視的根源來自“歷史偏見”和“現實困惑”兩個方面,包括由來已久的反修辭傳統造成的誤讀,學科定位、人為因素、隊伍建設等造就的現實困局。③馮廣藝則指出,中國修辭學科學術隊伍梯隊分布不合理,缺乏像陳望道那樣的大師級領軍人物,而學科的中堅力量不穩固,年輕學者中成果突出者寥寥無幾。④汪國勝肯定修辭學的長足進展和繁榮局面,同時特別提醒人們認真思考和正確對待五組關系的協調發展:理論與事實、廣度與深度、靜態與動態、實用性與科學性、學科發展與學風建設。⑤任何學科都需要在研究中不斷突破自己。修辭學界關于學術突破的話題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被提及和探討,新世紀以來無論是認識和實踐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討論較多的問題有:一、學科的重新定位;二、理論和方法的更新;三、問題研究的深廣度;四、其他相關方面的問題。新世紀以來中國修辭學研究,幾乎一直伴隨著學科定位的爭執。譚學純指出:語言學的修辭學學科定位,強調語言學的理論資源、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技術路線。交叉學科的修辭學學科定位,吸納、改造、整合多學科的理論資源、闡釋路徑、研究方法。鑒于現有的局限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學科建設與發展,譚學純主張并實踐以語言為本位、以交叉學科為外延的開放性定位。⑥對修辭學理論和方法的更新問題,學者們議論最多。前述“首屆望道修辭學論壇”就將研究方法設定為兩大中心議題之一。高萬云認為,缺少問題意識、方法意識、目的意識,是修辭學陷入當下尷尬處境的內因①,因而有必要創建修辭理論和方法的分層體系,“把一般修辭學與個別修辭學、本體修辭學與交叉修辭學、廣義修辭學與狹義修辭學等各種對立關系區別開來”②。譚學純則從全球化語境下的發展角度提出要求:中國修辭學融入全球視野中的同類研究格局,需要了解基于不同學術機制和社會認同度的修辭學學術空間,需要消化外部智慧,更需要以自己的學術形象和民族身份的清晰度,進入全球視野⑤。“缺乏深度是當代修辭研究的主要癥結”,具體表現在:“對修辭學的學科本質屬性缺乏深入的研究,對修辭現象缺乏深入的分析,對修辭學與鄰近學科之間的關系缺乏深入的了解,對修辭學的理論和方法缺乏深入的把握。”⑥張煉強先生的這一看法,用于概括當下中國修辭總體研究的根本或主要問題之一,應該不會有太大爭議。當然,這決不意味著對修辭學過往和現狀的徹底否定或貶低,相反,事實是中國修辭學從來都不缺乏富有影響力的大師或學者,也從來不缺乏富有深度的論著。科學的真諦和生命在于創新,在于新問題的發現,更在于對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不斷取得新進展,“缺乏深度”對于任何學科而言都是可怕的甚至致命的傷害。中國修辭學當下因為存在多方面的病源,特別是某些特殊病源,相比不少學科而言,“缺乏深度”的問題也許更嚴重,也更令人擔憂。特殊病源之一,對于“科學化”和“人文性”的關系存在片面理解或模糊認識;之二,對于狹義修辭或語言學的修辭學學科定位的認知和把握上存在局限或偏差;之三,學科邊緣性或多邊性特點對研究者學養、研究手段等的較高標準或特殊要求往往不易達到,而高學歷高素質人才的培養一直都不具備任何與語言學其他分支學科的比較優勢,更何況還受困于隊伍斷層、流失或自信不足等現實問題。
二、學科建設和發展的方向、路徑和側重
如何直面現實,應對問題,深化研究,重振形象,是擺在修辭學廣大同仁及眾多關心支持中國修辭學發展的有識之士面前的第一要務。新世紀以來,學者們在繼續查找問題的同時,更注重探尋問題的解決之道,設計具體方案,并付諸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實踐。
(一)學科發展方向:“走向大視野”,“融入大生態”
找準發展的大方向,無疑是學科反思的首要目標。譚學純對此極力主張,并多方論證了其必然性。“消除學科誤解的最好辦法,是拿出讓人重新認識這個學科的研究成果”⑦。而要拿出原創性、標志性的新成果,基于交叉學科性質和跨學科視野的修辭學,就必須敢于突破囿于或偏于修辭技巧的傳統研究模式,自覺投身開放的學術話語場,“融入大生態”。只有融入大生態,才能更好地體現學科存在價值,推助問題驅動的學術創新,提升學術成果的公共影響,推動大生態中的相關學科共同發展。⑧譚先生還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力主修辭學研究“突圍”:“走出‘就語言談語言’的技巧論,走向更為開闊的公共學術空間”。“突圍”是研究視野和方法意義上的,是避免在相關學科“修辭學轉向”難得的歷史機遇面前“旁觀”和“失語”,開展“對話”的需要,是開拓學術空間的現實需要,是“走向大視野”,從而“融入大生態”。因而,“突圍不是意氣之戰,不是放棄修辭本位,而是更為開放的堅守,是為修辭學研究重建一個更大的平臺,為修辭學研究者尋找更大的舞臺,在更闊大的思想背景中,面對多學科審視的目光。”⑨雖然在對“大視野”“大生態”“突圍”的理解上不可避免地還存在一定的分歧,但這一主張事實上已經越來越為人們所了解、信服和重視。正如宗廷虎先生評價的那樣,修辭學走向大視野、融入大生態的主張“植根于古今修辭實際,基礎厚實,立論牢靠,得到了眾多學者的贊同”。也有學者提出其他設想。有人主張將中國修辭學建設成為語言學中的一門核心分支①,也有人提出建立以修辭為綱的語言教學體系和以修辭學為中心的學科體系②。劉亞猛則認為應該借鑒當代西方人文學科的范式轉換,重新思考中國修辭學的發展模式③。
(二)學科發展路徑:多元化
方向一旦確立,接踵而至的就是道路的選擇和開拓。“首屆中國修辭學多學科高級學術論壇”圍繞“大修辭觀”的學科定位、學術研究的原創性(孫紹振)及提升原創性的途徑:通過中國古代修辭理論資源的發掘和現代轉換(朱玲),通過走向社會、貼近生活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胡范鑄),通過關注學科外的需要(王希杰),通過更新修辭學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論等,以及拓寬修辭學的研究領域,開拓修辭學的研究視野(馬慶株、譚學純、張宗正),加強修辭學學科隊伍的建設、提高修辭學學術期刊的水平(李熙宗、張先亮)等問題,貢獻了建設性意見。④新世紀以來,學界在以往研究范式的基礎上,注重新的“研究范式”的構建和實踐,如劉亞猛主張“修辭象征研究”、劉大為倡導“修辭構式研究”、胡范鑄提出“新言語行為研究”,還有不少其他學者試圖引入“互文性分析”“語篇分析”“批評語言學”“社會心理分析”“傳播理論”“認知學科”等新興理論和方法建構修辭學研究范式。其中,新的研究范式中影響最大、成果最豐的無疑是譚學純等“廣義修辭研究”,不但有系統的理論闡發,如《廣義修辭學》,更有深化細化的理論展開和一系列成功的實證檢驗,《廣義修辭學演講錄》《文學和語言:廣義修辭學的學術空間》《修辭研究:走出技巧論》《修辭認知和語用環境》等。這一范式“能從多門科學的結合部看到修辭學的新生長點,能從多種方法的融匯處找到修辭學研究的新途徑”⑤,作為學科建設和科學重建的突出成果,已經并將繼續為新世紀中國修辭學的理論創新和學科創新發揮良好的示范、引領作用。面對各種“范式”“模式”層出,各種“理論”“方法”競爭的局面,我們贊同譚學純的觀點:“在目前的學術生態環境下,中國修辭學研究如何選擇學術走向,不一定急于定調。不同的修辭學理論、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的研究套路和技術路線,可以多元并存。”⑥實際上,修辭學研究也正呈現出多元研究的態勢,比如高群《跨話語標記“夸張地說”及其否定形式》,立足跨學科視野,結合語法理論對修辭現象進行闡釋。⑦在認可引進、創新、突破的重要性、緊迫性的同時,有必要注意其他一些聲音。如劉煥輝特別強調:中國修辭學有其自身的學術傳統,必須堅持走傳統與現代對接的自主創新之路,構建獨具中國修辭學歷史傳統和新時代風貌的“對象、目的、方法”相統一的研究范式⑧。胡習之則堅持:修辭學研究無論怎樣拓寬、拓深都應該堅守自己的研究基點:以語言、語言運用,以表達為立足點。至少核心修辭學必須堅守自己的研究基點,否則修辭學會喪失自我,最終在多元化的背景之下慢慢地從學科群中消失⑨。學術的精髓在于創新,在于解決實際問題,絕對不應機械地搬套、克隆現成模式,更要力避脫離實際、罔顧事實的“貼標簽”“假大空”的虛浮傾向。(三)多元選擇的背后,是眾多學者在認識上有所側重與殊途同歸從研究的科學性上著眼,曹德和從對修辭學基本概念內涵和外延的界定切入,就修辭學的一系列理論問題提出獨立見解,強調修辭研究必須遵循系統原則和實踐原則瑏瑠。張煉強則認為“修辭學當前的任務是既要走出以為數量化、形式化就是修辭研究科學化的全部內涵,修辭學的出路僅僅在數量化、形式化這樣的一個理論的誤區,也要加快數量化、形式化的步伐,走出數量化、形式化舉步維艱的實踐的困境。”①高萬云進一步指出應區分“科學方法”與“科學的方法”兩個不同概念,重新認識“修辭學方法的目的性、層次性和契合性”②。從研究內容的近期側重著眼,有學者主張至少應該在語法修辭相結合的研究、漢語修辭史的研究、新媒體時代修辭新現象的研究③等三個方面有所側重;有學者則建議加強和深化消極修辭和修辭格的研究,用詞造句修辭要聯系到語篇,深入探究修辭格背后的機制及其與其他語言現象的關系④;有學者強調修辭研究的兩個發展取向:側重修辭語言與一般語言的共同點;側重修辭語言與一般語言的不同點,“無論哪一種取向,都要立足漢語事實,挖掘深層機制。”⑤在吸納多學科營養、利用鄰近學科資源方面,學者們結合親身認知和體驗,發表了不少有針對性的見解。如袁毓林結合研究案例,分析了社會心理學、心理語言學、傳統語法、認知語言學等在拓寬研究領域,更新研究方法,提高解決實際語言使用問題能力等方面對修辭學的啟發。⑥陸儉明建議學習語法學,不斷挖掘、發現語言事實,不斷更新理論和視角以發現問題,深化研究。⑦胡習之主張借鑒語用學、系統功能語言學等加強各類修辭行為的研究,借鑒傳播學理論和方法,深化細化精密化對修辭效果的研究。⑧此外,還有學者從宏觀上論及破除中國修辭學危局的“當務之急”。有人認為首先要廓清各種對修辭學科的誤解,確立正確的、科學的修辭學認知觀;清楚明白地確立起自己的研究范式;確立研究隊伍建設為修辭學發展“重中之重”的觀念。⑨有人主張多方著手付諸行動:重新思考“修辭”的“雙重性格”;整合所有學科對修辭的認識;構建健康的研究環境。瑏瑠不少學者基于現狀,對學科隊伍建設、學風和環境建設等修辭學“內部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
三、結語
相比條件、平臺、評價等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外部因素,學科成員作為整體的心態、素養、合作、實際作為,才是長久的、決定性的內因。無論是學科形象的重建還是學術研究的突破,根本上取決于學科成員作為學術共同體信心的重樹和意識的覺醒:觀念、視野、方法、范式等的“突圍”;大視野、大生態背景下的多元化選擇和重新出發。令人欣喜的是,譚學純及其團隊在修辭學研究突圍和走向大視野、融入大生態的理論探索和學術實踐中已經開辟了一條成功之路,為集結和壯大學術隊伍、提升研究實力和學科水平,重建學科形象,提供了諸多信心、經驗和啟示。
作者:段曹林單位: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 上一篇:電力系統作業設計論文范文
- 下一篇:人工影響天氣信息系統設計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