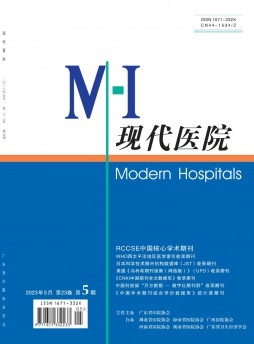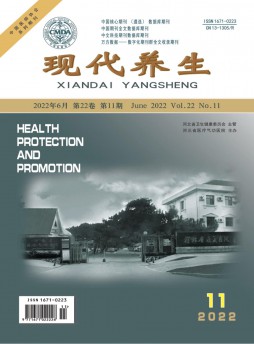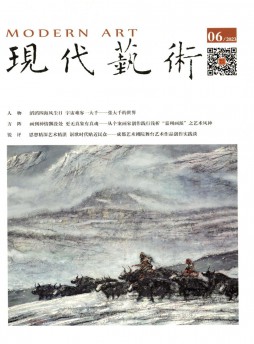現代新儒家文化方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代新儒家文化方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斯賓格勒和卡西爾文化哲學的批判性研究,引入現代新儒家探討文化的基本方式——內省證悟的方式。再以徐復觀的文化研究為個案,進一步指出:這種內省證悟的方式來談文化實際上是在儒家反求諸己的精神或工夫中來講文化的創造與發展。在現代新儒家看來,這是文化創造的根本精神和動力。由此可以解明:現代新儒家對中國文化的護持,乃是對反求諸己的精神或工夫的守護。
關鍵詞:文化現代新儒家歷史性整全性徐復觀
一.人類社會與動物群落之間的最大區別乃是在于,人類社會是一種文化的載體,而動物群落則是一種本能的集合。此即是說,人生活在文化之中,而動物生活在本能之中。人雖無時不刻不是生活在文化之中,但稍一究詰,什么是文化,則是一個令人茫然而難以回答的問題。所以,羅威勒(A.LowrenleLowell)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形狀,我們想用字來范圍它的意義,這正像要把空氣抓在手里似的;當著我們去尋找文化時,它除了不在我們手里以外,它無所不在。”[1](P26)由此可見,文化問題確乎是一個“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繁復問題。
然文化總是人的文化,故無論怎樣談文化,總割棄不了與人的聯系。以一定的方式來談文化,必定以一定的方式揭示了人的本質,這種關涉便是文化哲學的內涵。因此,所謂文化哲學其實是一種談人的方式,其根本任務就是要“揭示在抽象文化結構上的人的文化存在,亦即人的本質”。[2](P91)人的本質是什么?中外哲學史上對這個問題都有過論述,如亞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動物”,孔子所說的“仁者人也”。這些論述都是一些實體性的定義,即分別用“理性”或“仁”來圈定人的本質,其唯一功能就是把人和動物作一區分。人和動物的區分雖然很重要,因為人不能降低到動物的層次,但人生是豐富的,人不能只停留在與動物的比附上,故這些實體性的定義雖然點出了人的本質的最內核的部分,但由此也確實遮蔽了人的本質。如非理性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若我們不能在這種具體的存在方式中感受這種理性與非理性的區別,則理性只不過是一種抽象的概念,由此而說明的人的本質亦只是一種抽象的本質,它是空洞的,而不是具體可感的。因此,文化哲學欲以文化來說明人的存在,進而感受人的本質,并不是對歷史上有關人的定義的否定,而是對這些定義的豐富和超越。
這里因受劉述先《文化哲學》的啟發,擬先對西方斯賓格勒和卡西爾的文化哲學及其限制略加探討,由此引出現代新儒家對文化問題的思考。這里之所以對斯賓格勒和卡西爾的文化哲學加以討論,乃是因為二者分別代表西方兩種典型的文化哲學形態。以此二者作為引路切入,更能深切地體認到現代新儒家探討文化的方式的價值和意義。
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的主旨是嘗試對各文化系統的興衰作一歷史的探討。斯賓格勒拒絕采用一般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文化的問題。他認為,歷史文化的特質在于它有一個活潑的生命世界,一個不與一般機械物質的自然界相同的世界,我們對它的關心在于性質而不在于數量,而自然科學的方法卻是徹頭徹尾的量化觀點。依斯賓格勒的看法,生命的第一特質乃在于其個體性與不可替代性,但盡管如此,生命在其演化的過程中,彼此卻有合拍附節的共同形態出現。這種共同的形態最普遍的表現便是對“世界之希祈”(world-longing)和“世界之恐懼”(world-fear)的原始情感,把人類從世界的暗謎之中帶入到了清朗明晰的科學世界,從而引生了大部分人類理智的文化,而逃避了世界恐懼:
在原始曖昧的人類靈魂中,正如同最初的嬰孩時代一樣,有一種原始的感受,驅使它要尋找各種方法,來處理廣延世界中的各種陌生力量,這些陌生的力量,嚴酷而堅定,布滿了整個空間。而人類的這種防衛行動中最精妙、最有力的形式,便是那因果的定律與系統的知識,把陌生的一切,用符記和數字來加以軌范。
當理智的形式語言,已鑄成了一些牢固的銅瓶,把神秘的事物撲獲進來,并加以了解之后,世界恐懼便靜靜止息了。[3](P78)
斯賓格勒認為,以上所述是所有偉大的文化所共有的方法。不過,在斯賓格勒看來,盡管“世界之希祈”與“世界之恐懼”為人類普遍的原始情感,但在各民族的具體表現中,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如有的民族對“世界之恐懼”感受特深,有的民族對“世界之希祈”企望特盛。這種特殊的表現便構成了一個民族的“靈魂”與“觀念”,一個民族的文化便是在其特定的靈魂之下的觀念的興衰史。因此,在斯賓格勒那里,便不存在有“世界史”的觀念,只有各個文化興衰的局部史。這種局部史只要發現了代表其靈魂的象征符號(即觀念),如古希臘的阿波羅靈魂,西方近代的浮士德靈魂,中國的道德靈魂,印度的宗教靈魂,埃及的“石”之靈魂,墨西哥的美揚靈魂,俄羅斯的“平板”靈魂及阿拉伯文化的昧津靈魂等,在歷史中的命運就是可以被“計算”的,這便是他所自詡的“歷史的邏輯”。依照這種邏輯,每個文化在歷史中的命運是不可抗拒的,我們無須懷念其過去,也無法幻想改變其未來。我們只能站在我們的崗位上,做著命運可能容許我們所做的一切。斯賓格勒把文化建基在一個民族的靈魂背景之上,表明他對各民族“共命慧”的表現,有著深切的了悟。也就是說,斯賓格勒在對一個歷史文化的性狀的描述上,表現出了過人的見識;但在對一個文化的發展與走向問題上,卻表現出了強烈的命定主義。他自認不能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對待歷史文化問題,然卻以命定主義的態度來“計算”歷史文化,實不知不覺滑入了自然科學方法之中,而絲毫不能觸及歷史文化中的理想主義,這不能不說是斯賓格勒的悲哀。他把人類的文化劃分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互不聯系的文化系統,好像人類完全是在黑夜里胡亂摸索的孤魂。他曾美言活潑的生命世界,實則他根本未能契合人性之全,“他的歷史觀念依然完全是西方即一套機械的世界觀念的翻版,內中一點生命的光輝未見”。[4](P79)
卡西爾是新康德主義者,他的符號形式哲學發軔于康德哲學,并聲言為其學的一個繼承和拓展。按照卡西爾的看法,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分別從知識、道德和藝術的領域來表現和指示一個共同的人類精神。卡西爾從這一思路得到靈感,接上康德并不止于康德。他把康德的理性批判擴大為文化批判,欲從這里來表現和指示人類精神,即揭示人的本質,其代表作《人論》就集中地體現了這種思想。他的基本觀點是:人類文化的每一內容不只是個孤立的現象,都是建立在一個普遍的形式原理,即人類精神的創造力的活動之上。人類文化的諸領域盡可各異,但卻是人類精神同一創造功能在不同領域活動的結果。唯如此,理想主義、唯心論的基本論點才能得到真正的與完全的證實。這種人類精神的創造功能就是符號的創造活動。卡西爾認為,符號并不是對外在事物的簡單模仿,而是象征一種內在的精神動力,這一動力表現于文化活動的各個方面,而為其統一的基礎。這樣,人類的文化,即卡西爾所說的符號系統,便既不是純主觀的,又不是純客觀的,而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如此,人們通過對這種符號系統的考察,便可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這個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藝術、哲學、科學從各個不同的方面為他開放的”。[5](P53)由此可進一步揭示人性:
毫無疑問,人類文化分為各種不同的活動,它們沿著不同的路線進展,追求著不同的目的。如果我們使自己滿足于注視這些活動的結果——神話的創作、宗教的儀式與教義、藝術的作品、科學的理論——那么把它們歸結為一個公分母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哲學的綜合則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東西。在這里,我們尋求的不是結果的統一性而是活動的統一性;不是產品的統一性而是創造過程的統一性。如果“人性”這個詞意謂著任何什么東西的話,那么它就是意謂著:盡管在它的各種形式中存在著一切的差別和對立,然而這些形式都是在向著一個共同目標而努力。從長遠的觀點看,一定能發現一個突出的特征,一個普遍的特性——在這種特征和特性之中所有的形式全都相互一致而和諧起來。[5](P90)
在人類的文化創造活動的功能性統一中來揭示真正的人性,卡西爾的符號形式的文化哲學的理論追求約莫如此。并且他從神話、宗教、語言、藝術、歷史和科學等六項文化成就中,試圖說明人類萬殊的文化現象無非是同一精神的作用而形成。卡西爾的這種文化哲學的理論架構,確實展示出了他的一個偉大的綜合心靈,及理想主義的文化追求。他看到了整個的人生,未嘗以一個抽象的原理來代替甚至犧牲人生的豐富的內容。但他通過人類文化的符號系統來展示這種人生的豐富性,又表現出了他的文化哲學的極大的限制性。卡西爾的文化哲學處處都假設有一種共同的活潑精神主體力量作為基礎,符號方得以發用,這本表現出了精神的高致,然遺憾的是卡西爾始終未能契合此一精神主體而有一當下的證悟,故他僅只能從文化的現象層面描述精神的活潑作用,真可謂舍本逐末,外而非內。他以外在的歸約觀照取代內在的省察證悟,無形中便以科學抽象取代了價值主宰。事實上,他所列舉的人類文化的六項成就中獨缺“倫理”或“道德”一項,說明他對價值主體的把握不足,其興趣全放在對人類文化作平靜玄遠的抽象歸約的理趣上。他把科學安排在六項成就中的最后一項,是以科學作為人類精神的最高成就。所以,當他在《人論》一書最后一章收結時說:“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化,可以被稱之為人不斷自我解放的歷程。語言、藝術、宗教、科學,是這一歷程中的不同階段。在所有這些階段中,人都發現并且證實了一種新的力量——建設一個人自己的世界,一個‘理想’世界的力量。”[5](P228)實則在卡西爾那里隱含著人是在科學中自我解放,科學是建設理想世界的力量。盡管他在在不放棄人類精神豐富性的理想,但在他這樣一個外在歸約觀照的文化哲學系統中,在科學方法及其價值的擠壓下,人類精神的豐富性的理想就免不了萎縮和落空了。
二.斯賓格勒和卡西爾的文化哲學,雖各有其勝義,但亦有其掩飾不住的缺點,其中一個最大的缺點是:他們都是就人類文化的外在成就來談文化的問題,這是一種外在解析的方式來談文化。以這種方式來談文化,盡管也可以美言生命、精神和價值等問題,但這是切就人類文化的外在成就的解析,而不是就生命當下的內省與證悟。雖然他們都能從與自然相對置的立場來界定文化,但所走的依然是實在論的路子。這樣一來,談文化,要么像斯賓格勒那樣陷入命定主義,要么像卡西爾那樣只能談由知識建構的理想主義,而不能談道德的理想主義。如此,則人生的豐富性必喪失而掛空。唯有在道德的理想主義的文化中,方能盡人生之全蘊。但要談道德的理想主義,不能走外在解析的路,而必須走內省證悟的路,這正是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所在。
現代新儒家對中國文化所走的內省證悟之路可謂體會尤深。所謂內省證悟之路,就是從生命的念愿或生活的情調本身處來談文化。
擴展閱讀
- 1現代德育
- 2市場營銷現代到后現代
- 3將現代因素融入戲曲現代戲
- 4現代文化
- 5傳統與現代抉擇
- 6劇院現代轉換
- 7中國現代幽默喜劇
- 8現代后殖民文化
- 9現代廣告招貼設計
- 10現代家具實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