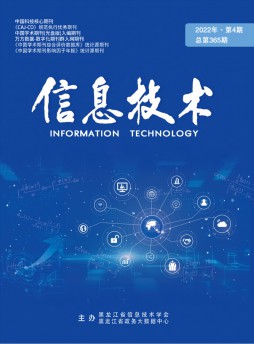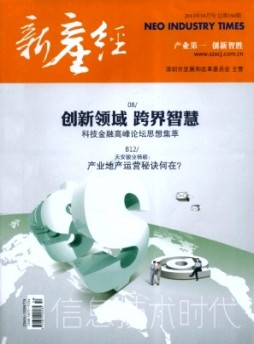信息技術哲學的展望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信息技術哲學的展望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國外于20世紀末提出了philosophyof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概念,與此相關的提法還有“信息科學與技術哲學”、“信息和通信技術哲學”等,拜納姆等認為這一哲學如同一只鳳凰正在起飛,哲學隨之轉(zhuǎn)型,一種新的哲學范式出現(xiàn)。進入21世紀后,著名技術哲學家米切姆在他參撰的由信息哲學家弗洛里迪主編的《計算與信息哲學指南》一書中,專門介紹了“信息技術哲學”,認為它可視為技術哲學的一個“特例”;他從“信息”和“技術”均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的含義,組合出四種意義上的“信息技術”:拼音書寫、書籍和相關文本、電子和源代碼信號的傳輸、高表征電子通信的媒體,這樣才可囊括它的全部含義;他認為信息技術中包含四個層次的哲學問題:倫理學、政治哲學、心理學-認識論、心理學-人類學,而最終都導向本體論層次。米切姆還認為在技術哲學中存在的工程傳統(tǒng)和人文傳統(tǒng)同樣存在于信息技術哲學中。一些相關的國際學術會議上也將信息技術哲學作為會議的議題,如2005年6月2—4日在瑞典馬拉達倫大學召開的歐洲計算與哲學年會的議題三就是“信息與信息技術哲學”。2009年荷蘭特文特大學的技術哲學家布萊(Brey)和索拉克(Sraker)發(fā)表的長文《計算和信息技術哲學》對信息技術哲學的綱領和研究框架加以了初步的描述,認為該研究的綱領應該是寬廣的和多樣化的,涉及的問題有計算系統(tǒng)的性質(zhì)、虛擬世界的本體論地位、人工智能的限度、數(shù)據(jù)模式的哲學方面、賽博空間的政治規(guī)則、因特網(wǎng)信息的認識論、信息隱私和安全的倫理方面等等;他們將信息技術哲學的研究領域概括為五個:計算哲學、計算機科學哲學、人工智能哲學、新媒介和因特網(wǎng)哲學、計算機和信息倫理。他們認為,信息技術將新的光亮投射到傳統(tǒng)哲學問題之上,提出了一些在傳統(tǒng)哲學框架內(nèi)不易觸及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作為技術哲學新型分支的信息技術哲學,其內(nèi)部還有更加微觀的分支,形成“分支性的信息技術哲學”。在這方面,國外的研究可以說形成了兩個方向的“分支”,一是關于信息技術的“分支哲學”研究,二是關于“分支信息技術”的哲學研究。關于信息技術的“分支哲學”研究,即是從哲學的不同側(cè)面(如本體論、認識論、社會哲學或人本學等)對信息技術加以的研究。麥克盧漢的媒介哲學,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卡斯特的“信息主義”可以說構成了關于信息技術的“社會歷史哲學研究”,所形成的“信息技術決定論”的哲學觀念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在這個方向上還有關于信息技術的道德哲學研究;關于信息技術的美學研究和關于信息技術的人本學研究(例如關于cy-borg①的超人主義研究)等都是目前的熱點問題,呈現(xiàn)出這一領域的不斷成長和走向興旺的局面。
可以說對信息技術的人本哲學研究是信息哲學的這一分支研究中最為興盛的領域,其中賽博人與虛擬主體所引發(fā)的哲學問題最為引人關注。在研究者看來,信息技術正在開始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就像假肢技術所發(fā)揮的功能一樣,后者取代或增加了人的生物功能,將人類變成賽博人,從而改變?nèi)说男再|(zhì)。那么這種變化是好事從而是值得的嗎?來自于認知哲學家的看法以安迪•克拉克為代表,他認為信息技術已經(jīng)延伸和協(xié)同建構了人性,特別是人的認知。他得出的結(jié)論是:人是自然出生的賽博人。西蒙•楊的超人主義(transhumanism)也對賽博人理論持正面的看法,他認為這一技術的目的是通過人的增強來增加人的自治和幸福,消除人的苦難和疼痛(可能的話也包括死亡)。于是達到一種超人類或后人類的狀態(tài),其中身體的和認知的能力靠現(xiàn)代技術而增強。生命保守主義(biocon-servatism)則反對上述看法,認為人性不應該通過技術來改變,人的增強是非自然的,會損害人的尊嚴和平等,并且是身體上和物理上有害的。而謝莉•托克認為虛擬身份的變化證實了后結(jié)構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關于主體的理論,表明自我是被建造的、多重的、境遇性的和動態(tài)變化的;這些不同的虛擬身份背后沒有一個穩(wěn)定的自我,這些身份連同在真實生活中投射出來的其他身份一起,集合地建造了主體。馬修斯看到電子人和虛擬身份之間的關系,認為兩者都為相似的原因受到支持或譴責,也就是它們都顛覆了傳統(tǒng)的固定身份的概念,甚至還掩蓋了人的真實性,使人缺乏責任感。信息哲學的創(chuàng)始人弗洛里迪對因特網(wǎng)的意義加以了理論性的探討,認為21世紀出身的人可能是能將下線和在線清楚區(qū)分開來的最后一代人,并認為信息社會正在變成“信息器官的鏈接”或“信息人”(Inforgs),抑或說我們正在成為“唯一的能夠創(chuàng)造并適應一種綜合環(huán)境的生物物種”。而一種更包容的看法,是認為人的身體與數(shù)字技術存在一種協(xié)同進化的關系。關于“分支信息技術”的哲學研究,就是對信息技術的不同領域或側(cè)面所進行的哲學研究,目前較為流行的有計算和計算機哲學、網(wǎng)絡哲學、通訊技術哲學、賽博哲學、數(shù)字哲學、媒介哲學、虛擬實在哲學、人工智能哲學等等,例如阿伯丁大學哲學教授戈登•格雷厄姆的《網(wǎng)絡:哲學的探索》是網(wǎng)絡哲學的早期代表作,書中討論的問題有:網(wǎng)絡是怎樣影響我們的身份概念、道德觀念、審查制度、虛擬現(xiàn)實和社區(qū)、民主、想象力的?他還調(diào)查了如下問題:網(wǎng)絡的新意、網(wǎng)絡中新的政治方式和形成社區(qū)的可能性、還有個人隱私問題等。也有將哲學分論與信息技術分支結(jié)合起來形成的研究領域,如“數(shù)字形而上學”(DigitalMetaphys-ics)、“互聯(lián)網(wǎng)認識論”(“Internetepistemology)等。
互聯(lián)網(wǎng)認識論最初是由保羅•薩嘎達(PaulThagard)用來稱呼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科學信息活動中的認識論的,而今它得到了更廣泛的應用。互聯(lián)網(wǎng)認識論所探討的問題包括: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的認識論特征,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生產(chǎn)和消費的規(guī)范內(nèi)涵,互聯(lián)網(wǎng)相關活動(包括信息利用、管理和生產(chǎn))的認識論,阿爾文•古德曼(AlvinGoldman)把互聯(lián)網(wǎng)的認識論問題歸結(jié)為相關性和可靠性問題。如果相關性問題未能有效解決,就導致信息過載的問題;信息過載導致受眾的信息疲勞,甚至變得在決策能力上的癱瘓,或使他們對關心的問題停留于不知情。可靠性問題主要在于任何人都可以把信息放到互聯(lián)網(wǎng)上,網(wǎng)站缺乏選擇信息和提供參考文獻的標準,這被安通•韋德(AntonVedder)稱為內(nèi)容標準和系譜標準(contentcriteriaandpedigreecriteria),后者是信息背后的人或組織是否具有權威、守信、信譽的認識論標準。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到,信息技術提出的哲學問題很多,但在目前的哲學研究視野中并未形成總體性的提升,從而使得信息技術哲學處于“分支研究繁榮,總體層面不足”的狀況,尤其是作為一般信息技術哲學的框架并不系統(tǒng)和完善。有的研究者雖然深入到了其中的具體問題和內(nèi)容,但又基本僅限于對局部信息技術的哲學探討,尤其主要是對“網(wǎng)絡”、“計算機”、“賽博人”等對象的探討。這些分支性和局部性研究雖然是對信息技術總體研究的必要前提,并為總體性的信息技術哲學研究提供了智力基礎,創(chuàng)造了先決條件,但它們的繁榮無疑還不能取代后者的興旺。由于對總體性的信息技術的總體性哲學分析不夠,使得在當前的信息技術哲學研究中還沒有關于信息技術的一般哲學問題(例如信息技術的哲學含義和哲學特征是什么、信息技術“進化”的普遍法則、當代信息技術與傳統(tǒng)信息技術的內(nèi)在關聯(lián)是什么)的揭示,信息技術的哲學分析框架或哲學問題系統(tǒng)還未建立,因此對于信息技術的深刻哲學意義遠未充分把握。有鑒于此,目前急需用更開闊的哲學視野來分析整體性的信息技術,形成一種對信息技術的總體性的哲學研究。這種“總體性”一是包括時間上的總體性———不僅指當代信息技術,而且指歷史上的信息技術;二是包括類別上的總體性———不僅指計算機、網(wǎng)絡等,而且指觀察儀器、顯示手段、輸入裝置等等。這種總體性這就是將信息技術擴展為一個一般的技術范式,從而使信息技術哲學的對象從信息技術特殊上升到信息技術一般,并進一步把信息技術哲學擴展為一種一般的技術哲學范式,使信息技術與哲學形成更為內(nèi)在的關聯(lián)。在這種擴展中,信息技術哲學或許要重點探究新的本體論問題,包括:信息技術的本質(zhì)是什么?信息技術對世界的本源論、存在論和實在論提出了哪些新的問題?歷史上的信息技術革命導致了哪些本體論觀念的變遷?在米切姆看來體現(xiàn)這種本體論追問的具體問題還有:軟件控制硬件的本體論問題、“程序”的本體論地位問題,它們和“意圖”的關系是什么?尤其是涉及“實在”時,“信息技術可能會以遠比簡單的信息過載更為基本的方式隱匿實在,使我們不能得見。這可能在較心理更深刻的層面扭曲我們的存在。”這里不能不提到當代信息技術所造就的“虛擬實在”,它使得真實與虛擬、數(shù)字與模擬混合在一起,原型將越來越難以辨認,人們將無法弄清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于是,客觀世界本身是否如同虛擬世界一樣不過是對我們的一種刺激?下線的世界與在線的世界在我們的感知活動中有何實質(zhì)的區(qū)別?從本質(zhì)上虛擬技術是否增加了對哲學基本問題解決的新方案?它是否會導致這個世界的某些根本性的改變?它對我們理解“終極性問題”提供了什么新的啟示或方向?凡此種種,均是虛擬實在與現(xiàn)實實在的本體論關系問題。由于這些哲學問題從根本上是當代信息技術造就的,無疑也成為信息技術哲學興起的深厚土壤乃至整個哲學探新的“富礦”。
二、技術哲學走向新形態(tài)
信息技術哲學的興起為我們開啟了更大的哲學探新的疆域,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對技術哲學所起到的推進作用。如果說信息革命使得信息哲學正在成為科學哲學的新形態(tài),那么信息技術哲學也同時正在成為技術哲學的新形態(tài),其具體表現(xiàn)是:它正在使技術哲學走向“當代形態(tài)”、“分支形態(tài)”、“微觀形態(tài)”和“會聚形態(tài)”。
(一)技術哲學的當代形態(tài)信息技術哲學的對象雖然是信息技術一般,但其重點是當代信息技術。如前所述,當代社會的特征主要是由當代信息技術所造就的,當技術哲學從技術上把握時代的哲學特征時,無疑需要把握當代信息技術的哲學特征,這就需要技術哲學將自己的重點對象從一般技術或傳統(tǒng)技術推進到當代信息技術,在這個過程中使自己步入當代形態(tài)。信息技術哲學主要是關于當代信息技術的哲學,這一側(cè)重點使得信息技術哲學的“本義”就具有當代性。如果信息技術是當代技術的主導形式,那么信息技術哲學也應該成為技術哲學的當代形式或主導形式,或者說是技術哲學的當代形態(tài)。也就是說,由技術轉(zhuǎn)型必然導致技術哲學的轉(zhuǎn)型,唯有進行了技術轉(zhuǎn)型的這一哲學提升,才能回應數(shù)字時代對技術哲學的新挑戰(zhàn),使技術哲學的探索更富時代氣息,并通過探討當代技術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問題,為更好地解決技術現(xiàn)實問題提供理論上、智力上的支持。目前,在技術哲學界談論著各種當代“轉(zhuǎn)向”,如技術哲學的“經(jīng)驗轉(zhuǎn)向”、“生活世界轉(zhuǎn)向”、“實踐轉(zhuǎn)向”、“認識論轉(zhuǎn)向”、“信息轉(zhuǎn)向”、“后現(xiàn)代轉(zhuǎn)向”……,而信息技術哲學可以說集合了這些轉(zhuǎn)向,體現(xiàn)了所有這些當代特征。這是因為,信息技術中有著比一般技術更具體的內(nèi)容,所以它具有了更豐富的“經(jīng)驗”和“生活”的元素,從而成為一種更加趨向參與現(xiàn)實、進入日常生活的“技術實踐哲學”;同時,信息技術從直接性上就是充當人的認識手段,延長人的感官和大腦,幫助人處理和傳播信息,因此信息技術本身就是“認識論”轉(zhuǎn)向和“信息轉(zhuǎn)向”的技術載體;此外,由信息技術導致的“信息社會”是與“工業(yè)社會”相對照的,常常也是“后工業(yè)社會”或“后現(xiàn)代社會”的同義語,因此談論技術哲學的“后現(xiàn)代轉(zhuǎn)向”實際上就是指謂技術層面上的由現(xiàn)代性的工業(yè)技術向后現(xiàn)代性的信息技術的轉(zhuǎn)向。這些集合性的當代特征,使得信息技術哲學成為技術哲學的“當之無愧”的主導性的新形態(tài)。在上述的意義上,當我們說要“走向當代技術哲學”時,也就是說要將技術哲學從經(jīng)典范式轉(zhuǎn)變?yōu)楫敶夹g范式,即信息技術哲學。技術轉(zhuǎn)型的時代潮流使得信息技術哲學代表了技術哲學發(fā)展的未來方向,因此技術哲學關注信息技術并倡導對信息技術的哲學研究,既順應了信息時代的要求,也使自己獲得了新的發(fā)展契機。這樣看來,如果技術哲學給科技哲學展示了新的前景,那么信息技術哲學無疑給技術哲學展示了新的前景。
(二)技術哲學的分支形態(tài)目前技術哲學的研究形成了多種進路,較為有影響的有:人物進路:主要研究技術哲學領域中的代表人物的技術哲學思想或?qū)V瑥目ㄆ盏嚼眨瑥幕瑺柕降律貭枺瑥鸟R克思到海德格爾,從芬博格到伯格曼,從伊德到米切姆,目前已成為技術哲學研究中的“熱點人物”,當然這個名單還在不斷擴展。由人物進路必然衍生出“流派”或“理論”進路,較著名的技術哲學流派通常直接以人物命名,如杜威學派(實用主義技術論)、埃呂爾學派(技術自主論)、馬克思主義學派、海德格爾學派(存在主義技術論)等;在重要性上稍遜于“流派”但也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的技術哲學理論有德韶爾的第四王國理論、芒福德的技術文明論、伯格曼的裝置范式論、伊德的后現(xiàn)象學技術論、平奇的社會建構主義技術論、芬伯格的技術批判理論等。與流派或理論相關、但視野更高的一種進路是哲學范式進路,目前主要有“分析的技術哲學”和“現(xiàn)象學技術哲學”兩大進路。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技術哲學進路也是一種更早就形成的研究范式;如果“哲學范式”還可以被界定得更為廣義,則在這一進路中還存在與解釋學相結(jié)合的“技術解釋學”、與人本哲學結(jié)合的“技術人學”或“技術人本學”、與政治哲學結(jié)合的“技術政治哲學”等等。此外,還有基于哲學體系內(nèi)部分工的“分論進路”,形成了諸如“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價值論”等等的研究;基于技術哲學在“工程性”與“人文性”之間的不同偏重而形成了“工程傳統(tǒng)”與“人文傳統(tǒng)”的技術哲學研究;基于國別的不同而形成了“中國的技術哲學”、“德國的技術哲學”、“美國的技術哲學”、“日本的技術哲學”等研究;基于歷史分期而形成了“古代技術哲學”、“近代技術哲學”、“現(xiàn)代技術哲學”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不同的進路對于技術哲學的發(fā)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然而,還有一種更重要的進路是目前的技術哲學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那就是“分支進路”。我們知道,科學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分支或部門研究(如數(shù)學哲學、物理學哲學、化學哲學、生物學哲學、天文學哲學研究)而走向繁榮的,以至于時至今日,還有不少科學哲學家認為科學哲學的出路和前景仍然在于部門科學哲學的進展,因此科學哲學的綱領必須建立在更加重視部門科學的哲學研究上,即將重點放在具體科學的哲學問題研究上。由此推知,技術哲學的繁榮也必然不能離開分支或部門技術哲學的興起與發(fā)展,尤其是離不開當代新興技術中所形成的分支技術哲學的研究。例如,如果說“四大會聚技術”代表了當代最前沿的技術領域,那么技術哲學就需要大力開展相應的“信息技術哲學”、“生物技術哲學”、“納米技術哲學”和“認知科學技術哲學”的分支研究,這些研究一方面使技術哲學的對象從“技術一般”過渡到“技術特殊”,使得技術哲學不再停留于對“技術一般”的“宏大敘事”上,而是向“打開技術黑箱”的目標更為邁進,從而使技術哲學的內(nèi)容更實在、更充實。另一方面,由于這些技術領域代表了技術發(fā)展的最前沿水平,對其加以哲學研究而形成的分支技術哲學也就同時獲得了上面所說的“當代性”或“前沿性”,這也是技術哲學的重要發(fā)展趨勢:趨向在會聚技術統(tǒng)領下的分支技術哲學的興起。可以說,目前走向這樣的分支技術哲學的條件已經(jīng)具備,因為技術哲學的“總論”已經(jīng)形成,其他進路的開展已卓有成效,部門技術尤其是“前沿技術”的作用顯現(xiàn)出來,甚至對分支技術哲學的興起起到了“倒逼”的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部門技術哲學的興盛將是21世紀科技哲學發(fā)展的一大特色。”這也反映了技術領域上的細化不可避免地要成為技術哲學進一步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維度,抑或說走向分支技術哲學是技術哲學發(fā)展的一種必然趨向。這樣,對于技術哲學研究來說,不僅“沒有基礎研究就沒有水平,沒有特色研究就沒有地位,沒有應用研究就沒有前途”,而且沒有分支研究就沒有繁榮。
(三)技術哲學的微觀形態(tài)信息技術哲學作為技術哲學的分支,使技術哲學不再僅僅停留在“宏觀”的研究水平上,雖然它還稱不上是對技術的“微觀”研究,但卻成為走向微觀的“中介”或“橋梁”,通過它,我們的視野可以通向更加微觀的領域,如前述的計算機哲學、網(wǎng)絡哲學、人工智能哲學、數(shù)字哲學、賽博哲學、邏輯機器哲學、媒介哲學等等,它們也構成信息技術哲學的下一級分支,即前面所說的“分支信息技術”的哲學研究。可以說,信息技術下設多少個領域,就可以形成多少個分支性的信息技術哲學,從而形成對信息技術所有領域的“全覆蓋”的哲學研究。在走向微觀形態(tài)的技術哲學研究中,信息技術哲學成為對上述微觀形態(tài)研究的概括和提升,并與這些微觀形態(tài)形成動態(tài)性的互補。一方面,對這些微觀分支性的領域所進行的哲學研究可以豐富和充實一般的信息技術哲學的研究內(nèi)容,并使其從這些“第一線”的信息技術發(fā)展中獲取新的問題和實證材料。這些微觀領域的興盛雖然不能替代信息技術哲學研究,但無疑為后者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資源和智力基礎,并形成推動信息技術哲學發(fā)展的強勁動力。另一方面,信息技術哲學所形成的普遍適用于各分支領域的一般原理,又可以為上述的微觀形態(tài)的研究提供方法指導和形式指引,使其形成智力探究上的合力與理論創(chuàng)新的突破。
(四)技術哲學的會聚形態(tài)“會聚”是當代前沿技術發(fā)展的特點,目前“四大會聚技術”的形成就是這一特點的突出體現(xiàn),而作為其中之一的信息技術與其他三大前沿技術的會聚,體現(xiàn)在哲學形態(tài)上,就是信息技術哲學與生物技術哲學、納米技術哲學、認知科學技術哲學的會聚。會聚是交叉、整合、融合從而協(xié)同發(fā)揮集群效應,產(chǎn)生出更大的價值和效用,形成單項或單類技術難以具備的影響和功能。不僅技術本身可以會聚,技術的哲學問題也同樣可以會聚,如“接口問題”、“界面問題”、“網(wǎng)絡問題”就是在上述技術在交叉和會聚中產(chǎn)生的哲學問題,它們使得質(zhì)料論、形式論、系統(tǒng)論、動力論、基因論、微象論、信息論等哲學視角和方法交織在一起被我們探討。這些技術哲學問題通常貫穿于所有會聚技術之中,并且有賴于其協(xié)同發(fā)展和解決,才能取得期望的效果。由于信息技術在會聚技術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信息技術哲學成為當代技術哲學的主干部分,甚至核心部分。因此從信息技術哲學也必將走向“會聚技術哲學”;在這個意義上,它的研究對象信息技術就是“一種新的人工制品,是一種雜合物”,從而具有十分強大的會聚功能。可以說,由信息技術哲學所形成的會聚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例如在學科上,信息技術哲學是信息哲學與技術哲學的交集,承載著哲學的信息轉(zhuǎn)向與技術轉(zhuǎn)向的雙重使命;在技術領域上,信息技術哲學與認知哲學、心智哲學具有自然的會聚,像腦機接口、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人機界面等等,就同屬信息技術和認知技術的研究范圍,其中的哲學問題也同屬于信息技術哲學問題和認知技術哲學問題。借助技術性的會聚,信息技術哲學可以從哲學層次上消弭一些傳統(tǒng)的二元分離現(xiàn)象和觀念。如物聯(lián)網(wǎng)正在融合處理信息的技術與控制物質(zhì)的技術之間的鴻溝,知行接口正在融合身體信息技術與器具信息技術之間的鴻溝,這兩大技術所行使的會聚功能,使得我們可以從哲學上將信息世界與物質(zhì)世界、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之間的絕對界限加以“軟化”、模糊甚至打破,由此也使傳統(tǒng)的身心二元分離、知行二元分離等等得到一定意義上的消弭;還有,由信息技術造就的“信息型實踐”或“虛擬實踐”由于并沒有對實在世界形成真實的改變,因此也屬于認識活動的范疇,從而同時具備了實踐和認識的雙重特征,使得實踐和認識趨于融為一體,其直接意義就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縮小以致消失。虛擬技術使得虛實兩界不再是截然分割的兩個世界,虛界可以取得實的效果,實在則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虛化,并且被無限地復制。總之,當代信息技術使得一個消弭主客二分的無縫之網(wǎng)的世界正在形成,使得技術的會聚也延展到我們的整個世界觀。
當代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通過“生物芯片”、“DNA計算機”等的會聚,也為我們從哲學上消弭上述二元區(qū)分提供了新的技術支持。因為這種會聚使得“轉(zhuǎn)化物質(zhì)”的技術和“轉(zhuǎn)化信息”的技術在上述結(jié)合部不再具有明顯的區(qū)分,甚至導致主體與客體之間區(qū)分的相對性。如在進行基因治療時,作為中介和手段的技術操作在主體身體中所形成的技術性后果成為主體自身的內(nèi)在構成要素。這樣,技術本身既是客體也是中介,而后還成為主體的一部分,使得主客體之間具有了流動變換性,一定意義上主體就是客體,客體就是主體;甚至在人和機器之間,會聚技術所設定的目標就在于使兩者能夠更加有效地融合。這也是技術的會聚所導致的一系列矛盾特征的融合,即通過消解傳統(tǒng)技術造成的若干二元對立而走向“視界融合”。總之,當技術哲學走向信息技術哲學這種新形態(tài)時,我們所看到的是技術中更多哲學問題的呈現(xiàn),從而有待我們從中發(fā)掘和提升出更加豐富的哲學觀念。
作者:肖峰單位:華南理工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科學與公共事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