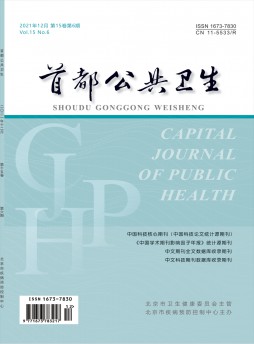公共領域差異的政治學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公共領域差異的政治學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上世紀60年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概念及相關理論以來,公共領域問題的研究逐漸受到了國際學術界重視。Mittler,Barbara等女權主義者關注的是公共領域建構和維系過程中女性的角色和權利的保護;SarahSorial等學者研究的是公共領域的限度;QingLiuandBarrettMcCormick研究的是當代中國傳媒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中國公共領域轉型及其對中國政治變遷的意義;BarbaraA.Misztal等學者研究的是公民之間的信任與合作對民主公共領域(thedemocraticpublicsphere)的重要作用。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公共領域問題的研究在國內學界勃興,公共領域的研究者認為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一個自由、平等、開放和包容的公共領域必將在中國形成。雖然國內外學者對公共領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如何理性認識公共領域的價值,如何看待民主政治和威權政治對待公共領域的迥然不同態度,仍是目前公共領域研究的一個盲點。那么,什么是公共領域呢?民主政治將公共領域視為一種機會和建設性力量,而威權政治卻將公共領域視為一種威脅和破壞性力量,這種不同認識形成背后的政治邏輯是什么呢?在公共生活中,如何理性看待公共領域呢?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
一、何為公共領域?
與國家、權力、公民、民主、正義等政治學的核心概念一樣,公共領域是一個存在爭議的概念,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理解。在阿倫特看來,公共領域是由獨立而自由的公民組成的、與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不同的、并以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為基礎的、神圣的政治生活場域。而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是一個介于私人領域與公共權力領域之間的中間地帶,它是一個向所有公民開放、由對話組成的、就一般性的利益問題展開公共討論、旨在形成公共輿論、體現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眾傳媒為主要運作工具的批判空間,“公共領域說到底就是公共輿論領域,它和公共權力機關直接相抗衡。”AgnesS.Ku將公共領域理解為“政治共同體成員一起討論共同體問題的場域。”本文遵循哈貝馬斯所開創的思想傳統,將公共領域(publicsphere)理解為自由平等的公民通過理性對話和公共協商方式建立和維護的、位于國家和私人領域之間的、旨在化解相互沖突和達成共識,形成公共輿論,影響國家或政府決策,監督和約束國家權力的、批判性的公共空間。公共領域是位于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一個領域,國家和社會的分離是公共領域形成的社會條件。公共領域不同于國家權力場域,相對于國家權力場域,公共領域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公共領域不是分配公共資源、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的政治領域,也不是政治領域的延伸,更不是政治領域的附屬品。公共領域在人、財、物等方面具有相對于國家權力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使得公共領域既可能成為國家權力的批判者,也可能成為國家權力運作的支持者。公共領域也不同于像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在阿倫特看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存在三方面的不同:家庭是不平等的場域,而平等、開放和包容是公共領域最為重要的一個特征;暴力支配著家庭的生活,權力準確地說是話語權力構成了形成和維系公共領域的軸心;由于充斥著暴力,家庭生活是無聲的,由于依賴話語權力,公共領域是有聲的。公共領域關注的是公共事務,私人領域關注的則是個人化的私人事務;公共性是公共領域的本質屬性,而私人性則是私人領域的重要特征。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維系不是無條件的,必須以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分離為前提。也就是說,在極權國家中,公共領域是不存在的,這是因為,在極權國家,國家權力吞噬著社會,國家權力消滅了社會的存在。極權國家的使命不僅是要使國家權力滲透社會,而且要運用權力改造社會。社會難以獲得公共領域形成和維系所需要的、相對于國家權力的獨立性和自治性。社會缺乏影響國家政策的意愿、能力和條件。與極權國家相對,在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公共領域是可形成的,因為在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國家權力并未滲透到社會的所有領域,社會權力與國家權力適度分離,而這種分離為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維系創造了條件。
公共領域是自由平等的公民通過理性對話和公共協商方式建立和維護的公共空間,自由平等的公民是公共領域形成和維系的主體條件。公共領域的主體是現代國家的公民,在公共領域中,公民是自由的、理性的和相互平等的。自由意味著公民有獨立的意志,能就關心的國家事務表達他們各自獨立的立場,能在法治的框架下表達他們對國家決策的看法;理性意味著公共領域的公民在公共討論中是以理服人的,懂得換位思考的。雖然公民在公共討論中不可避免會使用修辭的技巧,在對國家事務討論中會動用情感的力量來引起其他公民對國家事務的關注,但說理(或講道理)始終是形成和維系公共領域最為重要的支撐力量。公共領域的公民并不是彼此沒有矛盾的,對公共事務的看法也不是沒有分歧,但他們可以通過講理的方式來化解彼此的矛盾和分歧,通過理性協商的方式來減少彼此之間的沖突,最終形成共識;平等則意味著公共領域中,公民之間在道德、尊嚴和人格上是相互平等的,公民或公民團體在知識、信息、組織、技術等資源上也是大致相同的,這種知識、信息、組織、技術等資源上的大致相同,是公共領域公民平等對話的重要條件。公共領域是一個開放且包容的領域,該領域不會將部分社會群體排除在外,也不會使進入公共討論的社會群體的聲音被淹沒、被扭曲和被壓制,恰恰相反,在公共領域,不同社會群體都能發出他們的聲音,都有機會讓社會來分享他們的生活經歷。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包容性是公共領域最為重要的一個屬性。公共領域是公民形成公共意見、影響國家或政府決策的領域,能否約束國家權力和影響國家決策是公共領域存在與否的重要標志。公共領域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討論公共事務的領域,也是就公共事務展開討論形成公共意見的領域。“權力本身成為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的討論對象。”
公共領域不僅要形成公共意見,而且要影響國家決策,制約國家權力。眾所周知,合法性是任何政權得以存續的基礎,所有政權對合法性都有內在的訴求。國家為了尋求合法性,必須傾聽公民的心聲,滿足公民的利益訴求,在傾聽公民心聲和滿足公民訴求過程中,國家權力獲得了合法性。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它為公民發聲提供了一個場所,依賴這個場所,政府了解了公民的訴求,知曉了公民對公共事務和決策的態度。公共領域存在的意義絕不僅僅是形成公共意見,公共領域存在最為重要的價值是對國家決策產生影響,約束國家的權力,進而優化現存政治秩序,提升公民公共生活質量。從國家和社會關系角度看,由于社會具有一定自主性,這種自主性使得社會具有約束國家權力的能力。無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在威權國家,公共領域都是社會不同力量影響國家決策和約束國家權力的一個有力工具。公共領域并不符和政治精英的偏好,對國家政策和政府行為也并不總持認同的立場,公共領域不會蛻變成國家權力合法化和國家權力“制造同意”的工具。公共領域的公民是自由而理性的,也是充滿懷疑和批判精神的。他們并不簡單認同國家權力,對政府所制定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會持有不同看法。公共領域所形成的公共輿論是政府決策的民意基礎,公共領域的批判取向則是政府公共政策不斷調整和合理化的一個重要條件。
二、公共領域是一種機會
民主是現代國家的一種政府形式,“正當的政治權力的源泉和根源在于人民”[3]165,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民主政治既是一種參與型政治和開放型政治,也是一種責任型政治。在民主政治邏輯中,國家是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組成的一個合作體系,公民是民主共和國的真正主人。國家存在的目的是服務于公民的福祉和提升社會的福利,國家不應成為政治生活的目的。在政治生活中,公民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應是相互提供服務和承擔義務的平等交換關系。公民有向國家納稅和承擔國家運行所需成本的義務,有義務對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保持政治忠誠,國家則有義務通過提供優質、低廉和便捷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來換取公民的政治忠誠。民主政治是一種參與型政治,它鼓勵公民關注國家公共事務,國家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它相信公民是自由而理性的,因而對公共事務的理解是多元的,甚至是相互沖突的。民主政治將公共領域視為是一種機會,因為公共領域具有公民參與和權力監督的功能。民主政治要求公民參與政治,要求公民在國家的決策過程中貢獻智慧,公共領域則為公民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空間和條件。在公共領域中,圍繞公共事務,公民可自由而獨立地表達他們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可傾聽和分享其他公民對公共事務的不同觀點,可向國家或政府表達他們的心聲。在公共領域,公民是自由而理性的,利益、文化和背景存在諸多差異,因而對公共事務的理解是多元的,甚至是相互沖突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多元性和差異性是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屬性,也是公共領域存在的前提,而多元性和差異性的消失則是公共領域消失的一個重要標志。“共和國的公共領域是由平等者之間的意見交流所構建的,一旦所有平等者都正好持相同的意見,從而使意見的交流變得多余,公共領域就將徹底消失。”
也就是說,“當人們只從一個角度去看世界,當人們只允許世界從一個角度展現自己時,公共世界也就走到了盡頭。”公共領域是公民平等對話的領域,而平等對話的前提是公民對公共事務有不同理解和認知。正是公共領域的多元性和差異性,保證了政府決策的信息的豐富性,也為政府政策的調整提供了可能性。對于民主社會而言,公共領域是一種建設性的力量。公共領域為公民自由表達提供了平臺,是“人民主權”原則得到貫徹的制度安排。依賴這一制度安排,民主國家建立起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有效政治溝通的渠道。公共領域是民主發展不可或缺的建設性力量,具有權力監督的功能。民主社會的選舉是社會約束精英的一種政治安排,但一旦精英掌握權力,選舉的監督功能被弱化。對民主社會而言,公共領域存在的一個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種社會力量監督權力的常態化機制。公共領域所形成的公共意見是約束國家權力的一種重要力量。民主社會的公民依賴公共領域來表達對政府的不同看法,依賴公共領域的相互團結,尋求共識,對政府產生壓力,敦促政府對公共政策做出調整,對濫用權力的官員進行問責。民主政治將公共領域視為是一種機會,因為公共領域具有意識形態平衡和提出替代性政策的功能。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威權政治有不同的人性預設和認識論基礎。民主政治相信普通人的智慧,對“超人政治”深表懷疑,它相信人是有理性的,面對復雜、多變和相互沖突的世界,任何人或者任何社會集團都不可避免地是無知的,理性是有限的,這是因為,人類的知識是分散的,“知識可以交流,可以擴展,但卻不可能完全集中于個別人或個別機構手中,更不可能被個人所完全掌握”。既然世界是復雜、多變和相互沖突的,那么,在政治生活中,任何人或者任何社會集團,都不應擁有壟斷真理的權力,也不應聲稱憑借壟斷真理的權力而剝奪其他社會群體分享、傳遞和解釋真理的權利和機會,政治生活應“為沖突的觀點留有充分討論的余地。”公共領域對民主政治的意義在于它捍衛了民主政治對多元性的追求,防止政治領域“話語霸權”的出現。在公共領域中,公民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間的利益和意見是相互分歧的,對政府的態度也是充滿差異的。公共領域是公民自由表達意見的領域,也是不同社會群體呈現不同社會意識形態的領域。在公共領域中,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是相互平等的,也是相互競爭的。公共領域的存在,不應天然假定一種或幾種意識形態要優越于其他社會意識形態,也不應憑借這種假定就剝奪一些社會群體表達看法的權利。社會意識形態,要通過“說理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暴力的方式來獲得社會支持。民主政治將公共領域視為是一種機會,因為公共領域具有維系民主國家團結和促進民主發展的功能。“作為一個共有的世界,公共領域可以說把我們聚在一起。”
公共領域是公民平等對話和理性協商的領域,“溝通在生產和塑造社會團結中起著重要作用。”民主社會是多元分化的社會,民主國家依賴公共領域實現國家團結和社會整合,“激活平民群體并允許它在全國性政治中發出一些聲音。”公共領域是自由平等公民構建的理性對話和平等協商的領域,公民通過參與公共領域,擴展了視野,解決了沖突和分歧,達成了共識,激勵了社會合作所需要的社會資本。從國家與社會關系角度看,公共領域建立起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溝通渠道,這種政治溝通媒介是國家政治有效整合的基礎。公共領域也是促進社會正義的場域,而社會正義是社會團結的重要條件。公共領域還是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的場所,為社會抗爭提供了平臺,社會弱勢群體通過公共領域使自己的利益訴求被呈現。公共領域具有重要的賦權功能,為社會弱勢群體挑戰強勢群體提供機會,讓權力握有者感知社會壓力,使“相對弱勢的群體挑戰更為強勢的政治家,使他們對法律和競選承諾承擔責任”,這對于改變民主政治中的多數主義邏輯所帶來的問題、消除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緊張關系具有重要價值。在公共領域中,社會弱勢群體的斗爭不僅會改變國家的政策,推動政府政策的調整,促進社會的正義,而且也會增強社會弱勢群體斗爭的經驗,為進一步斗爭提供基礎。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每個人有能力充分參與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是正義的一種形式;或者相反,一些人受到排斥,顯然是社會不正義的一種形式。”
三、公共領域是一種威脅
與民主政治對公共領域的看法相左,威權政治將公共領域視為一種威脅。按照比較政治學通常的理解,威權政治指處于民主政體和極權政體之間的一種非民主、非極權的政體形式。“要求無限權力正是極權政體的本質。”威權政體相對于極權政體而言,權力有限;而相對于民主政體而言,則缺少責任感。威權政治不同于極權政治,“它們缺乏可靠的合法化和一種全面的意識形態;它們不對人們進行什么思想灌輸;它們偏好政治冷漠并接受‘有限的多元主義’。”極權政治對社會的控制從范圍上看是全面的,從程度上看是深度的,從控制方式看是任意的。威權政治并不要求全面的、深度的和任意的控制,它要給社會的發展提供一定自主空間。威權政治區別于極權政治之處在于它不將改造人民和向社會滲透作為己任,而滲透社會和改造社會是極權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威權政治也不同于民主政治,它不是一種參與型政治、開放型政治和責任型政治,權力壟斷和獨占是威權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威權政治下,權威被賦予少數人或抽象的一個政黨,而非政治共同體或者國家。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也不是一種平等的、相互承擔義務的交換關系。在威權體制下,“統治者既不被法律,也不被競爭性選舉約束”,政治權威依賴父權理論構建其合法性,公民與國家之間,缺乏制度化的聯系,權力運作具有封閉色彩,政治忠誠的對象往往是領導人而非制度。
威權政治將公共領域視為是一種威脅,因為公共領域破壞了威權政治所推崇的同一性和一致性。從政治哲學角度看,民主政治承認公民自由,尊重公民的自由選擇權,相信世界是差異的,多元的,公民或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和觀點是相互沖突的。也就是說,世界的差異性、沖突性和多元性,是國家治理必須尊重的客觀事實,也是公共生活亟待應對的問題。與民主政治不同,威權政治對同一性和一致性有著內在訴求,威權政治對多元性尤其是權力的分散性充滿恐懼。這是因為,威權政治并不將公民視為是自由的,政治權威與公民之間也并不是相互平等的。在威權政治中,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權威與公民之間不平等以及政治權威對公民承擔責任這兩個基礎之上的。政治權威是智慧的,公民是愚昧無知的,因而政治權威理應統治,政治權威的權力不容挑戰,也不應被分享。政治權威與公民之間的關系,類似家庭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政治權威有責任關注公民的福祉,提升公民的福利,而公民對這些福祉和福利,只能接受,不應表達他們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沖突的看法。威權政治將公共領域視為是一種威脅,因為公共領域與威權政治有不同的哲學基礎。公共領域承認公民是自由的,公民與政治權威之間是相互平等的。權威政治否認公民的自由,否認公民與政治權威之間的平等性;公共領域承認公民的自由的同時,也承認和接受世界的多樣性,公共領域存在的意義在于要保護這種多樣性。威權政治否定公民自由和選擇的權利,認為世界的多元意味著無序,混亂,威權政治依賴權力來消除世界的多元性,追求同一性和一致性;公共領域承認世界是復雜的,權力握有者的理性和知識是有限的,因而是容易犯錯誤的,而威權政治則承認公民是幼稚的、無知的,權力握有者是智慧的、有德性的,用于承擔責任的,因而限制權力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威權政治將公共領域視為是一種威脅,因為公共領域限制了國家權力,損害了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對權力握有者而言,限制和約束權力,是一件令人不悅的事情。公共領域的存在無疑代表社會約束和監督國家權力,這是因為,公共領域鼓勵公民就公共事務進行自由討論,倡導公民就政府政策發出批判性的聲音,對于威權國家的政治權威而言,公共領域的存在分享了國家權力,限制了國家權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國家權力。顯而易見,這種對國家權力的挑戰與威權國家的父愛主義相沖突。威權國家依賴父愛主義(Paternalism)論證合法性,這種父愛主義賦予國家代替公民為自身福利做出選擇的權利。“為了幫助人民過上好的生活,國家有義務應支持那些值得推崇的生活方式。”公共領域的存在損害了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公民批判政府,損害政府的形象,降低公民對政府的認同。在民主的邏輯中,政治權威的理性是有限的,所要協調的利益沖突是復雜的,因而政治權威是可能會犯錯誤的,因而對公民對政府的批評不會損壞政府的合法性,恰恰相反,會有助于政府糾正錯誤,提升合法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言論自由以及公開合法地反對政府的政策和行為被視為自由民主觀念的中心。”
與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威不同,威權國家的政治權威有不同形象,集智慧和德性于一身,公民批評政府犯錯誤,會損害威權政府的合法性。公共領域的存在與威權國家建構文化霸權相沖突,侵蝕威權國家政治權威意識形態領導權,而這種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領導權是威權國家政治權威合法化的重要基礎。公共領域中呈現的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不同類型的意識形態,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是平等的,也是相互競爭的,這無疑增加了文化霸權建構的難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意識形態領導權。當然,公共領域對政府合法性的損害之處還在于它培養了一種懷疑政府、批判政府和理性反思政府政策的公民文化,這種公民文化使公民對國家的批評公開化,而公民對國家批評的公開化會部分削弱政府執政的基礎。威權政治將公共領域視為是一種威脅,因為公共領域損害國家治理的有效性,甚至產生不可治理的問題。國家治理的有效性,依賴國家對社會有效的控制、動員和汲取,公共領域的存在,對威權國家的控制、動員、汲取行為構成了限制。公共領域成為公民抵御國家社會控制的工具,在威權國家,由于公共領域存在不同于國家權威機構的聲音,這意味著公共領域既可能是國家有效動員的工具,也可能成為反國家動員的場域。國家治理需要大量資源,而國家治理所需要的資源來源于國家權力對社會的汲取。國家對社會資源汲取能力的大小,不僅取決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而且也取決于國家的合法性。對國家而言,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它能提升公民與國家合作的意愿。公共領域對政府進行批評損害政府合法性的同時,也降低了公民與國家合作的意愿。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威權國家的政治權威將公共領域視為弱化國家有效治理的工具。公共領域之所以損害國家治理有效性,導致不可治理問題的出現,這不僅是因為公共領域使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顯性化,導致政府難以行動,而且也因為公共領域所提供的多元的、甚至相互沖突的應對社會問題的方案使得政府難以做出決策。更為重要的是,公共領域在國家權力之外形成了一種平衡國家權力的社會權力,國家權力需要與公共領域所形成的社會權力進行協商和妥協,才能對國家進行有效治理。公共領域所造成的國家多中心治理造成了治理主體之間的沖突,帶來不同治理主體之間合作上的困難,這種困難無疑是不可治理問題產生的重要條件。從國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關系角度看,公共領域之所以損害國家治理的有效性,主要原因是它損害國家治理的合法性,而國家治理的合法性,無疑是國家有效治理的重要條件。
如上分析表明,公共領域既可能是一種機會,也可能是一種威脅。然而,在國內學者對公共領域的研究和引介過程中,存在對公共領域一定程度的非理性認知,這種非理性認知主要表現在公共領域的公共討論被自由民主或憲政民主話語所支配,公共領域的負面問題被公共討論所遮蔽,公共領域與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之間的復雜性被簡化。大多數研究從自由民主傳統來強調公共領域的價值,認為公共領域對國家建設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公共領域培養了理性的公民,監督和約束了國家的專斷權力,有利于政府決策的合理化,也有助于政府公正分配公共資源,同時也為多元的現代社會整合提供了條件。然而,比較政治學的研究發現,公共領域并不只存在民主政治中,威權政治也存在公共領域。威權政體往往是壓制性的,但即便這樣的壓制性威權政體也會“允許一些群體、甚至是政黨表達(有限)程度的不滿。”[不同的政府形式對公共領域的認知是有差異的,不同政府形式對公共領域的態度和政策選擇也是不同的。對民主政治和威權政治而言,公共領域具有不同政策蘊含。實踐表明,在現代國家建設中,公共領域既可能是一種建設性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在認知公共領域的過程中,公共領域的負面問題不應被遮蔽,公共領域對國家權力的挑戰也不容忽略。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中,公共領域的建設和培育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問題,如何在培育公共領域和發揮公共領域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避免公共領域挑戰國家權力,產生國家的不可治理問題,應成為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嚴肅思考的一個問題。
作者:曾水英 余項科 單位:長春工業大學
- 上一篇: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的學術價值范文
- 下一篇:周易的政治學思考范文
擴展閱讀
精品推薦
- 1公共投資論文
- 2公共關系案例分析論文
- 3公共財政研究
- 4公共管理主體理論
- 5公共事業管理畢業論文
- 6公共政策論文
- 7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 8公共管理學論文
- 9公共政策分析論文
- 10公共事務治理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