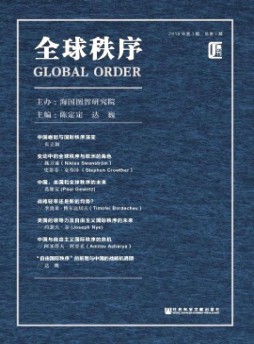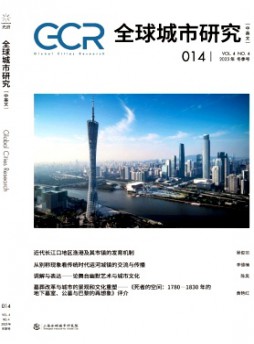全球醫學教育要求及推廣問題探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全球醫學教育要求及推廣問題探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999年6月9日,國際醫學教育學會(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在紐約成立,隨后建立了網站[1]。IIME是一個非盈利機構,得到了美國紐約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MedicalBoardofNewYork,Inc.)的資助,其主要工作是在定義大學醫學教育的“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GlobalMinimumEssentialRequirementsinMedicalE-ducation)方面發揮領導作用。IIME通過收集和研究世界各國醫學教育的要求和標準,制定出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標準,使得不管在任何國家培養的醫生都達到在醫學知識、臨床技能、職業態度、行為和道德規范等方面的最基本要求。IIME將“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歸納為七個領域和具體的60條標準[2,3]。其主要內容包括:
1.醫學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敬業精神和倫理行為是醫療實踐的核心。敬業精神不僅包括醫學知識和技能,而且也包括對一組共同價值的承諾、并自覺地建立和強化這些價值,以及維護這些價值的責任。該領域對畢業生共有11條具體標準,包括認識醫學職業的基本要素,職業價值,保護患者利益,影響醫療實踐效果的因素,解決倫理法律和職業之間沖突的能力,自我調整能力,尊重他人和合作能力,對臨終關懷的認識,對患者檔案、剽竊、保密和知識產權的認識,有效的自我計劃管理能力和應變能力,個人責任等。
2.醫學科學基礎。醫學院校畢業生必須具備堅實的醫學科學知識,并且能夠應用這些知識解決醫療問題。畢業生必須理解醫療決定和行為的原則,具有適應變化的能力。共有10條具體標準,包括正常人體結構和功能,疾病時機體結構和功能的異常,正常和異常人體行為,健康與疾病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的重要因素和危險因子,保持機體穩態的分子、細胞、生物化學和生理學機制,人類生命周期和生長、發育、衰老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影響,急、慢性疾病病因學,流行病學和衛生經濟學,藥物作用的原理及其應用和不同療法的效果,在急、慢性疾病、康復和臨終關懷中適當采用生化、藥理、外科、心理、社會的干預措施等。
3.溝通技能。醫生應當通過有效的溝通創造一個與患者及其家屬、衛生保健成員與同事和公眾之間進行相互了解的環境。為了提高醫療決策的準確性和患者的滿意度,畢業生必須達到9條標準,包括注意傾聽以獲取相關信息,運用溝通技能使患者及其家屬理解醫療決策,與同事、職員、社會以及其他部門和媒體的有效溝通,通過有效協作與其他專業人員的合作,具備教學的基本技能和積極的態度,具有對文化和個人因素的敏感性,具有有效進行口頭和書面表達進行溝通的能力,建立和維護醫療檔案的能力,綜合和表達能力等。
4.臨床技能。畢業生在診斷和處理病例時必須講究效果和效率。畢業生必須達到10條標準,包括采集病史,體格和精神檢查,分析和解釋發現并確定問題的性質,遵循挽救生命和應用循證醫學的原則采取適當診斷和治療策略,運用臨床判斷以確定診斷和治療方案,能識別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能處理常見急癥,能高效地管理患者,能評價健康問題并指導患者,能合理應用人力資源、診斷、治療和保健設備等。
5.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醫學畢業生應當知道他們在保護和促進人類健康中應起的作用,并采取相應的行動。他們應當了解衛生系統組織的原則及其經濟和立法基礎,應當基本了解衛生保健系統的有效管理。畢業生應當達到9條標準,包括了解影響整體人群健康和疾病的生活方式、遺傳、人口學、環境、社會、經濟、心理和文化因素,了解這些因素在疾病、損傷和事故預防、以及保護、維持和促進個體、家庭和社區健康中的作用,了解國際衛生狀況、慢性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全球趨勢、移民、貿易和環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以及國際衛生組織的作用,認識到其他衛生相關人員在為個體、人群和社區提供保健中的作用,理解在健康促進干預中需要多方面的共同負責,了解衛生系統的基本要素和運行機制,了解決定衛生保健、有效性和保健質量的公平性機制,在衛生決策中運用國家、地區和當地的監測、人口和流行病學資料,需要和適當時愿意接受領導等。
6.信息管理。計算機和通訊技術的進步為教育和信息分析及管理提供了強大的工具。畢業生必須理解信息技術和知識管理的用途和局限性,并能在解決醫療問題和決策中應用這些技術。畢業生必須達到5條標準,包括從各種數據庫中檢索、收集、組織和分析健康和生物醫學信息,從臨床數據庫中檢索特定病人的信息,應用信息和通訊技術輔助診斷、治療和預防、以及對健康狀況的檢測,了解信息技術的應用及其局限性,維護醫療檔案等。
7.批判性思維和研究。批判性的評價現有知識、技術和信息的能力是解決問題所必須的,如果醫生要勝任現有的工作,他們必須不斷獲取新的科學信息和技能。良好的醫療實踐需要科學思維的能力和使用科學的方法。醫科畢業生必須達到6條標準,包括在職業活動中表現出批判性方法、有根據的懷疑、創造性和以研究為導向的態度,了解科學思維的能力和局限性,依靠個人判斷來分析和評論問題、主動尋找信息,應用科學思維并基于不同來源的相關信息識別、闡明和解決病人的問題,了解在醫療決策中復雜性、不確定性和概率的作用,提出假設、收集評價資料、并解決問題等。
二、推廣“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的必然性
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有約600萬醫生為60多億地球居民提供醫療服務,但是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質量隨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有較大的差別,這種差別的原因主要來自于各個國家或地區的醫學教育體系所生產的醫生質量的不同,部分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醫學教育體系存在著明顯的國與國之間的區別,這約600萬醫生絕大多數畢業于全球的1600余所醫學院校,具有不同醫學教育體系的醫學院校所生產的醫生的質量是參差不齊的。這種畢業醫生質量的參差不齊一方面影響了醫療服務質量,甚至導致危及患者生命的嚴重后果,另一方面,給國際交流帶來了障礙。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醫學教育和醫療服務的全球化也越來越明顯。但是,還是經常會遇到學歷和專業資格的承認方面的麻煩。另外,在一些國家(包括我國),缺少教育質量保證的新辦醫學院正在不斷增加,這些醫學院生產的醫生不要說能達到國際上對醫科院校畢業生的普通要求標準,就連國家衛生部的基本要求也不能完全達到。現有我國的醫學院教育質量評估體系尚不能對這些新醫學院的教育“產業”進行一票否決,粗制濫造醫生的現狀在繼續。目前,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以及生物技術的發展極為迅速,在帶來極大的物質財富和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醫學倫理、社會和法律方面的挑戰。這就要求在新時代畢業的醫學生們必須具備更全面的知識和能力,以適應日益發展的科技時代的需要。
三、實行“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的全球權威性問題。制訂“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的任務由IIME的核心委員會(CoreCommittee)承擔,該委員會由世界各地的醫學教育專家組成,現在的核心委員會主席為Dr.M.RoySchwarz(現任CMB主席,美國California大學醫學院臨床教授),成員包括美國的5位,巴林、西班牙、墨西哥、英國、澳大利亞、蘇格蘭、加拿大、南非、哥倫比亞、泰國、波蘭和中國各1位。另有8位具有國際聲譽的醫學和醫學教育專家組成的指導委員會(SteeringCommittee)(美國3位,瑞士、委內瑞拉、中國、挪威、波蘭各1位)協調指導IIME的總體工作并起核心委員會的作用。有14個國際醫學教育組織的主席和高級代表組成的IIME咨詢委員會(AdvisoryCommittee)(共17人)為IIME提供咨詢意見,成員主要來自美國醫學會、世界衛生組織、日本醫學教育協會、中國醫學院校協會、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歐洲醫學教育協會、泛美洲醫學院聯盟、俄羅斯高級醫學研究院等。雖然三個委員會隊伍壯大,但是,關鍵的具有全球范圍內指導醫學教育和醫療職業的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咨詢委員會中的成員為已經退休的來自日內瓦的Dr.CharlesBoelen,可能在推動“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方面的作用有限。另外,由于推行“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需要得到各國政府相關部門的準許,在IIME咨詢委員會中的成員是否需要考慮政府職能部門的成員參加,在這方面將有大量的工作量。
2.實行“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的階段性問題。從項目的進度看,目前已經完成了“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項目實施的第一階段——“制定基本要求”階段,進入了第二階段——即“試行”階段,下一階段(即最后階段)為“全面實施”階段。在目前的“試行”階段,“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已經完稿,已經在中國的8所醫學院校(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北京大學醫學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中國醫科大學、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試應用。然后,“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及其配套的評估方法和程序將在更多的學校、國家和地區不斷實施和不斷完善。最后將被各國際教育機構和國家(地區)認同,成為國際上評價醫學教育的基礎。從上述三個階段的內容來看,第二階段的任務應該是最重的,除了在試點醫學院推行“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的系統評價方法外,各個醫學院在7個領域60項標準基礎上確立的有自己學校特色的評價方法可能帶來不可比性,不利于項目的國際性評估。因此,筆者認為,在第二階段,應該建立完善的反饋機制和有醫學教育評估專家參與的科學的評估體系。
3.“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不是一個世界大一統的“要求”。正如IIME自己所強調的,“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這一概念并非指全球醫學課程計劃和教育過程的統一,制定“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并不違背醫學教育的基本原則,即醫學教育必須闡明和遵循醫生接受培訓和提供服務的地區的特殊社會和文化需要。各國醫學院可以采用自己的課程系統,但必須保證畢業生具備“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所規定的核心能力。也就是說:“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國家和地區要求醫生具備的能力=醫學院畢業生的能力。這個理解是實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各國醫學教育現狀的。從另一個角度講,“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的可操作性比較強。但是,同時帶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醫學院的學生是否需要學習更多的內容以適應來自國際和本國的兩個標準?是否會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對于一個可能一輩子在國內從事醫療職業的醫生來說,他或她是否學習了過多可能一輩子只用一次的知識,即通過畢業評估的那一次。
4.“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與目前國際上的其他醫學教育國際標準的關系。由于“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的推出,可能與國際上已經存在的醫學教育標準有沖突或重復。如1992年WHO衛生人力開發教育處DrBoelen提出的“五星級醫生”(HveStarDoctor)的標準等[4],如何處理“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與各種現存的國際醫學教育標準以及各國醫學教育標準的關系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綜上所述,到目前為止,“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是一個可用于我國醫學教育畢業生評價的基本要求,但是,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有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背景問題等,因此,在“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的基礎上,在國家衛生部的導引下,較快制定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與國際接軌的醫學教育評價標準刻不容緩,這一標準的建立,對于較快地使我國的醫學教育有序化、全球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